「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
從《中國人的性格》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 觀照學術發展脈流、探索科際對話新視域
2018-04-18
回應 0
「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

主持人:劉斐玟(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與談人:瞿海源(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前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黃樹民(中研院院士、前中研院民族所所長,現任清大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胡曉真(中研院文哲所所長)、沈志中(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日 期:2014年12月19日
時 間:10:00 ─ 12: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劉斐玟:今天邀請到四位包括先輩和青壯代表的專家學者,來跟我們分享他們跨學科研究的心得。第一位是《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當時的作者群之一,瞿海源教授。瞿教授既是社會學家,也有心理學的背景;瞿老師也是《中國人性格》主編之一楊國樞院士的學生。第二位是中研院民族所的所長黃樹民先生。黃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李亦園院士的學生。第三位與談人是中研院文哲所所長胡曉真。文哲所本身涵蓋很多不同的學科,如經學、子學、哲學等,胡所長在這方面,一定有很多的經驗跟觀察可以分享。最後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的沈志中教授。不論是《中國人的性格》還是《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心理學與人類學在對話時,有二個學科一直如影隨形:精神分析和哲學,而沈教授剛好兼治兩者。相信沈教授在這方面,有很多理念是可以給我們啟發。
瞿海源:《中國人的性格》是根據1970年開的一系列的研討會結集而成。在那個年代沒有所謂的學術研討會,只有單一的演講會,民族所稱為「講演會」,也是一個人來報告,大家討論。《中國人的性格》研討會的發起很有意思,而且很值得肯定。它的程序是這樣的,先去約了研究各學門的相關學者,所以範圍就很廣。第一波是你要寫計畫書,不管你是大教授還是小研究生。計畫書不是你寫了就算了,計畫書要討論,每一次要討論兩個計畫書,討論通過後要回去修改,然後第二波開始寫論文。那個年代還沒有電腦,寫完了論文就交給民族所去中文打字、油印,然後發給每一參加的人,然後再開會。從1970年的4月開始開會,開了11次的會,每一次一篇,等於是以演講會的形式只討論一篇,討論之後再出書,而且把討論的內容也附在文章後面,很精彩,討論真的很精彩。這樣的過程不只是當年沒有,後來也是沒有的。後來的學術研討會開兩天或四、五天,隨便霹靂啪啦就過去了,一般報告10、15分鐘,討論5分鐘,很短啊,所以只有主要評論人看,其他根本沒人看。可是那時候那個討論會是大家都看,看了大家都提出討論,而且互相批評,不同學科之間互相批評,這是我要特別指出來的這本書的特徵。
這本書在1972年出版,出版速度也很快,’70年開完會、’72年出版。它一出版不僅是暢銷,而且還受到各界肯定,後來是國民黨查禁…...。那時候黨國不分,國民黨透過中研院黨部書記來說:你們這書不能再發行了,因為是隔海唱和。我們那本書也是「反孔」,批二十四孝,有講皇帝是從流氓來的……。那這個不得了了,就好像在罵誰,所以就查禁。但禁不勝禁,有一天,中研院國民黨部又跟李先生說「叫你們不要出版,怎麼又出版了?」李先生說:「我們沒有再出版啊,那是翻版的。你再幫我查一查看是誰在翻版?」那時候翻版書很多(笑)。這算是「上古史」!
今天能來也是有點小典故,說起來也滿感觸的。李亦園先生在《中國人的性格》的〈序言〉講的十二位作者,有三位已經過世了。楊懋春,楊教授是1904年出生,有一次還在他家裡開會,很可愛的長者,他是早期的社會學者,很有名的。文崇一先生也走了,朱岑樓先生也走了。楊國樞先生跟李亦園先生身體不太好,今天不能來。曾炆煋、徐靜很早就去了夏威夷,所以今天也不能來。韋政通身體不錯,是學思想史的,項退結是學哲學的,不過思想史和哲學離你們〔民族所〕還是遠了點,所以你們沒有請他。吳聰賢跟我們的距離也稍微多一點……。其實這個《中國人的性格》跟我的碩士論文研究有關係,那時候楊先生在做「中國人的性格」,我找他做碩士論文指導,他說:「我有三個方向,你要選哪一個?」我選了「現代性」,所以我才有幸有一篇論文跟楊先生聯名在這裡發表。那時候我還是研究生喔,才27歲,匆匆就40多年過去了。
在今天這個討論會的介紹裡面,特別提到說「《中國人的性格》是引領台灣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先驅」,這應該是對的。可是科際整合的滄桑,我待會兒再討論。
《中國人的性格》的作者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有三位心理學者,有兩位精神醫學者、四位社會學者、兩位學哲學的,人類學只有一位,就李亦園李先生。李先生故意把文崇一也歸成人類學,按理他應該歸成歷史學或是社會學,可能李先生覺得太孤單了,就拉一個進來變成人類學,這很有趣。《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這本新書有五位心理學者,包括兩位臨床心理學者和二位人類發展學者,那人類學就多了,四位,其中一位是民族音樂學,還有哲學一位。這樣子比較清楚的整個形象就出來了。在《中國人的性格》裡面的一個主題是就是「中國人的性格」,或者像「民族性」或「國民性」,最基本有三篇論文: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人格發展、中國的農民性格。那麼心理學家發表的是:中國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跟心理需要。「中國」兩個字當初引起很大的爭論,說幾個大學生怎麼能代表整個國家呢?!有些人當然已經沒有用「中國」這兩個字了。我們其他大概五、六篇,是從各個角度來看對中國人性格形成的影響,比如說發展、家族主義、儀式行為,或者價值取向。所以大體上是大的範疇,然後從不同的角度來做研究、寫論文,等寫完論文以後再來討論。《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的性質就不太一樣,所以我也不太能多做評論。下面我要提到幾點,就是《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

崇尚批判精神
《中國人的性格》最大的特色不是科際整合,科際整合不算成功,只是不同學科平心靜氣、理性地,以學術的立場來討論,這個很重要。這本書的特色是從計畫書的寫作、討論的過程中,彼此批評的滿重的。那個批評精神很重要。那個批評精神結合兩個東西,一個是台大心理學系的批判精神,第二個是中研院民族所的批判精神。心理系批評是毫不保留、就事論事的批,是老師,也照樣批。那民族所也有長期的批判傳統。這兩個傳統結合起來,在1970年初,就來辦研討會,在研討會過程裡面大家可以看,比如說楊懋春的論文。楊先生那時候年紀很大,將近70歲了,他寫的這篇論文結構非常嚴謹,架構也很大,他講完之後,楊國樞、韋政通、文崇一、李亦園啊,都提了很多意見,而且很不客氣的批評(大家可以看169頁)。但楊懋春先生答覆說:「不過,我不贊成你們的說法,我要為我自己的寫法做辯護。我覺得,第一點,中國人為什麼很注重生物性的生命?」他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那有人就說,你不能講是生物性啊,這個都是道德性啊,中國人喜歡講道德啊。他講:「大家都有一個問題,死了有什麼結果呢?大家對於死亡的感覺是一個很悲慘的、很可怕的事情,於是乎宗教家們就提出人死後有一靈魂,或是說有一個鬼可以永遠存在。中國人不太願意接受宗教的說法,尤其是儒家不願意接受,那麼他們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他們就看動物植物,如果是男女結婚能生後代,父母之生命就在身體裡面,父母之精與血就代表生命,生物的生命就在子女的身上……。」這裡他強調的是,「我講的生物沒有錯啊,也沒說你們不對啊!」結果大家又起來說,喔我不是那個意思啊,是這樣、這樣、這樣……。我雖然用開玩笑地方式說,可是這裡面看得出來他們是對同一個問題,很嚴肅地去對話,這裡面沒有謾罵。但有些時候就回答說,「你說的是對的,我會考慮。」這些討論非常的多,所以李先生統計過,全書有80頁是討論的紀錄,這個討論紀錄的功勞在哪裡呢?那個年代沒有電腦,要借那個卡帶錄音機來聽,很辛苦的欸,還有逐字寫。那個年代(1970年代)還有這麼詳細的錄音稿整理出來,還整理得非常好,作者也都看過。
用「心」對話,開展個人學術視域
還有,大家看第304頁的韋政通,我一定要舉這個例子。韋先生是一個思想家、哲學家。那時候每篇論文都有一個主評人,第一個發言的是主評人,主評人要提出一些基本觀點,然後後面再跟著討論。韋政通評誰的文章?楊國樞的文章,評的是心理學家一個很實證、很量化的文章,講中國人的人生觀。楊教授根據調查出來所做的統計分析,你想這個哲學家他怎麼評呢?很厲害喔,他終於看出一些門道,韋先生說,「有關於楊先生的文章,我有幾個問題想要提出來討論一下。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楊先生根據資料的分析,認為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是以『社會』為中心的。但就我個人的瞭解,傳統的中國社會卻是以家或家族為中心的。如果以社會為中心是事實的話,那便代表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不是應該這裡解釋一下。」這個不容易啊!我覺得他抓到一些重點,雖然有一點的誤解。所以楊先生就說:「在這裡,『社會(society)』是廣義的,是相對於『個人(individual)』而言的。因此,家庭也應該包括在『社會』之內。」這當然是一種回應,那李先生就提出意見,喬健也提出意見。接著,韋先生又提出第二個問題,那楊先生又回答了一下。韋先生還有第三個問題……。所以光從這個程序來說,就知道他們是非常認真的。韋先生是哲學家,他不懂心理學,可是他很用心去看,然後又提出意見。我在前一年(2013年)9月,因為楊國樞先生的囑咐,要把1970年代、90年自由派學者的事情整理一下,講一下那一代學者的事情。所以我就去訪問胡佛、韋政通啦,現在還沒訪問完。我訪問韋政通時,我要特別提一點的是,韋先生說,「當初參加『中國人性格研討會』對我影響非常大,因為從那時候我開始認識心理學、社會科學,我後來很多有關中國倫理的研究,都受了影響。我研究中國倫理是從心理學角度來寫的。」這個我想是很值得提出來的。這可以看得出來當初相互有激盪,所以產生一些很重要的影響。
科際整合的方向
我從大學,至少是大三開始,就知道有「行為科學」這個詞,也知道那年代在美國是在提倡行為科學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那時候我還在學生時代,就曾經跟一些同學發起一個讀書會,叫「行為科學讀書會」,就邀請過李先生、楊先生來演講。我自己也經歷過屬於心理學者的身分,也許是「中國人性格研究」的關係,有幸進入民族所,在民族所又接觸社會學、人類學,然後再轉到社會學,我本身就有點想從事科際整合。可是我覺得科際整合並不容易。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我不會說「失敗」,我只有說「不是成功的」。下面我提出幾個觀點或者觀察跟感想。
張光直的整合典範
第一個是張光直先生。1970年代中期,他在民族所推動「濁大計畫」。張光直先生後來說了一段很有意義的話,他說「科際整合要集中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一個人身上整合。」也就是說,這個人必須要懂這些不同科際,才能把它整合起來。不同人在一起也不能整合,因為彼此不了解。張光直先生做到了,因為他努力,他本來也就學會了很多古生物學、地質學,他就把這個整合起來,張先生他是真的把這個整合起來,其他能整合起來的人不多。
第二點,整合是要「有機性」地結合起來的,不是拼盤式或拼布式的。拼起來的,看起來還不錯,像在吃拼盤一樣,但拼盤不算是整合。
「道不同,相為謀」
第三點,前年初(2012年)胡適紀念館邀請我們中央研究院合唱團去演出胡適的歌,當時他們主辦了一場「道不同‧相為謀」的特展,講的是胡適與蔣介石的特展。胡、蔣兩個人完全不一樣,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接近獨裁,那這兩個怎麼會在一起呢?「道不同」,可是必須「相為謀」,因為他們都反共,所以胡適還是支持蔣介石。他們中間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可是還是在一起,所以「道不同‧相為謀」就是科際整合的意思啦!大家坐下來一起商量看看,我們要怎麼樣來整合。
研究議題:小、大之間
第四個是小大之間,「中國人」我們做得那麼大,「性格」也那麼大;「同理心」就有點小。這之間對比很強,這個之間怎麼求得一個中介?年輕人應該想辦法做一些大的東西,很多大的、確立科學的課題,我們要去做,我們不要在每個研究室裏作小東西,小東西要跟別人合也不容易合啊。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學術潮流可能需要做一個努力,我覺得目前來說很多學科都越做越小,小到就只有你自己明白啦,別人都不知道了,這個對整個學術發展並不是很好。
從學術專業到知識普及
最後兩點很簡單講一下。第一個,「同理心empathy」 是楊國樞先生翻出來的。當初翻的時候,還有人不同意,所以他後來在《中國論壇》(1982)寫了一篇「同情心與同理心」,那之後有很多人就引用他這個同理心的觀點,很多心理學者、教育學者也曾經以他的這個觀點去做研究,所以還不少研究,可是你們卻沒提楊先生的同理心,這個好像不太同理啊。另外一點,是我剛在吃早餐跟我太太提,我說「《同理心》這本書好難看得懂喔」,她就翻起來看一看,「這個啊,設身處地去看就看得懂啦!」然後就翻到彭仁郁的文章,她就說:「怎麼那麼多的名詞啊?看不懂啊?」她設身處地了,可是還是看不懂,因為這個太專業了。當然,我們是寫學術專業的東西,可是有沒有可能寫得讓一般人看的懂?最好有一個版本一般人就看得懂,或至少讓別的學科也看得懂,那可能就會有好的整合的機會。當你寫的東西別的學科也看不懂,只有你那個學科看得懂,你怎麼談科際整合?
最後一小點,這個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講科際整合,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科技。我們中研院有一棟大樓叫「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那些跨領域生物科技,像病毒研究,他們就發現一個學科不夠,要很多學科一起來研究,它就整合起來了,那是一個整合成功的例子,因為他們要什麼很具體。他們也是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所以這也是值得注意的趨勢。科際整合可能還是一個重要趨勢,可是有一些條件。

劉斐玟:謝謝瞿先生帶我們回到過去,讓新一代的學者可以瞭解前輩們怎樣用「心」在做學問。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請也是「上古」時代的黃所長來跟我們分享他的心得。
黃樹民:「中國人的性格」的研討會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幾位主要的參與者跟我都很熟,其中還有一位並沒有出現在《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裡,就是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先生。殷先生其實是對台灣1960、70年代學術界影響非常大的一個哲學家,但因政治因素,他後來是被台大解聘了,也不能夠出現在任何的文字上。
剛剛瞿先生已經講了很多比較細節的東西,那我就從一個比較廣度的結構上來分析、來討論我們過去這40多年來不同學科間對話的一個過程。從結構上來講,民族所是滿特別的。我們早年的前輩怎麼設計出這樣一個機構呢?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中研院民族所就包括了不只是人類學、民族學學者,還包括了心理學、社會學,還有農村社會學,像剛剛講到楊懋春先生、吳聰賢先生,他們都是農村社會學的學者;還有就是精神醫學,剛剛提到的徐靜、曾炆煋,還有林憲,他們這批人都是當時在民族所非常活躍的。因為民族所經常辦活動,邀請這些不同學門的人來參加。當然這個時代的背景也很清楚,因為李亦園先生跟文崇一先生是1960年代前後到哈佛大學訪問的,那時哈佛大學提出來的所謂行為主義或行為科學研究,蔚然成風,成為一個潮流。他們把不同學科整合起來,用不同的視野、不同的方法、不同理論架構來討論問題,提供了一個結構上的機會,讓不同的學門可以在一個機構底下,經常接觸,互相對話。這個傳統到現在還繼續維持下去,我們民族所現在除了有人類學、民族學之外,也包括了社會學,還有民族音樂學、心理學,尤其是所謂的「本土心理學」。像這一種狀況呢,實際上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在不同的場合,或是在同樣的一個場合裡,不同的學門的人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對話。
從國際潮流到本土反思
《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剛剛瞿先生講得很清楚,是1970年開始開會,然後持續進行的讀書會,等於是個別的報告,最後篩選出12篇文章編成一本專書。以題目來講的話呢,說真的,這已經不是一個非常時髦的議題了,因為所謂「中國人性格」,所謂national character,我們不管叫它「中國人的性格」或者叫「民族性」,這個是從美國的culture & personality學派而來。這個學派從1940年開始推動,大概研究最多的是40年代末期、50年代,在這之後已經慢慢減少了,它的影響力已經分化到不同的區域研究了。尤其是culture & personality 的研究,慢慢轉向一個是「兒童教養」的研究,就是研究文化跟兒童教養之間的關係;另外一個是轉向所謂「現代化」的研究,現代化的研究又跟社會心理學結合在一起。所以從某一個角度來講,在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提出這個「國民性」的研究,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學術界尖端的研究課題。不過在台灣來講,當時確實有它重要的意義,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1960年代後半期,在中國大陸有瘋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清除傳統文化裡面的殘渣敗絮,然後進行政治鬥爭,要建立毛澤東的一神崇拜。這是一個完全瘋狂性、毀滅性的社會運動,那是1966年開始的。那在台灣呢,也是1966年,為了對應大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就提出了「中國文化復興運動」。這完全是對應式的,你要摧毀傳統文化,那我們就要重建、保持傳統文化,這是由一些極右派的學者提出來一些論證,就是要維持我們的正統、我們的道統。在這個狀況之下,是用另外一種社會運動方式,來建立蔣介石的一神崇拜。在這個夾縫中,真正碰到問題的是:台灣當時的學者、學術界,要怎麼樣維持學術尊嚴,怎樣維持學術的自立性?實際上就是說,李亦園先生跟楊國樞先生當時提出來要辦這樣的研討會,就是很直接地用行為科學的方法,來解剖中國人的性格,來看傳統文化到底是什麼,這是一種非常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做法,用來檢討文化到底是什麼。其實殷海光先生那時候也出了一本書,叫《中國文化的展望》,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潮流,就是對於用狂熱的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運動、控制學術界的一個反駁,或者反擊。那我們也看到李亦園先生、楊國樞先生1972年出這本書,那在1971年的時候,國民黨的大掌櫃王昇就提「三反」:反自由主義、反存在主義、反行為主義。這種對學術的暴力干涉、侵犯,完全不尊重學術尊嚴的做法,在當時是一個很可怕的潮流。李、楊兩位先生就是用很委婉的方法來提出看法,來抗拒這種政治運動的影響。
剛剛瞿先生也提到說,科際整合是他們(李、楊)提出來,那當然,這個也是受到李先生在哈佛大學受教育的影響。張光直先生是1972年之後兩年回台灣,才提出「濁大計畫」的。因為當時張光直先生還是受到台灣官方相當的禮遇,所以在這個狀況下,科際整合就變成一個可以被容忍的東西。不過,當時整個過程之中,我們也知道1971年台大哲學系發生了八個教授被解聘的事件,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國民黨整肅學術界的一個前兆,在這種狀況下,學術界能夠用一種很委婉的方式,把資料攤開來說,「對不起,你們講那一套,其實我們不一定贊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看法,我們由學術界角度來看的話,我們認為所謂儒家的理想意識形態是什麼、大學生的想法是什麼,家庭關係又是什麼,親子觀又是什麼……。」像這種以一種很具體的方式,把一些人際關係、傳統的特質把它坦呈出來,這對於當時用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的當權者,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我想也是為什麼後來《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在2009年,會被日本選入「100本影響亞洲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的一個背景。
學術典範的轉變:從實證科學到人文取向
當然,我們講到所謂empathy的研究。《中國人性格》在當時可以琢磨一個大架構,非常有企圖心的想要把不同學科整合起來,然後提出具體的看法;然後為什麼現在的這個《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的討論,反而有點退到比較「個人」的層次?
行為科學研究到了1970年代之後,有一個很大的趨向,就是對於所謂「現代性」、「現代化」的一些解釋。尤其是社會心理學,像Everett Hagen或者是Alex Inkles,他們這些社會心理學者,都提出很具體的一些看法,他們認為「現代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向,那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怎麼樣得到「同理心」?他們很理直氣壯地說,我們要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就是要看現代化要怎麼走下去,然後看這些所謂的傳統社會怎麼樣取得現代性,那現代性的表徵就是所謂的「同理心」。我想 Inkles 的研究是最清楚了,他比較四個國家的國民所反映出來的empathy level,他完全是用量化的表格,來討論土耳其是怎麼樣、埃及是怎麼樣,這四個不同國家經過怎樣的過程後,同理心的程度會提升;換句話說,取得「同理心」這個目標就達成了「現代化」。這跟我們現在40年以後出版的《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所講的「同理心」,在意義上就不太一樣了,因為這本書所謂的同理心,在scale上,剛瞿先生也講了,不談大問題,不談大方向,不談怎麼取得現代性。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同理心」,就比較強調個人的感受,我們怎樣基於人跟人之間的一些基本的條件,而產生所謂「感同身受」的想法或念頭。換句話說,40年前楊國樞先生、李亦園先生他們所提出討論這個大哉問的時候,他們是有一個很大的目標的,目標很清楚,方法也很清楚,完全是科學實證式的:要怎麼樣用一些很具體的工具,來取得實證資料,來說明社會怎麼發展,文化怎麼改變。這一點跟現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這本書上所談的就有點不一樣了。
從科際「整合」到科際「對話」
《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這本新書所談的,實際上可以說是比較直接反映21世紀以後,當以前所謂「科學主義」已經受人懷疑,然後實證科學也不能代表是唯一的一個學術取向的時候,這時候我們所談的 empathy,已經轉變到另一個層次。換句話說,我們所要瞭解的,是怎麼樣通過這種展現不同文化、借用不同的表達方式,來理解「感同身受」背後的文化背景,不管我們是叫情感啦、理念啦,或者是個人的感覺。這時候我們強調的是個人作為一個文化載體,怎樣能夠進入另外一個文化。換句話說,這時候我們已經不談科際「整合」了,我們談的是科際「對話」,也就是兩個不同的學門怎麼樣能夠建立一個 Gadamar 所講的這個fusion of horizons,怎麼樣經過不斷的互相適調,然後把我們的語言層次拉到一起,讓我們彼此的意念、想法可以溝通。這個很明顯地就是一個學術典範的轉變。換句話說,以前那種大理論、大規模、科學式的取向呢,現在已經受到各種挑戰,然後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在研究上也慢慢變得更謙虛了、更隱晦了,比較不願意說我就是要走到這個目標,或者走到不同方向去。換句話說,這兩本書代表的是不同的時代所具有的不同學術風氣跟取向,也產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
人類學跟心理學長期合作,尤其在民族所已經超過40年了。在不同的時代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或影響,這兩本書就是最明顯的──顯示出學術理論典範的轉變,怎麼影響到後面學術的成果。但是最主要的,我們從這些發展可以看得出來的是,我們要怎麼樣走出自己個人的象牙塔,怎麼樣跟別的學門學習不同的新觀念、不同的新想法,或者新取向,我想這是這兩本書在民族所能夠開花結果最重要的一個成果。

劉斐玟:非常謝謝黃所長幫我們點出學術發展的「時代性」。黃所長剛剛也提到學術發展的重要心念,就是不斷地提醒自己,如何以謙懷的心,去面對不同的學科,怎樣可以從不同的學科汲取營養,走出「象牙塔」,而人文素養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們現在就聆聽文哲所胡曉真所長的發言。
胡曉真:剛才我們已經從「上古史」進入「中古史」,那現在可以進入「近代史」。同時,剛才我們聽到的是非常內部的,而且專業的意見,那麼我所能提供的呢,那就絕對是一個外緣,可以說就是外部的一些,不能說是意見,只能夠說是聯想、association。我自己的專業是明清文學,而且是明清的敘事文學。對我來說,每一樣東西都是敘事,我寫論文也是一個 narrative,因為它要有首、有尾、有中間,而且要傳達一個特定的message,而且我希望可以說服人家;它是一個修辭,同時也是一個敘事。我的每一次上台呢,不管是演講或者是發表,或者如同現在做一個引言也好,對我來說,都是一個narrative,所以我常常把自己想像成每一個場次都是「說書」,那我就是這個「說書人」。那麼說書人的任務是什麼呢?就是要用它語言的藝術,想辦法把他的聽眾帶領進入他所要講述的那個世界,同時,試圖讓聽眾跟這個說書人用同樣的、類似的觀點以及邏輯,去想像一件事情。讓說書人跟聽眾有一個同樣的敘事邏輯,那其實呢,就是在建立一個同理心吧!
入話
所以呢,我今天一開始就要模仿傳統說書人,就是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先講一個「入話」,就是所謂的 cushion story。這個 story 是什麼呢?就是我正在為今天的引言煩惱的時候,前兩天我的朋友人類學家王鵬惠博士,很興奮的告訴我說他看到了一個「出土文物」!那麼這個「出土文物」是什麼呢?就是他在整理一些舊的期刊資料時,找到了很多年前的《台大青年校刊》,而且是台灣大學40周年的特刊;也就是說,王博士在1985年出版的《台大青年特刊》裡面看到了我的文章。這件事情我完全不記得,但是王博士把書拿給我看之後,事實俱在,真的有我的文章。顯然,那時候的校稿實在不太精良,在目錄裡面把我的名字都打錯了,但是打開一看,這真的是我的文章,我自己看了真的嚇了一跳,因為我寫的這篇文章叫做〈中國民族學的開山宗師凌純聲老師〉。我真的太吃驚了,而且我沒辦法想像,1985年那時候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我,到底為什麼有這個膽子,覺得可以寫一篇文章來介紹凌純聲老師呢?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追溯那個年輕的心靈到底是怎麼想的,我猜很可能就是那時候為了籌備40周年特刊,所被分配到的任務吧。同時,也非常顯然地,我一定是處在外文系的邊緣地帶,不然為什麼我的同學們分到的都是英千里、夏濟安、黎烈文,都是我們外文系的本科,而我,卻分到不是我自己專業的凌純聲老師。但是我看了我自己寫的文章,一方面覺得「嗯,當時文筆還相當通順」,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是覺得害羞,因為顯然是從頭抄到尾,就是參考了很多前輩學者的著作之後,想辦法把它順出一個 narrative。這是我當時的一個做法,但是這豈不是就是我一個非常早期的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經驗嗎?雖然這經驗完全就是一個 accident,但是這個意外似乎也說明,每個人的人生之路似乎自有一個安排,因為這跟我後來的學術興趣其實也有若干關係,因為我一直都希望可以跨越出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學術疆界。比方說,我從外文系英美文學的訓練走到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再走到中國文學;在中國文學中,我希望可以有一個東亞視域、比較視域等等,以及在其他的學科訓練上,希望可以拓展一些眼界。
我在這裡就讀一段我當時所寫的話:「凌教授認為學者不可侷限於個人的研究範圍,雖然要以研究的題目為主,但是只要有關的材料,不論是屬於考古、民族、歷史或是民族學,都應該要兼顧。這是張光直先生分析凌教授為學精神所得,也是凌教授對中國民族學界影響最深遠之處。」不知道有沒有誤解張光直教授的意思,但是至少那個時候還知道一點學術倫理,雖然沒有註腳,但是知道要把張光直先生的名字拉出來。當然,張光直先生對於凌純聲教授為學精神的分析,跟我們現在所說的跨學科、跨領域,也許不完全相合,但是它有一個基本精神是相通的。這是我幾十年前意外的跨學科經驗。到現在,我覺得對我自己還是有點啟發。這就是我的「入話」,我的 cushion story。也就是說,這種跨學科或者是跨領域的視野,或是自我期許,其實是人文社會科學界一個很長遠的傳統,它並不是說是近一、二十年的發明。
跨學科視野的挑戰:背景抑或前景
提到跨學科對話,不管是要科際整合,或者僅僅是要對話,其實它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非常難為的,特別是看我們要把它放在我們研究的「背景」還是「前景」。放在背景相對來說容易,放在前景呢比較難。怎麼樣叫放在「背景」呢?其實每一個人選擇了不管是人文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我們興趣都是廣泛的,所以在整個學習或者甚至是研究的過程當中,我們閱讀的範圍或者是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向,一定都會是跨學科、跨領域的。這樣的一個閱讀以及研究興趣,多多少少都會影響我們在做研究時的選題、選材,還有思考方式;而且,最後在我們的研究成果中,總是能夠找到蛛絲馬跡。所以如果未來有人要來探討這一代人文學者或是社會學者的研究,一定能夠在他的論文專書裡找到其他學科的影響。問題是,其他學科或者是其他領域的影響,卻不一定能夠在研究者的思考架構裡完整地展現出來。
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說,我是台大外文系畢業之後,到美國先念了比較文學,後來轉入東亞系的系統。各位知道美國的東亞系,它的師資其實都是有限的,能夠開出來的課程也是有限的,所以每一個研究生絕對不可能只選他自己那個單一領域的課,因為那就真的沒有那麼多課可以選。我的專業是古典文學,但是我絕對不可能只上古典文學,而是會想辦法去上歷史的課,我也上過文化人類學的課──那時候真的是顯學,如果不上文化人類學,都覺得自己不是人了。所以在那個學習過程中,自然而然會期望自己研究的「前景」裡面,不但有古典文學,而且也有英美文學、歐洲文學、比較文學,有歷史的視野,有思想的深度,甚至也有文化人類學的影響等等,自己會給自己圖譜一個非常好的研究光譜。但是呢,等到真正要把它落實成為學位論文的時候,就知道至少在當時是沒有能力把自己方方面面的興趣,都落實到研究及學位論文的撰寫上面。所以我覺得作為「背景」,在我自己的學術領域裡,那些其實都在,但是當我要把它 foreground 的時候,就真的沒有那麼容易。就像剛才瞿老師講的,我們整個跨學科的訓練,它要能夠真正的深入我們研究肌理的話,其實恐怕是需要非常多的實驗跟失敗、很強的意志力,以及很多年的積累等,才有可能有一些具體的呈現。
文哲所的模式:浮動式的平衡
接下來呢,我想要回到主辦單位邀請我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所任職的單位是中研院的文哲所,那麼文哲所在本質上可以算是一個多學科、多元的所。文哲所基本上有三個大的領域:文學、哲學與經學。這個當然都是人文學科,也可以放在傳統中文系的架構來思考,因為本來文史哲不分家,中文系裡面確實有思想,有文學,又有考證、文獻。但是確實呢,這幾個領域在實際進行研究時,往往會呈現非常不同的研究特色,其路徑也是挺不相同的,所以在同一個所裡面,有這樣三足鼎立的領域,究竟要怎麼樣去推動它的研究?是各自發展呢?還是應該要進行某一種整合,或至少是對話?雖然我不敢亂講,因為回去可能要受批判,但是我想很公平地說,我們從籌備處到現在,我剛才說的那兩種方式是不斷的在調整、實驗,它是永遠處在一個浮動的狀態。因為完全的混合在一起固然不可能,畢竟每一個學科的訓練真的不同。我們的哲學家同仁往往沒有辦法認同我們文學研究者「隨便的association 」;同樣地,我們文學的研究者往往會覺得,為什麼我們哲學研究的同仁對於文獻的梳理是「這麼不在意」等等。所以它有一些基本上不能夠理解之處,但是在同一個所的架構裡面去進行研究,又必須彼此尊重,而且試圖互相了解。這當然也是「同理心」的一種實驗,它是艱難的,可是我們還是會用不同的學術活動或者是研究計畫,試圖把我們所裡面不同領域的同仁,放到同一個平台上,至少建立平台,讓對話是有可能性的,這個會是一個起步。
科際對話的神經傳導效應:突破「困寫」
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來看,我們古典文學的同仁流行一個特別的詞叫做「困寫」。論文寫不出來,簡單說,就叫「困寫」。「困寫」的時候要怎麼辦呢?我自己個人的發明就是,困寫的時候,絕對不會去找一個我自己行內的同仁來講話,絕對不會去跟同樣做古典文學、明清小說的同仁來聊一聊;我找的一定是跟我不同學科的同仁。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如同剛才瞿老師講到的,我們現在寫論文,如果別的學科都看不懂,那你這個東西怎麼做大?我的策略就是想辦法把我現在想的事情,讓一個不是學古典文學的人,能夠聽得懂,而且覺得有趣,那麼在跟他談話的過程中,很奇妙地,幾乎每一次都能成功的找到一個敘述的方式,找到一個邏輯是我自己以及我的聽眾會覺得有趣的,而這就幫助了我的論文能夠繼續寫下去。雖然這是相當個人性的一個對話,但是我覺得它也未嘗不可放在一個更高的平台上面,就像今天這樣的場合,它也還是有可能可以運作的,有可能在思想的某一個層次,我們的腦子裏面的那個 connection,經過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某一種刺激,而在瞬間就好像什麼神經傳導的,就會打通,那麼在這個層次上面,我覺得「對話」絕對是有可能,而且是有意義的。
學科對話仍待深化
當然,文學這個學科,即使在人文學裡面,它也比較特別,比方說,相對於歷史學來說,它往往被認為是一個「最不科學」的學科,也因為如此,我們做文學專業的人,往往希望可以跟別人對話,但是別人未必願意跟我們對話(笑)。這並不是一個批評的意思,但是我覺得這有它的背景。不好意思,瞿老師冒犯一下,比方說在這個《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裡面,剛才瞿老師有分析一下它的學科所落在的位置,其中有兩位思想家,但卻沒有做文學的人,這難免代表人文學科跟社會科學的分野還是比較大的,特別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好像是非科學性,至少在以前的學術傳統裡面,會被認為可能是「有點問題的」。我們文學的文本其實常常成為其他學科的學者利用的材料,比方說,歷史學者他要讀 Jane Austen,就可以理解那個時代的社會;中國歷史的學者讀《三言二拍》,就可以知道晚明時期的社會以及當時人的精神狀態;政治學的學者可以從科幻小說中,讀到很多的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我也真的必須說,歷史學者、人類學者、政治學者等,他們在利用文學作品的時候,他們閱讀的深度,有的時候真的讓我們文學研究者非常佩服。再舉一個比較近的例子,楊國樞教授,那時還沒有 big data 這個名詞,但是他當時就利用了大量的明清時期的筆記小說材料,來研究中國人的心理,這個企圖是非常宏大的。利用筆記小說的資料來研究,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大的vision,但是作為文學研究者,我們仍要不無遺憾地說,把筆記小說當作數據的做法上,它確實不太可能用到文學分析或者是文學層面的層次,就這點來看,或許科際之間的對話,我們還需要有其他努力來深化它。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今天同樣再用筆記小說的材料來探討某一個問題的話,我會認為文學詮釋的層次或許也是不可缺少的。
互為主體的文學閱讀
最後呢,讓我回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的〈導論〉中。本書對於三個關鍵詞,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都分別有很清楚的定義跟討論,特別在談到「同理心」的時候,〈導論〉提到,「同理心是情感、理智、想像與自我投射等因素的相互表述,彼此激發由之所形塑的綜合體」,因此「同理心是兩個主體間的對話」,同理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當我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我覺得這裡描述的,豈非就是我們文學閱讀以及文學詮釋的一個過程嗎?事實上,所謂的 literary reading 或者是 interpretation,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我作為一個讀者,跟我所要閱讀的作者以及他的作品,就是必須是互為主體的。雖然當前流行的文學理論,應該說前一陣子流行的文學理論,告訴我們說「作者已死」(the author is dead),可是我覺得文學詮釋正是要 reading into the dead author, reading inside the dead author。我們本來就是說「尚友古人」,閱讀就是一個要「追古人之心」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一定是infinite retreat,就是你越追他跑越遠,永遠都追不到,但是對於文本的尊重,正如同兩個不同的主體之間的彼此尊重一樣。〈導論〉中關於「同理心」的說法,讓我想到文學詮釋其實也是用同樣的一個視野來進行的,就這點來說,我們其實就看到了兩個學科之間對話,彼此影響、啟發,甚至朝向同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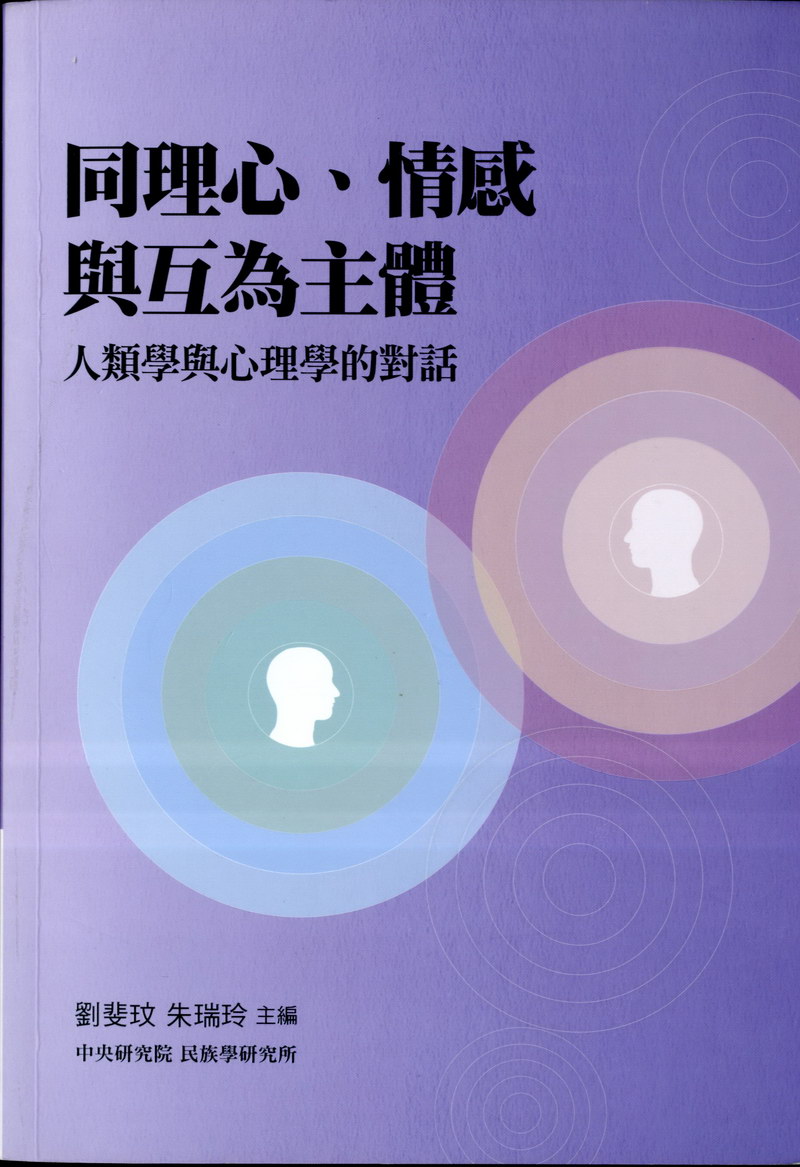
劉斐玟:謝謝胡曉真所長的「說書」。我想透過剛剛三位的發言,大家已經感受到不同的學者在陳述方面,呈現出不同的風格。我們剛剛聽了所謂的「上古」、「中古」,跟「近代」,現在來跨一跨時空,請哲學家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另類的觀察。
沈志中:各位在這裡,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傳承的意義十分重大,問題是各位可能要有心理準備,接下來我們打算從一個嚴肅的歷史頻道,突然轉到兒童台,雖然我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兒童,不過你們也知道兒童台總是一些老人在裝兒童。當然,在我開始講之前,我還是要藉由這次的機會……,因為非常榮幸能夠跟《中國人的性格》,曾經參與這個研討盛會的這些前輩們,一起坐在這裡,因為我必須跟他們致敬。自從我過了青少年以後,大概沒有看一本書可以這樣一個晚上把它看完,特別是關於每一篇論文後半段的討論,你可以很具體地感受到幾乎是某種幾近天真地對於理性的信仰,他們相信「討論」跟「對話」。我自己試了很多次,但是沒有一次成功;我的意思是說,在我進入學術圈之後,也曾經參與過許多這樣子的討論,但是沒有一次能夠延續到超過三次以上,所以我特別要向瞿老師致敬。
從同理心談起:審美、感受、理解
關於這個同理心,英文 empathy是來自於翻譯德文的Einfuhlung,字面意義是 feeling into,它原本表示的是在審美的經驗當中,對於那些無生命物的想像與認同。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想像自己可以化身為物,可以是石頭或者是樹木,去進入客體當中去想像它會怎麼感受等等,而德國心理學家Lipps則把這個構想,發揮在人可以對於其他人的心理狀態,進行某種程的的感受跟了解。那麼我們首先就必須要問,這種進入他人身體去感受是如何可能?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換句話說,同理心的作用是不是像心電感應這樣子,真的可以把心靈投射到他人的身體裡面,還是說充其量只是一種主觀的想像。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同理心」除了是一種sympathy ,是一種共同的感受,一種compassion 的情懷之外,那empathy 有什麼客觀性可言?
愛倫坡的文學啟發:互為主體與囚犯悖論
其次,即便以上這些巨大的困難都可以被克服,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設想,在所謂的「相互主體」關係之下的同理心會是什麼樣的狀況,會以什麼樣的情況產生?我可以舉一個例子,這也可以是一個文學的例子,也就是在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說〈失竊信件〉裡面,他提到一個小孩子玩的猜謎遊戲。有個小孩他手裡握著一或二或三個彈珠,然後讓對方去猜他手中的彈珠是奇數還是偶數,如果對方猜中了,就可以贏走這個彈珠,如果猜錯了,就要輸掉一顆彈珠。這個小孩八歲,是個大玩家,因為他最後贏走全校同學的彈珠。在小說裡面,主角就去問他說,「你是怎麼做到的?」很簡單,這小朋友就是透過「同理心」,他會先去揣摩對方的表情,他去模仿對方的表情,他就看「這樣子的表情在他內心裏面會產生什麼念頭?」於是他就推論出,如果他遇到的對方的表情看起來就是一個阿呆,那只要猜中一次,他第二次還會猜一樣的,那他自己手裡就換一個數目;那反過來,如果對方的表情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精的小鬼,那他就反其道而行,對方第二次會猜不一樣的,那他自己手裡握著的彈珠數量就是一樣的。原來透過同理心,他怎麼樣都贏!很顯然,這個小孩可以成功的前提是什麼?就是他跟對手處在一種互為主體的同理心關係;也就是說,我會猜想對方會怎麼想,去感受對方會怎麼感受。但問題是,這只是一個故事,因為實際上對方也會猜我是怎麼想、怎麼感受,這個就是非常著名的囚犯悖論,在1950年代發展成賽局理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囚犯悖論。也就是說,你會處在一種鏡像的映射關係,我們稱它為賽局理論。那並不是認為說這樣子的關係會「無解」,但是「有解」的前提是說,這個賽局的雙方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利益。所以我們要問的是,在心理跟情感的層面上面,這樣子一種互為主體的同理心的關係,可以對研究者跟被研究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巴夫洛夫和他的狗
同理心既然是對人或對物的同理感受,但我們從剛剛的例子看到的是,其實「人」的感受跟猜忌實在是太為複雜,而我們對於「物」的感受又不太確定,所以我們就舉一個介於這兩者中間的一個例子好了,也就是心理學者都知道的巴夫洛夫的著名實驗。一般對於這個實驗的認識,都是去強調反射跟制約,也就是說當狗看到肉牠會分泌胃液,這是反射,而巴夫洛夫則是透過鈴聲或者哨音來取代肉塊,達到制約的目的。其實巴夫洛夫要研究的,一開始並不是制約行為,而是消化系統。他其實是透過手術,在狗的咽喉上面裝了導管,他想要試試看,讓狗吃食物,可是食物沒有掉到胃裡,那消化系統會起什麼樣的反應?巴夫洛夫後來發現,食物沒有掉進狗的胃部,可是消化系統仍然會起作用;換句話說,胃液還是會分泌出來。這時候他發現,好像精神因素也同樣可以引起消化系統的作用;也就是說,不光是食物在嘴巴裡面會引起胃液的分泌,只要狗看到帶著食物的人,甚至研究人員在場他沒有帶食物,只要聽到研究人員走近的聲音,牠也都會分泌胃液。換句話說,這些因素跟食物一點關係都沒有,跟消化系統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會形成反射作用,於是最後這場實驗才會簡化成為用鈴聲跟胃液,來對應這樣的制約關係。
我們會問說,在這個實驗裡面有沒有「同理心」的作用?當然有啊,因為很顯然,是因為研究者巴夫洛夫讓鈴聲跟胃液產生關係。簡單的說,這個實驗在本質上是一個欺騙的效應,就是研究者騙了這條狗;因為被研究的這個生命體被騙了,所以牠啟動了自然的消化反應。這顯示這實驗其實跟狗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它也可以發生在人,或者其他的生命體、其他動物身上。顯然是因為同理心的作用,所以巴夫洛夫才會去想,如果他是這隻狗,他會因為鈴聲而產生飢餓的感覺,以致於巴夫洛夫只看到反射跟制約的現象,他沒有察覺到自己在實驗中「欺騙」的向度。那你會問說,至於狗有沒有對巴夫洛夫產生同理心?當然,我們不是狗,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個關於這個實驗非常有名的笑話,幾乎所有心理學的書都會寫到。那就是那隻狗很得意的告訴另外一隻狗,「欸,你看我的實驗成功了,因為只要每次我一流口水,巴夫洛夫就趕快搖鈴,然後趕快在他的筆記上面抄抄寫寫,不知道寫什麼東西。」以上這兩個例子,都是在研究中引入同理心的作用,這顯示出同理心的引入所帶來的問題,恐怕比它所能夠解決的問題更多。
蘇格拉底的知識論:對話與欲求
那麼我們要問說,研究者跟被研究者之間的對話關係,如果不能夠建立在這種互為主體的同理心之上,那還有什麼可以參考的模式?那我們不妨看看最古老的對話當中的知識研究模式,也就是蘇格拉底的對話。蘇格拉底的〈門諾篇〉(Meno)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對話,那個精彩的程度恐怕跟我剛說《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附在每篇文章後面的討論一樣精采。蘇格拉底的對話可以讓我們看到,知識如何在對話當中產生,而不涉及「同理心」的問題。他對話的主題是:什麼是美德?以及我們所要追求的知識,到底是天生的或者是透過學習而獲得?在這個過程中,蘇格拉底為了要向Meno 證明說,其實學習只不過是去回憶起原本靈魂就有的東西,他就跟Meno 說,你隨便找你旁邊那些小奴隸來,最好是沒受過教育的,只要會說希臘文就好。所以Meno 就找了一個小奴隸來,那蘇格拉底就在地上畫了一個正方形的圖,然後就問這個小奴隸:「這面積多大?」這個小奴隸沒學過幾何學,他當然不知道怎麼樣去求面積的大小。於是蘇格拉底就跟他說,你看好喔,他在地上把一個正方形劃成兩半,然後告訴他說,這個長邊是2公尺,那短邊的邊長是1公尺,那麼這半邊的面積就是2平方公尺,那問小奴隸,你現在知道這正方形多大了吧?!奴隸就說是4平方公尺。這時候蘇格拉底就很得意地跟Meno 說,「你看吧,沒有人教他欸,是他自己回想起來這個幾何學知識的。」
當然,你們會質疑,Meno 也質疑:「真的是這樣嗎?」蘇格拉底就說,那就再試試看。他就真的再問奴隸說,「你會不會計算並繪出面積比這個正方形大2倍的正方形?」奴隸說:「我會,我會。」於是他就在地上把正方形的每個邊長都加長兩倍,這當然是錯的了,因為這樣變成四倍了。蘇格拉底就跟Meno 說,「你看這小子,他明明知道自己無知,然後還沒有求知慾。他事實上並不知道答案,可是他卻以為他知道。你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會去學習嗎?當然不會!」在這裡,蘇格拉底要強調的是,任何知識關係的建立,必然是一者是處在要求的狀態之下。不過,剛才蘇格拉底要說的是,即使這個奴隸處在沒有要學習的狀態之下,他還是能夠透過跟蘇格拉底一起對話,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知識,而不是從蘇格拉底那裏獲得知識。於是,蘇格拉底就把先前的正方形擦掉,重新畫一個正方形,然後依據這個邊長,再畫出另外三個同樣大小的正方形,然後問他說「這樣是原來正方形的幾倍?」奴隸看一下,「啊,原來不對,這樣是四倍,不是兩倍。」可是蘇格拉底就跟他講,「可是我們要的只是兩倍大的正方形不是嗎?」奴隸說:「對」。於是,蘇格拉底就畫出其中一個正方形的對角線,問他說:「我們可不可以把原來的正方形分成兩半?」奴隸說:「可以」。「那如果我們把全部的正方形都分成兩半,那麼我們當中所得到的,就由對角線所構成的這個正方形總共有幾個一半呢?」奴隸就說:「有四個一半。」「那四個一半湊起來是多少呢?」「四個一半剛好就是原來四方形的兩倍」。這時候蘇格拉底就很得意的問門諾,「他的回答有沒有用到任何不屬於他的意見?沒有,完全都是他自己的。」
精神分析的觀點:「被研究者」變成「研究者」
當然,我們不難發現,蘇格拉底畫圖給這個奴隸看的時候,已經在給他上幾何學了啦!不過這當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例子凸顯出蘇格拉底並沒有自居於擁有知識的研究者的位子,而把奴隸當成研究對象去研究,比方說,奴隸的學習過程。如果蘇格拉底這麼做,他就可以提出兒童發展心理學了。那相反的,蘇格拉底是透過「對話」去陪伴奴隸,和他一起探索,藉此讓這個奴隸成為一個主動的求知者,主動產生求知的慾望,進而產生知識。這當中有任何跟同理心相同的現象嗎?並沒有!這當中有的其實是被精神分析當作是transference 的操作,這是為什麼人們現在不稱那些接受精神分析的人為「被分析者」,而是以具有主動意義的「分析者analysant」來稱呼他們。那麼同樣的,如果精神分析能夠替同理心這個議題帶來一些方向上的修正的話,或許是應該思考「如何讓被研究者成為主動的研究者」。這麼一來,原先的研究者我們應該怎麼稱呼他們呢?如果各位不反對的話,我們就稱呼他們「研究員」好了,而「被研究者」才是真正的「研究者」。
佛洛伊德:讓石頭自行說話
最後,我想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引述佛洛伊德所說的一個比喻。1896年,佛洛伊德在發明精神分析、在思考什麼是精神分析的時候,引用的是人類學跟考古學的例子。大意大概是這樣:我們可以想像有一個人在旅遊的過程當中,來到了一處廢墟,這些廢墟引起他非常大的興趣。那他可以做的,比方說,做紀錄、描述,最多就是去訪問一下住在附近的居民,關於這處廢墟曾經有的歷史。但是佛洛伊德說,我們也可以邀請這些居民,給他們工具,給他們鏟子、勺子,並且邀請這些居民跟我們一起共同工作,去清理廢墟的塵土,去讓這些殘存物被發掘出來。佛洛伊德說,如果運氣好的話,我們搞不好會挖出一些,比方說,剛好有刻著兩種文字的石碑,那這些石碑就會傾吐出讓我們意想不到的關於舊時的歷史真相。這個時候他說:「我們的理想就是讓石頭自行說話。」相較對同理心的強調,這個是精神分析所帶來的一個不同向度的思考。

提問
劉斐玟:非常感謝沈志中教授這段具有哲學論辯的評論。現在,我們就把時間開放給所有參加的來賓,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心得,或想法,想要提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蔣斌:前幾天主辦單位打電話邀我參加這個會,我很高興就來了,因為我心裡有很多問題,尤其是我知道瞿先生要來。我的問題不見得一定是問瞿先生,我想也可以提出來問大家啦。我手上的《中國人的性格》是1975年買的,而且已經是第三刷了,1972年出版的,到 ’75年已經是第三刷了。那時候我還在讀大學,讀政大民族社會學系,文崇一先生是系主任,他完全是按照中研院民族所的模式把它搬到政大去。現在回頭來看,要描寫當時讀這本書的心情,就是「除魅(disenchanting)」。當然,當時讀的時候腦子裡面並沒有這個概念,可是就覺得說,「哇,二十四孝是關於食物的。」非常的興奮,回去還跟我媽說:「你知不知道二十四孝講的其實是食物的關係?」我媽就說:「胡說八道,你在大學就學這個東西啊?」可是那時候就覺得說,所謂行為科學或者社會科學是如此的迷人,它是一個讓我們對於主流論述一種「除魅」,或稱它是「解構」或者「顛覆」。當然,這本書之所以被禁,剛剛瞿先生也講了,也是因為disenchanting 的關係。
回過頭來看一下《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這本書,我們可以發覺這中間有個不一樣。《中國人的性格》是針對自己,我們假定作者都是中國人,針對自己,而且針對主流的權威的論述,所以當時的「除魅」或者「解構」,變成是一個你有權利這樣做,而且你也有義務這樣做,是學術的義務,而且是一個成功的達陣。可是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這本書裡,我覺得朱瑞玲「放生」的研究,在題目上具有類似的對於自己、社會的主流論述的一個除魅的潛力,可是朱瑞玲這篇文章基本上還是把它引導到方法跟跨學科對話的這個角度去。可除此之外,所有的文章基本上就是研究他者,研究弱者、弱勢團體。作為人類學家,我們在研究他者、研究弱者的時候,相對來講,好像除魅就不是你的任務了,反而你是要去enchanting。我們現在指導的做原住民研究的學生論文,最後結論常常就是「好感人喔」,「這個好迷人喔」。好像說在主題上,已經沒有這個disenchanting 的使命,你好像也覺得disenchanting 變成是一個不道德、不倫理的事情,因為你是要去promote,你是要讓這些弱者、他者變成enchanting。所以是不是我們在研究弱者跟他者的時候,我們不應該disenchanting,我們應該enchanting,讓這些東西變得很迷人?
我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那麼對於台灣當代的主流論述,我們是不是也有一個 disenchanting的學術使命?比方說,我們能不能預期有一本書叫《台灣人的性格》,針對台灣當代的主流論述,像是台灣主體意識、公民社會、民主、NGO啦。所有研究慈濟的論文,我都還沒有看到有這個disenchanting的,好像還沒有?像《台灣人類學刊》曾經出過一篇維吉尼亞大學Frederick H. Damon寫的 ”What Good Are Elections”,這是我心目中比較接近disenchanting 的論文。那麼我不太曉得是不是我們已經放棄了[這個使命],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不像當時像政戰部這些的dominant 的威權論述,所以沒有必要去disenchanting anything,或者是這個disenchantment 的任務已經散在很多地方,而不需要一本書來做;或者是說,我們科際整合的理想,還是可以有一個隱隱約約的《台灣人的性格》這樣子的一本書在腦子裏面。
瞿海源:蔣斌講得非常好。關於除魅(disenchantment),我想提兩點。第一點就我們人類學跟社會學研究原住民還是不太一樣。李亦園先生也做過原住民山地政策的研究,我跟蕭新煌提的意見就比較不是那樣子,就是比較會有意見,會說就是要這樣這樣這樣做……,李先生就比較客氣啦,不會有太多的去冒犯,所以這個是角度不一樣。第二點,我覺得很深的感觸,就是蔣斌講的「台灣人的性格」,這個研究大概以前沒人敢做,因為沒有同理心啊(笑)。可是,我覺得其實都在做,不是學術在做,是從社會批判……,在批判這個台灣的主體性格、台灣人的民族性格。可是你說真正學術,那是沒人做的,所以大家可以再考慮看看是不是要來做一做,看看「台灣人的性格」到底怎麼回事,因為確實從「除魅」的角度來看,是非常有趣的。
郭佩宜: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非常醒腦,我只想簡短地回應兩點。一個是蔣斌剛剛講到的 enchantment 和 disenchantment,其實像「芭樂人類學」都是在寫disenchanting 台灣社會的一些議題,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發展成學術研究,開個研討會啊,或是回到過去「講演會」的模式,這些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另外,我想回應沈志中教授。您剛剛講的「如何開始讓被研究者開始研究」,「讓石頭自己說話」,這其實跟人類學家在田野中遇到的情境滿類似的。如果是閱讀文獻的話,或許是讓石頭自己說話那個層次;在田野中與田野地的朋友一起聊天的那個過程,反而比較像是讓被研究者開始研究。比如說,當你問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是他沒有想過的,但是透過這一個對話,激發他開始去想,比如說,「什麼時候不是頭目的人也可以穿戴頭目的裝飾?」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平常不盡然會有系統性的去思考,或者他不是完全無知但也不會特別提出來講,但是透過「對話」,這個對話其實是透過他的嘴巴,透過他重新的reflection、思考,然後他談出了他的「研究」、他的分析、他的歸納、他的價值觀。所以我覺得在田野中相互對話那個過程,就是在讓「被研究者開始研究」;同時,他的reflection 也讓原來所謂的「研究員」也會有重新又開始研究的一個過程,所以我覺得「互為主體」真正迷人的地方似乎是在這裡!
石磊:我想今天大家講的,某個程度還是方法的問題。因為我以前的研究大部分是做原住民的,或者做古代社會的,這兩個方面都是說你要到田野或者做文獻,那你是設身處地的思考被研究者什麼樣的,怎樣去了解他,但是這跟「同理心」是不是一樣的問題?如果我們說,在原住民社會、當代社會裡,我們跟他溝通、跟他對話,然後瞭解他們的情況、他們的社會、他們的文化,這種情況會不會真的跟他完全同理?不知道!問題是說,不同文化是不是有一個同理心?我們只是用我們認為是同理心去研究的,還是真正一個同理心在那邊?這就是人性的問題了。我不是學心理學的,可能我現在講的話是外行話,但到底有沒有一個像傳統社會講人性,是善、惡或者其他東西?這些東西有沒有真正一個共同的標準?就是說,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同理心在,真的有一個共同的人性,或者什麼東西在,而不是因為文化所造成的?如果有的話,如果能抓到那個東西,那大家互相溝通就容易了,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我就向大家請教請教。
余舜德:剛剛瞿先生在講當時科際整合的背景時,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當時張光直先生提出來的一個意見,他說整合常常不是真正的整合,而是整合在一個人身上。因為我過去也參加過兩個整合型計畫,那的確在整合上面,面對很多人、很多問題。我今天想問的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想問問《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這本書的作者們,當初你們在考慮這本書的時候,在過去在辦研討會的時候,你們是怎麼想人類學與心理學的整合的,你們的期望達到了嗎?
劉斐玟: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代表大家回答。其實我們當初只是非常天真的認為說,民族所既然有人類學家也有心理學家,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因緣可以聚在一起,那我們如何能善用這個因緣,然後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既是對我們人類學、心理學的刺激,也能對台灣整體的學術帶來一些不同的觀點,這就是我們當初非常單純的想法。我們開始籌辦研討會時,面臨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以什麼議題,讓各種不同的學科來參與我們的討論?後來我們發現說,其實不管你是心理學家還是人類學家,或者是什麼專業,你一定牽涉到一個「方法」的問題,所以我們就從方法論開始,思考研究者跟被研究者之間、文化跟文化之間,凡是跟方法有關的議題,這是我們當初研討會的主題。研討會結束之後,我們又開了幾次會,根據每篇論文做很細膩的討論,然後我們才慢慢聚焦到所謂的「同理心」。當然,這個「同理心」,就像黃所長剛剛提到的,跟早期的社會心理學的「同理心」在概念上不太一樣。基本上,我們只是把個人當成是文化載體,來瞭解你怎麼樣進入另外一個「他者」。再加上生物科學1990年代有所謂「鏡像神經元」的發現,證明「同理心」有它生理學的基礎,我們等於是在這個基礎上,慢慢把這個焦點凝聚在同理心、情感跟互為主體。
剛剛瞿先生提到,張光直先生對於科際整合的說法,所有的學科是以一個人來做整合比較好,還是我們可以透過群體的討論來達成?當然,以跨學科對話來講,我想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夢想,胡曉真所長剛剛也提到,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夠多才多藝,能懂文學也好,哲學當然一定要具備,然後社會科學的理論也不可或缺,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廣度。當浸淫在各種不同學科的過程時,那是快樂的,可是當你要把那些知識帶到你自己的研究主題,怎麼樣放進來、怎麼樣整合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非常的困難,而且你還要考慮如何讓同一學科,或不同學科的人,像是投稿的期刊的reviewers或是讀者,可以理解你要講的東西。這條路是困難的,可是雖然困難,我們還是要嘗試去做,所以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一書出版後,我們才會想說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比較開放性的討論,讓更多人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刺激,看這個跨學科到底可以怎麼樣的進行。
今天真的滿值得驕傲的,在於說可以請到這四位主講者,完全不同的背景,然後在跨學科上面,可以給我們不同的啟發。再次感謝四位與談人。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劉斐玟 「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從《中國人的性格》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 觀照學術發展脈流、探索科際對話新視域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56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