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民族誌影展] 從軍之身,赴死之深
「戰爭與和平」主題紀錄片
之一・海洋的傷痕是無邊無際的深:《來自密克羅尼西亞的美軍》
島嶼士兵Sapuro Nena的棺材乘著飛機回家了。死亡地點是阿富汗,軍隊隸屬美方,死者的家卻座落於Kosrae,密克羅尼西亞。來自美國的導演Fitch不禁自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年輕密克羅尼西亞男子離開這個如天堂般寧靜的島嶼,去到阿富汗與伊拉克為美國打仗,而我,一個美國人,卻不必為美國打仗?離開天堂去從軍打仗是什麼感覺?回來又是什麼感覺?
以喪禮開場,死亡一開始就被預設為從軍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因為歷史、種族與全球地緣政治的不平等所騰出的空間,我們在一開始就被提醒,為軍事犧牲奉獻的意義,必須被懸置,加上一個深層的問號。
Maryann Nena,死去士兵的母親,她的姿態、神情與說話的方式,如此堅強、溫暖、充滿魅力。受害,卻從不軟弱,正如其他人也在試圖與命運搏鬥,好比又是漁人又是牧師的Madison。我們從影片穿梭自如地觀看來自密克羅尼西亞到到阿富汗,從夏威夷到德州到喬治亞州,從華盛頓再回到島嶼,卻不得不感受到生命的顢頇。一個在Kosrae島嶼上的家族,必須承受國際強權發動戰爭的消耗品:士兵。越是如歌般的蔚藍海洋,越是如海洋般寧靜的琴聲鳴唱,越是叫人心痛。一群溫暖和平的人們,偏偏就是必須為世界受傷,為世界死亡。但奇妙的是影片的沈穩,彷彿海納百川一般,沒有歇斯底里的控訴,只有無邊無際的無奈。
是士兵,但不是公民。美國退伍軍人所享有的所有福利——先不問是哪些種族哪些階級的男子必須自願從軍,也不問這些福利是否真的能補償所有的軍事遭遇——與密克羅尼西亞無關。
我永遠無法忘記Madison遠赴華盛頓那一幕如何精準地捕捉了美國軍事官僚機器的偽善。再沒有任何一部片可以如此溫暖、如此令人神傷,卻又如此犀利,如海水割破了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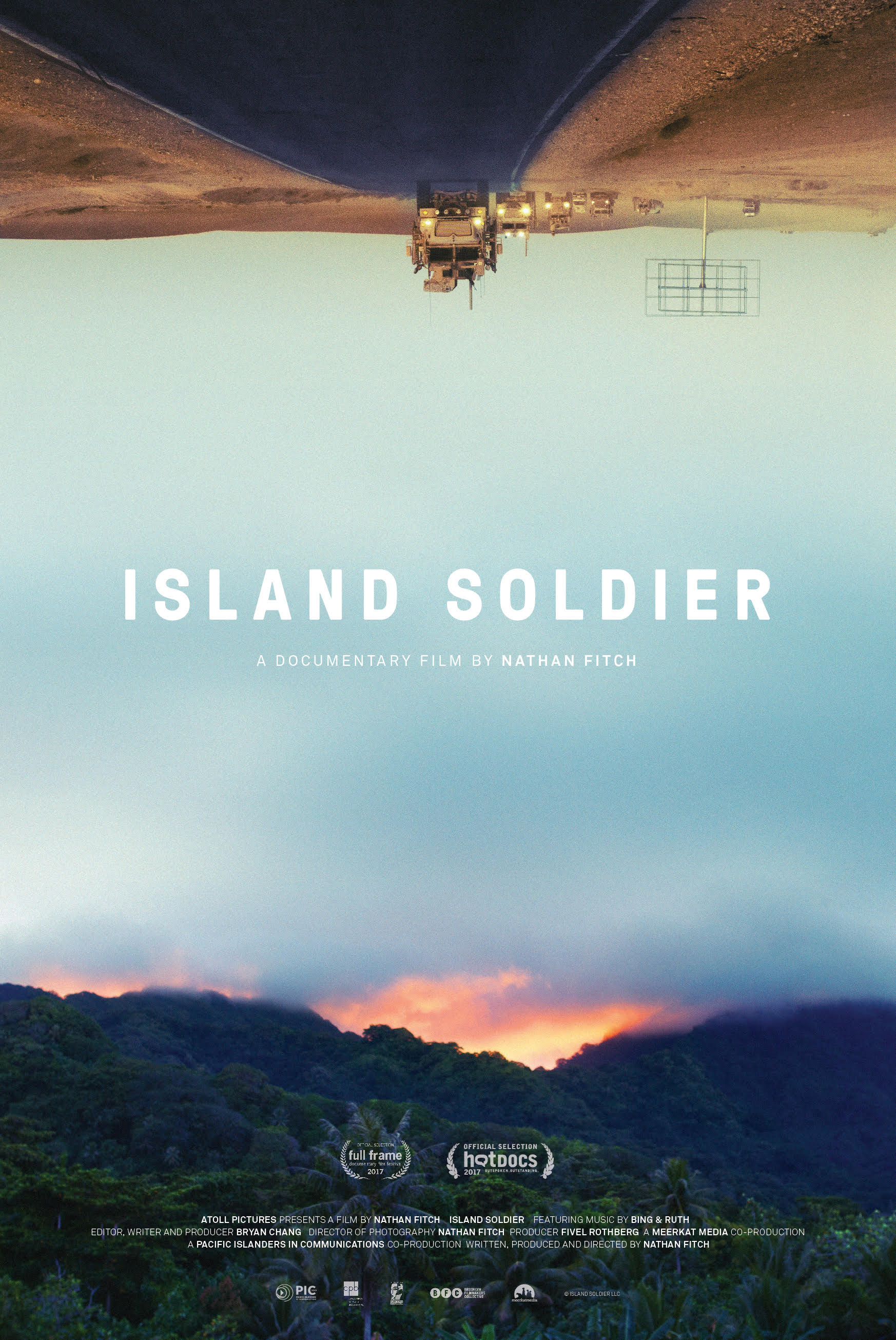
之二・殺人命運前後,那些被禁錮的溫暖時光:《天堂裡的惡魔》
想像你是一個五歲的孩子,你生於混亂,但對此一無所知。你搭上了斯里蘭卡從南部往北部的列車,但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種族暴動的難民。慢慢地,你發現你所崇拜的叔叔是家族中的英雄。但世界卻說,叔叔是恐怖份子。
這是近年來我看過最沈重的影片。在人類學者們熟悉的後殖民「整合革命」中,斯里蘭卡是個著名的案例。少數族裔而大部份為印度教徒的泰米爾人,在英國殖民期間受到禮遇而階級上升;多數族裔而大部份為佛教徒的僧伽羅/錫哈拉人,一掃殖民時期的晦氣,獨立後掌權。但即使是錫哈拉人,也認為自己是少數族裔,只要他們心中的假想敵是整個印度,那麼佛教徒的人口就微不足道。從殖民後期開始到獨立後,這種社經階級與族群大量重疊的不平衡並未被修正,獨立的新政權走向單一民族式的國族主義,更進一步埋下日後70年代泰米爾獨立運動的種籽。
但80年代泰米爾獨立運動軍事化的浪潮,卻是完全新的抗爭品種。泰米爾老虎解放軍,被國際強權視為恐怖組織,但他們卻是80年代全國各地針對泰米爾人的種族暴動的產物。面對著無所不在的壓迫與殘酷,他們決定,任何政治妥協都將是一種背叛。為了讓老虎們之間可以集中一致對外,泰米爾人軍事派系之間的殺戮也同樣令人顫慄。打輸了就等於讓這一切變成「內戰」;打贏了,這一切就是一場獨立戰爭。因此二十五年後,發生的一切被稱為「內戰」。 從此以後,北部與東部地區的少數族裔就開始長期活在斯里蘭卡政府的軍事監控之下。
導演Jude Ratnam沒有花費任何影像來做以上的歷史政治學鋪陳。這些理性的論述,完全無法更細緻地將我們拉入個人生命的體驗。因而,片頭是一兩句畫外音「殖民的幽靈」輕描淡寫,然後是泰米爾人在城市換裝,試圖抹去身上印度教的痕跡,希望可以pass by被當作一般的錫哈拉人,不要被認出而被歧視。政治與族群認同的背景主題,就這麼四兩撥千斤地,成為影片進入許多個人生命歷程的序曲。
一位錫哈拉記者拍下了暴動當年,一位孤苦無援的泰米爾男子,全身被扒光,赤裸地在一個巴士站旁,被一群人模人樣的錫哈拉青年恥笑後活活打死。這是影片中一段昏暗的插曲,自此不論是記者或死者都沒有下文。執著於有頭有尾的影評人會對此感到疑惑,甚至視為影片的缺失。但這一場景難道不是為了凸顯出,並不是所有錫哈拉人都是壞人;他們當中一定有人知道如此任意的殺戮,只因為對方與自己不同,是錯的。那麼泰米爾老虎之中,是否也有人能明白他們已經犯下許多滔天大罪?人是否可以為了正義、為了更高的理想而殺人?如果可以,殺人的限度該如何定奪?這似乎正是導演的思路。人性的溫暖,如同那位錫哈拉記者對於不認識的泰米爾人的同情;人性的殘酷,不僅僅是錫哈拉人對泰米爾人的趕盡殺絕,也是泰米爾老虎對內部異議份子的趕盡殺絕。
正是這樣的溫暖與殘酷的思路,貫穿了導演叔叔回鄉後的記憶之旅。當年在泰米爾老虎裏頭奮戰,後來移民到加拿大,如今已經略露白髮。叔叔在Ratnam的盛情邀請之下,為了拍攝這段探索回憶的影片,回到了斯里蘭卡。他走入小時候長大的村落,那個多數人都是佛教徒錫哈拉人的村落。少小離家老大回,人們必須在提醒之下才相認。他們破涕而笑,給予真摯的擁抱,乃至「佛祖保佑你」等祝福。一路深入到當初居住的小角落,他與過去曾經保護過他們一家人的雜貨店老闆娘重逢。這位年邁的錫哈拉女性對著鏡頭自信地描述,當年這泰米爾一家人被「追殺」時,她義無反顧地選擇安置他們在她的家中。她邊說著外面的人要傷害這個如今是中年大叔的小男孩一家,但她絕對不會讓暴徒動這家人一根寒毛。邊說著,她流下了積抑多年的淚水。
這或許是這部片最感性的時刻。人性的溫暖,無庸置疑在重逢後的歡笑與淚水之中,在一起熬過的恐懼與勇氣之中,尤其是在跨越生死只為保護弱者的情義之中。
然而,接下來的老游擊隊們的重逢之旅,除了兄弟之情之外,更多了冷血回憶。許多時刻,突然湧出的大叔們的淚水,幾乎讓人無話可說。「我們怎麼會那麼無情?」、「就這樣殺了那麼多人?」、「那是……一個曾經救了我們的大學女生(她後來就被殺了)」一切,都讓人思索這些突然湧現的澎湃,是否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都被完全按耐住,或僅僅是掃到記憶的黑暗角落中鎖住。退伍的老虎們談起過往,拜訪過去殺人與被殺的地點。最後,他們在野外席地而坐,日落後分圍繞著一個小火推,彼此詰問:當年的暴行是否真屬必要?他們當年是否有別的選擇?究竟他們當年為什麼可以突然變得如此殺人不眨眼?
無人能提供輕鬆的答案而使人折服。
Eelam是家園,在泰米爾解放軍的愛國歌曲中,也是天堂。天堂裡的惡魔,原本是錫哈拉人,斯里蘭卡政府,但後來惡魔變成了自己人,變成自相殘殺的老虎們。
導演在片末加上了他直言不諱的評論,一個反高潮的結論。他的結論引來許多泰米爾人的不滿,甚至使得他的影片在某些相關的影展被抵制。不論評價為何,在泰米爾獨立運動之成敗與檢討之外,也許讓人更加擔憂的是,現在面對困難險境的不再是退伍的老虎們,而是國內的少數穆斯林族裔。斯里蘭卡極右派佛教至上意識形態近年來不減反增,官方與民間論述將國內的穆斯林少數族裔妖魔化,已是行之有年。2014年極右派佛教組織Bodu Bala Sena甚至在政府默許下暴動,讓可倫坡將近一萬名穆斯林流離失所。
究竟誰是天堂裡的惡魔?是否天堂本來就不應該存在,才不會有惡魔為了天堂而廝殺?或一旦有了天堂,就必然會有天堂的背反,也必然就會出現那些該被剷除掉的惡魔?
死亡顯然不足以給予我們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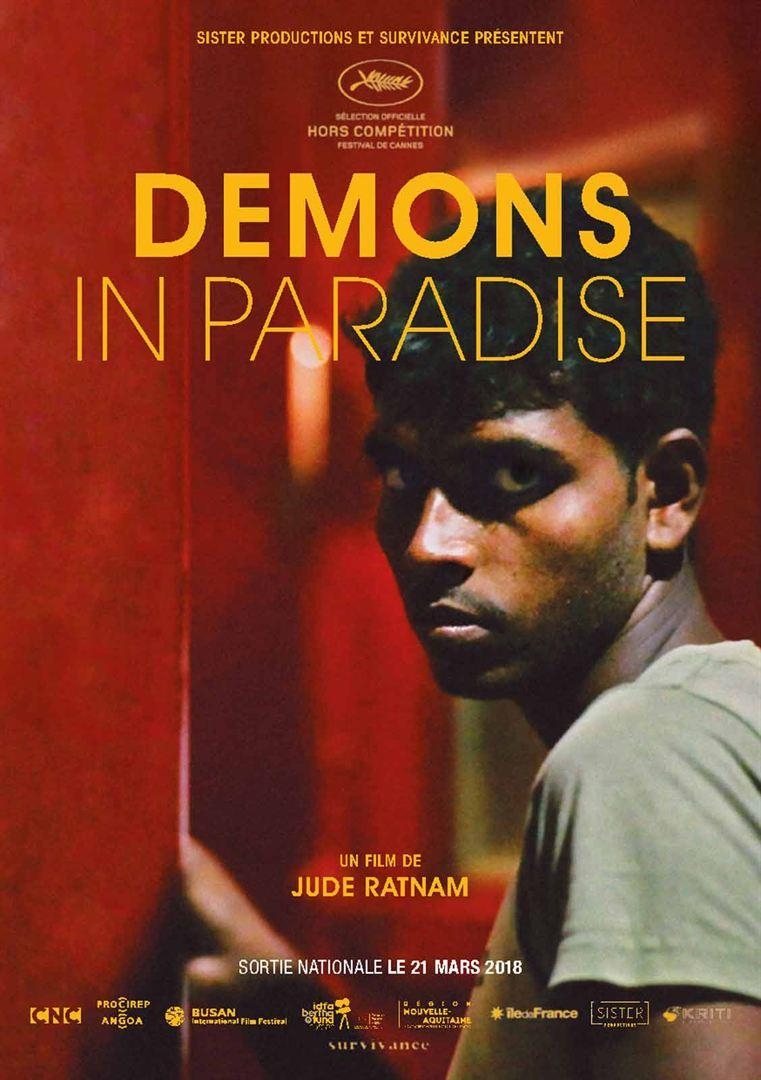
之三・服從的展演即服從:《世紀新生》
中國自1989年以來強制規定所有學校必須有軍訓營隊。2018年,39所一流大學的軍訓天數,從12天到26天不等,其中有六所高校超過了20天,分別是吉林大學、東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山東大學。清華大學的軍訓更是出了名地令人聞風喪膽,除了必備的隊列及軍體拳,還有定向越野、實彈射擊等項目。
但到底為什麼要軍訓?習得任何組織技巧?記住任何軍事隊形?
湖南大學,導演陳實相當誠實的記錄著軍訓的一切,包含台上台下,前台後台,訓斥的演出與服從的演出。最後,就連參與者都認為這一切相當乏味,索然無趣,甚至是沒有必要、平白無故的消耗。認識同梯的學生?站在一起不能說話,如何能認識人?結交朋友?連說內心話都沒有時間、更沒有機會交心,是如何能結交朋友?但即便如此,已經從軍訓畢業的學長學姊們,仍是趾高氣昂地讚嘆軍訓的奧義與絕對的必要性。
究竟軍訓的意義為何?是否軍訓只是為了將身體銘刻,讓服從的記憶成為肉身?假裝自己是軍人,假裝自己可以服從,可以被罵得狗血淋頭,可以被規範而改善,可以有紀律而存活。
然後一切就都是真的了。高等教育能生產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必須懂得服從軍令,從一開始就必須是。這顯然是中國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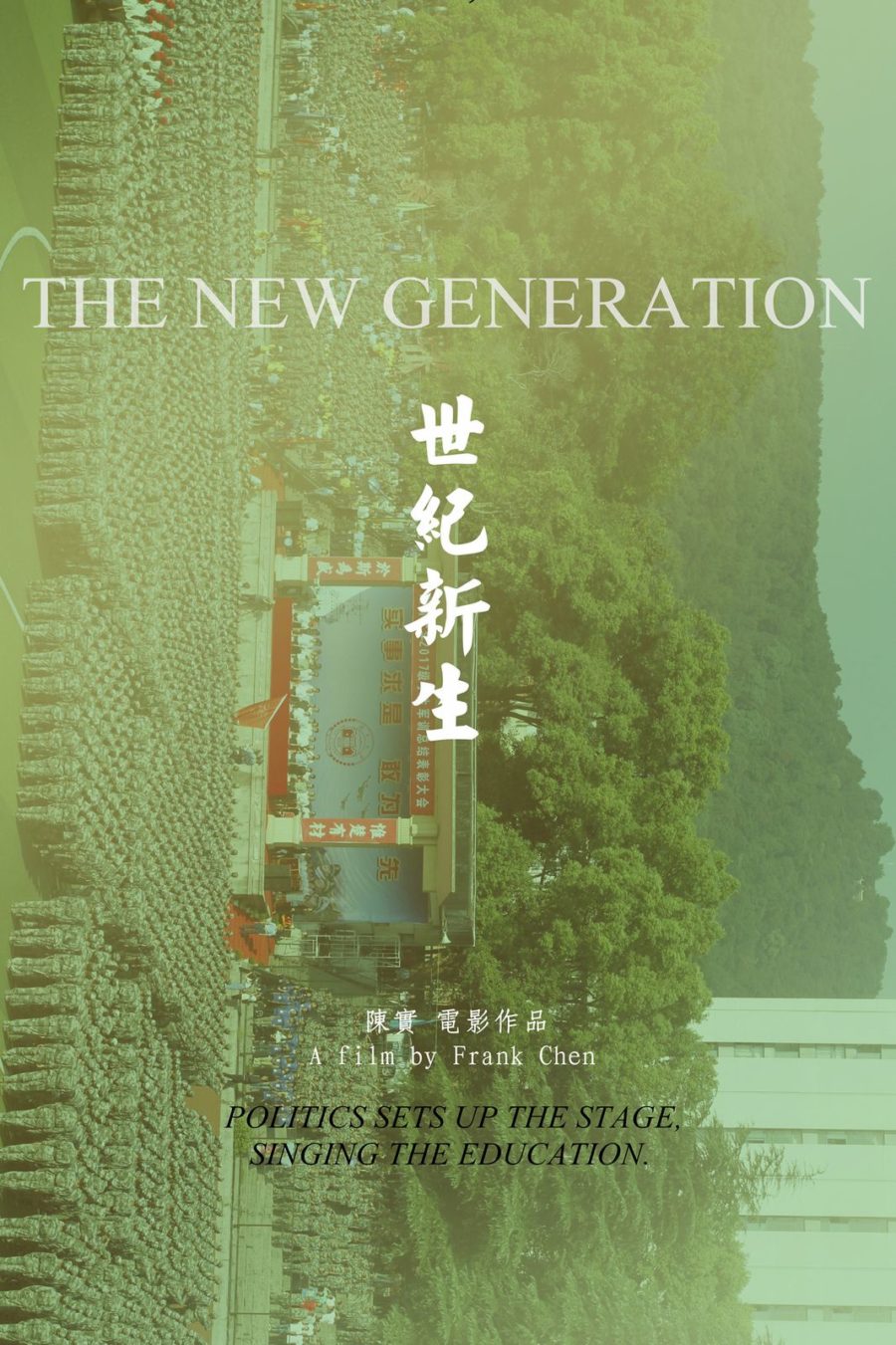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恩潔 [2019民族誌影展] 從軍之身,赴死之深:「戰爭與和平」主題紀錄片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54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