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或是巫師
從曼恩看台灣環保先驅林俊義老師
我很喜歡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行文之間充滿了一種跨域導讀的知識深度與樂趣,不管是從科學啟導人文,或是從人文反思科學的題材,他總是能處理得相當到位。其次是,他撰寫的主題剛好是我長期研究的課題,也就是貫穿於自然、社會、文化與歷史的生態文明發展的思維。他是一位撰寫科普文類的資深作者,也是重量級的《科學》(Science)學術期刊特約記者。不久前,衛城出版的編輯希望我為他2018年出版的書《巫師與先知》寫推薦文。能夠介紹心儀作者的中文版譯書,我當然是義不容辭,另外也因為之前曾寫過他《一四九三》與《一四九一》兩書中文導讀的緣分所致。有趣的是,寫這篇推薦文卻讓我想起一些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生態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的對話,多少也呼應了曼恩的寫作基調。簡言之,就是科學與人文之間的互補與跨域。以下是一些學思歷程的往事。

1995年,我記得在博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時,口試委員首先要我講一下我的文獻閱讀心得。我當時很誠實地講出,“I get lost!” (我迷路了)這句話。此話一出,所有口試委員眼睛都睜大大的,於是我開始解釋是什麼原因。我說,我本來以為英國是「上國」,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地理系應該是學界首選之一,也應是我這個自認為環保人士吸取經驗與學習的上好地方,但是唸了博士班以後,我在文獻堆中卻發現原來真理沒有想像中那麼清晰而簡潔,為什麼各路學者為了「何為環保?」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如此爭論不休呢?更嚴重的是,似乎沒有明確的結論。我解釋完之後,發現口試委員開始露出些許的微笑,甚至還有一點讚許的感覺。似乎是在告訴我,好像走對路了。這聽起來是否很矛盾,明明是迷路了,卻被認為是走上一條可行的道路。但巧的是,曼恩的中文版新書《巫師與先知》似乎正是在處理類似的環保價值觀分歧的迷惘。
在這本書中,曼恩以威廉‧佛格特(William Vogt)和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這兩位美國科學家兼社會倡議者為主角,再度運用引人入勝的文筆展開他細膩的人文考察與生態反思。在自然中,人類這個物種究竟何去何從?以及這個物種所牽動的普世影響,例如當今熱議的「人類世」主題,究竟人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一直是他寫作的主軸。不同的是,在《一四九三》與《一四九一》中,他所關切的是由歐洲崛起的現代文明與衝擊,也就是「人類世」的可能起源,然而在本書中,他則是處理在二十世紀開端,初瞥「人類世」後果的兩種環境價值觀的衝突與對話。針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他分別用佛格特與布勞格這兩位人物來作為代表。
其實,若深讀下去便會知道,作者並非要將先知與巫師對立。誰對誰錯不是他真正關心的事,因為他真正關心的是,人類究竟何去何從?在本書中,他用土、水、火、風來表達人類在自然中隨時遭遇在糧食、水源、能源以及氣候上的挑戰,並且讓先知與巫師的觀點在此間交織、衝突與對話。曼恩的真正用意應該更深層,用他不斷在書中引用著名的演化生物學者琳恩‧⾺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觀點來說,究竟人是否異(或是優)於其它生物,可以逃脫悠悠的演化長河選擇淘汰的機制呢?畢竟,不管是巫師或是先知都還是意圖改變人類命運的其中一員而已。這個發問,跳開以人為中心的思維,觸及了深層的宗教與哲學探問,亦即人在自然中的存在與位置。
事實上,在閱讀《巫師與先知》這本帶有強烈傳記性的生態反思作品時,不知什麼原因,我的腦海中不時出現我的恩師林俊義教授所寫的自傳《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在自傳中林老師活脫地展現出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生態先知與巫師對壘的諸多情節,更有趣的是他用的教科書就是曼恩講到的一些人物,如奧登的《生態學基礎》(Fundamentals of Ecology)以及邁爾的《邁向一個新的生物學哲學》(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即是。曼恩不僅是個優秀的記者,他更像是一個經驗老道的民族誌寫手,在他的筆下不僅有文獻回顧的詮釋功力,更驚人的是他的文字中有太多他自己設身處地,跟人類學者一樣去到異地探詢與求知的親身經驗。以下,我也來效法曼恩,試著寫寫一些在台灣的脈絡下生態與人文思維如何互動的個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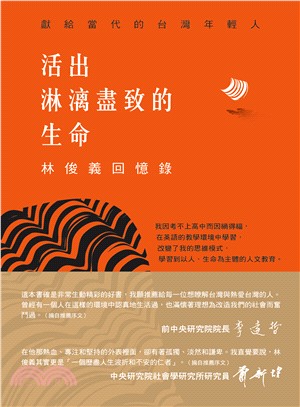
一、科學的啟蒙:對,我就是要給你們挫折!
常常,啟蒙時刻的當下並不真正有那種了悟的感覺,往往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才自己確定地說,對,就是那個時刻,那就是改變的開端。我被林俊義老師啟蒙,種下了在科學訓練中很重要的批判精神,是像這樣的感覺。
回到大一入學的那個秋天,我們整班的同學被林老師「生物新知」的作業搞得心浮氣躁,充滿怨氣,只能在東海的舊圖書館書架的走道間攤開一本一本的Biological Abstracts,在細小的字體間找著各自被交代的拉丁名生物的相關文獻。我印象當中,那是一種像是在大海撈針的感覺,一方面是不熟悉查找文獻資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則是語言的問題,我們對於學術英語閱讀的能力確實尚未被開發。於是,三五同學癱坐在走道間除了咒罵,還是咒罵,心想有那個老師會出一種自己都不知道標準答案的題目呢?
曠日費時的尋找,當時學習效果極差,對於這門課大家就有點意興闌珊。那應該是初秋的課堂,天氣還熱,上課時大家就姍姍來遲,林老師看到課的情況不佳,心情應該是不好,於是就開始點名同學起來問問題,嚴肅的氣氛於是開始凝結,本來很散漫的課堂大家開始緊張起來。剛稍稍被解放了的大一自由心情,一下子又回到高中以前規矩的上課狀態,我看到同學們開始正襟危坐,自己也開始緊張,心想最好不要點到我。因為我在作業的成果上真的一事無成,一方面是確實找不到,另一方面則是時間都被佔滿在大一的活動了,像是不小心被找去打橄欖球校隊。
好死不死地,突然林老師就指著我,說,你來說說對這個作業有什麼感想?我記得當時就是恭恭敬敬地站起來,滿心羞愧地不知如何講話是好,只能誠實說出:「我感覺很挫折!」這句話。這真的是無話之話啊。結果,想不到林老師的回應,竟然是非常迅速地,激昂地說:「對,我就是要給你們挫折!」。這個突如其來的回應,瞬間又讓我腦袋一片空白,站在原處不知如何是好。無法理解,這是一種讚許,還是諷刺呢?或者是老師的一種自以為是呢?
多年後,我自己也當了老師,我才慢慢明瞭那就是一種機會教育,在某種情境中,讓學生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存在處境,這無涉於所要傳遞的客觀知識內容,而是直接進入到學生自我的生命情境,從內在去反思自己對於當下生活與行動的意義。換句話說,那個作業本身究竟是否有達到老師所要求的三十篇學術摘要的成果,已經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究竟我們是怎樣去面對這個過程,去咀嚼與品味其中的滋味,這個過程不一定是順遂的,甜美的,反之,它常常是苦澀與艱難的。坦白講,老師給了一個超難的題目,幾乎很少人可以達到。但,其實他真的只是要知道我們每個人如何咀嚼出其中的滋味,每個人都是不同的。至少,他當頭棒喝的那句話,我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偶而,我會講給學生聽。我不相信有什麼快樂學習的方法,求知的過程沒有苦澀與挫折,實在很難進入到學問的真諦啊。
老師教我們的,不是標準答案,或認真地講也不是一定會有一個答案。這樣的啟蒙,成為我日後做學問的基本態度。我記得林老師在課堂上都會提醒我們,最新的,最進步,最有挑戰性的知識不會在教科書裡面。就科學發展而言,縱然教科書傳遞的是被肯認與具有某種權威性的知識內容,但科學進步的精神無非就是要去打破這些權威與超越這些認識。在追求科學進步的基本意義上,教科書的知識是等著被推翻或是超越的知識。那麼,我們要得到的知識又是什麼呢?就是在不斷挫折的過程中,批判性地認識到的暫時成果。挫折,不是要讓我們氣餒與放棄,反而是從中進行一種自我內在的反省,只有這種不斷內化的力量才真正地讓知識的意義呈現出來。多年後,我重新咀嚼當時林老師的話,覺得還是很有味道,值得慢慢地回味。這真的是一種啟蒙啊。
二、跨域的學習:數字背後的生物意義在哪?
1987年,神秘地消失了好幾年的林俊義老師回到東海生物系任教,正當我從研一要升到研二的夏天,我在阿里山的老鼠生態研究一直沒有太大的進展,當時的指導教授歐保羅(Paul S. Alexsander)老師因為是宣教師,必須回美國述職,而真正幫助我研究的是學長林良恭老師,他正在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所以我的研究指導,是處於空窗的狀態,雖然每個月都跟著學姊陳彥君以及同學李奇英在嘉義鄉下的六腳鄉以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抓老鼠研究他們的生態,但我的研究題目與方法卻始終是懸空的狀態。研究老鼠的食性,是我本來想做的題目,但由於胃內含物與糞便內容的鑑定一直是很困難的分類門檻,在系上也沒有老師的專長師可以支持我做這樣的題目,於是後來我只能轉做老鼠的「微棲地」(microhabitat)研究。但,始終是在沒有指導教授的情況下,靠著閱讀國外文獻以及學長姐的砥礪來摸索前進。
在我的閱讀中,分析鼠類的微棲地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透過高等的統計方法來分析老鼠棲地的眾多變數之間的關係,其次是先主觀地認定老鼠居住的類別,例如樹洞,地洞,樹上或是草叢等棲地類別,然後再進行老鼠出現的喜好度分析,後者的統計不如前者複雜。我研二的時候,台灣開始流行個人電腦,也開始有一些SPSS或是SAS等電腦軟體的工具出現,但當時在生物系卻是沒有這樣的師資,我因為教會團契的關係,認識了當時在社會系攻讀博士且在社會系負責電腦統計教學的陳宇嘉老師,他是我們的團契輔導,於是透過他我開始學習用PE2寫電腦程式,跑高等統計分析在山上蒐集到的老鼠棲地資料,當時能用電腦跑統計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樣子,班上幾位同學必須用ANOVA分析的統計,也在社會系的程式設計支援下得到協助。
我一時迷醉在電腦統計的神效,得到許多的數據分析結果,雖然苦於無法解釋,但卻因為新穎的電腦軟體而洋洋得意。於是,就在一次研究所seminar(學術論文報告)的場合中,出了大事。那一次輪到我報告,我只記得自己show了一大堆的數學公式與統計結果,但卻心虛地胡亂解釋結果,感覺上是很厲害的數據呈現,但卻心知空無一物。我記得林俊義老師是第一個發言質問的,他說:「林益仁啊,不是有很厲害的電腦統計軟體,或是show了一大堆的數學公式與統計結果就是好的研究,重點是這些數字背後的生物意義在哪呢?你要說出來啊。」這個質問剛好就不偏不倚地正中核心,問得我啞口無言,滿臉通紅。Seminar,是當時我們唸書時最可怕的一門課,在那門課中老師與同學是毫不留情地問問題,絲毫不給面子的,因為我們相信學術的進步在於無情的批判。
所以打蛇隨棍上,接下來就繼續有老師開砲。其中一位老師問我,這些統計方法是到哪裡去學的,為什麼不先來問問所上的老師呢?社會系的老師懂得生物學嗎?當時老師們給我們的訓練是,不管問的問題合理不合理,學生都必須設法回答。對於這些問題,我心中直覺就是「因為生物系沒有這些教高等統計的師資,我才會跑去社會系啊」。這位老師的問題,分明是要我講出「忤逆」且讓人不堪的話語,這真的是太難了。我遲疑了一下,後來我說:「其實我沒有老師,我的老師是書本」。我誠實地道出當時我沒有指導教授的窘境,也試圖辯解即便去社會系找幫助,主要也必須靠大量的閱讀自修而來。結果,這話不說還好,一說真的是「忤逆」了一堆老教授,直言這個學生實在太狂妄了。當時,我站在台上滿臉更是通紅,不知道自己竟然闖了更大的禍。
這時,林俊義老師站了起來,表示要發言。他於是緩緩地說:「其實林益仁這樣講也沒錯,東海生物系不是常常說要訓練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學生嗎?如果有學生可以不單單依靠老師來做學問,主動地求知,我們是應該要鼓勵才對啊。」我記得他講完話坐下來,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人繼續講話,所長很快地就宣佈報告結束。我自己站在講台的地方許久,腦袋還是一片空白,很難想像自己做了什麼事。
再過幾週後,我去找了林俊義老師懇談,正式被他接受成為與歐保羅老師共同指導的學生。他當時已經忙於解嚴後的政治事務,到處演講與發表公開言論,我的論文確定回到少用統計,多注意生物意義的分析路數,一直到口試前他只看了兩次論文草稿,第一次說結論還沒寫趕快寫,第二次則說趕快送給口試委員,有任何的修改口試完再說。我的口試完畢,他說先跟女朋友去慶祝吧,下週去找他。我隔週去找他,他說論文其實真的不夠完整,要我用英文試著改寫發表。我知道我的碩士論文確實不是很好的研究產出,但我確信自己在那段時間的學習投入真的很值得,也滿心感謝不同老師用不同的方式所給予的啟發與鼓勵。當然,學得好或是不好,真的不是他們的責任,而在於我自己。
三、獨立的思考:不是所有書的作者都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林俊義老師對我們學術能力的養成是嚴謹的。其中,他帶我們做摘要,是我終生受惠的訓練。不管是看一本書,或是一篇文章,他要我們能夠去摘要出行文的邏輯與架構,並且找出文章真正要講述的重點。最後,如果行有餘力(基本上當時以我們的功力是做不到)還要提出批判性的評論。他指定我們輪流閱讀並摘要他所指定的讀本,在每一次報告的時候他自己也會準備一份相對應的摘要,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摘要與老師的摘要差別之所在,這樣的訓練剛開始痛苦萬分,但久而久之卻也逐漸對於掌握論述的重點有一些能力。
有一次,他在帶領我們摘要的討論之後,突然有感而發,這種浪漫且天馬行空的人文表現其實是常有的現象,學生其實最期待這個時刻,因為這表示會暫時脫離枯燥嚴謹的學術論證,而進入自由的隨想發問。他說:「你們要知道,其實不是所有書的作者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寫什麼」。這話聽起來很聳動,也很挑釁,打破我們對於作者的權威感,這就是林老師的風格。多年後,我自己也成為一些論文的作者,慢慢能夠體會這句話背後的深意,作者不知自己在寫什麼,不單是專業或是寫作能力所限,有時是受限於時代背景與意識型態的左右,無法跳脫。
其實,林老師對我而言一直是一個謎樣的啟蒙人物。我大一修過一門他的課之後,他就消失一直到我研二成為我的指導教授。真正受教於他的時間,真的不長,大概只有一年多而已。多數的時間,我是透過他所撰寫的文字來認識這位老師,我記得我大學時期在床頭常常放著一本他寫的「科技文明的反省」,沒事就似懂非懂地拿來翻閱。更早以前,我也去買了「文明的躍升」這本書,想不到他連這本書也拿來批評一番,並且與當代學人包括科博館的館長漢寶德先生展開「科學是什麼?」的對話,他對於科學中立的觀點一直抱持著極大的疑問。
林老師對我的啟蒙,大概就是一種批判與獨立求知精神的培育。這個精神在1980年代台灣風起雲湧的政治轉型,正好躬逢其盛。1987年我是研二的研究生,當年人間雜誌與新新聞雜誌創刊,成為我認識台灣社會與政治的知識養分,跟其他的學長姐與學弟妹不同的是,我的學長姐有更多與林老師跑田野做生態研究朝夕相處的時光,我的學弟妹則是加入林老師的競選團隊擔任義工,毫不掩飾地就進入選舉的場域,我則是夾在當中,與前者相比我還沒入學,而跟後者相較我卻已經入伍當兵。所以,很多的啟蒙自然都來自在林老師的課堂交談與文字的閱讀之上。但,這樣就很足夠。
林老師大半生對於科技抱持著謹慎小心的態度,特別是對於像是核能等資本,知識與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科技,特別抱持著嚴厲且批判的態度。但是科技確實有著許多不同的面向,他也引導我們去看像是《美麗小世界》(Small Is Beautiful)這樣深具啟發性的書籍,從中讓我知道何為「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或是intermediate technology) ,科技不只來自人性,科技還必須引導出更好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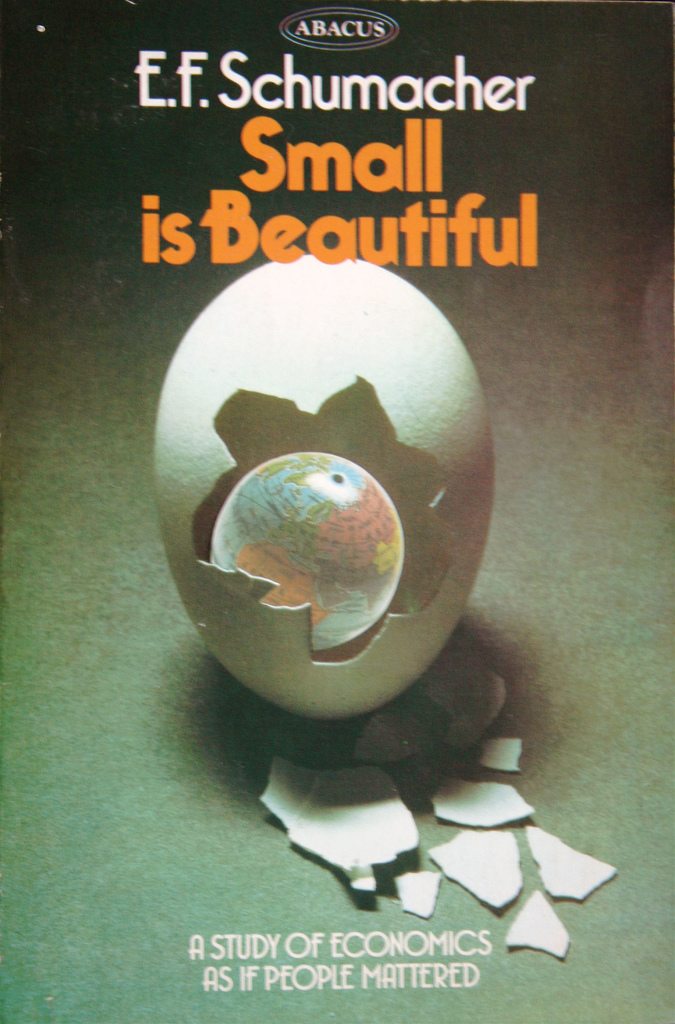
我在學術上的人文社會轉向,肯定是受到林老師的影響。在他的課堂上,他批判科學中立的神話,帶我們閱讀Ernst Mayr的生物哲學,從島嶼生態學的理論看台灣的保育處境,以及教授台灣最早的環境影響評估方法(環保署還沒成立),還要我們直接應用到對於台中港中火第四號機組的增設進行評估,我們還在東海的茂榜廳開公聽會報告調查成果。林老師在我的生物與生態學的訓練上,增添許多人味,以及對於台灣社會的關注與關懷,這是後來我毅然離開演化遺傳學的實驗室抽DNA的工作,轉念文化地理學的主因。
四、知識與政治:高爾街(Gower Street)上的片段記憶
我在1994年再次回到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讀地理學博士,能夠進入英國名列前茅的地理系就讀,是我從來也想不到的事。我在1990年得到UCL生物系的博士班入學許可,因爲獎學金的緣故,轉進去念英國最老牌的自然保育碩士學程,這個學程的設立跟二次大戰後著名的Julian Huxley爵士的鼓催有關。我的博班指導教授,生物系的遺傳學講座教授R. J. Berry推薦我先去念這個碩士班,此外答應我安排去倫敦動物園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去學抽DNA的技術。在課程裡,我遇見了同校的地理學者Carolyn M. Harrison,她在帶領我們到工業革命的起源地旅行中引導我進入人文地理的學習,後來我得到她的支持在英國轉念地理學了。
1994年我剛到倫敦不久,在高爾街附近的學校電腦中心收取電子郵件。高爾街上的Darwin Building是生物系的系館,也是達爾文在倫敦的故居。我收到一封信,是林俊義老師寄來的。在此之前,我們已經許久沒有聯絡,這封信來得意外。信中的內容大致如下:…I am assuming the director of EPA…然後,林老師希望我可以考慮回去擔任他的秘書,一起打拼。初看到信,我連EPA都還搞不清楚,後來才知道他即將要出任剛選上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先生的環保局局長。這件突然的事讓我猶豫了一段時間,我必須承認老師對我的啟蒙不僅是在學術思想上,更是在對於社會與政治的關懷上,如今似乎是一個政治實踐的機會來臨了,是否要接受這樣的呼召呢?
我一下子陷入兩難。在另一方面,我再度來到倫敦,選擇放棄紐約大學演化遺傳學博士班的全額獎學金,再度跑到UCL自費且轉行念地理學博士,是人生的重要抉擇,是否就該因此中斷呢?幾經思考之後,我很婉轉地寫信解釋且回絕了老師的邀請,心中當然覺得有不少歉意與遺憾。至此,我就專注地走向學術轉型的道路,但其實林老師的演化學與生態學哲思都還是在我的地理思想研習當中不斷地影響著我,特別是他曾經在課堂上介紹美國科學史家Lynn White Jr. 的"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性根源)一文批判基督教思想的文章,更是我博士論文的重要文獻。我越是在國外的學術深入,越感受到林老師帶給我們的「新知」完全沒有落後的現象,反而我可以講出一些關於台灣脈絡的獨特發展。
事隔多年之後,1999年我回到台灣,在世新大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任教,在這裡的同事或是夥伴有更多認識林老師的人,才發現林老師有許多左派的朋友。隔年,總統大選中央政權第一次轉移,林老師又獲邀擔任環保署署長,當時我以生態關懷者協會理事長的身份接待美國環境哲學家J. B. Callicott在台灣進行學術演講,他們兩位也是舊識,於是很自然成為環保署的座上賓,並且在署內發表專題演講,當時我是擔任Callicott教授的翻譯。署長親自擔任主持人,我發現學生時代台上意氣風發且神采飛揚的教授學者似乎再度重現,他講的話好像沒有比Callicott來得少。
談話內容觸及許多的勉勵,希望環保署的官員們不要只著重於技術面的考究,必須多一點環境價值的審思與人文精神的注入,我在現場心想他把官府當成課堂似乎太過天真,但也一方面欽佩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林老師。演講完畢,我們一起搭電梯回到他的辦公室,他意味深長地跟我講一句話,說:「林益仁,你不一樣了喔,做得很好。」我愣了一下,心中感到一陣溫暖,一向嚴厲自持的指導教授這樣講話,自然是勉勵的成分居高,我趕快把話題帶開,一方面也感謝他一路上的指導。心想,其實就是老師一向鼓勵學生獨立求知的精神,才造就我在學術上不斷冒險與跨域的性格,雖然成就很微薄,但重點不是在成果,而是那個點滴在心頭且刻骨銘心的過程。但回頭一想,如果當時答應老師回來擔任秘書,又會是怎樣的人生風景呢?
五、社會的關懷:反核就是反獨裁
2003年,我應徵靜宜生態系的教職,系上資深的前輩問了我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這問題是「請評論林俊義教授因為2000年政黨輪替,在立法院備詢時說政治民主化後,現在可以不用反核的說法」。眾人皆知,「反核是為了反獨裁」是林俊義老師的名言,考官有點要試試我這個林老師的學生究竟怎樣面對老師的話與事理對錯之間的抉擇。其實,當時這個新聞報導出來,環境運動界確實一片譁然,而我並未親自問過他這回事。
我記得我的回答是,林老師的說法是經過媒體的傳播,我無法確知他的完整想法,也可能無法討論這個說法。但果真因為政黨輪替,就可以不用反核,我個人是反對的,我認為核電科技與產業的獨裁體質與結構不會因為政黨輪替就輕易地改變的。其實,在靜宜生態系受到林老師影響的同事也不少,問這樣的問題純粹是對事不對人,此外也是承繼了他一貫批判的學問態度,我們在他的課堂上就很喜歡以「詰難」的方式來跟老師「答嘴鼓」,他也歡迎我們挑戰他。
多年後,我有機會在他關渡的寓所拜訪時,再度問起這樣的事。他才娓娓道來,當時在質詢時確實意猶未盡,但卻也因此就這樣被斷章取義了。他指出,政黨輪替當然有機會將台灣的政治帶往更民主而不獨裁的方向,但在核電的背後那些台電的科技官僚專家體系以及核電本身這種科技背後的獨裁確實是他一直反對的,但是在當時的質詢卻無法詳細說明,我懷疑記者也不會想聽這些複雜的討論。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核四風波,簡化為正反兩邊對立的氛圍,本身就是一個認識與抉擇上的災難。在激烈的攻防過程,並沒有促成整個社會對於核電之於台灣社會有更多的了解。
2004年,我開始在靜宜大學生態所傳授「生態政治學」(Political Ecology)這門課,生態政治直探不同社會群體對於環境的認知具有不同的價值觀點,這些價值觀點的衝突背後有著複雜的權力關係運作,而這些運作的結果所導致的社會正義與資源永續的問題是值得關切的議題。我一直以為林老師的「反核是為了反獨裁」論述是台灣生態政治學的重要論述,在生態政治中如何作為一個「公民」與「台灣人」的課題構成他反獨裁與追求民主的基調,相當值得認真地考究。除此以外,他的文集中「政治的邪靈」「台灣公害何時了」「自然的紅燈」「科學中立的神話」都是一篇篇台灣早期環境意識發展的歷史證言。中研院蕭新煌教授曾經將台灣的環境運動分成「軟路線」與「硬路線」兩種,林老師顯然是後者,針對環境破壞背後的政治權力結構毫不畏懼地批判,並且親身參與在政治實踐當中的作法,都樹立了學界的特殊典範。
六、信仰的抉擇:Shalom (下樂姆),願你平安
幾年前,我到關渡林俊義老師的寓所拜訪,當我們天南地北聊開之時,他因為知道我的信仰背景,就給了我一本小冊子,叫做「下樂姆」。問我,知道有這一本雜誌嗎?雖然已經退休,但是在他那裡隨時都可以發現一些你所未知之事,他的知識探求層面真的不是普通地廣。
「下樂姆」,是希伯來文shalom的音譯,是猶太人常用的祝福話語,平安的意思,這一本雜誌是由鄭廷憲教授苦心經營的一本基督教思想的小冊子。「下樂姆」受到日本的無教會主義影響,強調不需要受到教會組織與制度的約束,獨立研究聖經的奧義並廣傳福音,「下樂姆」集結了這類思想的台灣基督徒,在日本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內村鑑三,他的學生之一,也是無教會主義者,就是極力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人道主義者,曾擔任過東京大學校長的矢內原忠雄。「下樂姆」透過原典的聖經考察,積極的文字工作,傳遞聖經在當代社會的啟發與意義,林老師很欣賞且希望我多加留意。我很慚愧沒聽過這本小冊子,但是關於日本無教會主義的思想卻是多所聽聞。
其實,我之所以一直親近林老師,一方面是東海生物系學生的緣故,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長老教會長青團契1980年代的氛圍。在1980年代的台灣做為大學生,我的民主政治啟蒙是在教會的大專團契裡,並非在當時封閉的校園內。林老師常常是團契與教會邀請的講師,所以往往我也很好奇他的基督信仰態度。雖然很多人還是認為林老師是一位基督徒教授,但我知道他對於基督教並非照單全收的,換句話說,他始終採取一種帶有濃厚啟蒙與人文思想的理性批判態度在檢視著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明顯的例子是如何融合演化論與基督教思想,以及批判帝國與殖民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這兩個問題當然也在我的生命中長期盤踞,比較貼切地講,林老師應該是一個帶有極高批判意識與自我反省力的基督徒。那麼,他會接觸到「下樂姆」的無教會主義追隨者就沒有太過於意外了。
回到當代的演化與生態思潮,這是林老師的專業本行,我意外地跑到一個基督教大學的生物系唸書,似乎也是冥冥當中必須面對這些思潮與信仰的關係。其實這方面的探索,我跟另外一位指導教授歐保羅老師討論的比較多,後來到英國追隨的指導教授,曾任林奈學會會長的R. J. Berry給我更多的養分,他作為倫敦大學生物系的遺傳學講座教授,同時護衛著達爾文的演化論與自己的基督信仰,並撰寫專書來回應這些令人困擾的議題。林老師教導我用批判的眼光,這種批判並非惡意的批評,而是有意識地分辨事理背後的真正價值所在,對於複雜的基督教歷史與教會發展,當然不是所有的作為都是合理且合乎正義的,他給我們閱讀1967年在Science出版,科技史家Lynn White Jr. 所寫的"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logical Crisis"便是一例。我在念博士班時還特別將這篇文章翻譯成中文,刊登在曠野雜誌上。Lynn White Jr. 正是一個自由派的基督徒學者,但是他卻是猛力地批判某些基督教思想的內容,引發了極大的爭論,後來還間接導引出生態神學的領域。
在新書中,曼恩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在講達爾文演化論者與基督教護教者對峙的一個著名故事,就是有暱稱「達爾文的看門狗」的著名英國學者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與英國大主教山姆.威爾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的大辯論。曼恩說,演化學的教科書常常說在那場辯論中赫胥黎用科學的理性教訓了大主教的說法,是嚴重的誤導,也忽略了大主教在辯論中提出了一個嚴肅且理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人究竟與其它生物有何不同?按照演化論,人與其它非人有親緣關係,人的出現是演化天澤的作用產物。既然如此,人的理性能力真的能超越自然的選汰嗎?也就是說,赫胥黎高舉科學的理性,認為這是解釋世界現象包括人的起源問題,並以此為決鬥基督教信仰的利器,果真有如此神效嗎?果真如此,不正也證明了人異於非人的獨特性嗎?而這正是兩者辯論的核心,可惜的是赫胥黎並沒有回答。曼恩講了這段故事,明確地跳脫在「巫師」與「先知」之間做選擇的困局,不管如何他們都是人,且相信人的作為可以解決眼前「人類世」的危機,只是做法不同。但果真如此?曼恩丟了一個大問號下來,直接把主題拉到科學與宗教信仰的對話層次。
「下樂姆」在相當意義下,是一種具有強烈反省力與獨立思考的基督教知識分子的精神。我記得在課堂上,林老師曾經這樣講過,他說基督教文明之所以強大,是來自一種強烈的自我批判精神,顯然他也找到了自己性格中如何跟基督教精神相容與對話的位置。在演化論知識的傳遞中,科學與基督教常被塑造成是對立的。但在最新的科學史研究中,卻告訴我們兩者的關係是互相增進的程度,不亞於彼此敵對。同時有趣的是,在這幾年的見面中,我注意到林老師在看待信仰的態度上慢慢地柔和了起來,更強調信靠,不再僅是理性批判的進路,而是在恩典的光照下去接納。人們常說,人越老會越固執,但是我在林老師身上卻時常可以看到一種令人驚喜的調整與轉變,真是奇妙的事。
結語
以上,是我在過去幾十年的歲月中親炙台灣前輩級環保人士,且了解他們環保價值觀的親身經驗,而對象正是我一生感恩的老師林俊義教授。用曼恩新書的比喻來看,他是先知嗎?還是巫師?我勸大家先不要對號入座,這不是一個好的問法,我承認它是詭詐的陷阱題。其實,連曼恩本人都不願在兩者之間選擇他的立場。曼恩的書寫,喜歡帶讀者進入實際的歷史社會脈絡,讓筆下的人物在事件,議題與處境的行動中逐步顯露出他們的價值觀與態度,這樣我們可以充分地領略到這些人物以及他們所處的大時代與社會脈動的關係,他所描述的科學家們於是一個個成為有血有肉的人。我的功力遠遠不如他,但是在閱讀他的書時,心中卻是充滿了悸動,想要講出其實台灣也有不少像是曼恩《巫師與先知》一書中筆下的人物,有些人有著巫師的身影,有些則像是先知。還有一些,恐怕是另外的典型。文章篇幅有限,就先讓我以此文字表達對恩師的啟發與感謝。此外,還有曼恩的文字帶給我的諸多靈感。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益仁 先知?或是巫師:從曼恩看台灣環保先驅林俊義老師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885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