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中)
一月中,芭樂人類學刊出了非典型影評:在《幸福路上》遇到人類學家。藉由與備受好評的本土動畫電影《幸福路上》對話,帶出近年來人類學關於「幸福」(happiness)──以及其相關主題如追求well-being、共善、道德、價值、希望的討論。回顧十分詳盡,說明淺白清晰,相當推薦給人類學或非人類學的讀者。
這篇續篇,除了接續上次未提及的「暗黑人類學」(謎之聲:拖戲要拖多久?),還希望把戰線拉長。為什麼我這麼不自量力呢?一方面而言,關於Joel Robbins所揭櫫的「幸福人類學」與Sherry Ortner標舉的「暗黑人類學」之討論,是被名為新自由主義的晚期資本主義背景下人的存在境況之一體兩面。另一方面,它牽涉到人類學知識圖譜中長久存在的「他者」議題──只是這個「他者」所佔據的空間,在「幸福人類學」的討論串中,由「野蠻間隙」(”Savage slot”暫譯)蛻變為「受苦間隙」(”suffering slot”暫譯)。一旦牽涉到「他者」,就是人類學知識的重大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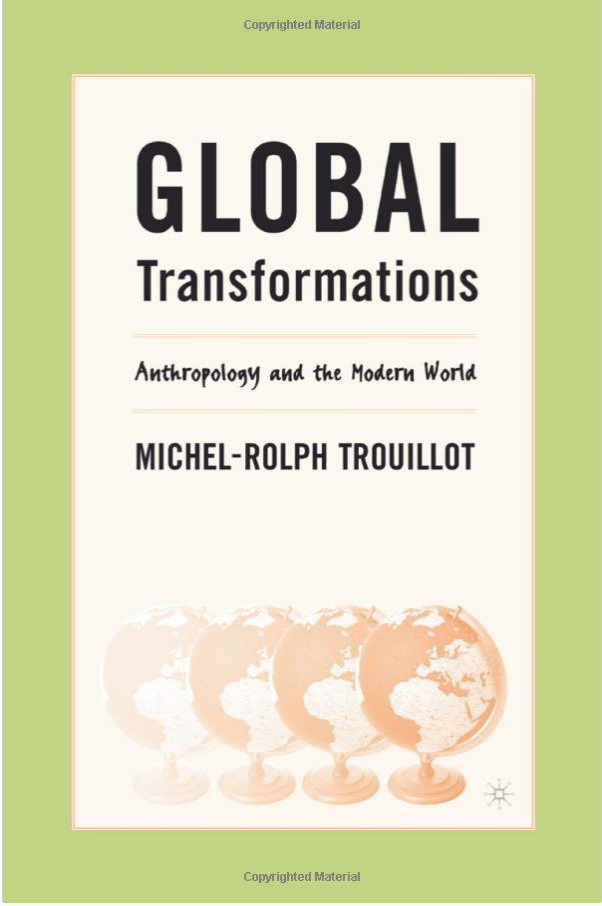
Savage slot典出任教於芝加哥的著名海地裔人類學家Michel-Rolph Trouillot的文章〈人類學及野蠻間隙:關於他者的詩學與政治〉(Anthropology and the Savage Slot: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Otherness)。文章初版於1991,後收入作者所著Global Transform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3)。
「野蠻間隙」(Savage slot)的觀念與西方與他者(West/Other; West/Rest)之討論相近,但意涵更為豐富:它是個空間上的想像,指涉想像的地理與管理的地理(geography of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y of management)之雙重投射。而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就是”Savage slot”中的居住者(註 )。這是讀過東方主義的學生們所熟悉的母題: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想像空間中的居民,是作為西方的反命題,也是某種西方的未竟許諾而存在。當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改變,「西方/他者」不再是有效的世界史區分方式,而西方旨在了解自我的探照燈也隨之轉移方向之後,這群被置於想像間隙中的居民便「被遺留於黑暗之中」(Joel Robbins語 )。
在當前人類學討論中,「照亮黑暗」的方式之一,便是透過受苦的探照燈,而此種訴諸苦難的同情共感論述常常是強而有力的。Robbins在2013年發表於人類學指標性刊物JRAI的文章〈超越受苦主體:關於善的人類學〉(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之中,便舉了自己關於新幾內亞Urapmin人之民族誌,以及當前人類學界中標舉受苦的優秀著作,是如何喚起(西方)讀者懷抱的人道精神,激發同情共感。同情共感之範圍,自然也包括了前篇談到的: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的同情共感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 但是Robbins並不希望人類學研究對象就等同於「受苦間隙」中的居民,也不願意否定這個間隙。他很客氣地表示:提出關於「善」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good),並不在批判受苦間隙,而是提出一個(十分豐富的)補充──這個補充作業,包括了關於價值、道德性、well-being、同情共感(empathy)、關懷(care)、禮物、希望、時間與改變(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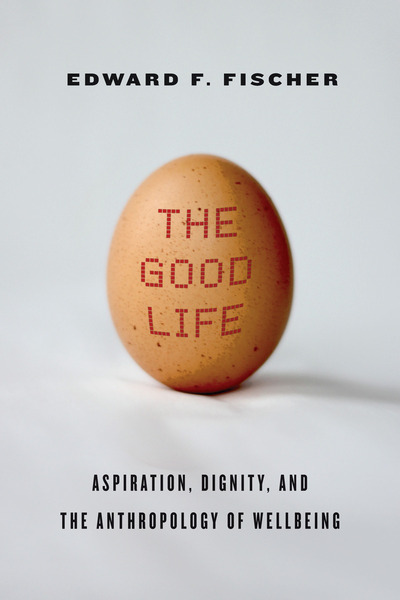
幾個關鍵字開始出現:西方、他者、野蠻、受苦、想像的間隙。(人類學系的學生開始感覺自己置身於學史課堂了……)自然還有:黑暗、同情共感(以及被歸納於此範疇下的vulnerability)。
敏感的學生必回憶起著名人類學家Marshall Sahlins在一篇人類系學生必讀文章〈何謂人類學啟蒙〉(What is Anthropological Enlightment?)裡對於西方/他者二分論述的犀利批評,比如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蔚為風潮的「失望理論」(despondency theory)──認為倖存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的當地人只能(無論是在經濟社會或思想上)與西方同化。而啟蒙思想主導下的人類歷史理性進化論、或者其變形──Rostow所提出的現代化理論,或者名為反制但骨子裡還是同樣啟蒙主義精神的依賴理論之中心/邊陲結構觀,無非是複製了這樣的「失望理論」思想。。
Sahlins進一步表示:若不去重視當地人如何主動地在結構局勢下以各種新方式極具創造性地延續或再生產其文化,人類學在晚期資本主義就將成為一種「贖罪式的文化批評」,將其他民族視為因應西方各種宰制型態的被動他者。這是尖銳的批評。對人類學家而言,很少有比被指責為東方主義者更嚴厲的指控了。
Ortner的〈暗黑人類學及其他者〉(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是出現於Robbins上述文章之後,是對於Robbins所揭櫫「關於善的人類學」之回應。她的學史意圖也是很明顯的──在1984出版(同樣是學史必讀)的〈1960年代以降的人類學理論〉之後(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2016年,Ortner想藉由「暗黑人類學」這個主題,重新喚起人類學家對於晚期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全球權力宰制、壓迫、不平等、大規模驅離的重新重視。但是這麼做是有些風險的。該風險,在將近二十年前,Sahlins就已經指出人類學面對西方霸權論述的雙重困局:
因為談起原住民族的歷史能動性,儘管可能為真,卻會變成忽略西方世界體系的專制,於是在智識上與暴力和支配同謀了。相反地,如果我們討論帝國主義的制度性霸權,儘管可能為真,又變成忽略了人民為文化生存所進行的鬥爭,於是在智識上也與西方暴力和支配同謀。或者,我們可以讓全球支配和地方自主這兩者看起來在道德上都有說服力──也就是站在(原住)民族那一邊──只要將後者(地方自主)稱為抵抗即可。這是穩賺不賠的策略,因為這兩種特徵(支配與抵抗)是對立的,組合起來的話就能涵蓋任何一種歷史終極性…… 文化差異被世界資本主義的同質化力量從前門丟了出去,又以原住民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顛覆支配性論述、或原住民異議的政治(或詩意)的形式從後門爬回來。(Sahlins, 1999: What is anthropological enlightenment? 中文翻譯參考趙旭東、但小編重譯)
既然有了這麼充分的辯論,而Sahlins很早很早就為Robbins這個方向背書,那麼為什麼我還是會想談關於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華語世界人類學對於Ortner所稱「暗黑」──也就是權力宰制、不平等、壓迫的關注,儘管並非付之闕如,但大多數都是將之視為背景,而非聚光燈下的焦點。Ortner怎麼談暗黑,在幸福人類學討論中引起何種回應,請見下回分曉。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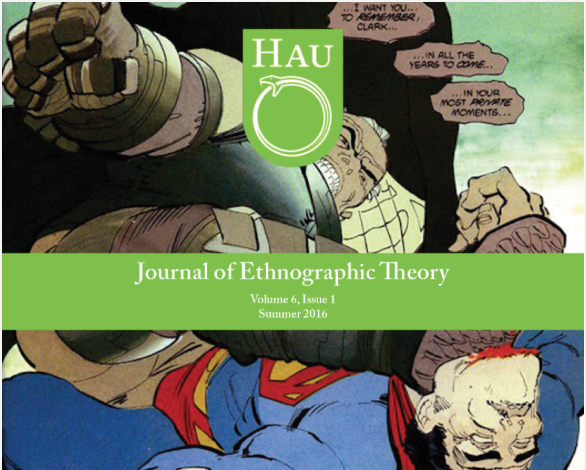
註:Trouillot有意識地以大寫的Savage表示抽象概念範疇,小寫的savage代表特定歷史中的主體人群。只是在Robbins(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論證Savage slot如何蛻變為suffering slot的文章之中,均以小寫取代。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bricoleur 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中)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48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感謝優秀的芭樂編輯,將註腳編入正文不說,還代潤Sahlins譯文!應該是所有學普網站中最出色的編輯了(沒有之一)!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