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上)
文章企圖談兩個部分:傷心,以及暗黑。所謂「傷心」,來自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所談的vulnerability──人類學田野工作者的脆弱性、易受傷性。而「暗黑」則是Sherry Ortner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暗黑人類學及它的他者」。[1]兩者如何相容──儘管這是個咸認黑暗的時代,且我們大多數人都時時刻刻傷心(若非麻木的話)?以我的寫作慣例──一句話都會分兩三次講完──這次先談部分的傷心。之後再談暗黑。
為避免文長夢多,不如結論先行:認識到時代的性質就是黑暗,不可能不傷心;然而與選擇其麻木與虛偽,還不如傷心。經過深度反思與高度節制的易感性往往具備撼人的力量。但是同時,如果傷心流露出淺薄廉價,問題可能不在脆弱易感,而在於……(下回或下下回分解)。

這種人類學(按:傷心人類學;脆弱易受傷的人類學)不是為了心腸軟的人(This anthropology isn’t for the softhearted.)。
它也不是為了那些人:他們「讚嘆任何人都可以選擇這種深刻疏離和反覆失落的職業」。但那還不是人類學最糟的部分。不,人類學最糟的是,不僅觀察者是脆弱的,就連我們觀察的對象也是脆弱的,甚至更加深切。(《傷心人類學》中譯本頁30)
人類學歷史上是以為他者「賦予聲音」(give voice)而存在,在人類學裡沒有比自我揭露更大的禁忌了。(同上引書。頁32-33)
今天並不是要談後現代民族誌或者「書寫文化」式的再現政治反省,或者談女性主義對民族誌書寫帶來的影響,亦非互為主體的同理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然而以《傷心人類學》開場,似乎無法避免這樣的黑箱──與民族誌田野工作配套的黑箱。[2]其實我想談的只是一件事情,也就是《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或「易受傷的觀察者」)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是,我想談田野工作者的易受傷性(vulnerability),但這是一個巨大命題。對從事過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我可能談得太少;對於未從事過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我可能談得太多──未從事過人類學田野工作的人,有不少對「田野」懷抱著各式各樣的想像。以我的接觸經驗,大部分年輕學子對田野的想像源於害怕受傷,或者迴避「易受傷性」(vulnerability)。不同性質的田野工作與研究課題,也有著傷心度(易受傷度)之別。在談太多與談太少之間,先講一兩個故事。
每位人類學專業者(也可代換為時下的流行用語:「人類學的學徒」)在訓練過程中,從田野回到書齋之後,都有著自己的療癒儀式。田野中的大小事件點滴,透過書寫與紀錄初步客觀化之後,有的很難寫成論文,卻也很難迴避。就像海明威所說的,如果作品是一座冰山,在水面下的部分是在水面上的七倍,而是那水面下看不見的部份支撐了水面上看得見的部分。田野亦同。田野中的時刻與事件,可能是論文成品的十倍,甚至百倍。我常想,如何消化在田野中難以言說的經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研究的格局。
我所就讀的學校著重人類學古典理論──古典到就讀哈佛的同業感覺我們簡直是在學習不同學科的程度──當然,敝系也強調長期深入的田野工作。但這「長期深入的田野工作」應如何訓練起,也秉持著古典傳統──那就是一門幾近於藝術的「不可說」技藝。事實上,漫長求學生涯中唯一堪稱正式的田野訓練,就是人類系大學部必修的「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我始終記得大學的最後一學期,一位芝加哥畢業的前輩學者在課堂上表示:田野怎麼教呢?田野是沒辦法教的。在芝加哥,是藉由田野工作坊的形式來「教」──從田野回來的博士生舉辦工作坊,尚未從事田野的博士生就從前人的實際案例中略知一二。敝系似乎也承繼了這樣的傳統。從田野回到學校的學生,會在老師與學生共組的「田野工作、倫理與民族誌」工作坊中分享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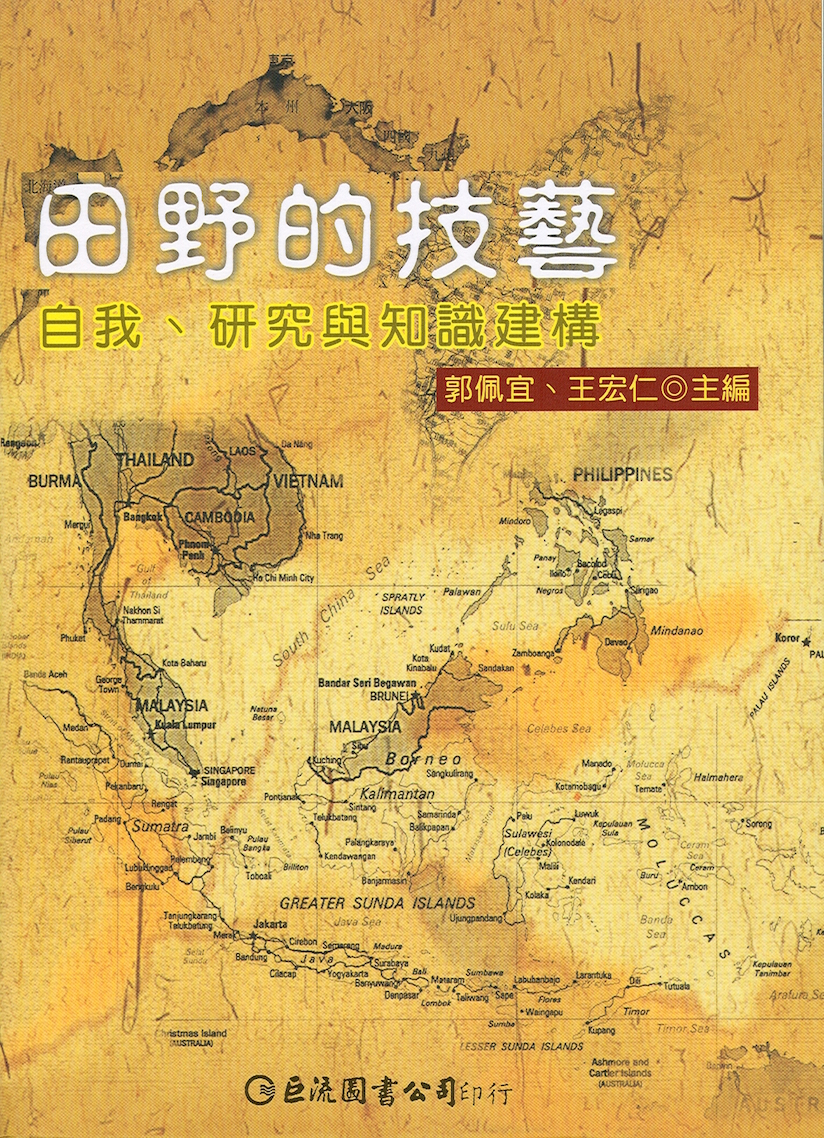
我要說的第一個故事,就來自這樣的工作坊。那場工作坊是關於田野中的死亡。
一位在西非進行博論田野的美國同學,[3]大約是耶誕節到跨年期間返國暫休期間,在當地的一位往來頻繁的熟識朋友(通常稱為「主要報導人」)意外過世。當時他身處東岸。回到田野後從村民的異樣表情中得知噩耗,震驚難言──一個在返國度假之前還經常見面的朋友硬生生地從生命中消失,而他不在場。田野前期與後期的斷裂彷彿再也無法接上。村民的複雜態度使他不斷自我懷疑──難道是因為自己的無心小過造成朋友的意外過世(儘管事實上並不是)?在工作坊中,他提到這樁事件所帶來的衝擊,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巨大。回到學校之後,是靠著友人持續地陪著他在校園內散步,一再一再地走著,他才能逐漸地把這事件談出來。在工作坊中他說:陪伴、傾聽、散步,效果遠勝學生保健中心的諮商。
同一場工作坊中,另一位在南美進行博論田野的同學報告田野中所遭遇的死亡經驗──他在場,還帶著垂死的小孩去醫院。儘管親眼目睹雙親的深度悲傷,他所受的衝擊沒有這位不在場的美國同學來得劇烈深刻。這自然與不同的生命經驗有關。
以與他同學多年的旁觀者身分,我很確定,這樁西非田野中的死亡事件,深深地改變了我這位同學。它已經溢出了「田野」這個可被客體化言說的場域,形成田野工作者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另一個故事來自於自己的田野經驗──一樁冰山表層的事件。
我的博論以財團在西太平洋島嶼的觀光開發案為主題。島民對於這樁受國家與州政府支持的大規模觀光開發案意見分歧──部分贊成,部分反對,有更大一部分持觀望態度,暫不發表意見(至少在我面前)。由於強烈不贊成財團圈地,我與持反對意見的島民團體關係密切。又因島嶼政治的迴避邏輯,意見迥異的人不太容易遇到彼此,就算遇到也竭力避免當面衝突,因此,鎮日與反對者相處的我不太容易遇到贊成者。也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搬離原居的中低階村落,遷往反對者占多數的高階村落。
此舉完全有研究上的正當理由──要理解階序社會,我無法只待在中低階村落,也必須往高階村落盤桓。但此種「如企業家一般地向上攀附」已經溢出了原居家庭的親屬範圍。數年之後,原居村舅舅的女兒還是問我:「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搬到某村去呢?」(言下之意:是不是不喜歡我們?)我努力解釋,連指導教授都搬出來(深深了解島嶼政治的教授很早就提醒我:遷居時可以拿他當擋箭牌)。但我永遠也不曉得到底他們理解了多少。而數年後寄宿家人的名字出現在集體的租約簽署名單上,與我這個出邊出沿的寄宿姊妹之遷居他處,關聯性又有多少。(我經常想著,如果我在田野中不遷移到高階村落而留在原本的低階村落,是否數年後的集體租地,就不會發生?然而這只是個無效的假設性命題。)。
在離開田野兩年半之後,原居村落與財團簽署了一筆效期一百九十九年的租約,租賃範圍是村外一片占地遼闊的無人土地。我在社交媒體上得到消息,聯絡島外親戚稍知詳情,擔心不已,然而島嶼的秘密政治與村落階序,使當時我簡直完全無法直接從村人/家人處探聽一二。又過了一年半,我終於畢業,重訪田野,還是一如往常地帶了禮物回去。但是我與寄宿家庭的關係再也不如以往一般自然親密。他們收下了禮物,道謝,而我們很快地別過。
這是一樁不那麼傷心的小事件。非常容易以複雜因果律解釋的事件。[4]真正令人脆弱困惑的重要事件,如威脅恐嚇的戲劇化場景,事涉政治上與情緒上的敏感,還停留在冰山的底層。(我承認:我同學所經驗到的死亡事件,是傷心。而我寫出來的,只是表層的困惑。)
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傷心人類學》中譯本頁226-227)
傷心沒有高下之別;傷心就是傷心,脆弱就是脆弱。但是如何處理傷心,的確有格局高下之別。脆弱並不是玻璃心。然而在傷心(或者說易受傷性、脆弱性),與民族誌之間,還有一些別的。那些「別的」,Behar引用Geertz的話說:「有一種文類消失了」。
……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又是一種多公開的活動?是的,我們前去並與人們說話。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甚至抱著耐性、善意及慷慨來和我們說話。我們試著好好傾聽;對於我們所誤解的每件事,以及之後將顯得微不足道、非常生活表面的事,我們都寫下田野筆記。然後,是時候打包行李回家去。接著開始我們的工作,也是最艱難的工作:憶起民族誌的時刻、使它復甦、拉近我們的所見所聞與無法在我們的表述中對它公道評論的距離──太快展開以致不會感覺像個無底洞。我們的田野筆記變成羊皮紙,除非用來探測遺忘的天啟時刻、未表達的渴望及悔恨的創傷,否則將是毫無用處。如此一來,即使我們以走入公眾開始,卻仍以自我反思來延續我們的工作。
然後,我們再次走入公眾。如果我們第一次處理的事物幾近悲劇,那麼第二次我們顯然處於鬧劇之中。當我們站上講台--在希爾頓飯店裡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我們向著其他緊張的民族誌學者,大聲讀出自己的民族誌作品,那裡懸掛著吊燈,冷氣則令我們感到寒風刺骨──我們的確定感及對田野對象的依賴都被轉移到權威的位置上。甚至Geertz承認存在著一個問題:「當我們實際上在工作時,我們缺乏一種語言來表達發生了什麼事。似乎有一種文類消失了。(《傷心人類學》中譯本頁12)
然而我想在這裡嵌入Ortner所說的「黑暗」。黑暗,下次再寫。
有時想起2014年夏天回台時讀到的硬頸自白書《左工二流誌》。跋言開篇:「長征路上的傷兵是要帶走,還是乾脆斃了?或是安置何處呢?」(頁490)那些從田野返回書房的人類學家,有沒有療癒儀式?或者都得靠有效無效全憑運氣的心理諮商,讓媽祖、筊杯、聖母、耶穌、十字架、符水、收驚効勞生、濟公來處理?這些同袍們,是否能像我的同學那樣,有人陪著他們在校園裡(或不管哪裡)一趟趟地走著,談著,讓當事人感到些許撫慰?憑什麼我們認為這些(多半)年輕的工作者就可以理解田野中的複雜現象,並能全身而退?這似乎只能訴諸研究者的「福德」、「業」與「命」。「傷心」或者「易受傷性」這個尚無法進入學術論述的黑箱,目前還沒準備好開啟──至少在談「暗黑」之前,還不是開啟的時機。
(待續)
[1] 暗黑人類學,依照Ortner所說,關注社會生活之艱難(如權力、宰制、壓迫、不平等),以及這些面向的主觀經驗,如當地人的憂鬱與絕望。Ortner, Sherry B.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1 (2016): 47-73.
[2] 關於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書寫,中文世界已經有謝國雄等《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2007)與郭佩宜、王宏仁編《田野的技藝》(2006)、以及林開世〈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2016)。更早則有黃應貴〈從田野工作談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的關係〉(1994)、謝國雄〈田野的洗禮,學術的勞動〉(收於《純勞動》一書,1998)。
[3] 經當事人同意刊登。
[4] 關於複雜因果律,我還是喜歡引用這段小說:
「事實上這件事開始於數千年前;開始於馬克思主義論者到來之前;開始於英軍攻下馬拉巴爾之前;開始於荷蘭人往北推進之前;開始於Vasco da Gama抵達之前;開始於馬拉巴爾的札摩林征服加勒卡特之前;開始於被葡萄牙人謀殺的三位穿紫袍的敘利亞正教主教,被人發現浮在海上之前──盤繞的海蛇騎在他們的胸膛上,牡蠣和他們糾結的鬍鬚纏繞在一起。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件事開始於基督教乘船到來,並且像茶包上的茶那樣滲入克洛拉之前。」(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吳美真譯。台北:遠流。頁36。)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bricoleur 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上)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36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