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歸剛ㄟ」
騙的多義與文化實踐
2024年6月一位遊客在探索被譽為「亞洲第一高瀑布」的中國「雲台天瀑」源頭時,意外發現這幅壯麗的景觀,居然是由幾根大水管出水製造,瞬間傻眼。然而,景區管理處並不尷尬,回應這是因應枯水期「做了一個小小的提升……豐富遊覽體驗」、「水管是為了調節水量」。隨後,針對瀑布的「造假」出現了兩種評價,一方認為遊客花錢想看的是自然景觀,如果是人造,就是「欺詐」行為;另一方則對此反駁:人造景緻只要夠美,真假並不重要。當地居民也表示,早已知曉瀑布是人造的,只是看破不說破。*類似的造假事件對於我們來說並不陌生,隨著2021年爆發台灣人被誘拐至柬埔寨的詐騙案件,也喚起了社會對詐騙的高度警戒,近期頗受好評的日劇《地面師たち》,同樣是以土地詐欺為題材,呈現其行騙手法,並刻畫受騙者的悲慘處境。

圖1:中國「雲台天瀑」被遊客揭露造假。(圖片來源:壹蘋新聞網)
*對於雲台天瀑事件,歡迎讀者參考:民視新聞網。2024/06/04。〈全都假的!「亞洲第一高」雲台山瀑布竟是「水管放水」〉;星島。2024/06/05。〈雲台天瀑被揭靠水管放水〉;網易。2024/06/05。〈雲臺山瀑布涉嫌造假惹爭議,網友:理解萬歲,全國十之八九是人造〉。

圖2:《地面師たち》改編自2017年日本的「積水ハウス地面師詐欺事件」。(圖片來源:「集英社」官方網站)
毫不意外,欺騙、說謊、詐騙行為**向來引發人們的厭惡感,在我們熟知的價值中,誠實乃是一項美德,欺騙則是道德錯誤。6歲的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故事,在許多人的成長階段扮演重要角色,這則故事在彰顯名人的美德之際,也加諸給讀者誠實的價值。荒謬的是,這則故事本身卻不是事實,而是由曾經作為牧師的美國作家Parson Weems所捏造,且當時絕大多數的讀者對捏造一事並不知情(6歲小男孩拿斧頭砍倒一棵樹?不過看魚逆流而上,立志奮發的故事有比較合理?)
**作者補充:本文暫不區分欺騙、說謊、詐騙或詐欺概念之差異,特別是詐騙與詐欺如今更多指向犯罪,被強烈的錨定在負面意涵,此一傾向恐不利讀者理解本文欲呈現的多義性。

圖3:描述華盛頓砍倒櫻桃樹故事的畫作“Father, I Can Not Tell a Lie: I Cut the Tree”。(資料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誠然如此,誠實神話的揭穿並不影響我們的信念,針對欺騙的抨擊,康德的普遍化論述以嚴格著稱,他指出:「不說謊是一種義務,也不允許存在任何例外」(Dubbink 2023);社會學者Erving Goffman(1959)也說明欺騙會破壞人們對於正確行為的觀念,對社會構成嚴重的秩序威脅;哲學家Sissela Bok(1978)基於誠實至上的道德哲學,主張「謊言總是對承受者的攻擊」,傾向完全禁止。話說回來,難道欺騙就這麼一無可取嗎?精神病理學家Charles Ford(1988)等人則反向的指出說謊是人類重要、基本的過程,它與建立自主權有關;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同樣認為欺騙與人類自由有所關聯(Barnes 1994)。
實際上,「欺騙」的主題呈現出一種文化張力,人們普遍將撒謊視為人性弱點,而多數文化也將「誠實」視為教育下一代的首要概念,儘管如此,欺騙依然無處不在(同上)。或許可以說,在文化規約的負面價值之外,欺騙也具有某種正面意義,使得欺騙存續、獲得特定的合法性,也由此凸顯了複雜性。
欺騙的文化邏輯
究竟什麼樣的文化會鼓勵人們欺騙?殊難想像,如同前述,欺騙將損害社會秩序以及基於信任構築的關係網絡,而欺騙的實踐也往往由於被賦予的負面價值而使行騙者難以言明,據此,它不太可能以「直球對決」的姿態現身。但在少數的人類學民族誌中,卻展現了欺騙以祕而不宣、明貶暗褒的形態存在。Janet Siskind(1973)描述祕魯的Sharanahua人性格慷慨,喜好分享獸肉,但是若一個人直接拒絕分享,意味著對要求分享者的羞辱,因此人們就需要經常對自己的肉存量說謊,來避免因贈予期待帶來的衝突。此時,欺騙是用來調解社會關係並兼顧自己家庭的生存。

圖4:謊言未必都是破壞社會關係,有時是因維持關係而存在。(圖片來源:筆者與Leonardo AI合作)
Ernestine Friedl(1996)也指出希臘鄉村的父母有時會刻意對小孩撒謊,作為一種教育方法,讓孩童在成長階段學習到「如何透過操縱來謀取利益的生存技巧」,而孩童如果利用了家庭或鄰居之外的人,往往會得到父母的默許,而父母則可能會向人吹噓自己的孩子是狡猾、機巧的,因為他們深知這是一項對於在未來職場或生活中生存至關重要的技能。Friedl同時以自身任教的經驗,說明學生認定考試作弊、欺騙教師是合理的,其中包括了成績優異的學生,都認為自己有協助朋友作弊的義務,而欺騙Friedl的行為是直到她與學生打成一片後,才逐漸減緩,這是因為她開始被認為是群內成員,不能繼續欺騙。在希臘社會中,欺騙經常在與外部群體的關係中,作為維護群體及家庭榮譽、聲望的一種技能,欺騙有時是履行該項責任的有效手段,這種榮譽來自於對於群體內部成員的照顧、分配資源和尊重,其範疇是家族、姻親與朋友。欺騙在意識層次受到譴責,然而在特定情境下卻是合理的。
Michael Gilsenan(2016)探究黎巴嫩社會中的謊言實踐,指出「說謊」(kizb)是構成整個文化世界的基本要素,並且與意識形態、榮譽、社會實踐和結構有關。謊言在黎巴嫩社會被廣泛使用,涉及優越感與支配,說謊者最終對說謊對象揭穿謊言並且宣告勝利,在孩童的遊戲中,他們非常擅於欺騙對方,從中獲得支配權,同時培養戰勝他人的言說能力。此外,說謊也是一種追求極具有社會意義的個人榮譽、聲望追求的手段,用以建構社會自我。此外,謊言不僅僅是加強了人們對事件的洞悉能力,人們在實踐中也能運用謊言來揭穿謊言,由此貶低對方的身分價值、羞辱其榮譽。
回過頭來,在我們的文化中似乎不太需要捏造食物存量、經常為幫同學作弊而欺騙老師,更沒有透過謊言來捍衛榮譽的必要,然而,日常生活實際上也存在各種具有社會意義的「謊言」:當購物時店家殷切的稱呼你「帥哥」、「美女」,就嚴格意義上而言,有極高的可能性是說謊(誤);與此相似,還有「恁女兒拿ㄟ甲水」、「下次約吃飯」、「我家的貓會後空翻」與「我媽媽叫我去洗澡」……等,我們的生活被大量此類社交辭令和隱喻式語言所包圍,即便它與客觀事實、主觀認知或者字面描述均不相符,但這仍不會被視作一種欺騙行為。相對的,秉實以告和信以為真(「原來我的臉蛋如此俊俏」、「上次你說了要一起吃飯」),反倒會被認為是有失禮儀、對文化脈絡的理解不足或欠缺讀懂空氣的能力(空気を読む),運用、識別與應對則被認為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基礎能力。這同時意味著,欺騙的判定──是否算是欺騙及其程度──遠不是事實層次的非黑即白,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欺騙」在藏人社會中的意義與實踐
必須強調,誠實在藏文化中是極為重要的價值,而在我的田調經歷也確實如此,不過也曾有過幾次「上當」經驗。原本該要跟著冬蟲夏草採集人足跡的我,意外成為在青藏高原上「做土水」的無償勞工(前情提要:男版小松菜奈。2020。〈你得狠狠幹一場架,而且必須打贏:文本中隱匿的研究者、情緒與情感關係(上)〉)。在藏區的另外一座城鎮,當我看中街邊小攤出售的一頂藏式禮帽,與店家展開議價攻防,自詡老練的我從三折開始出價,但店家苦笑著回答:「不行啊,這樣活不了」,霎時,坊間盛傳的「藏人經商比漢人誠實,因此定價較低,但殺價幅度也小」的說法浮現在腦海,我心軟了,最終以八折成交。然而,正當我得意向友人展示,一位本地女孩戴著同款帽子從我們身旁經過,追問之下才知,她僅以不到三成的價格購入,而這是本地公認的合理價位。
「我被騙了嗎」?「做土水」一事尾聲時,報導人對我說:「這是你自願的」,的確,田野工作並不是一種明確的契約對價,而對方始終清楚你對他的依賴。同樣的,買賣也是在雙方同意價格的基礎上進行,貨比三家則是交易前需做足的功課,況且,店家可能負有照顧本地人的義務,而須針對對象調整售價。若將這些狀況均解釋為欺騙,將令人遲疑,騙、坑對其中一方或許難以接受,但「欺騙」在實踐上總是存在著某種彈性或區間。鑒此,曾經「上當」的我反而開始對此道著迷,投入在蟲草交易中我稱之為「障眼」手法的研究。
佛教信仰深刻地融入藏人的日常生活,謊言(རྫུན་)或欺騙(མགོ་སྐོར་གཏོང་)的行為因此頗具負面意涵,其中,「不妄語」的原則就被寫入吐蕃時期由松贊干布所頒布的律法,如說謊者要割舌頭……等(班班多杰 1997)。語言也因被人們認為具有靈性,如詛咒被認為有致人於死的性質,所以欺騙他人所造成的業,最終將會返回自己身上,基於這項觀念,起誓就成為判決定案的關鍵,而盟誓詛咒也成為藏族人崇尚誠信的標誌(倫珠旺姆、昂巴 2003)。此外,說謊也被視為是對於信仰不夠堅定的表徵。
不少報導人向我表示:藏人對於說謊相當厭惡。即便如此,它還是存在例外,以一個藏區普遍流傳的故事「莫頓帕洛」來說:
懶惰的帕洛成天待在家裡吃和睡,從不外出工作,於是他的妻子為了丈夫的健康與家中生計著想,心生一計,謊稱自己做了一個吉夢,對正在睡懶覺的帕洛說今天出門向左方走去定會有所收穫,於是帕洛循著路線,果然在樹下找到一些牛肉,喜出望外,從此開啟了出門的興趣,但其實牛肉是妻子預先放置的。(博格勒,木扎縣,20230901,田野筆記)
帕洛的妻子即使欺騙,但用意是讓丈夫出門活動、打獵,所以被評價為賢淑、睿智。許多藏人長輩也會透過類似方式訓練孩子,驅使他們出門挖蟲草,這類技巧被認為是無傷大雅。相對的,若涉及為了私利而造成他人損失的欺騙,就會被定調成負面,在「莫頓帕洛」故事中,帕洛隨後假裝精通卦術來行騙,儘管獲得一時名利,卻也因謊稱一位婦人的孩子已死、戳人痛處,遭受眾人唾罵。現實中,藏區偶爾會發生「盜賣氂牛」的詐欺事件,有些人受到牧民委託協助放牛,卻謊稱自己是牛主人而將牛私賣,待他取得款項之後便惡意失聯,造成委託方或買方的財產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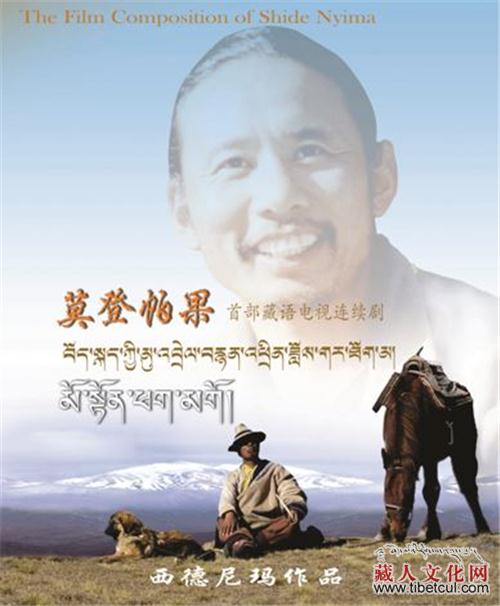
圖5:2007年莫登帕果(莫頓帕洛)藏語電視劇,由藏人演員西德尼瑪飾演帕果。(資料來源:藏人文化網)
誠然如此,欺騙的負評還是會因對象的作為與地位而有例外,藏人社會還流傳著「阿古頓巴」的故事:阿古頓巴是一位機智型人物,經常以遊民、農奴、僕役等社會底層的角色現身,具備聰明、智慧、不畏強權及劫富濟貧的性格。故事中的他擅用謊言去哄騙、教訓欺壓底層的官員、財主或牧主,運用個人口才和設計的詐術,對壓迫者還以顏色,是個頗受歡迎、愛戴的人物(劉秋芝 2012)。展現在阿古頓巴身上的「機智」(སྤྱང་གྲུང་)概念,除了聰明之外還帶有詭計、設局,運用技巧戰勝對手,為自己或他人獲利,謊言便是重要的技巧,因此鈴木健之 (1983)評論阿古頓巴本質上還是個騙子。無論如何,阿古頓巴的故事展現了欺騙與機智在實踐上具有某種共通性,欺騙行為放在社會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中,可能具備正義與積極的意涵,即使在欺騙被視為禁忌的藏人社會,也並非在任何條件下均不允許,端視行使的情境、社會相對位置和意識型態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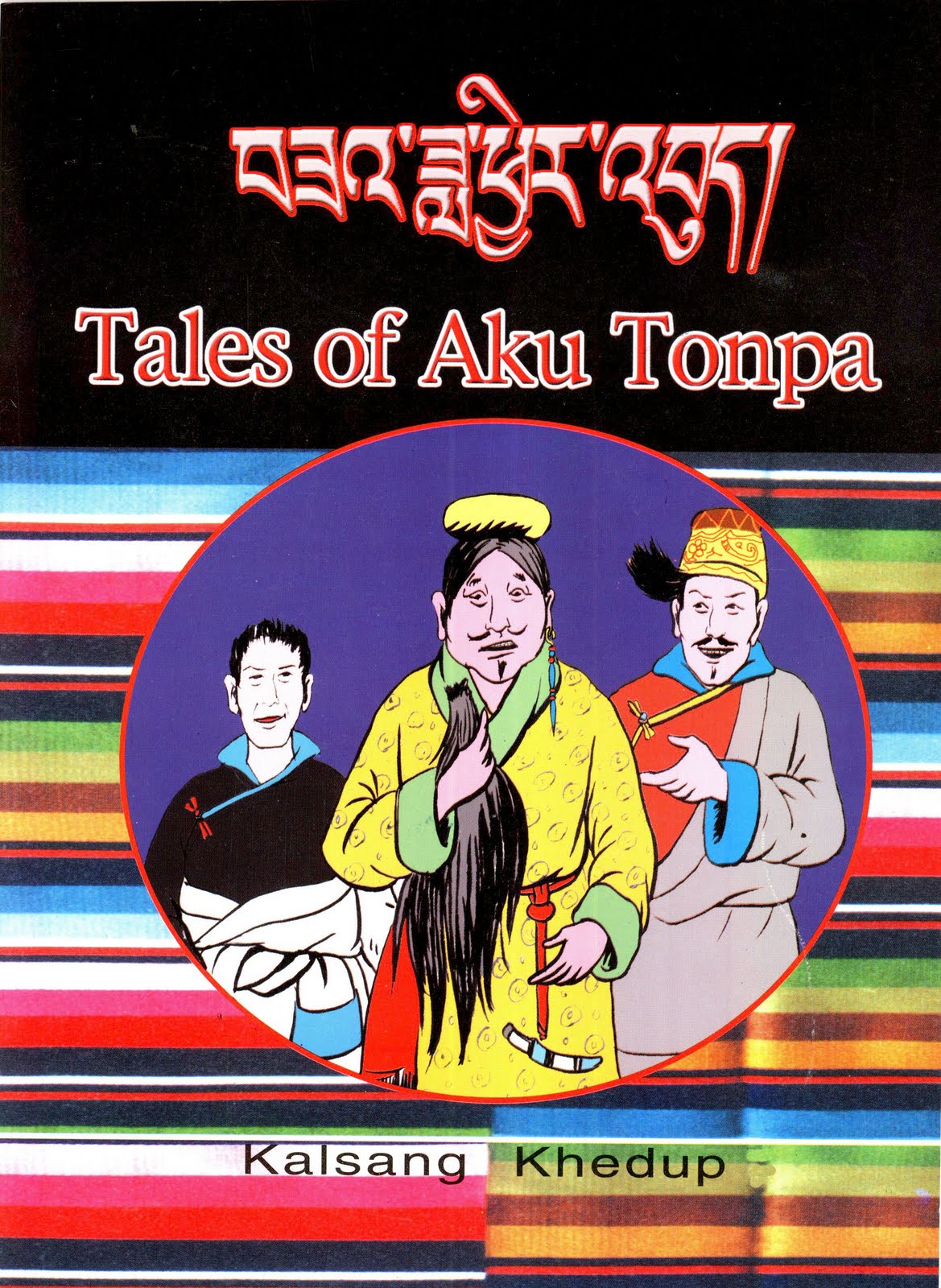
圖6:阿古頓巴是藏人社會中頗受歡迎的故事角色,該圖為Tales of Akhu Tonpa一書封面。(資料來源:ཁ་བ་རི་པ་བོད་ཀྱི་དེབ་ཁང་།部落格)
我的朋友格桑,有時將某些(在我看來)疑似欺騙的行為解釋為「玩笑」,如一些人編造自己的人脈、經歷、虔信程度。她也表達了自己對於欺騙的看法:「耿直是一種美德沒錯,但欺騙我倒不太在意……從佛經來看,佛祖也會騙人,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話語教育、感化,因地制宜,佛陀是很聰明的」,並補充道:「關鍵不是欺騙行為本身,而是欺騙造成的影響,若是傷人性命才是不好的」。雖然我不確定佛祖是否深諳此道,但是格桑顯然點出了一項判別的關鍵──傷害,對他人造成生命損傷──這仍與信仰有關,帶有傷害性質的欺騙,對於虔信的藏人來說是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線,並由此衍生與其他文化欺騙行為的差異。
換言之,人們確實厭惡欺騙,但是一件事是否被認定是欺騙,有其一套默會知識、文化脈絡,此外它也與行騙者的意向及影響程度有關:為了私利並對他人造成生命傷害的欺騙,才是區間中最糟的。然而,欺騙的意向性是良善還是私利仍然相當模糊:帕洛妻子欺騙的動機,是為了丈夫的健康,還是減輕自己的生計壓力?阿古頓巴的欺騙是為了懲奸除惡,還是為了私利、滿足惡趣味?或者回到最初的「造假瀑布」,景區是為了騙取遊客量,還是維護遊客體驗?它確實可以視為一種避重就輕的話術,然而,也正是由於這種不確定性,人們得以居中運籌帷幄,運用欺騙作為攻訐和抵抗的武器。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男版小松菜奈 「詐騙歸剛ㄟ」:騙的多義與文化實踐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706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