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類學的可能
從David Graeber談起
每次去參與AAA(美國人類學會)會議,我就會看我的老同學們的身體表演方式來了解美國人類學(或至少Chicago派)的方向轉變。今年去舊金山的時候,發現有一些人從典型「教授」的樣子轉到比較輕鬆的打扮,從比較嚴肅、學術的姿態轉到非宣讀論文稿而用比較口語的方式來演講,而且偶而緊張地笑出來,就知道我學長David Graeber的夯度。雖然這個現象有點好笑, 但,同時我也覺得Graeber在人類學界紅起來是件很好的事。

為什麼Graeber最近吸引那麼多人類學者的注意呢?或許對交換理論、價值觀理論及Madagascar的民族誌等議題有興趣的人,早就看過他的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2001)。但,在Graeber出版了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 一書後,他更廣泛地引起了很多人在人類學期刊及部落格上的討論。不只是Debt一書的內容引起人類學界的興趣 (我自己覺得他2007年出版的論文輯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的內容更豐富),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從很早期開始便參與了紐約市的Occupy Wall Street(OWS)運動,且他也常常出現在媒體上,解釋OWS運動的目標、方向與實踐原則。因此,在人類學界(包括芭樂人類學!)正在熱心地討論「公共人類學」的時候,Graeber便成為了一個很令人樂觀的公共人類學者典範。
我在這裡不要詳細地講他對貸款、資本主義、奴隸等的理論,只講一點點我欣賞他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我並不要把Graeber英雄化;無論是在他的理論方面或他的社運實踐方面,他獲益於很多前輩跟同行者,而且有許多其他學者和activist的工作一樣有很值得思考的論點與方法。由於Graeber在人類學界目前比較容易被看到,下面我想提出幾個當公共人類學者的可能,以Graeber 為例。
1. 提倡跨文化與跨歷史的比較:
很多人類學者發現(包括郭佩宜上次的貼文),其他領域的教師和作家談到「人類學」的時候,他們看到的只是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而已。Graeber回復且合成了一些在18、19世紀及20世紀中公共人類學的面貌。與20世紀的Boas及其學生相同,Graeber也是用「人類學的文化比較」來做為參於公共議題討論的起始點。跟他們一樣,Graeber強調人類的文化多樣性,同時也強調人類的共同性即在於不同的人能互動與互相溝通的可能性 (“incommensurability is greatly overrated” Possibilities p.1) 。
他跟Boas, Mead, Benedict一代的人類學者的不同點之一是:他對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關係的看法複雜許多 (過了這麼多年,這也是應該的) 。而且,他不認為僅提出兩個社會的差異能證明什麼。我們需要把每個問題──比方說價值的來源,權力不平等的結構等──放在全人類的歷史的脈絡中進行比較,或至少應比較一些不同類型的社會在不同時代怎麼面對某一個問題。在Debt那本書中,他所比較的文化範圍實在超大,他提及地中海、印度、中國等大文明的5000年的歷史,也把一些比較人口較少的社會例子加進來。在這方面Graeber可能比較像啟蒙時代的哲學家;Keith Hart就把他拿來跟18世紀的思想家盧梭Rousseau作比較,認為他是繼承了”anthropology of inequality”的傳統。 (感謝Kerim在Savage Minds提了這個link – 如果你想看一些關於Debt內容的討論,推薦你先到 http://savageminds.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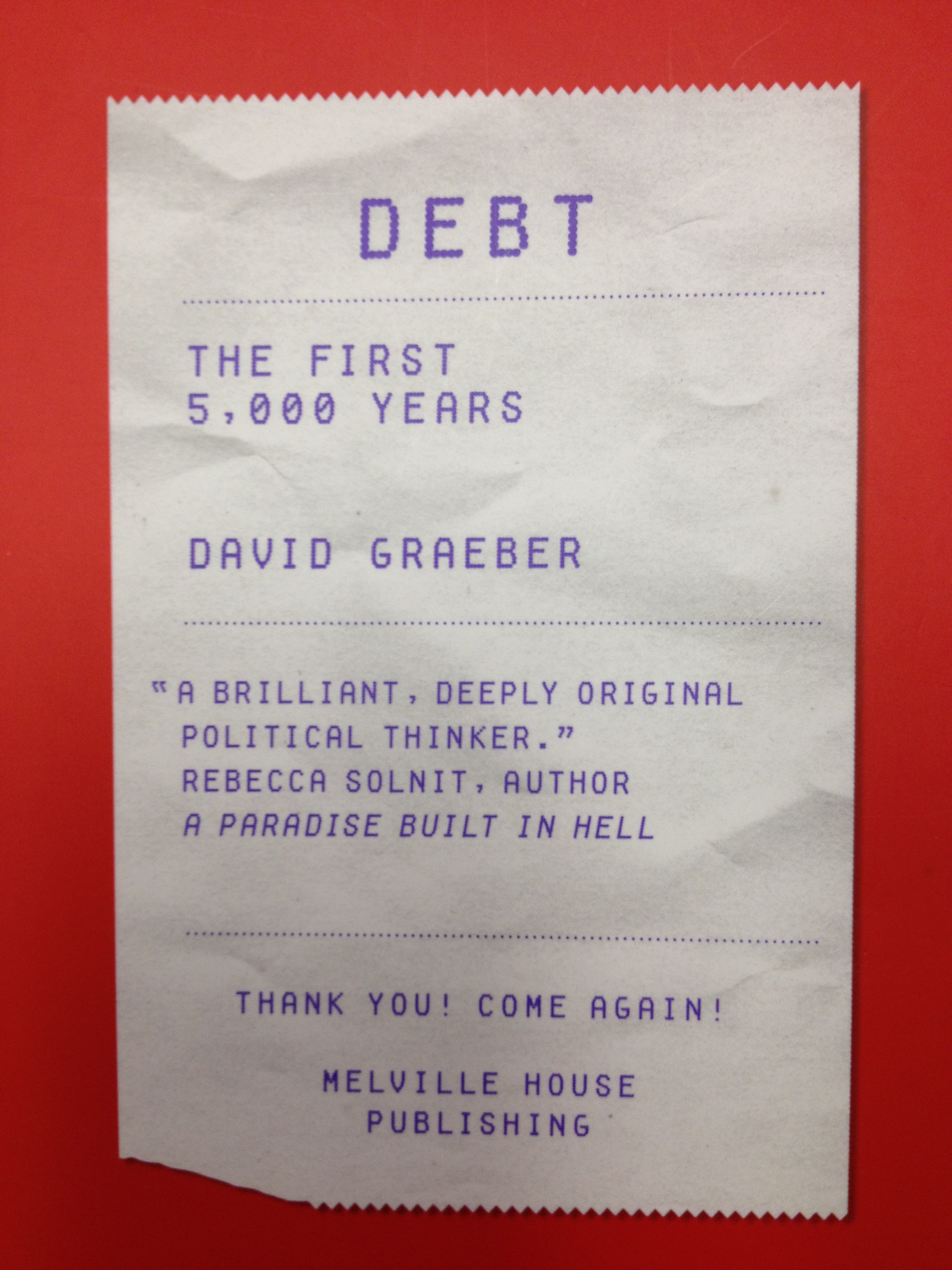
2. 選擇activists作為對話對象:
我們也可以把Graeber放在一個activist anthropology的傳統中討論。大部分的activist人類學者是為了他們的研究對象的基本人權而鬥爭 (像Terry Turner, Eric Michaels等人)。也有一些activist人類學者,他們的社運參與他們的研究沒有什麼明確的關係 (像Boas的反國族主義)。Graeber在馬達加斯加的田野經驗跟他的論點則有很明顯的關係;不過他參與的不是Malagasy人的運動,而是美國無政府主義的團體Direct Action Network,和OWS (他2009年的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一書很詳細的描述了他參與運動的經驗)。
很多人想到公共人類學者, 就會想到有管道與政府或大眾媒體接觸的學者。 Graeber最重要的對話對象其實是他的社運同志們。Graeber的文筆很吸引人;他用的理論專有名詞都有清楚的解釋,他的英文很口語式,很有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論點的邏輯寫的清清楚楚,因此說服力很強。重點是,他的目標是要討論怎麼解決實際的問題。他的文筆很特殊,可是他的閱讀性讓我連想到後結構主義的潮流之前,1970、80年代,女性主義、同志運動、黑人運動等,剛開始進入學術界的一些經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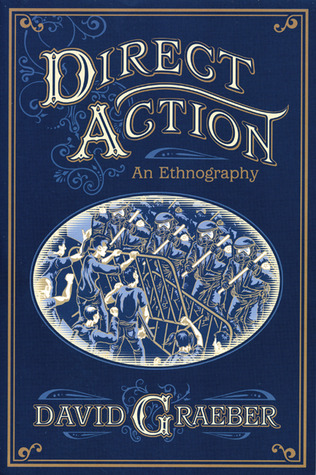
3. 把activist的問題當作人類學的問題
在今年的AAA會議,一個明顯的現象是越來越多人類學者開始研究金融制度,例如貸款、IMF、WTO等,以前比較屬於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議題。 Graeber參加的panel的演講者包括在2009寫了很精彩的Wall Street民族誌 Liquidated的Karen Ho。
可是Graeber 自己沒有跟Karen Ho一樣去做田野調查來探討那些金融等制度的實際作用。他常常問的不是「自己社會的民族誌怎麼可以讓我們了解我們自己的現況?」,而是「人類學的文化比較方法,能夠提供什麼新的策略去改變我們的世界?」在”Oppression”的一篇論文,他的起始點是:大部分的語言都會用很類似的比喻(如「被很重的東西壓下」)來描述壓迫的感覺。他說,大部分人類學者的研究對象是很窮的人,也是平常被國家系統邊緣化的人,可是人類學者平常不願意用「被壓迫」這個詞來描述他們的受訪者。他提到了人類學relativism的矛盾──因為人類學者很了解弱勢,將人斷定為弱勢,很容易變成得以控制他們的一種藉口;同時,為了進行人類學研究,需要定義一個文化的結構──也就是說,在民族誌實踐上,因為一個社群裡面所有人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必須選擇誰最有資格代表這個文化,平常也就是其領導人:
“[T]he entire project of cultural relativism depends on being able to identify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and thus certain individuals who, more than others, can legitimately speak for the Nuer as a whole.” (Possibilities, p.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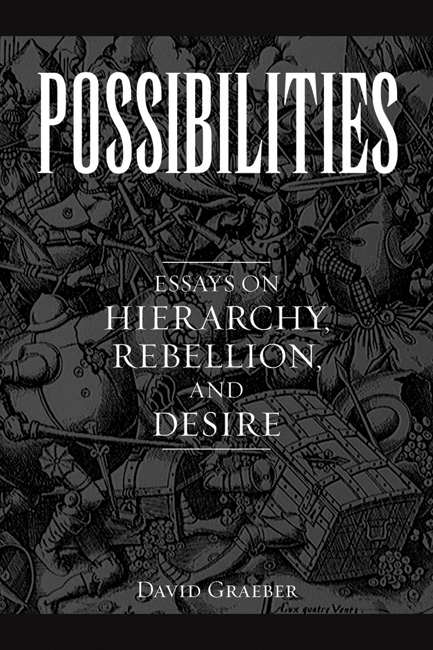
因此,我們被卡在三個不好的選擇:我們可以用自己的道德觀來判斷所有的人,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判斷來決定誰有權力代表每個文化,或者我們可以純粹拒絕做任何道德判斷。不過如果判斷者完全沒有權力控制被判斷的人,問題就會不見。 真正的問題在於一個全球的官僚系統,能用軍隊或經濟的暴力來執行它的判斷。因此,人類學應該問的問題是: 我們怎麼能夠消滅那個官僚/暴力系統?
“The real problem, it seems to me, is not with the mere fact of universalistic judgments, but with the existence of a global apparatus of bureaucratic control, backed up by a whole panoply of forms of physical and economic violence, that can enforce those judgments…If one accepts that some such apparatus is inevitable, then yes, we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agonize over the moral quandaries it creates. But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we can ask what it would take to eliminate such coercive structures entirely.”
後來,這篇論文透過Madagascar的民族誌(親屬系統,政治系統,殖民歷史, 等)說明了「被壓迫」的比喻在Malagasy的具體性。可惜的是,在結論上,Graeber只回到「不同文化的人應該看出彼此有共同問題,互相尊重,有平等的對話」這樣的論點而已,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可以消滅全球官僚系統的策略。不過, 在那樣的架構中,讀一篇關於完全陌生的文化的民族誌,與進入一個社運的alliance,跟不同運動的成員開始對話,慢慢把一個基本的consensus弄出來,其實有蠻類似的練習實踐的功能。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司黛蕊 公共人類學的可能:從David Graeber談起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3841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Hi, 你們的網站好有趣。我在Coursera上一堂和人類學有點關係的課,搜尋相關資訊,才找到你們的網站來。謝謝分享,人類學的視野真是廣呀!
謝謝讀者鼓勵,有空多來玩,我們每週一下午固定出刊
太好了!Teri把這本書帶出來了,我打算在課堂上好好找機會帶領學生讀這本書!
感謝分享!
Graeber 真是我心目中的另一超級英雄和偶像! (雖然我已經蒐集了很多這類人類)
前不久讀了幾頁 Marshall Sahlins寫的 What kinship is - and is not. 我還以為芝加哥大學
的人類學者都是寫這麼艱澀的文章, 心想千萬不要去那裏讀書, 不然可能會讀不畢業呢!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