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群體間的性別政治溝通+酷兒臺灣的跨境地緣政治困境
同婚通過距今已經有兩年了,似乎沒有人無照天理,天無照甲子的狀況發生。然而過去常有一種同志「西方進口說」,至今還是往往成為爭議的角力。
在當代台灣的價值衝突之中,性別政治的位置近年來變得相當凸顯。除了同性婚姻的合法運動之外,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跨文化以及跨地域的思考?小編特此精選彩虹芭樂給各位讀者,收錄了趙恩潔老師與劉文老師在中研院文哲所舉辦的一場「臺灣性別政治實踐之價值衝突」工作坊內容,分別就東南亞的前現代史中的性別實作,以及台灣在全球當代酷兒論述中的位置,一方面澄清亞洲酷兒本身的非線性史觀與多元傳統,亦思索酷兒理論在台灣在特殊的地緣政治與國族論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本工作坊由吳嘉苓主持與評論,趙恩潔與劉文發表,並由王鍾山博士記錄。
跨文化群體間的性別政治溝通
趙恩潔
首先,趙恩潔老師從這場工作坊當初的一份廣告文,同時也是許多報告書、許多新聞媒體的報導中會出現的一句指標性的陳述句:「聯合國開發計畫 (UNDP)2018年性別不平等指數,台灣性別平等表現為全球第9名,居亞洲之冠,甚至高過許多歐洲先進國家……」來開始她的論述。從這句常識性話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它背後的預設:它明顯預設了西方中心史觀,它用「甚至高過許多歐洲先進國家」一語,顯示出它預設了在全世界的文明中最進步、最值得學習效法的就是西方歐洲;其次,它也預設了單一進步線性史觀:它要所有其他文化都在同一條量尺上,去判斷誰在那一個刻度上。
在這個反思的引導下,趙老師展示了她本次講座的主要要點:藉由對東南亞的前現代15到18世紀性史的闡述,來提倡放棄單一「解放」計畫。正是因為單一線性史觀不利於跨族群或次文化群體的溝通。單一量尺不但限制我們的想像,也會低估傳統的多元性。因而藉此,希望我們能在台灣穿越時空、紀錄我們的古今多元,而不僅只局限在與當代國際對話。
在開始談論東南亞前現代性史時,趙老師首先談到政治溝通與權力結構的關係:在政治溝通之前,所有溝通都是在政治權力結構下的話語權裏。以15到18世紀的東南亞為例,不論是爪哇人、暹邏人、或是亞齊伊斯蘭王國,在受到西方殖民以及殖民現代性所伴隨的性別美學進入之前,女性都是以上空裝為其日常裝扮。對當時的歐洲殖民者而言,這些上空裝的文化被視之為野蠻;然而對比於此,到二十世紀末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影響的頭巾長袍的裝扮,又同樣被歐洲觀點視之為保守。這樣的西方中心史觀,可能造成西方以外的「她者」對自身過往的無知,未將自身文化傳統視為啟發的泉源,亦將想像力侷限在以西方為中心這個單一尺標之中。
事實上,若參考Anthony Reid與Michael Peletz等人的著作,可發現在15到18世紀的東南亞文化的女性權益,有非常多記載顯示她們普遍在婚前可以擁有multiple partner、要求男性做入珠手術、普遍的無貞操觀念且性生活豐富,甚至也有少數的記載有所謂的「破處」專家可供協助女性無痛經歷初次性交活動(Peletz 2006, Reid 1993)。更有甚者,印尼蘇拉威西島上的航海族群Bugis的創世神話中記載著許多我們如今以單一西方標準難以想像的傳統性別文化:夫憑妻而貴、從妻居、女子交換男子(表姊妹交換男人,讓王子嫁去支那,其後代則被吩咐回到Bugis等),以及其社會中所具有的五種完全被接受為正當的性別:男、女、雌雄同體的薩滿、calalai(像男人的女人)和calabai(像女人的男人)(Davies 2006, Gibson 2006 )。

在這個篤信伊斯蘭的社會,所呈現出的「亞洲價值」並不是單一的、異已的,而是性別多元的。真實的傳統往往是多元的、具號召力的;重新認識自身多元的傳統,比起被強加一個帝國主義的標準,就改革的方案而言會更具有說服力。如果我們對傳統有太過單一的想像,其實並不利於進行更多的溝通與對話。
趙老師進一步指出,就改革的角度而言,有時候如若以一種帝國主義的方式進行溝通,就會導致反彈。相反的,若能以「多元傳統」的方式來改革,或許更有機會造成深層的改革的變化趙老師舉了四個例子供我們反思。首先是90年代普世女權主義者針對非洲各地的女性割禮,以「男性對女性的酷刑」來錯誤地理解這一異文化現象,在情況較不嚴重的西非馬里,因為法國女權團體的介入,反而導致民間的反彈,將之視為政治的文化帝國主義入侵行為,使得原教旨派的瓦哈比伊斯蘭詮釋在當地取得更大的正當性(Gosselin 2000)。而在英管時期的埃及,受英國思想影響的女性主義之父阿敏也類似,將埃及落後的問題只歸到頭巾,導致原本並不很強制的頭巾習俗,在民眾反殖的反彈中得到固化(Ahmed 1993)。第三個例子是21世紀初期的埃及的同志運動,在原先政府態度相對寬鬆的情況下,因國內外同志人權團體的不斷的鼓吹解放、要求教化阿拉伯人,導致民眾與意見領袖的反彈,同志酒吧被突襲清掃,最後外國人和有錢保釋的都沒事,底層反而都被判刑(Massad 2002)。最後,印尼的伊斯蘭女性主義思潮,在完全迴避「女性主義」的現代思想甚至字眼的情況,透過脈絡式的解讀古蘭經原有的平權思想,擺脫「女性主義」在當地的負面符號意義的影響,很大程度改變了中產穆斯林的想法(Doorn-Harder 2006)。
回到台灣的例子,同志遊行的裸露爭議或許可藉此反思。就此問題至少有三種觀點可參考:1. 性與裸露既然同屬社會的禁忌,遊行就是為了挑戰禁忌故應該對之推行;2. 考慮到社會脈絡,則祼露對異性戀者也是禁忌,如此在遊行中的裸露則只是在複製刻板印象;3. 則是去提問,究竟裸露的社會文化意義為何,是否真的代表突破窠臼?由此去檢視將裸露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自由解放,可能在背後存在的一些圈套和陷阱,例如,可能具有一種資本主義健身房所塑造出的碩美男健身規訓文化,種種規訓與「窠臼」反而逼迫廣大「弱雞」男同志自我貶低。如此似乎又形成另一種男同志霸權,而這種男同志的存在只挑戰了異性戀常規,卻沒有挑戰資本主義、商品化與標準化身體的常規。
趙老師最後評論道,裸露從不等於解放,它必須在文化脈絡中被定義,並且在異時空獲得分殊的意義。雖然上述三個觀點都有其道理,也應由不同的人同時去實踐,但如果身體永遠帶有文化意涵,考慮文化脈絡的身體展演可能會是對自己更有利、更獲得尊嚴的協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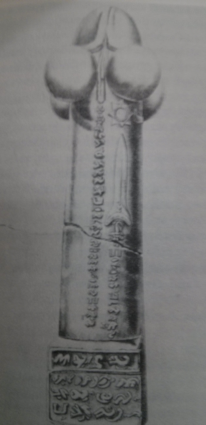
最後,趙老師提出,有時個人權利的最大化不一定有助於社會溝通,反而容易招致反彈。如果有多一些來自於在地文化的元素,這種方式未必是一種「委協」,而是以更長久的未來為著眼的改革策略。誠然,同志運動並不需要因為同婚運動的進展而去對政府或人民謝跪「龍恩」,但若轉換一種姿態,除了衝撞體制之外,同時也能以軟性訴求去面對社會大眾,進而得到社會普遍的「熊抱」。
「非西方」、「亞洲」或「中美冷戰結構」?
酷兒臺灣的跨境地緣政治困境
劉文
首先,劉文老師以英美知識生產角度來看,提問為何酷兒臺灣是重要?而關鍵的困境就在於該如何放置酷兒台灣?是該放在「非西方」?抑或是近期開展的所謂「跨國脈絡」?或是所謂的「酷兒亞洲」?抑或是許多台灣學者經常使用的「中美冷戰結構」?或許這些paradigm都有各自的問題,而該如何在地緣上去理解則是劉老師今天的主要問題。在最近的英美酷兒生產中能經常看到酷兒臺灣的「國族依附焦慮」。這個問題的起源可能還是要回到以北美為主的原本酷兒理論其中所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如此才使酷兒台灣要不斷去解決自身的國族焦慮。
在六O年代後因應同志運動的發展,美國的學術界開始以「正常化」的方式來進行同志研究,即以歷史的角度、本質化的方式來看待在美國的同性戀。然而在九O年代後,因為傅科將「性學」放置在西方特殊的精神科學歷史上,以反本質論的方式,標誌「同性戀」為現代性概念中的特殊範疇,而不是一個可以無限跨時空脈絡的身份。在這樣的觀點下,就容易產生一組二元對立,即傅科自己也強調的,西方的特殊性必須要有東方的參照,而中國的「性」就常被當作非西方的典範。然而,在許多北美的解釋下,許多社科研究中混搭各式酷兒主體,如“Queer Chinese,” “Chinese Culture,” “Tongzhi,” “Queer Asian,” “Asian American”,卻經常使用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特別是儒家社會的想像,來完全概括地對亞洲或東方的性進行解釋。
在這個二元對立下台灣的處境就非常尷尬,台灣到底是作為「儒家社會」(Confucian society)的一個例子,抑或是作為「亞洲特例」(Asian exception)?特別是在台灣同婚法案通過之後,後者作為所謂“Asian first”的台灣,在西方一種對亞洲的性的特定想像下形成了所謂的特例;而前者在大量的行為科學研究中可以看到,台灣經常被歸為亞洲四小龍的Chinese Confucian society的一員具有「性的後退」(sexual backward)的特徵。例如,到現在仍經常被引用的荷蘭心理學家Hofstede 的「文化維度理論」(1980),便將亞洲四小龍納入為同一性質文化,共同分享所謂的「儒家動能」(Confucian Dynamism),但文化心理學中卻很少討論文化背後的政治經濟動能,如七O年代的美援。在此觀點,台灣就作為性別運動發展相對進步的亞洲「儒家文化」國家。但其實根據一些實證研究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個觀點中的孔子其實是反同稻草人。例如2015年Amy Adamczyk和鄭雁馨的研究中,亞洲中的儒家國家(如日、韓、中、台、越)可能比歐洲、澳洲和北美來得反同,但並不比亞洲的非儒家國家(如泰國、印尼)來得更反同;反而個人的「反性工作」或「反離婚」的價值和反同的態度會較為相關。顯然,台灣在同性戀的態度上可能不那麼適合被廣泛地納入「儒家社會」的討論。

在這些比較研究之後,酷兒理論也有自己的反思。2000年開始,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CLAGS研討中提出的酷兒的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試圖要解救酷兒理論的西方中心。但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北美的學者(即便是有色人種)仍只能在酷兒跨國典範下將全球南方的「性」當作商品,當作北美酷兒理論有效或無效的驗證。因而,在這種跨國轉向下,Mikdashi與Puar二位學者在2016年指出北美酷兒理論反而作為不被地域限制、無限旅行的高端理論,而全球南方的經驗就只能作為性學研究(sexuality studies)的 “raw data”,供北美的理論使用,而不能真的挑戰北美的理論,更無法像文化人類學那樣直接由經驗形構出理論。而相應的實際問題,如在新自由主義的擴張下,學院為擴建其資金來源,在全球南方建立學術中心,酷兒理論的學院知識也以此輸入至全球南方,使全球南方學習酷兒或普世女性主義的價值語𢑥。而像Matt Brim在2020提出的Poor Queer Studies,則提出即使以跨國的典範也無法解決階級的問題。簡言之,跨國轉向無法完全解決「West vs. Rest」的知識生產問題,反而造成新型的全球不平等。
另外,在台灣,我們比較常遇到的則是以冷戰的模式去分析性別研究。而酷兒理論在近期的確有許多與區域研究結合,以達到去美帝國主義的問題。如史書美(2016)所言:冷戰的意識形態辯論使台灣成為critical theory可能發展的區域,但在急速吸收與引用美式理論之下,也逐漸失去它的激進性,使得文化馬克思主義較難對社會有實際影響。而原先因為冷戰而肇興的區域研究,也因著冷戰後的轉型,而落入商品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或者Rey Chow稱做的「輝煌的多元文化主義」(glorious multiculturalism)。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會將原先較基進的第三世界主義予以浪漫化,而在現代國家興起中藉由所謂本質化的「本土文化」來對國家想像,從而販賣自己國家的文化與知識。例如,中國2004年開始以孔子學院在全球部署,介入全世界高等教育對於亞洲研究內容,並以此重構「漢人國族文化傳統」。如此,對酷兒研究來說,在學院批判理論的「反帝」與「反資本」典範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常成為一種浪漫化的西方替代選擇:若想要理解一種超越西方的同志典範,似乎要去中國尋找。
以「同性戀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為例,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它是否可以作為旅行理論。在美國發生911之後,LGBTQ主體成為現代國家國族主義建立的新道德典範,亦即國家會包容一些白人、陽光、健康、中產的同志,並藉此合理化對於少數性倒退的種族(特別是穆斯林)的排除(Jasbir Puar, 2007)。這個理論原本在講的是非常美國的問題,但它也被挪用來解釋台灣的處境。在台灣同運與太陽花運動巧妙的時空連結,以及太陽花後的國族意識的興起,經常被英美與台灣的酷兒學者以「同性戀國族主義」予以批判,在同志與國族同時興起的脈絡,Gay racism排除了「中國大陸人」(Travis Kong, 2019)或「馬克思主義中國」(Petrus Liu, 2015)。因此,在這個批判下,「台灣同志國族」經常被綑綁為右傾的政治共同體 ,「中國」即成為這個共同體的「邪惡他者」。因此,這促使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思考,台灣是否應一直放在冷戰架構之中來討論。

將台灣放在中美冷戰架構下的理解有一些盲點:
1)似乎西方完全被本質化為一進步的、自由派的西方,然而台灣同志運動交手的跨國論述並非只有性自由主義論述,也有保守派的渲染。
2)在世界局勢轉變,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轉移之下,近年是中國經濟開放以來最嚴重的言論與社運打壓與境內外威權主義的高漲,而基本上並沒有在此架構中被好好討論,仍只以中國在2000年初NGO與社運仍勉強能生存的環境去想像它的激進性。
3)這個架構忽略了在華語語系社會中,中、港、台的運動者其實一直有非常強大的連結,特別是2000初開始的華人拉拉聯盟,這些社運者一直有很大的對話,但這個架構似乎完全抹滅了這種華語語系中同志運動與性別政治相互交錯的可能。
4)這個架構中的homonationalism理論反而會特例化種族少數的他者的特殊性,如在亞洲酷兒的中國人以及在美國脈絡的巴勒斯坦酷兒。
所以最後,台灣酷兒/酷兒台灣究竟該被放置何處?首先誠如剛才提到的「同性戀國族主義」現在其實大量的被引用到美國以外的地域與經驗,但經常被簡化成一種gay racism的解釋。因而,儘管它廣大的旅行,但它以北美為中心的論點,在簡化的解釋下似乎並沒有被好好的討論。第二,酷兒理論的壓縮旅行,以及與在地社會運動的脫離,例如在同婚的辯論之中,有些人主張婚姻只是增加台灣國族意識,對同志運動沒有好處等等,其實也是延續著北美酷兒的批判。第三,在英語語系的學術生產中,我們很難不去面對所謂的「中國因素」(China factor),而必需要去面對大家把台灣放在這樣的地緣脈絡中去解釋。如此,就有一些新的研究產生,如Chiang & Wong, 2017; Lee, 2017的「酷兒亞洲區域研究」(queer regionalism),便是脫離中美台架構,或西方與非西方(儒家)架構;Chiang & Wong, 2020的「華語語系酷兒研究」(Queer Sinophone),以去中國為權力中心的相互參照。唯有使酷兒理論與(超越冷戰)地緣政治結合,才能有新的、屬於真正酷兒台灣的理論出現。
(本文由王鍾山記錄於「臺灣性別政治實踐之價值衝突」工作坊,經兩位發表人修改後轉載。)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芭樂小編 跨文化群體間的性別政治溝通+酷兒臺灣的跨境地緣政治困境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74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