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反耶誕節
為何人們需要這個借來的節日
萬家香烤肉醬之於台灣的中秋節烤肉,正如肯德基之於日本的聖誕節炸雞,正如可口可樂之於聖誕老人的標準體態及儀容。
啥米?如果有人是頭一次聽見這件事,就彷彿會聽到玻璃心碎滿地。對聖誕老人懷有神聖之情的朋友,抱歉了。已經聽過這個故事的,沒關係,這個故事很快就要進入到其他故事。
聖誕老人這個人物,大致在十九世紀中葉才跟聖誕節扣連在一起,原型可能是外型清瘦、作風樂善好施的四世紀主教聖尼古拉斯——雖然有些民俗故事認為,這位主教也會派手下去「修理」不乖的小孩。聖尼古拉斯有時也會被描畫成一位穿著綠衣的精靈,因為某些地區的歐洲習俗相信綠色有禦寒的魔力。聖誕老人Santa Claus的稱號是來自荷蘭的Sinterklaas,而他的紅袍裝扮,最早雖然出於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插畫家Nast之筆,但他整個心寬體胖面色紅潤加紅衣白鬍的形象,之所以被穩定化且成為台灣人熟知的美國「經典」肖像,卻完全是因為可口可樂公司一直試圖在冬天抵擋冷飲滯銷,而在 1931年到1964年期間,成功端出插畫家Haddon Sundblom的作品,才有了這位全身穿著可口可樂招牌顏色的紅白胖聖誕老人。
但你不必覺得太幻滅,因為人類學家會告訴你,物有其自身的「社會生命」,就算是商品也一樣。到了六零年代或更早以前,紅白聖誕老人的形象已經獨立於可口可樂公司,而成為真實的文化肖像,在「全球的」大大小小的耶誕盛典中,尤其是美國兒童心目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某個特定日子要吃炸雞,過了四十年也會變成傳統。在日本排隊買炸雞排到崩潰的新聞似乎年年都有。而十二月的台灣商店,不管是全聯,頂好,家樂福,美聯社,或其他商店,也必定洋溢著各種耶誕裝飾與聖誕歌曲。就是在這樣的moment,我們一定會聽到有人說:「啊我們大部份人又不是基督徒,過什麼耶誕節,還不都是商業炒作!」
這讓我想到某年俄羅斯東正教的一位神職人員很不客氣地對媒體說萬聖節根本就是外來的玩意,俄羅斯人似乎很容易忘記自己的傳統,而只過借來的節日。其實,這段話把地名跟節日都換成台灣與聖誕節,也說得通。但問題是,過過「借來的節日」,真的那麼沒意義嗎?

乍看之下,這件事情問人類學家是最對的,因為人類學家在「異鄉」做田野或生活的時候,總是在過「借來的節日」。不過,這跟移植一個節日到另外一個文化地景,當然還是有許多不同。再者,說到底「所有節日都是借來的」,最後才變成自己的,但怎麼變成自己的,才是重點。只要想想歐洲的「異教徒拜樹,最後才變成聖誕樹」假說,也是在18、19世紀所流行的民俗文化復興,從世界宗教回歸本土民俗風情的脈絡才開始盛行的,而且盛行地頗不均勻,也會有反撲,比如李維史陀寫過關於聖誕老人在法國如何被「處決」的精彩片段。
那麼,到底耶誕節對不同人群的文化意義可能是什麼呢?
傻大姐我剛好在世界幾個不同國家的不同角落過過聖誕節,而且,剛剛好出生在講台語的虔誠基督徒家族,從小一路被迫過聖誕節,直到不想過為止。看來我真是適合回顧耶誕節之不同文化濃稠啊!
先說說小時候我最討厭與最喜歡聖誕節的事情,有的跟台灣特色很有關聯,有的則是跟大人特權與把小孩隔離開的大人世界有關。
可以吃的長輩圖&不必睡覺的好藉口
A。最討厭。一直彩排、練習各種分乘高中低音三部歌曲(很多走音)、戲劇、準備道具、美術製作。演來演去就是東方三智者要去朝拜聖嬰、聖母瑪莉亞怎麼生產的絕對不會演。有一年我拒絕飾演聖母瑪莉亞,自動自發發明一個新角色、演出那顆如GPS般神奇地引導東方三智者找到嬰兒耶穌所在之馬槽方位的「東方之星」(我真的有製作出一顆黃色大星星)。
B。最喜歡。摸彩抽獎。假的聖誕老人會大灑糖果,小朋友會尖叫搶破頭,熱鬧滾滾。(我小時候就知道真的聖誕老人也是假的,但在幻想中,稍微比真人演出的不假一點)
A。最討厭。「聖誕糕」,可能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明的傳統,一種台式的超甜綠豆糕之類的東西。但因為是免費的所以阿嬤都會拿幾塊回家吃,我則是會每年應景地吃上一口,然後吐舌頭覺得難吃。特色是其傳統包裝完全就是長輩圖的先鋒。這個跟台灣南部宮廟的平安糕超像的,兩者的系譜關係等你告訴我。
B。最喜歡。三更半夜「報佳音」:哇,晚上可以光明正大不睡覺,跟著大人趴趴走,在街頭上看著靜悄悄萬事萬物除了路燈之外都平息下來的世界,這對年幼的我來說真的太刺激了!


後來,我在天龍國上大學,對聖誕節沒什麼深刻印象,等到再次對聖誕節有感覺,已經是在美國讀博士班的時候了。事實上,到了在美國時,因為人在異鄉孤單寂寞覺得冷,竟然會特別想起小時候覺得超難吃的聖誕糕而流淚呢!
非裔遊民的聖誕節
2006, 2007, 2008連續三年我都在紐約與友人一起過聖誕。我對於長島上白人高級市郊住宅區的庭院上盡是爭奇鬥艷的聖誕裝飾與燈造馴鹿與氣球雪人等等印象很深刻。另外,如果說有農友與芭樂友也跟我一樣,很無法接受XX人造燈節或秋紅谷美學的話,其實紐約市洛克斐勒中心那一帶到了感恩節之後,醜陋的聖誕裝飾與人潮洶湧摩肩擦掌才能越過天使燈像走廊與雪花燈音樂秀,其實也高明不了多少。
除此之外,這段時間,我也曾在波士頓、紐約、華盛頓,都看到了不少的乞討者。路上攔截著旅車乞討,頸部掛著紙箱紙板上頭寫著”Merry Christmas”的,大多是非裔美國人。 有次剛好抵達華盛頓的某個晚上,十四街的教堂正在公園裡發放「愛心晚餐」。 只見一批又一批的黑人輕快地跑過道路,呼朋引伴,相偕拿免費食物。有人一次拿了兩盒,放回棲息處又再踅回來取。甚至有黑人對我說,嘿,那邊有free chicken ,妳也可以去拿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2008是美國次級房貸與高級金融商品大出錯,卻要納稅人買單、整件事情都被美其名地稱呼為金融「海嘯」或金融「危機」、彷彿都不是人為造成的、也不可預知的那一年。先別提哪些華爾街豺狼根本知道泡沫即將爆掉,連三巨頭的汽車工業都不斷要求政府支援。那一年看透的是,資本家錢財暢通時要求不要政府干預調節,破產時卻頻頻向政府身手要錢,去填那由多手轉賣轉移風險包裝成金融商品的泡沫所引發的經濟黑洞。
我在之後數年的美國聖誕節中,也看過中西部熱衷耶誕佈置的中產階級家庭如何收藏滿坑滿谷的聖誕節裝飾品,感恩節一過,家裡每個房間就全部換成不同的耶誕主題:聖誕襪、天使吹號角、麋鹿雪橇、空心禮物、各種布偶。當然,餐具、馬克杯、餐巾紙、桌巾、鹽巴胡椒鹽罐、甚至瓦斯爐蓋,也會全部換成雪人聖誕老人或相關主題的設計。


只是,我心中一直有那幅掛著紙牌說聖誕快樂的黑人流浪者,在危險的安全島上攔阻汽車的畫面。每次想到那幅畫面,在地球任何一個角落過耶誕節,我心中湧起的並不是對商業拜物主義的批判,而是對種族化盛典的批判。「全球」盛典所移植的,其實是白人的聖誕節。
美東的耶誕節政治正確
從中西部回到東部的自由主義同志婚姻最早合法地帶區,有時候在「自由圈」裡,那可真是必須要很政治正確地過生活。連在學校裡,大家都不太說Merry Christmas,深怕得罪了不過聖誕節的猶太人、無神主義者、或是對宗教感到OOXX的朋友。畢竟這些人確實都是在學院裡面、就統計而言、被「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ed)的群體(就是說這些人在總人口數中只佔A%,但在學院裡佔了B%,B>A)。Happy Hanukkah 說真的也不太安全,還是Happy Holidays最通用!
我曾在某個liberal college town的蕾絲邊酒吧大唱瑪麗亞凱莉的「聖誕節我要的只有你」,引來全場尖叫歡呼,但那根本是大夏天。也就只有在那樣安全的時節,我才可以不必害怕政治錯誤地祝福大家聖誕快樂,因為沒有人會認為我是認真的。
爪哇甘美朗伴奏耶穌受難記、聖誕節恐攻威脅與穆斯林護衛隊
後來,我因為田野的緣故,跑到地球的另外一邊——爪哇,去生活。我生活的地方是在一個中爪哇半山腰小山城中,姑且讓我稱呼它為猴糕城。雖然是個小城,但猴糕城是整個爪哇島上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方:中爪哇的穆斯林人口約佔95%,基督徒大部份都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因此城市可能會有10%~20%不等的基督徒人口。蛋糕城約有23%的城市居民是基督徒,而且越靠近市中心的鄰里社群(其實在當地是通稱為「村里」),基穆混居的特色就越強。每到了聖誕節,一個「模範」的基督徒市民,會在家裡開辦Open House,如同穆斯林也會在開齋節做類似的事情(但重點是會放在要求彼此寬恕),不只讓親友,也讓村里的人們上前來一同吃喝、祝賀。
至於在這個有很多教會、但過去三十年來也歷經了新一波的伊斯蘭復興的猴糕城中,聖誕慶祝也是形形色色的。比如靈恩派的教會基本上走的是一種有很多英文、除了男性牧師會穿著爪哇手工蠟染襯衫、會有一些看不出來到底是哪種文化的彩帶舞蹈表演(可能與印華靈恩領導階層有關),幾乎所有禮拜的語言都是印尼語,夾雜低爪哇語,不太有戲劇演出。老派的類似長老教會的爪哇基督長老教會GKJ,則在2009年耶誕慶祝時,上演「全爪哇語」耶穌受難記背十字架的戲碼,而飾演耶穌角色的這位演員(在圖中,是被羅馬士兵壓在地上,身穿白色頭髮黑長的那位),講了很多高爪哇語、但也跟著羅馬士兵隊伍在教堂裡穿梭遊行邊搞笑(我看得出神入迷),底下則有甘美朗伴奏,而觀眾幾乎清一色都是蠟染服裝。

聖誕節作為一種全球盛典,其實在每個在地都有很多「混搭」;混搭也不一定是全球與在地搭,也可能是過去與現代搭,這個在地與那個在地混搭,或是全部一起混搭。比如,在日惹市郊的一些原印度教神廟改成的聖堂中,也會有特殊的感念聖母瑪莉雅與耶穌的燭光。印尼基督徒集中的「外島」地區(=爪哇島以外的島,都被爪哇中心主義地稱為「外島」),島民的的聖誕節可是非常威的。安汶島上的慶祝會有很多傳統樂器,而安汶、摩鹿加、佛羅倫斯都有用船笛鳴響與教堂眾聲齊發來慶祝的方式。佛羅倫斯在是在平安夜時,各個角落都會有人使用自製竹炮來大鳴大放地慶祝耶誕節。萬那杜則是當年曾經想要加入尼德蘭共和國不想加入印尼共和國的一塊特別基督教化的地方,人們慶祝聖誕節的方式有嘉年華,但也有掃墓,也就是「聖誕節掃墓」。這可能是受到印尼穆斯林都在開齋節掃墓的影響。

耶誕節也可能令人覺得緊張。我有兩年的聖誕節都在中爪哇猴糕城度過,但每年也都注意印尼的消息。幾乎每年快到了聖誕節,報紙與電視新聞都會提醒,可能會有恐怖攻擊,警察必須加強戒備。聖誕夜的大慶祝,如果當年是在戶外舉行(曾經有幾年因為自殺炸彈客威脅頻繁,或一些本文難以詳述的政治因素,而改在戶內舉行,引起許多基督徒的不滿),那必定是在「建國五原則廣場」(就跟我們的中正路一樣,每個城市必有的一個廣場)。晚上開始的慶典,所有各種新教派別與教會都會暫時放下彼此的差異,輪番上陣演出歌舞或講道。當時猴糕城的基督徒市長(原本是副市長,因為穆斯林市長歸真了,自動替補)與戴頭巾的穆斯林副市長(已故市長的夫人,本身也是市議員,後來選上代理副市長),都有上台揭幕,表達政府全力支持聖誕節大型戶外活動的「政治舉動」。而聖誕節目會一路表演到凌晨四點,可說是爪哇人視不睡覺為一種高尚修煉美德的精神。最奇妙的是,整個廣場周邊,除了警察之外,還會有猴糕城的「穆斯林大學生聯盟」所組成的護衛隊,意思是要「保衛」這個聖誕慶典,不讓「可疑人士」進入。
也就是說,在全球聖誕節盛典觸及了我們與家庭親情、全球化與在地化(當作情人節或吃炸雞)、市場與物質主義等等層面之外,在很多地方,還有跨宗教關係必須獲得處理,而這可能是關乎人命的。
聖誕節的「反結構」
那麼,再回來說說台灣吧?既不是歐美的耶誕節,也不是穆斯林為多數的社會中的耶誕節。為什麼台灣需要這個顯然是借來的節日呢?這個問題,當然是以非基督徒本位的位置來發問的。這個問題,也未必是全球化或在地化,或全球在地化,就能完全解答的。因為不論怎麼攀鑿附會聖誕節,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種族與經濟結構,跨越了全球或在地。
先不說蔣宋美齡與她先生都是基督徒如何推動台灣慶祝耶誕節(?),還有美軍在台的文化遺緒,我認為聖誕節具有一些超越地方的「反結構」的特質,很能受到人們歡迎。「反結構」是人類學的老梗,如果不懂可以自己去查是什麼意思。可能所有涉及嘉年華與慶祝的節日,都可以被塑造為是一種「反結構」。問題只是在於,那個「結構」是什麼。是每天都要打卡上班嗎?是老闆很靠北但是你不得不忍氣吞聲嗎?是庸庸碌碌汲汲營營除了自己的生日(另一個現代個體的自我節日,取代了集體的「成年儀式」)和那幾個手指數得出來的節日與特休之外,都沒有休息的時間嗎?
可能都是。但也不只如此。我喜歡聖誕音樂,因為在這個場域中古典音樂不佔有最高最神聖的位置。古典樂不是聖誕音樂的主旋律。教堂聖詩也不一定可以跟輕快或悠然的爵士樂聖誕歌曲媲美。我喜歡爵士樂的聖誕音樂,因為裏頭有種黑人發展出來的各種音樂形式被白人偷走發揚光大成為全世界XX樂之後,好佳在還有爵士等不能整碗搶走的東西。當然主要原因是因為很好聽啦,很~放~鬆~

聖誕老人的角色也彷彿是一場「反結構」儀式中的人物倒反。Russell Belk在 Mater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Christmas (1993)一文中就提到,雖然耶老與耶穌兩人好像都可以帶來某種奇蹟,但是耶穌來自中東,耶老來自北極。耶穌年輕清瘦,聖誕老人又老又胖。耶穌很嚴肅,耶老很歡樂。耶穌穿得單薄簡約,耶誕老人穿馬靴皮毛,有時候還抽煙喝酒(十八禁)。耶穌叫人丟光財富與家庭來跟隨祂、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但聖誕老人卻給你所有想要的繽紛禮物。
禮物,就是這個禮物。聖誕節因為聖誕老人的關係,感覺有一大袋的禮物。而我認為,我們的生活,非常需要「禮物」。聖誕節彷彿等於禮物,而我們需要禮物。但是,到底什麼是「禮物」呢?
什麼是禮物?
牟斯的大作《禮物》,原文是Essai sur le don,也就是an essay on giving 或《論給予》。這篇論文影響層面廣大,但也時常被誤讀。
其實,認為有所謂概念上二元對立的原始禮物經濟vs. 現代商品經濟的不是Mauss,而是Malinowski。Mauss想要回應的不只是Malinowski,他更想要批判的是過於強調獨立個體之功利主義而犧牲社會互惠原則的政治哲學。他重申,沒有所謂免費的禮物這回事,不論是在原始社會、古代社會或現代社會,所有的「禮物」(給予),都是某種互惠系統之中的一環,不論那個系統是製造不平等或維持平等的系統。初步蘭島與周邊島嶼世界的項鍊與臂環之寶物循環,彷彿是一種純粹美學與道德的經濟,寶物本身即是重點,與寶物「順便」一起的是次要的、沒有那麼高貴的討價還價貿易。但對Mauss而言,寶物就是某種貨幣,差別只在於那不同於現代貨幣的形式,但仍然是一種社會信賴/信用建立模式,一種關於個人榮譽、權威地位、財富(honneur, autorité, richesse)也關於社會關係之維繫的「貨幣」。
簡而言之,「禮物」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免費的禮物是可能的嗎」?而是:「人在何種文化條件下,會認為『禮物』很高尚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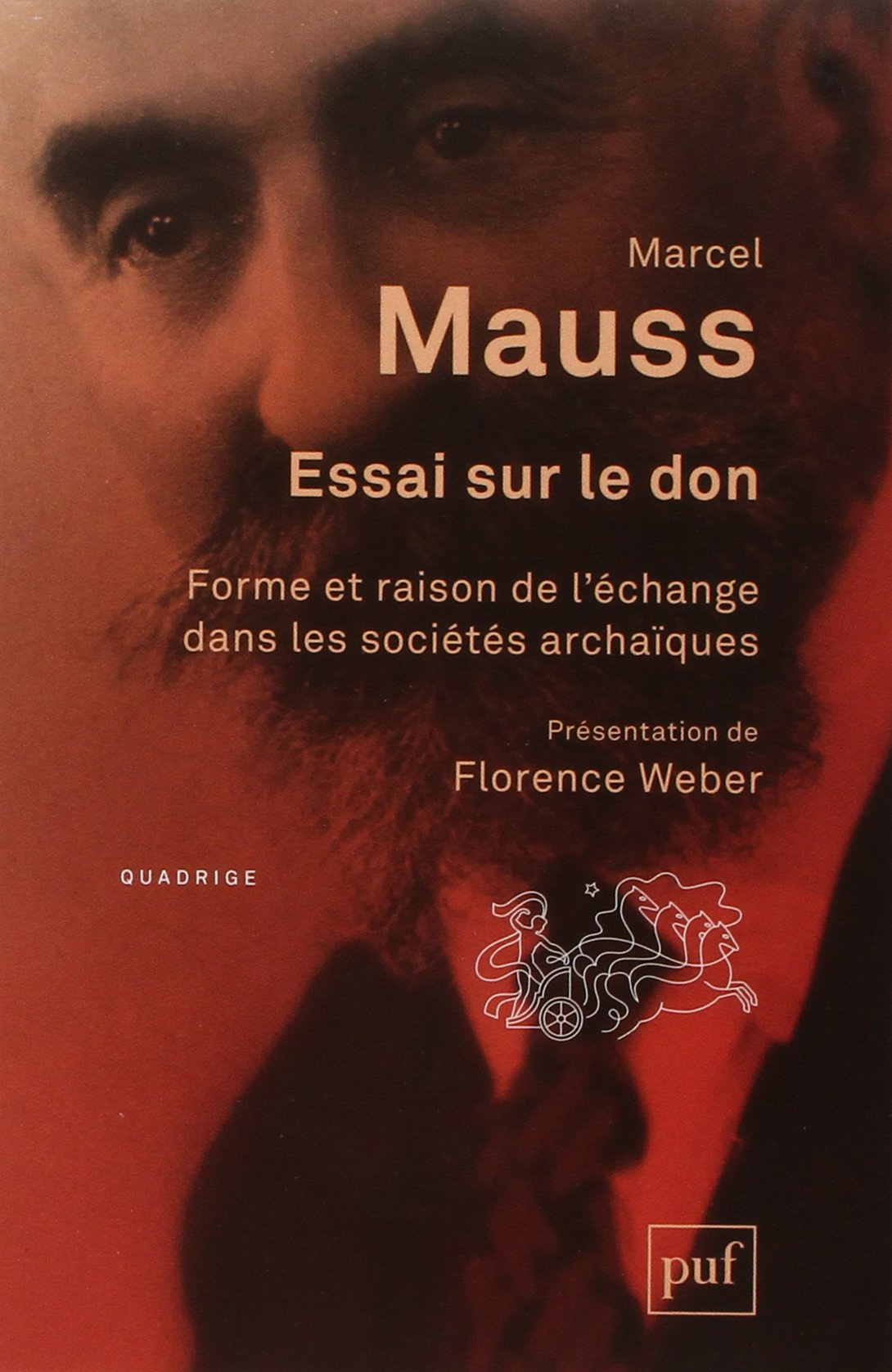
這整個免費的/自由的禮物觀念,完全是不自然的,是人類歷史的社會產物。並不是任何文化脈絡下,看似「不用回報」的禮物、以贈送或給予為主要目的的「給予」,都是那麼高尚而喜氣洋洋的。怎麼說呢?這在狩獵採集社會中最為明顯。一個人獵到了獵物,必須立刻把肉分享出去,因為下次不知道是誰會獵到,而這個人也必須等待下次別人分享給他。在這種生計模式中,拿到肉說「謝謝你」是很奇怪的,彷彿在說,我現在就肯認了你的美好的給予而不求回報的意圖,我現在就了卻照理說未來還很長久的互惠義務。給予者會這麼回應:我給你,你以後還要給我,我以後要還要再給你,所以你現在說謝謝是什麼意思?(打臉的意思)
也就是說,關於禮物的想法與「謝謝」作為一種口頭的回應,只有在依賴高度切割與分隔的社會關係中,才有意義。送禮本身的美德,有其政治經濟條件與其被當成空氣的背景。
用Mary Douglas的話來說,如果不是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關係高度分化世界中,「這整個免費的禮物觀念,完全是個大誤解。」
禮物作為一種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大確幸
正是由於處在高度切割與分隔的社會關係,人才會想要擁有「禮物」。因為沒有固定長久的互惠模式是可以依賴的,所以才會有「禮物」。否則在另一個時空中,根本不會有「禮物讓人興奮」這樣的事情。不求回報的禮物,呈現的是我們社會關係的稀薄,是一種要彌補稀薄的努力。而對充滿各種驚奇禮物的聖誕節的興奮,正是來自於其他時刻社會關係的疏離。
台灣既有的節慶從過去到未來,或許還可以增加或減少,但12月,不管曾有過什麼節日,後來也跟大部份按表操課的日子一樣,逐漸變成了班雅明所謂的現代進步史觀中「空洞、同質的時間」。不是農曆新年、端午或中秋,也不是掃墓或中元節。所以這個空洞同質時間填入什麼好?威權節日,沒什麼感覺。有堆疊而成的禮物,這個好像不錯。
天下當然要有「免費」的禮物,因為我們都想要在那空洞的現代時間裡頭,多填入一個幸福的日子。
這個節日,借來的沒關係,重點是要變成自己的。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左拉 反反耶誕節 :為何人們需要這個借來的節日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93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