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新竹縣市合併議題在去年12月18號四大公投結束之後突然增溫,身處熱灶的新竹市長林智堅說:站在國家戰略產業發展、大新竹民眾的期待,以及縣市民的福祉上,提出大新竹合併倡議。外界卻傳出「不可因人設事、倉促進行」聲音,對此,林智堅回答說:「這不是倉促,其實已經拖延了。大新竹創稅1920億占全國第五,超越2個直轄市,城市治理規劃早該超前部署。竹科會成功也是因為40年前政府關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預期半導體產業是影響全世界重要產業,先行超前部署,國家規劃上也該如此。」(2022/01/05 自由時報)。
縣市升格、新竹縣市合併升格,將所謂「國家規劃」的問題連上了「國家戰略產業發展」,讓人一下子感覺到事態緊急,彷彿準備戰爭般地開始了2022年。可是台灣不是才剛剛通過「全國國土計畫」嗎?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說明:「全國國土計畫」已於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係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前提下,就全國尺度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18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送內政部審議,內政部於109年均已審竣,並於法定期限(110年4月30日)前公告實施。是的,「全國國土計畫」和地方縣市升格不是同一種型態的規劃,但是才剛剛109年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顯然沒有預見「新竹作為國際級城市,民眾走出園區,不論是竹縣或竹市,皆呈現都會與鄉村混合城市,只要天冷、下雨就是塞車,這都是因為新竹縣市分治,導致建設、交通等無法串連」(林智堅語,2022/01/05 自由時報)。同樣是國家規劃,顯然「全國國土計畫」研擬了許多年並沒能先行超前部署,或是時勢快速變遷,又促成新的規劃。雖然以一般理解來定義「計畫」,也就是人們規劃出目標、找出並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和步驟。計畫必須提供一個對現在狀況的描述,通常是不完美的,因此需要計畫去改善以達到一個(較好的)未來。基本上,計畫的要素便包括了理性、知識、控制、進步等等,大致上和人們對於國家的期待和想像非常接近。我在20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計畫作為許諾」試圖指出:「計畫不僅將烏托邦、未來變成可以規劃的領域,而且計畫所揭櫫的未來讓人們有一個和整體發生連接的方式,國家擁有對未來的規劃能力對其作為整體意義(totality of meanings)系統是極其關鍵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此次的規劃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幾週前的芭樂文「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蔡侑霖、傅偉哲、鄧家洋、莊雅仲就這個議題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觀點(以下簡稱重組客庄升格),以下我以二個面向來對這篇文章予以後設閱讀,以及衍生當然作者群不必然同意我的閱讀和衍生。
首先,我們已經在與疫苗戰爭中度過了2021年。2022年才一開始,我們就要為了「國家戰略產業」的超前部署而必須打起精神。既然是國家的戰略策劃,自然連動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向的問題,這似乎證成了Foucault晚年所說,我們的現在是甚麼呢? (what our present is),是戰爭成為所有社會關係的一般模式。Foucault說,若老天再給他時間,他會在研究瘋狂、疾病、犯罪、性史等傳諸於世對現代性的考察之後,全力研究戰爭和權力的關係。事實上,在這樣所有社會關係似乎都必須為(想像中)的各種戰爭做準備的當代,或說戰爭已經不再只是發生於外頭而是佈滿於生活關係的當代,似乎人們不僅每天都在為生死存亡奮鬥,而且似乎只要是任何一個規劃被論述成生死存亡的奮鬥,我們便找不到理由去質疑作為戰爭的最佳行動體—國家—以戰爭為名所進行的戰略部署。所以Foucault在論述國家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時,以19世紀軍事戰略家 Carl von Clausewitz觀點來談當代權力和戰爭策略的關係決不是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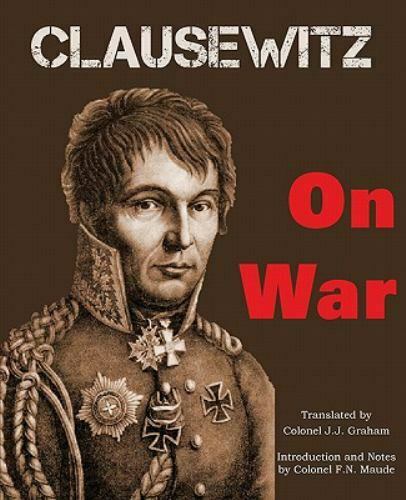
然而,我接觸到這個觀點卻是非常偶然,是我在New School博士班第一個學期必修Talal Asad的「當代人類學」的課。我原本以為會閱讀在1990年代當紅的人類學流派writing culture等等,沒想到syllabus一發下來,竟是要閱讀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On War)的一章。雖然我知道他那早已被引用到熟爛的名言,「戰爭只是政策以另一個方法的延續」 (war is nothing but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cy by other means),昭示新的戰爭觀與社會觀,但是Clausewitz和當代人類學有甚麼關係?! Talal Asad這位在1970年代反省人類學與殖民主義關係的先驅者要告訴我們甚麼樣的故事呢?可以這麼說,人們都認為現代社會相對於古代社會越來越少戰爭,戰爭也沒有那麼殘酷,至少沒有在攻城掠地之後大加屠殺人民。Clausewitz卻認為,當代國家之所以不大量殺人以及摧毀城市,不是出於文明及人道,而是出自於效率和經濟。經濟的考量高過於暴力的使用,進而促進理性的計算。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Foucault的原型。也就是說,當代權力的一個面向在於好好管理、維持、增進理性主體的生命,而這個權力的原型和戰爭同源地來自如何有效率地達到宰制。Clausewitz的現代戰爭觀驚人之處在於,相對於古代戰爭旨在攫取一個城市或領土,這些目標在現在已屬次要,摧毀敵人的意志力和反抗力才是首要目標。心理層面比起肉體層面的效果更為重要,因而使得戰爭中所有的事物都變得不確定,必須時時計畫、計算,這世界時時、處處佈滿危險,充滿競爭。在這個戰爭話語深深滲透當代社會的趨勢下,我們似乎找不到理由去反對為什麼一個地方的規劃會成為國家戰略,或是質疑為什麼國際(經濟)戰爭必須要以地方升格來因應?畢竟在國際各種戰爭進行之下,沒有一個單位(個人、團體,甚至地方) 具有內在不同的性質得以免於成為戰略的佈局。
但是真的只有如此嗎?至少從Foucault的觀點來看是似乎如此的,或許這也是他的作品為什麼很難給人有所出路和希望的感覺。
Gilles Deleuze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中有一個章節論到戰爭機器(war machine)時,就直接批評Foucault上述關於戰爭和現代國家治理的觀點。Deleuze雖然同意Foucault論述的國家權力與戰爭的策略高度合謀(他也同樣引用了Clausewitz),甚至連反抗的形成與想像也和脫不了戰爭用語;但是Deleuze認為,國家只是挪用了(appropriate)戰爭形式來完成了政治主權的基礎,正是因為挪用而開啟了鬥爭的可能,因為那正是戰爭的本質,戰爭不可能化約成為國家獨佔的元素。人們可以在國家機器之外,在其法則之外,找到另一種戰爭型式,在那裡是喧鬧對抗主權(a furor against sovereignty)、活力對抗收縮力( a celerity against gravity)、機器對抗機制(a machine against the apparatus)。也就是說,當社會的資源都像是被吸納收縮成為戰爭的一環時,沉重而生死攸關,Deleuze則強調不被戰爭吸力收縮的活力,靈活創發的機器、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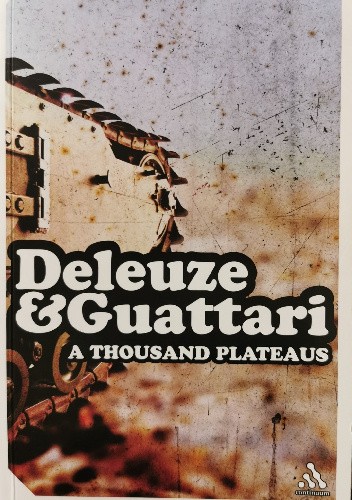
於是,「重組客庄升格」一文提到的基層與多重民主的實作──「隨著竹科的發展,在地事實上早已長出異質網絡。回應因地制宜的情境,從二重埔與三重在民主化之後回應公共性的親緣、地緣及地方政治網絡的展現,以及在竹南/頭份基層政治中萌芽的另類價值。」──拉長時間來看,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在不同階段持續宣稱治理效率的戰爭思維下,國家所欲吸納的各種元素的逃脫(或是剩餘)以及轉化。我不是說「重組客庄升格」所描述的這些異質元素具有Deleuze所說對抗機制的機器或行動,這些異質元素和國家之間的張力仍必須持續推敲。我意在說明,當國家規劃大量運用後勤網路、戰略佈局、超前(或跟上)部署、軍事策略、生存政治等用語時,我們應該更加探討、記錄、擴展已知或未知的活力與創意。這不是寄望鄉愁於地方,也不是從邊緣或偏鄉反思、反抗中心或都市,而是它原本就內生於國家機器之中,是由此中的論述塑造而成。我們總是能夠在機制之內找到另類抗爭可能。
第二,「重組客庄升格」一文對我而言最有趣的觀察是:「20多年下來,轉化後的社會空間仍以不同形式維繫著社會網絡與生活。其中之一,是伯公廟祭祀網絡的重組,….附近的科技大廠,多以集福宮為信仰中心。每年農曆七月是廟裡最為繁忙的時刻,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許多「○○○科技公司敬獻」的花籃。集福宮的成立不僅是國家透過徵收方式,使科技廠獲得土地;科技公司也藉由「奉獻」轉化自己,重新建立與地方的「聯結」。」這一段累積了長期的田野觀察資料,可說是一個對社會科學長久以來非常經典議題的記錄與描寫,那就是發生在許多時代許多地區的新興資本和原有的道德秩序的遭遇和競爭,它們的碰撞產生非常多的面貌。就以我接觸過的非洲發展主義的研究文獻而言,大致都出現將一個社會區分出二種秩序與資本的論述,一個是老舊、部落小團體式、甚至帶有令人畏懼的巫術力量;另一個是自由流通、與國際接軌、帶來光明進步的新興發展資本。原來的地方團體秩序、道德經濟因為只能流通於具有邊界的該團體,而且通常只掌握在當地有力的頭人手上,當然不利於現代資本講求的快速流通,有點像是「重組客庄升格」一文所描述「鄉鎮地方自治常被認為等於「派系統治、黑金溫床」,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及財政不當支出」。對於講究資本無國界的當代經濟,那些阻礙資本流通的障礙,無論它們是國界、道德邊界、甚至是人與非人的邊界都是必須被打通的關卡。而在後進國家的發展清除障礙的路徑中,還有甚麼比的上「西裝革履、客觀理性的資本家與國家官僚進入地方掃平貪腐、侍從、巫術、落後的小團體」更為讓眾人信服接受的進步論述呢?
當人們相信資本累積與分配的力量從地方頭人轉移到國家與資本家手上是現代進步不可逆轉時,也就是人們相信我們已從頭人與神明的庇護者變成國家與社會的持份者。「但是, 民主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好生活願景呢?」(「重組客庄升格」語)。新竹科技公司採取與地方既存的宮廟和諧相處的方式,一方面督促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地了解台灣地方社會政治、宗教的性質。另一方面,「如今親緣與地緣關係,乃至於地方政治運作,已難以是一個封閉的,只服務自己人與利益交換的紐帶,而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公共性。」(「重組客庄升格」語)地方社會真的並非現代論述所言沒有轉變,它的活力與創意反而常常超過國家規劃的設定。如此一來,它會是某種另類戰爭機器的蘊育地嗎?我期待著。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容邵武 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11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芭樂人類學不是要推動人類學公共化?
用期刊論文的語言來寫芭樂文章,民眾如何看得明白?我自己也看不太入眼….太難讀了
回到芭樂初始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3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