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教科書探尋「語言人類學」的軌跡
在大學的校園中常會看到大一、大二學生抱著厚重的中文或英文教科書的身影,而厚重的教科書也往往成為畢業學生回憶大學上課經驗的一環,不過修完課之後,要如何處理一本本厚重的教科書常是惱人的問題。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人類學的導論課程中常會以一本通論性質的教科書做為介紹人類學的入門書。使用通論性質的教科書風氣,從理學院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微積分、心理學課程到社會科學院的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到醫學院、工學院的基礎入門課程,幾乎每門課都會使用至少一本(或一本以上)介紹性質的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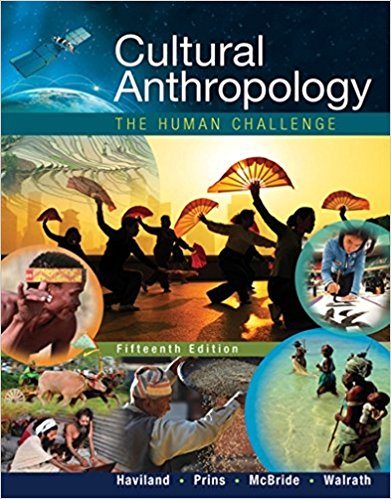
「教科書」(textbook或coursebook)成為教育機構的專業知識的書寫文類之一,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歐洲教育制度的興起,當時為了因應教育機構的需求而發展出教科書的書寫模式,而目前在臺灣乃至歐美各地的大學所盛行的通論性質的大學教科書則發跡於1960-70年代歐美大學的大學部教育體制的改革之時,需設計出專為剛入門的大學生而設計的基礎課程教科書,從此之後,也孕育了以大學教科書為主的全球出版市場,以及二手教科書的回收和銷售市場。買教科書常是剛入學學生的經濟負擔,一本精裝大學教科書往往定價在50美元以上,有些甚至超過100美元。亞馬遜公司於2007年推出Kindle電子書服務,以及2010年推出蘋果Ipad之後,以短期租用性質的電子版教科書也陸續在全球各地的大學校園中可見到。
大學教科書不同於高中、國中、國小的標準化教科書,如:教育部會針對普通高中的必修和選修的歷史課程訂出課程綱要,明訂學習目標和核心能力,在國內的不同出版社會根據教育部的課程綱要設計出不同版本的臺灣史、中國史、外國史的教科書,提供給各校的各科課程委員會來選擇使用,這也形成了不同學校可能採用不同版本的教科書,甚至同校不同年級選用不同版本的教科書的亂象。大學的導論課程教科書是由授課老師自行決定的,目前可適用於人類學大一導論課程的英文教科書就至少有7本以上,為了能納入受全球化影響而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人類學研究新成果,並因應龐大的大學教科書的市場需求,出版社皆會請作者定期更新教科書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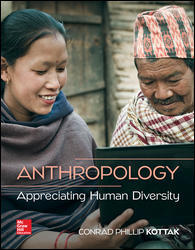
例如:由密西根大學Conrad Kottak人類學退休教授所撰寫的《人類學:欣賞人類多樣性》(Anthropology: Appreciating Human Diversity)一書,至2017年為止已出版了17版,其它出版社所出版的人類學導論教科書也都出版了10版以上。不同出版社為了能在人類學教科書市場做出一些差異化,會在書的副標題(如:《文化人類學:人類的挑戰》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Human Challenge、《人類性:文化人類學導論》Humanity: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書的章節安排、民族誌研究的選用上做出不同的設計與安排,並搭配1-2本當代民族誌做為輔助教材。人類學導論的教科書是欲提供剛接觸人類學知識的學生有一全貌性的瞭解,不過,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人類學教科書中,針對人類學知識史的背景、理論脈絡、基本概念、田野調查方法、研究分析方法的介紹則常是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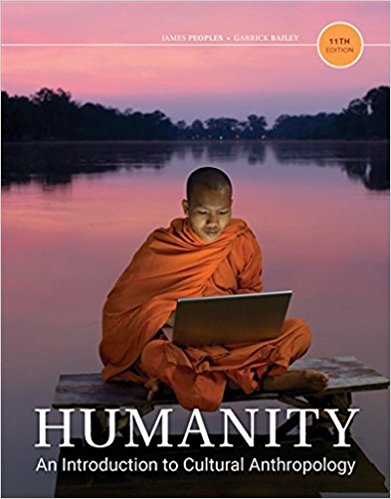
接下來,我將以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為主題,從1993年問世的第一本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談起,簡要地說明不同作者在更新語言人類學教科書的版本時,會修正哪些舊版本的說法,或加入哪些新議題。也嘗試說明1993年和2017年出版的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的基本差異之處,以探尋語言人類學自1960年代「溝通民族誌」(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1980年代的「語言社會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和「展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1990年代的「語言意識型態」(language ideology)和「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的研究取向興起之後,發展出不同於1960年代以前的語言人類學的歷史背景,此發展也與當代語言學的研究趨勢有其不同的關注焦點。
1980年代起,在強調以人類學四大分支為發展重點的許多美國大學的人類學系裡,語言人類學逐漸受到重視,語言人類學導論課程不僅成為人類學系大學部的必修課之外,1990年代起,這門課也成為非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的選修課。許多學校也開始提供語言人類學博士學位。根據語言人類學網站在2009年的統計資料,美國的大學提供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的博士學位的人類學系有64所,而沒有人類學研究所課程的學校,也有18所的語言學系在語言學的學科規劃中提供人類語言學(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的博士學位。
由麻州大學的Zdenek Salzmann教授所出版的《語言、文化與社會:語言人類學導論》(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1993)一書,是最早出版適合給大一大二學生使用的語言人類學教科書,這本書在2007年出版了第四版,隨後,在2011年由另外兩位人類學家James Stanlaw和Nobuko Adachi出版了第五版,第六版開始恢復由三人合寫,今年該書已出版到第7版。在這本書問世之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語言人類學家Alessandro Duranti在1997年出版了適合給大三大四學生使用的《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教科書,在書的謝詞中特別提起將這本書獻給他的學生。Salzmann和Duranti對於教科書的書寫方式有其相似之處,兩位人類學家皆強調在介紹傳統語言學的五大分支(音韻學、語意學、句法學、語源學、語用學)之前,由「語言和文化」的角度介紹語言人類學學科的特點與理論關注方向,並清楚地說明語言人類學與語言學的基本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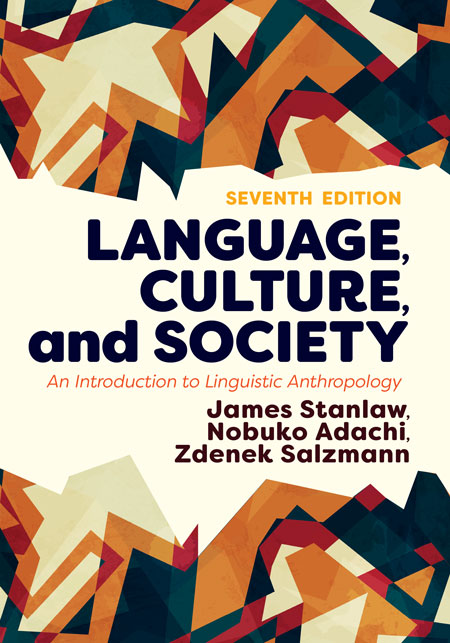
第七版,2017
Salzmann在書的第一版中介紹人類學、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三者間的關係,強調「語言人類學家不像語言學家,他們從不將語言區隔於社會生活之外,而是強調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社會結構間互為影響的關係。針對語言的技術性分析的目的是可以透過語言資料連結到更大的人類學議題… 因此,語言和社會群體的關係不能看成是理所當然的,而這樣的關係反而是需要透過民族誌研究方法加以探究的問題」(Salzmann 1993:4,劉子愷譯)。Duranti在1997年的書中,一開始即界定何謂語言人類學,他提及書中的部分內容與194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初期的「民族語言學」(ethnolinguistics)傳統,或是之後的「人類語言學」的學術討論有些雷同,然而,他對語言人類學的看法,則是沿用1960年代人類學家Dell Hymes的看法,由人類學的脈絡來研究語言和談話,意即:語言是一項文化資源,談話是一種文化實踐(language as a cultural resource and speaking as a cultural practice)(Duranti 1997:2)。
雖然,Salzmann和Duranti對於語言人類學的典範建立,皆追溯至Franz Boas於20世紀初期在美國印地安原住民所進行的研究,特別是《美國印地安語言手冊》(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1911)一書,認為掌握當地語言是能否正確地獲得和瞭解當地文化知識不可缺少的一環 [註]。不過,兩人對於語言人類學在人類學四大分支中的地位能確立下來,則認為是承襲自Dell Hymes的溝通民族誌研究取向的建立。這樣的說法,成為當代人類學家對於語言人類學知識史的普遍看法,在語言人類學的不同教科書中,也可見到作者由這樣的觀點所進行的延伸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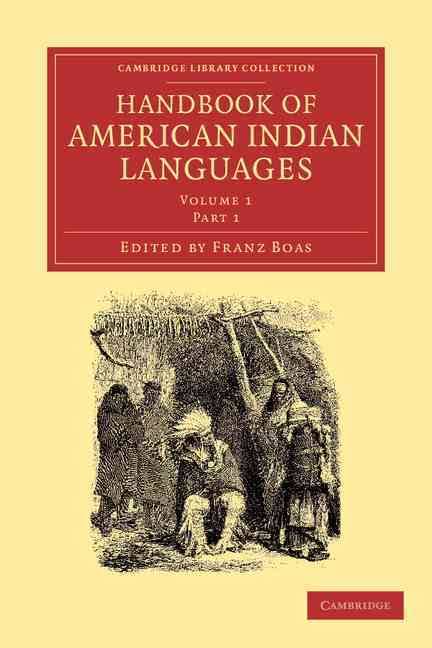
原來於1911年出版
語言人類學家Laura A. Ahearn在2017年所出版的《生活中的語言:語言人類學導論》(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的第二版教科書中,引用了三個語言人類學民族誌的例子來說明,為何語言人類學家看待語言本身即是具有社會性的,語言並不單單是我們從事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其中的一個例子是:
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位在澳洲北方的一個國家)有個名為加盆(Gapun)的小村落,1987年時,有些加盆村民是僅存仍會說一種名為Taiap語的人,當時還有89民村民會講這種語言。當時,村內的成人幾乎都能懂Taiap與Tok Pisin(巴布亞紐幾內亞三種官方語言之一)兩種語言,孩童在他們年幼時也仍有機會大量接觸到這兩種語言。但是截至1987年,當時村裡十歲以下的孩子已經不會說Taiap語,而八歲以下的孩童甚至對被動接受的Taiap語言知識沒有很好的掌握。一般認定語言如何消失、為何消失的理論似乎無法解釋Taiap語。像是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經濟和物質因素,對於地處偏僻的加盆村而言,這些因素還不能充分地解釋Taiap語的消逝。那麼Taiap語為什麼會逐漸消失呢?跟據語言人類學家Don Kulick的研究,加盆村人認為Taiap語會消失會發生都是因為村子裡的孩子(特別是牙牙學語的小孩)行為的緣故。Kulick記載道:「我問村民,村裡的孩子為什麼不肯說本地語,有個村人對我說:『我們什麼也沒做,我們一直想要讓他們開口講,但他們就不肯… 這些小孩個個都很bikhed(自大又固執)』」(Ahearn 2017:4-5。吳碩禹老師翻譯)

語言人類學家對於社會脈絡與語言共存共生的關注方向也區隔了與語言學家對於語言的研究取徑上的差異。Laura Ahearn在《生活中的語言:語言人類學導論》教科書中,以打毛線的例子來說明語法只是語言的社會性生活的諸多面向之一而已。
假設Noam Chomsky是一位打毛線專家,而不是一名語言學家,他唯一可能感到興趣的是編織針法的抽象規則(用大寫的字母寫出來,就如他處理「語言」的方式),像是:「第20排:上針1針、(下針1針、上針1針)重複11(或13至15)次…等等」。Chomsky身為毛線專家,認定人的大腦中存在一組「編織習得裝置」(KAD (Knitting Acquisition Device), 而非「語言習得裝置」LAD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語言人類學家推翻喬姆斯基學派和索緒爾學派的二分法(「語言」(langue)/「談話」(parole)),語言人類學家採用不同的取徑。有些語言人類學家認為「語言」/「談話」這樣的分野根本不存在。另有一些語言人類學者則擴大了「語言」的定義,將其包括在特定社會情境中有能力很熟練地、適切地使用語言的能力。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語言與談話同等重要。然而,所有的語言人類家同意的是,要「懂」一個語言絕非僅僅只是認識該語言的一套抽象語法規則而已。(Ahearn 2017:9-10,吳碩禹老師翻譯)
雖然,當代語言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在分析語言關注方向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在語言概念、分析方法、理論知識的背景仍有許多互為影響之處,特別是近年來語言人類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對於多語現象和跨語實踐的討論,在理論和分析架構上皆有所相似之處。也使得想採用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取徑,需要對語言學的五大分支有一些基礎認識,才能有辦法深入瞭解語言人類學的理論和分析架構。因此,對於傳統語言學的介紹也就成為當代語言人類學教科書內容不可或缺的一環。
自《語言、文化與社會:語言人類學導論》第一版於1993年問世後,2017年所出版的第七版已與第一版已有許多更新之處。這本教科書在24年間所更新的內容,所看到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全球化的跨國遷徙所帶來的「語言遷徙」(linguistic diasporas)、「語言接觸」、「語言意識形態」轉變的討論,第二是對於語言與性/別(sex and gender)的討論,能更深入地探討雙性別、跨性別、同志文化的內涵,第三是對於網路、手機和社群媒體所帶來的語言使用和身份認同關係的討論。譬如:過去語言人類學家探討語言和性別的議題,常會沿襲社會語言學家對於主流社會對於女性角色和談話方式的刻板印象的研究,像是社會語言學家Mary Bucholtz重新出版Robin Lakoff於1973年所出版的《語言與女人的地位》(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一書,將書的原來封面中貼住女人嘴巴的膠帶移除,代表女人意識的解放。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脈絡的轉變,也改變了語言人類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逐漸推翻以往以「嘮叨」和女性語言連在一起的討論,因為,嘮叨行為也出現在男性之中,而有些研究也提出女性之所以被認為是愛於嘮叨的,不是因為女人說得比男人多,而是社會期許的完美形象女性是安靜不語的,是這樣的語言意識型態所造成的影響延伸。

《語言、文化與社會:語言人類學導論》第七版中更進一步引用了文化人類學家Tom Boellstorff在《同志群島》(The Gay Archipelago)一書中討論生活於以回教為主的印尼社會的同志文化與同志語言Bahasa Binan,該語言不僅是凝聚印尼同志認同的重要力量,該語言也成為一種秘密語言,印尼社會對於同志行為是相對保守的國度,使用Bahasa Binan的談話方式是印尼男同志彼此間可以相對自由地使用該語言表達情慾和性慾,而不用擔心於別人會聽懂交談的內容。從教科書在不同版本的更新的例子,可以投射出語言人類學在不同時期對於社會和文化議題的研究取向上的轉變。
對於高年級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而設計的語言人類學課程,往往會以理論和分析概念的深入討論為主,因應這樣的需求,語言人類學家也出版了幾本以收集經典且必讀的文章,而編輯而成的參考書,目前廣為使用的有兩本:喬治亞大學Ben G. Blount教授所編的《語言、社會與文化:文章合輯》(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 Book of Readings, 1995)、Alessandro Duranti教授所編的《語言人類學讀本》(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 Reader, 2009)。另外,為了能更貼近最新研究的方向,也會請語言人類學家針對不同主題撰寫專文而編輯成書,目前也有兩本這類的書,《語言人類學的伴讀讀物》(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04),以及雪梨大學N. J. Enfield教授、耶魯大學Paul Kockelman教授、多倫多大學Jack Sidnell教授所合編的《劍橋語言人類學手冊》(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14)。不論是經典文章的參考書或專文合輯的書皆是語言人類學的進階課程的重要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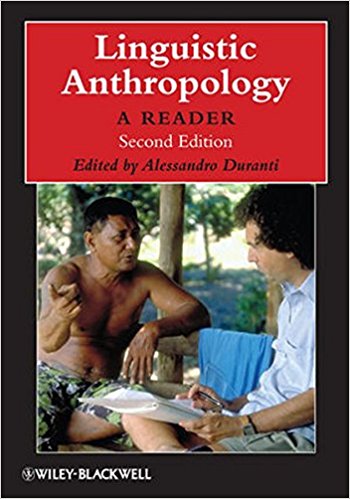
Alessandro Duranti教授大概是美國語言人類學界最為積極於編輯適合於美國的大學課堂使用的教科書的人,《語言人類學讀本》這本參考書從談話社區(speech community)、語言的展演、語言社會化、書寫實踐、語言和權力的分類範疇,收錄這些範疇內經典且高度被引用的文章,提供學生能對經典文章能有深入閱讀的機會。至於哪些文章是該被收錄的經典文章一直是值得被討論的。不過這類的參考書,往往不適合於臺灣的課堂中使用,不僅是文章中談及的語言人類學的經典案例,往往不是文化人類學課堂中會討論過的,有些主題(美國種族主義、非洲裔美國人美語、白人至上)對沒有在歐美生活經驗的臺灣學生而言,是難有深刻的體會的。另外,對於剛入門的學生或是對於語言人類學的理論知識史還不甚清楚的學生,如何連結民族誌的案例與語言人類學理論的知識「系譜關係」會是相當挑戰的。唯有運用臺灣學生為較為熟悉的臺灣或亞洲其它國家的語言資料或民族誌案例,才有可能讓剛入門的臺灣學生有機會與「系譜關係」搭上線。
2014年出版的《劍橋語言人類學手冊》是一種較為創新的教科書書寫方式。三位編輯者中有一位是語言學家,兩位是語言人類家,也因為跨學科的結合,讓這本書展現了不同於過去的入門式的教科書寫法,或是經典文章合輯的參考書類別,這本書在導論之外,由語言的「系統和功能」(System and Function)、「過程與形成」(Process and Formation)、「互動和互為主體性」(Interac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三大部分組成,拋棄以學科或子學門的項目為出發,由語言學家和語言人類學家針對不同主題而撰寫的專文。這樣的跨學科書寫,讓讀者能在同一本書中,看到異質的研究取徑,以及以對話為出發的學術寫作。這對於習慣浸淫於既有巢臼中思考的人會是一種啟發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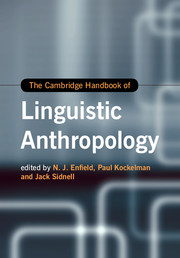
不論是哪一類別的教科書,總是有些沒有或無法被納入教科書的想法或聲音,若仔細檢閱提供給大一大二使用的大學教科書,使用的案例往往是長期被討論或甚至是過時的理論,或是長期被肯定的案例,對於創新的想法或是仍未有明確研究成果的方向,往往會被教科書的作者所捨棄,或是以簡短的句子做介紹。在《劍橋語言人類學手冊》一書中針對「互動和互為主體性」(Interac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主題的討論,包含的篇章除了「跨文化溝通」之外,也包括:「意圖與語言」(intentionality and language)、「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互動中的行動的本體論」(the ontology of action, in interaction)等。這類的概念往往會被認為是不適合放入語言人類學的教科書。
臺灣的語言人類學課堂會需要什麼樣的教科書?是老調重談的理論架構?是有趣的而能打動人心的案例?是能跨及世界各地的語言民族誌研究?是能引發熱烈討論的語言和文化的議題?等等。這大概是每位從事教學工作的人,或是坐在導論課程的學生們心中會浮現的可能問題。在結束我從教科書回看語言人類學的軌跡的芭樂文,想透過此機會介紹由東華大學傅可恩(Kerim Friedman)老師、中原大學吳碩禹老師、東海大學蕭季樺老師和我所共同參與進行的一項語言人類學教科書的翻譯計畫,我們正在進行《生活中的語言:語言人類學導論》(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二版的翻譯工作,Laura Ahearn教授長期於尼泊爾進行書寫和情書的語言人類學研究,也因為她對於書寫文化的研究興趣,《生活中的語言:語言人類學導論》一書嘗試由入門學生的角度來談語言人類學,第一章對於語言人類學的介紹不同於其它的語言人類學教科書的書寫方式,她由民族誌的案例談起,章節的標題也常以簡單而易懂的方式來下標題,例如:當她介紹由語言人類學的民族誌案例,討論語言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間的差異之後,她為接下來的內容給了一個章節標題:「那麼,你需要知道什麼才算「懂」一個語言?」(So, What Do You Need to Know in Order to “Know” a Language)。
回到,前述的段落談及若將Chomsky看成是編毛線的人,那麼他對下列問題卻完全不感興趣:
- 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社群的人們如何學習編織,又為何學習它?
- 編織的實踐如何隨著時間推移改變?
- 編織與其他手工藝在許多社會中的性別特質(在美國社會中,雖然編織通常
和女孩和婦女有關,比如在尼泊爾,一直到近期織布等手工藝技藝在傳統上
是由來自較低種姓階級的男性所生產的)。
- 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德
法奇太太(Madame Derarge)偷偷把反革命份子的名字織進編織作品裡。
- 全球政治經濟的角度,許多從事編織的不同民族所用的織線─從尼泊爾的氂牛毛到冰島羊毛,再到由合成的馬海尼毛。
(Ahearn 2017:10,吳碩禹老師譯)
而這些問題正是語言人類學想透過語言連結到更大的社會、文化、經濟脈絡的獨特研究角度。也因為這樣的角度需要有更多機會被運用於臺灣的人類學課堂中,啟發了我們進行臺灣的第一本語言人類學教科書的翻譯工作。如何找到更適合於臺灣的課堂中討論的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研究的案例,也將是一項挑戰工作和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唯有奠基於長期的人類學田野研究成果,以及教學的實際互動與經驗,才有辦法讓臺灣的語言人類學能有更深和更廣的紮根,教科書的翻譯工作將是開端而已。
[註] 當時,Boas對於所收集來的語言所進行的音韻分析和句法分析則是語言學的傳統方法,而不是當代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劉子愷 從大學教科書探尋「語言人類學」的軌跡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635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