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與「理解」之間的詠嘆
還在歐洲念書時,有一次和房東一家出門,老房東有兩個孫女,兩人為了爭奪一個沙發,吵得不可開交,最後由妹妹霸占到整個沙發,我聽到那個長兩歲的姐姐大叫:「她沒有『權利』可以這樣」。
是的,我清楚地聽到一個法律和民主社會運作的基石的概念:「權利」,出自一個10歲左右的小女生。這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在於她們的日常生活用語可以如此地法律和政治,是應該讚嘆人家的民主政治如此深植於日常生活,並且進入到家庭的親密關係裡,因此而確保了更大範疇的社會運作的「合理性」?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興趣,因此沒有追蹤相關的觀察,只記得我的歐洲同學的家庭關係比起亞洲人和南美人相距甚遠。譬如一位家住南部的法國同學告訴我,他只有聖誕節才回家,家裡的親人只有老爸和一位弟弟,平常也沒有怎麼聯絡。和其他法國同學聊天,足球出現的次數遠遠超過家裡親人。就連房東家也是四分五裂,房東自己也有兩個女兒,平常我只看到小女兒,原來大女兒遠嫁義大利,平常也很少回家,有一次小女兒向我抱怨她姊姊聖誕節時不過一張卡片交差了事,裡面的問候語,還相當官式,有如路人甲一般。
但是我一位墨西哥籍的同學可就展現截然不同的作風,就算她遠度重洋來到歐洲念書,我們還是隨時感覺得到她的家庭的存在。相較於法國同學的冷冷的感覺,她的大方和善,很得人緣,因此亞洲同學非常喜歡和她約出來玩。但是等到見面時,經常不只她一個人出現,旁邊總是夾帶著親人或她的同胞。一下子是嫁到法國的表姊和法籍表姐夫,一下子是她墨西哥的大學老師,來到法國交換一學期。一下子又是她的姐姐和妹妹在暑假來到歐洲旅遊,趁機到法國和她會面。一下子又是她的同在法國念書的墨籍的朋友。

和她的交往就像和一大家子交往的經驗,我們不但知道她的家庭狀況,她大學老師的背景,連表姊和表姊夫的羅曼史我們也知之甚詳:她父母的職業,家裡三姊妹,老大正在論及婚嫁,老么學大提琴,家裡請的幫傭是墨西哥鄉下來的女孩,我的同學因為是念社會學的,所以儘量平等待人,平常還會教她識字。表姊夫是廚師,有一年到墨西哥旅遊因此懈逅她的表姊,她的墨籍老師研究標誌車場工人在不同國度的表現…。我後來在家人的書桌上發現一位墨裔的美國作家的作品,其作品也是在鋪陳南美裔緊密的家庭關係在美國的經驗。
這些經驗上的落差,雖然深印腦海,卻一直沒有真正地發酵,一直到我自己深刻體認到一些切身經驗。由於我的父母對子女的深刻愛意,作子女的我們一直和自己原生家庭保持很緊密的家庭生活。父母對子女的愛所帶來的家庭凝聚力確實溫暖,但是我卻一直被家庭裡原有結構所產生的權力關係所困擾。我自己排行第二,我們家老大卻在人類社會的各種面向上都表現出「唯一老大」的作風。她喜歡的話題她可以隨時插播大家得洗耳恭聽,反之不然。在她周圍出現超過半個鐘頭大概就會開始聆聽「教訓」。總之,她可以做的,你不可以做。新聞用語叫「雙重標準」,說得露骨一些,「排行」已經「宿命」地決定了你的位階和權力關係,由於血緣的不可否定性,和童年生活的淬煉和固著,你這個後出生的人想要翻轉既定結構,可能得花下「海克利斯」當年清掃牛糞的努力,還未可知其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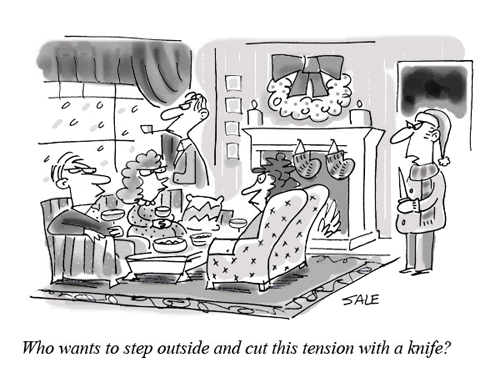
也許也在於在童年時我們的環境沒有氛圍讓我們說:「你沒有權利,這樣不合理」。當然,家庭生活交織著感情性和細節的微妙,我們也並非沒有接受親人的幫助和情感的支持,因此在極少的情況下,我們會願意冒家庭結構崩解的代價,來進行革命式的權力翻轉。因此大部分的「家人」也非常心領神會地理解到這層「保障」,因此不太平等的權力關係也經常在這樣的既有結構下匍匐前進。由於法律一般並不大願意進入到家庭的情感或私密的空間,因此家庭裡不甚平等的權力也就在非常「機動」、「本能」和「戰術性思維」的交織運用下得逞,讓你事後都很難以理性的語言來陳述,讓聽的人的覺得是「小事一樁」或「茶壺裡的風暴」,卻讓接受的人,有難以言說的不舒服。
我曾經認真地想要在在不導致結構崩解的情況下,努力,竭盡所能地(天啊,可見我的嘔心瀝血之處),從暗示到明示到打開天窗說亮話來昭示民主社會的價值-平權,但是經常努力了半天只在關係上挪動了幾公分,第二天醒來就像母親和我述說的風水地裡傳奇一樣,那個山頭不管你怎麼挖掘,第二天醒來一切似乎又恢復了原狀,或是成為拉回原有位階的起始點,真是一場終生的聖戰。我該如何來看待這個家庭規模的「運動」(當然他不是社會的),漸行漸遠?但是你必須防止你自己在任何的社會關係裡都採取不合就拆夥的現代式進行曲(網路的加入和退出是極致表現)。緊咬牙根撐過去,這樣似乎不能整合啟蒙時代以來的思想於真實生活,似乎表示你白念書了。總之,我認為盧梭應該重寫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排行」不是「私有制」。
各位讀者大概已經知曉我和民族主義的大師有著相同的obsession: 「宿命性」,這個令人不安的字眼(「令人不安」是最近的一個夯辭)。學術史上起碼有兩位大師認真對待過這個情感狀態,一位是Anderson, 另一位是Geertz。當他們行走在民族或族群的迷宮中時不得不面對的「真實」。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裡的第二章「文化根源」開始頻頻出現「宿命」兩個字,到了「舊語言,新模型」這章時,這兩個字又再冒出來。並且不斷提醒我們它是馬克思和資本主義都無法回應的頑強對手。同樣地,Geertz在「舊社會和新國家」裡也告訴我們「連帶或關係」(tie)本身在某些社會被賦予絕對的重要性,當然就是那些你一出生就被「給與」的關係。兩位老人家的著作其實都是編織在「宿命性」和「人類超脫宿命的意志性」的張力和矛盾上。這樣的命題就好像我們在家庭裡到底要使用多少法律用語,在人人平等的「合理性」和情感對象的「同理性」之間如何拔河的問題。

因此「宿命」是個充滿想像和「社會性潛力」的「概念」,它有幾種組合的可能,可以引發我們強烈的情感好惡:
1) 無法擺脫的宿命:意思是「認命」,充滿了妥協和無奈,似乎沒有任何干預的空間,令人產生永不得脫身的恐懼。
2) 不向宿命低頭:強調了人類的意志的無所不能,我們不應該局限在「被給予」的關係,我們要飛翔,要追求我們的遠大理想。
3) 為宿命的對象付出一生的承諾:引起眾人的讚嘆,譬如孝順父母。
4) 為不見得是宿命的對象,或不那麼是「宿命」的對象,付出像宿命的對象般的承諾:這不僅引起讚嘆,還會引起難以企及的感嘆,以及慚愧和罪惡感。
5) 在宿命和追求理性和效率之間擺盪:這是大部分人的情況,有不同的結局、完美度和遺憾度。不過在這個凡人的選項裡,通常隱藏一個通向宗教的路徑,因為宗教就是為凡人而設。人們由於無法立刻找到答案:to be or not to be?因此開始詢問何謂「意義性」?

這些或許可以說明為何民族主義或族群性總是引起兩極化,或在兩極之間擺盪的各種情感反應:
1) 對民族主義極端厭惡,因為不願意侷限在「被給予的關係」,認為它是一種「倒退」,引發恐懼。
2) 不被既定關係所限制,相信人類智慧足以克服既定的「限制」,科學和現代性的思維可以為我們排除障礙,達到幸福。科技人的基本信念。
3) 民族情感(我不說民族主義,因為是不同的東西)強烈,認為忠於關係是人類的情操的高尚表達。
4) 原先是科學和現代性的信徒,因為一種機緣巧合,轉而變成強烈的民族情感的擁護者。
5) 對於能夠為族群或民族而犧牲時間、金錢的人,有無名的崇敬以及內心引起的罪惡感又加強了這個崇敬。偶像的由來。
6) 在現代性的可解決性的信念和難以改變的既定關係裡「詠嘆」的一般人。他們找到了一種適切的尺度的歸屬體來擺盪,民族或族群?
不知道各位讀者屬於哪一類型?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有機草莓 「合理性」與「理解」之間的詠嘆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717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有機草莓,
你談家庭內民主的窒礙難行時,讓Kaka想起前一陣子讀到的角田光代所寫的小說[空中庭園]。作者描寫了一個現代日本家庭的樣貌:強調家人之間應該毫無隱瞞,開誠布公,看似沒有人可以支配或宰制任何人,因為在他人面前,眾人一律平等要對他人坦承,且不會招致批評。在這看似完美的家庭中,每一個人仍有不欲人知的祕密,為了隱瞞秘密而辛苦地掩飾日常生活的各種行動。
我們都對家有所想像與期望,然而它經常表現得與我們所期待的不一樣。
家內的民主化不一定比公共領域的民主化來得更快,因為家往往更堅持舊社會的傳統理念與價值並讓它變成一種Gramsci所謂的霸權之所在。更困難的是,這類霸權經常被倫理化,導致即使行動者看穿與act upon it,也不一定能產生可欲的作用及後果,因為有其他更多信服霸權的人與既得利益者,認為霸權乃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使其更難被撼動。
Marxists當然要面對民族國家與主義日益茁壯的問題,不過,我們要如何超越原有的想像,例如,不再將民族主義當成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是從貼近身在其中者真正關懷的問題,擺脫學派教條式的提問與質疑,我們有可能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才可能尋找不同的答案。不過,這很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希望與自以為是的解決之道囉。
這麼看來,Kaka屬於其他類,不在有機草莓列舉的類別中。
有機草莓,看看「虎媽的戰歌」吧。對我這個鄉下阿伯(還有加上虎媽)而言,家庭內的親密關係正是要好好運作、精緻微調,以求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之struggle遂行。我們就是因為希望書沒有白念,才在家人的共食共居共做中鍛鍊一種意志的淬礪。平權一詞豈不太輕薄乎,他並未涵蓋到親屬內全面且深刻的感覺結構。同理得證,民族情感亦然。
理性和同理心都有她迷人之處,也有她的危機。舊社會裡對關係的看重,有他真實的意涵,透過關係,生活才顯示出她的意義,而且它也告訴你,你最終還是要回到關係中,也是那個不可逃脫的[宿命性]。然而經常也是這種[看重],讓霸權有了[保障]。這也是關係集合體在當代的處境,to belong to or not to belong to?當我們總是用理性來檢視關係以決定去留時,大概就合了昆德拉那句名言:[不可承受之輕]。但是你如果因揹負太重而得憂鬱症呢?
但是當代的現代性具有太大的強制性,我們每個人都活在片面中,加上現代性造成的[羞愧感],[宿命性]反而成了[解藥],它成了拼圖中那個缺掉的那塊。也因此族群或民族主義在現代性之下非但沒有消失,還可能更旺盛。
這種要把全面性活出來的企圖,牽涉的是[主體性],或心理學上的[本我]。但是容格警告我們,這個本我,有她生命力和創造性蓬勃的一面,也有它的陰暗的一面。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以民族之名,有令人敬佩的一生以和平奮戰的民族英雄,也有暴力和恐怖主義的可能。也可以解釋,對民族自決的追求可以是一生的志業,生命力發揮之所在。但也可能淪為對羞愧感的彌補,對某些失衡的行動缺乏判斷。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