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的名字
人類學家進入田野時,隨著各種關係的建立,往往能獲得新的身份,而立即伴隨這個身份而來的會是一個新的名字,不論是基於擬親關係而來的稱謂、能融入社會文化體系中的語彙、或只是田野情境中的親暱日常綽號。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狀況,在一次重大事件之後被賦予了新的名號,從而破冰產生新的關係。我們或許能控制這個名字(請叫我某某某),但大部分時間這是當地人給我們貼的標籤、試圖理解我們是誰、來做什麼的方式。無論如何,人類學家田野中的名字都有自己的生命,以及相伴的情感、責任與故事。
我們的現代田野工作老祖宗Malinowski也有他的田野名字。根據其傳記作家Michael Young的考據,在Oburaku村落中村民叫他Tosemwana,直譯是「把自己放一旁的人」,也就是扮演別人的「演員」。這個稱呼其實有嘲諷的意涵,暗示這個演員扮得不像,而且時常出醜。這一方面反映了他會與當地男人一同嚼檳榔、學習當地語言和傳說的努力,但另一方面或許也是當地人對這種只做表面功夫,卻始終保持距離的田野關係的批評。除此之外,他的綽號還有Tolilibogwa,「收集故事的人」,以及Topwegigila,「穿著鬆垮短褲的人」,指的是他在拍照時會先把褲子拉緊的習慣。北美田野工作老祖師爺們也有他們的田野稱號。在蒐集親屬材料之餘,Lewis Henry Morgan因為協助Seneca人打官司抵抗土地被開發公司奪取,得到了Tayadaowuhkuh這個稱謂,意思是「跨越鴻溝的橋樑」,讚許他溝通兩個世界的精神。Franz Boas的田野名字故事相較起來則有些平淡,他在巴芬島的田野被當地的因紐特人稱為Doctoraluk,「大博士」。
Max Gluckman大概是最認真看待自己田野名字的人類學家。他在非洲Barotseland王國做研究時以對待當地的Lozi人的友善態度著稱,時常送給幫工茶、香菸、錢,在下雨時會讓他們進自己帳棚躲雨,甚至幫助一位逃稅的工人免受沉重責罰,也因此被稱為Makapweka,「大方的人」。他在田野筆記中紀錄了這件事,並表示自己的善行被比擬為當地國王Yeta三世。之後有研究者將這個稱謂翻譯為「凱子」(recklessly generous giver),帶有點負面意涵,但人類學家Lyn Schumaker在90年代前往尚比亞做田野時仔細詢問當地Lozi人,發現他們的翻譯都很正面,例如「給比預期還多東西的人」、「能夠滿足任何願望的人」、或甚至「聖誕老人」,有些人甚至還記得這是Gluckman的綽號。或許是非常喜愛這個名字,他在1955年的著作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的首頁上把Makapweka與自己的英文姓名並列於作者欄,並在前言最後說明其原因是很多當地人只知道他這個名字,「而且有個英國地方殖民官員偷偷把這個稱號拿去用」他如此酸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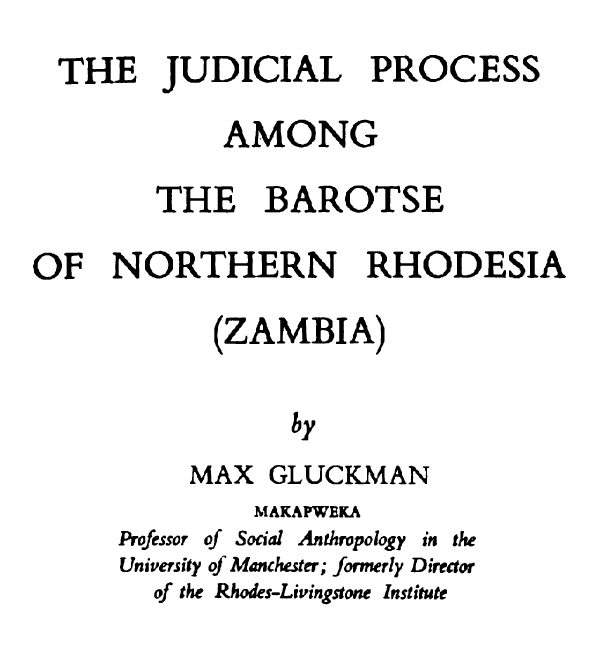
下面蒐集了包括我在內的幾位老中青台灣人類學家的田野名字故事與大家分享:
林浩立:
我在斐濟群島做研究,在想名字的時候自然往斐濟語化的「浩立」動腦筋。之前曾在一個太平洋島民社群中用「浩立」介紹自己,惹得裡面的夏威夷原住民朋友大笑,因為聽起來很像haole,也就是白人的意思。所幸斐濟語沒有[h]的發音,浩立於是變成了「阿里」Ali,忘記是我在南太平洋大學的語言老師還是村落的長輩說這很像斐濟名字Alifeo,這就變成了我的新身份。離開田野時,村落親友幫我做了一塊樹皮布,上面寫著Alifeo Waqa Lin,Waqa是我斐濟爸爸的姓氏。這塊布現在就貼在我辦公室門上頭。

謝艾倫:
2014年菲律賓Ifugao的考古田野,我的主要工作是照相紀錄所有探坑發掘進度跟管理影像檔案,以及隨時支援各組。我們在山區梯田小村的住家旁開了幾個1mX2m的坑,遇到的都是擾亂的黏土層,於是多使用大平鏟下挖。因為看不慣幾個美國大學生青澀沒有效率的挖土方式,我一把接過平鏟,在眾人驚嘆聲中炸飛土層,然後在幾分鐘內把平鏟給毀了,從此被計畫主持人封為Taiwanese Tiger —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考古田野靠肌肉獲得聲望。
鄭肇祺:
是田野的媽媽起初不想叫我英文名宇時,說了一句「你就叫小鄭吧!」然後就變成小鄭了(到現在!)然後的然後是,在漁村自我介紹時都會被說是莉莉的男朋友嗎?初時不為所以,後來google 才知道小鄭與莉莉的甜蜜故事!這成為我進入鄉民社會的一扇小窗。自我介紹時會笑說「我是小鄭,但很久沒有見莉莉了。」
李梅君:
MG,這是我給自己的田野名字,MG Lee的簡稱。MG不是Maggie的縮寫、也不是OMG沒了驚嘆詞Oh,就只是M-G-,簡簡單單的,兩個子音沒有母音。更多的時候,我是@mglee,帶上小老鼠並小寫著,一旦有人呼喚我,我的名字變會化為藍色,通上電流接上網路,光速地傳遞身處任何一地的我,「叮咚,有人敲你了」。
我是個數位人類學家,我的名字經常不是拿來「叫」的,而是用來「tag」的。和我數位田野裡的伙伴們一樣,我們的名字是自我意志的表現,可以是本名的諧音,也可以是常用的英文名字、遊戲ID,或者只是一串只有自己才理解的符號。在黑底白字的編碼世界裡,我們不預設彼此的語系、性別、與出身。羅馬字母和數字是共通的意符,而顏文字是我們招呼彼此的方式。mglee ++ 是鼓勵;\ MG / 是歡呼。你不一定要會念我的名字(少了母音也許讓你失語),但隨時歡tag我。@mglee若不在網路上,就是正在連線中。
羅素玫:
1997年我因為尋找博士論文的田野,來到位於台灣東部海岸距離台東市區二十公里的阿美族都蘭部落,剛到部落時,在一個耆老聚會的場合,當時的前頭目沈新永faki捏著我的耳朵幫我進行了命名禮,取了阿美族的名字--Alik。老人家解釋說,Alik的意思是從tatalikan(搗〔米的)臼〕來的,表示我是個勤勞的女孩,像以前的人辛勤地樁米那樣,一直很認真地在請教和學習阿美族的文化。我的部落哥哥Siki的女兒在我進行田野期間出生,他們夫妻倆也用了我的名字為她命名,現在小Alik已經高中畢業了呢!這些年,除了偶爾有人會稱我羅博士之外,大部分的老人家喜歡看到我就親切叫我Alikaw,部落的弟弟妹妹會叫我Alik姊,還有我最喜歡部落的孩子們叫我Alik阿姨,成為自己長期田野工作地的家人,也是我感到最安適的所在。
2009年我還在抵抗不想使用社群媒體臉書,有一天蛋蛋博士(@蔡政良)跟我聯絡,說因為要串聯部落成員進行都蘭傳統領域的抗爭,所有人要用臉書封閉社團做連結,但部落年輕人都有臉書帳號啦卻只有我沒有!!哇這未免也太震驚了,其實我也是比部落老人家晚申請手機的,但這回我沒得抵抗了只能立馬申請一個臉書帳號,也因為一開始是要跟部落運動連結,我連想都沒想就直接用Alik做註冊,但已經有人用來註冊了,所以就用阿美族名字使用的原則加上了我部落媽媽Nikar的名字,這個ID也成了我臉書世界裡的虛擬身分。
吳燕和:
2016年三月底, 跟內人日野みどり建議, 一起回台灣,去東部旅遊。我六十多年人類學生涯,很想重訪台灣東海岸。日野雖然多次訪台,從來也還沒去過東部。
四月初回到台北以後,第一個目標,就想重訪1963-64年,大學四年級之後,獨自赴台東太麻里和金峰鄉排灣族村落的田野。我們從台北直飛台東,安排好汽車,次日清晨一早,先送我們去金峰鄉宋賢一鄉長家,見面非常親切。他說:「吳燕和你回來啦,我們太高興了。現在族人都是靠你的書:《太麻里的東排灣人》來學習我們傳統文化。你知道嗎?你是我阿媽的好朋友,小時候你常常來我家、跟阿媽聊天。」
我恍然大悟,原來他的祖母宋梅江女士,是我當時的重要報導人。每天大清早,介逹、比鲁兩村的大人都上山去種田了,留下老弱和幼兒。我每天先到村中閒晃,抓住沒事的老人家,要求講祖先、神話故事給我聽。想不到,在一邊玩的小男孩,就是至今還記得我的宋鄉長。記得當時翻譯人曾孝先生(這次也歡聚了)私下說,村人给我取了外號(我忘了排灣语),我是那個「整天不工作,到處閒逛,沒用的人!」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浩立 田野中的名字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16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