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動的春之祭禮
儀式與原始主義

1913年5月29日夜晚,位於巴黎蒙田道、甫落成一個多月的香榭麗榭劇院(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大廳和迴廊擠滿了衣冠鬢影的群眾,盛況空前。追逐時尚潮流的巴黎觀眾們,引領期望在此嶄新劇院觀賞一場當代的芭蕾舞劇與音樂演出,首演場亮眼的票房佳績,讓劇院和受邀演出的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 Russes)經理狄亞格列夫(Sergei Diaghilev)眉開眼笑,特別是後者,畢竟對頗具生意頭腦的他,水漲船高的首演票價意味著舞團的招牌,唯獨少數已經觀賞過彩排的樂評家,對於演出過度前衛的風格隱隱感到不安。
只是沒有人料到,等在他們前面的會是一場風暴。

其實在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春之祭》的序曲結束後,現場的觀眾已經開始騷動了,不知究竟是針對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或是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的編舞,兩派明顯意識形態極為不同的觀眾先是彼此叫囂,然後一齊將氣出在管絃樂團身上—加上手中所有可用的投擲物。到後來編舞者、本身也是傑出芭蕾舞者的尼金斯基不得不到台上去幫舞者喊拍子,彼時台上已經完全聽不到樂池中管絃樂團的樂音了。騷動愈演愈烈,最後劇院不得不動用警力把幾十名的鬧事者抬出去,而儘管演出者鎮定自持地持續完成表演,這場演出已經免不了成為隔日各大報紙議論的主題,一週後,連大西洋彼岸的紐約媒體也加入論戰。
如果不是因為主題與祭典有關,這場演出或許不會演變成這樣的局面。當時在音樂圈初露頭角的史特拉汶斯基,先前已經為狄亞格列夫的俄羅斯芭蕾創作了兩支芭蕾舞曲:《火鳥》和《佩卓希卡》。《春之祭》的靈感,源自身為俄羅斯人的他心目中對於祭典的想像:「我想像一場肅穆的異教祭典:一群長老圍成一圈坐著,目睹一位少女被要求跳舞直至死亡為止。她是他們用以祭祀春天之神的祭品。」《春之祭》一曲以沈緩又帶點不安的巴松管序奏開始,全曲分為兩幕:〈大地的崇拜〉和〈獻祭〉,共由十四個樂段組成。撇開首演的騷動,史特拉汶斯基為樂曲注入特有的俄羅斯風格,加上其中的張力及戲劇性,已經使得這支樂曲成為二十世紀現代音樂的經典。

不只是音樂,連舞蹈的動作,在當時都堪稱前衛。本身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芭蕾男舞者之一的尼金斯基,編排動作時刻意拿掉炫技的跳躍和旋轉,他讓舞者們反芭蕾其道而行,時而用力跺地、時而扭動身體。他所編創的動作、和舞者身上與美洲平原原住民頗為相似的服裝,莫不流露出濃厚的原始主義(primitivism)情調。從西方現代藝術的角度而言,原始主義代表的是歐洲在帝國擴張過程中,挪用被殖民地藝術理念或形式後所產生的融合與創新。根據William Rubin 的說法,「原始」一詞其實最早是文藝復興時期先進的義大利等地用來指渉相對而言藝術較為落後的地區,甚至包括藝大利以北的歐洲。可說「原始」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用以區辨自我與他者的標誌,從專門的藝術、到普遍的文化,皆可應用。

仔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可說是位於帝國擴張和殖民主義的高峰,小小的一塊大陸,匯集了自世界各地搜羅而來的物件與人事,透過視覺、聽覺、味覺、甚至觸碰等感官的刺激,直接撩撥歐洲人的經驗,呈現在香榭麗榭劇院舞台上的音樂和舞蹈,亦是當時世界觀刺激下的產物,而由藝術家為之賦予形式。畢竟對熱衷於發展分類秩序的歐洲人而言,還有什麼比祭典更能表現他者的原始性呢?騷動當晚鬥爭的兩派觀眾,不也意味著當歐洲人試圖建立全球性的秩序框架時,內部更深沈的一種矛盾和衝突嗎?
其實並非只有藝術家和創作者勇於探索祭典的原初性,文化詮釋和歷史編纂者也沒錯過人類社會中儀式所蘊藏的秩序觀。相當巧合的是,就在《春之祭》首演前四年,Van Gennep才發表了他為人熟知的著作《通過儀禮》( The Rites of Passage),在書中他巨觀地將通過儀禮視為一種人類社會的共同範疇,他以一種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觀點所提出的儀式三階段論,不但影響了後來的人類學儀式分析(以Victor Turner最為顯著),更顯示出當時一種智識論(intellectualism)的文化秩序觀。1913年,比Van Gennep還要年長的古希臘研究者、也是英國最早的女性學術專著者Jane E. Harrison則出版了《古代藝術與儀式》(Ancient Art and Ritual),縱使她的著書目的主要在於溯及宗教與藝術(在二十世紀的歐洲已經分化成兩個互不相容的範疇)的源頭至希臘的儀式,然而以儀式為某種整合性的文化根源,卻是她和許多二十世紀初期作者的共同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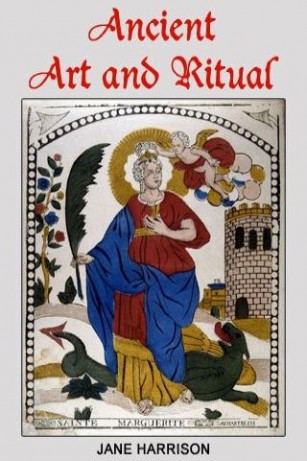
《春之祭》的故事並未結束於香榭麗榭劇院,事實上其音樂偉大之處就在於它持續召喚了不同時空創作者的情感與想像,特別是對儀式的想像。假使劇院的興盛代表了宗教在現代社會中其整合性的角色不復存在,則舞台上的儀式其意義就可能超越狹義的演出。一個多月前,舉世聞名的德國烏帕塔舞蹈劇場來台演出其已故藝術總監、亦為世界知名之後現代舞蹈創作家碧娜鮑許(Pina Bausch)兩支早期經典名作:《穆勒咖啡館》(Café Müller, 1978)與《春之祭》。鮑許的《春之祭》版本,被台灣雲門舞集藝術總監、知名舞蹈家林懷民先生譽為二十世紀詮釋《春之祭》第一人。舞台上,當年寫實風格強烈的佈景和服裝已不復見,鮑許用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服裝、以及同色的一台沙土,提供舞者們揮灑肢體的空間。然而,緊扣著韻律和節奏的集體舞動,和獻祭過程中少女抽慉的身體、對照出其他參與者的默然,則為「反抗」和「衝突」提供了具象的寫照。身為觀眾,而且是慣於以書寫掌握儀式意涵的我,當場也無法不為舞台上的演出撼動。鮑許版本的《春之祭》,實則為二十一世紀吾人共同面臨的壓迫和掙脫:不論是介於性別、階級或是族群之間。
儀式再度成為社會議題的顯像。回顧過往,不論透過展演抑或論述的文化詮釋,對於儀式的追尋,或許可說共同標註了跨越一百年這趟現代人文主義對自我、他者和社群探尋的未竟之旅吧!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綺芳 騷動的春之祭禮:儀式與原始主義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4555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