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多樣性、田野與新幾內亞
推介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
我還是博士生時,閱讀了幾篇關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犯罪與罪犯 (raskol) 的討論。其中,一篇名為 “Heroes from Hell: Representations of ‘rascals’ in a Papua New Guinean village”。作者的名字我漸漸淡忘,但文章的故事情節卻非常深刻,也影響我前往新幾內亞的博論田野心理準備。直到一、二年前讀了Don Kulick的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內容似曾相識,“Heroes from Hell” 一文又重新浮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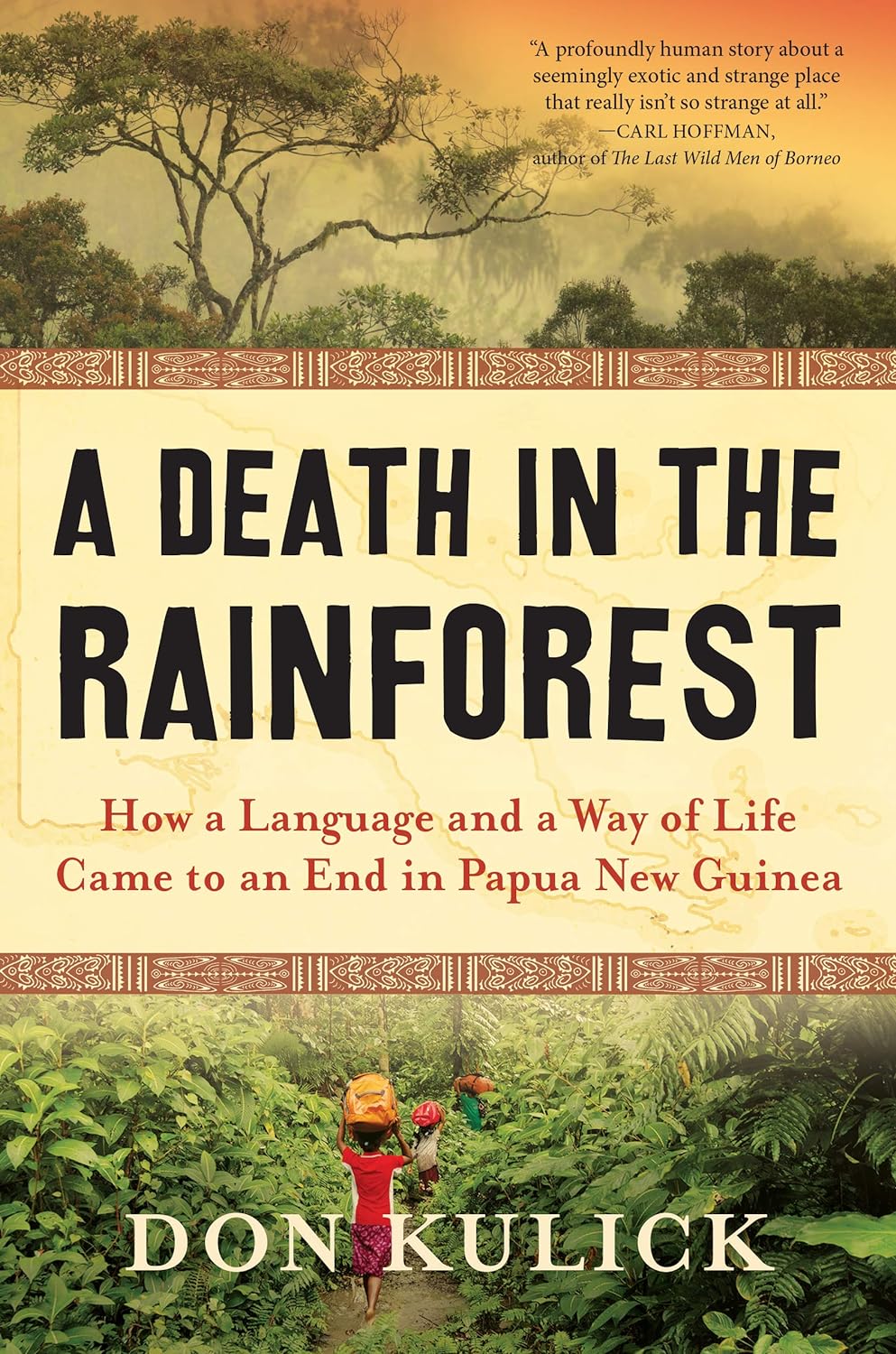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com/Death-Rainforest-Language-Papua-Guinea/dp/1616209046
Don Kulick是一位語言人類學家,Kulick出生於美國,在新幾內亞從事田野調查並取得博士學位,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後移居瑞典。他的田野地包含了新幾內亞、巴西與北歐,研究主題也非常廣,涵括了語言、性別、LBGQ與disabilities,以及人與動物溝通等議題。他目前是瑞典的Uppsala University的Engaging Vulnerability計劃的研究主持人。這個計劃是由Swedish Research Council出資八千萬瑞典克朗(約合九百萬美金)的一個跨學科、十年對於vulnerability的研究計劃。
Kulick是在1980年晚期在新幾內亞北部Sepik River下游的Gapun村落,當時他還是位博士生,他想要去記錄並研究Gapun人的語言Tayap如何消逝。當時約只有100位村民會講流利的Tayap語,目前只剩不到50位流利的講者。語言被認為是文化深層的部份,文化也透過語言的詞彙與結構方式以表達概念與對世界的理解;語言是情感的,對許多許族群而言,語言是和過去的交流,對於族語的流失而感到心酸痛楚;語言是政治的,它是國家或是社群主權宣稱、辨別「我們」與「他們」的指標。更不用說,語言也是種族性的、性別化的與階級性的。既然語言是那麼全面性的,當我們說一種語言死亡的時候,是否文化也滅亡?
Kulick在1992年出版了Language Shif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一書,並於2019年出版了Tayap的字典 (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of Tayap)。不同於前面的兩本語言學的專論,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除了用清晰、易讀的文字,解釋他對於Tayap語言的觀察外,這本書也是Kulick回顧他在近三十年間,前前後後、短期、長期在Gapun的田野調查,書中包含了大量Kulick與Gapun村民的互動、田野災難與道德問題等。

Don Kulick (https://www.katalog.uu.se/profile/?id=N15-1000)
根據語言學家的調查,新幾內亞是語言最多樣性的地區,約將近有一千多種語言,一般我們常用物種的多樣性來理解這種語言的多樣性,也就是說因為地理環境的隔絕,在歷史中缺乏交流,物種為了適應環境而產生出差異性。相似的,新幾內亞語言的多樣性也常常被理解為各部落佔地為王,彼此因山川的隔絕,使得彼此的語言互不相通。但,Kulick指出從語言的多樣化是一種社會文化關係的結果,而不是自然或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後果。他指出在新幾內亞,一個語言非常多樣的地區,基本上語族之間往往並非是孤立的,不同語族可以透過河流彼此聯繫。然而,不同語族為了標示彼此的不同,他們發展出語言上的差異。相反地,分散在各地,彼此難以到達的村落,常常彼此都是講相同的語言。也就是說,人群之間因為太接近而發展出不同的語言,來標示出彼此差異;人群之間因為太孤立遙遠,因此彼此之間使用相同的語言,以便溝通。
歐洲人的殖民主義,把土著勞工引到熱帶墾殖園裡,日本的入侵,二戰後天主教的傳入,Tok Pisin漸漸取代當地語言的使用,Gapun會講Tayap的人愈來愈少。然而,這種歷史洪流導致Tayap的消逝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相反的,Kulick更細膩地討論這歷史洪流是如何和與Gapun的人觀、他們對於「語言」作為一種財產的看法,以及人們對於發展的期望等社會因素與文化邏輯之間的緊密關係。例如,在第七章,Kulick描繪了Gapun父母和小孩的互動過程,透過記錄親子互動過程中語言的使用,以了解為何下一代愈來愈不講Tayap語。對於Gapun的人而言,小嬰兒是不可受教的,他們是頑固的,使性子的,因此,父母在與小孩的互動過程中,大多是使用轉移注意力或是說謊的方式來安撫小孩,而這也賦予了小孩很多的自由與權力,例子,小嬰兒可以拿打火機或是砍刀。這裡嬰兒會講的前三個字並不是「爸爸」或「媽媽」,而是”okɨ”(「我要離開了」)、”mɨnda”(「我受夠了」)、“Ayata”(「住手!」)。當然,Kulick並不認為這是真確的前三個字嬰兒會講的三個字,而是父母認為他們會講的三個字,也表示了父母對於嬰兒與世界之間互動的關係的想像。自1980年代開始,小孩子開始精通Tok Pisin,Kulick認為除是父母認為小孩子頑固的只聽Tok Pisin外,另一個原因是父母們不知不覺得把Tok Pisin視為最重要的語言,是未來和外面世界的重要媒介,也是想要改變生活環境的一個重要語言。
Kulick在本書的一章中試著問Gapun人在Tayap語言裡「彩虹」如何說。Kulick感到非常訝異,因為沒有一個人記得這個字,或者更精確地說,每個人對於這個字有不同的版本,同時每個人對於別人的版本也爭論不休。在這一章中,Kulick要指出,語言常常被視為是一種共享的知識,但是對於Gapun人而言,他們沒有這樣的概念,語言可以是私有財產。所有東西都是被私人所擁有的,在這樣的財產權的概念下,他們得記得哪些東西是被誰所擁有,Gapun人也常常爭論彼此對於物的財產權。這樣也間接影響到Gapun似乎對於Tayap語言的消失,他們並沒有一個共同的失落感,是各別村民對於Tayap語言的學習與取得有最大的責任,而非一個Gapun共同體。
因此,Kulick認為語言的死亡,不可以類比為物種的滅絕,因為這樣的類比過渡地將語言的死亡視為「自然」的現象,但它卻是一個社會現象(頁26-27)。語言的消失,像是剝洋蔥一樣,最先不見的是艱深的神秘語言,最後才是常見或是髒話(第九章)。在Gapun,Tayap的髒話也漸漸消失了,這已經快接近洋蔥的核心,另,當我們講語言「死亡」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個很正確的描繪,語言的消失是一種流逝的過程,漸漸地對於某些語言的小細節沒有辦法正確使用。
我喜歡這本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Kulick對於語言的討論是建立在他與Gapan村民日常生活互動當中,例如,他和年青人討論他們的情書、村民彼此爭論「彩虹」的Tayap字彙、女人如何罵髒話、他與村落語言老師之間的互動與誤解。而他與村民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是深厚的,這也表現在日常生活的互惠當中:「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樣,禮物的交換在Gapun是一種雙面刃:我要不斷回饋村落送給我的禮物;同時,他們在接受到我的禮物之後,也有義務不斷地來看顧我。這種不斷地循環使得我們的關係更加緊密」(頁85)。
然而,他的田野反省也是很沉重的,巴紐亞新幾內亞獨立(1975年)之後,政治的成效不彰,國內的貧富差距加大,以及新幾內亞與工業國家之間的差距,許多年青人成為了raskol,尤其在1980年代以後,治安成為一個持續惱人的議題。他也曾經在田期期間不斷受到生命的嚴重威脅,甚至當地村民為了救他而無辜犧牲。這個問題也直指了田野倫理與災難之間的問題,Kulick也在文中誠懇地說明了他的作法與說法。
對於想要了解一個語言如何消逝,以及語言的多樣性對全人類以及村民的意義為何,以及想要了解新幾內亞這個國家,尤其長從1980年到今天一個新幾內亞村落生活的改變、他們對世界的想像,或是探討田野的災難與可能的道德問題,這是一本很合適的書。這不是一本關於Tayap的語言書,裡面充滿了細膩的人物描述,以及研究者與Gapun村民的互動。這本書沒有專門術語,有的話,作者也用了淺白的文字說明。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Madi 語言多樣性、田野與新幾內亞—推介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7009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老師您好,我想問詢問關於巴布亞新(紐)幾內亞的相關中文文獻有沒有具體的資料?
因為我想要試試看透過找出新幾內亞的多語言、多民族的特色去反思到台灣原住民的爭議上,然後我有透過GPT找到(但我找遍了圖書館都沒有看到...)
1.張慧雯(2012)。〈多語社會的語言政策與認同建構——以巴布亞紐幾內亞為例〉。《語言與社會》,第13期,頁55–83。
→ 探討官方語言、母語教育政策與族群認同。
2.林淑華(2010)。〈語言多樣性與教育平等:以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多語政策為中心〉,《民族教育研究》。
所以想要詢問老師有沒有推薦的中文文獻拜讀的?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