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媽媽的多重勞動
當我們提到學術勞動或學術媽媽的同時,其實也已把一般職業婦女的勞動內容從學術媽媽們的勞動內容區分出來。不過,學術勞動有什麼特殊性呢? 學術勞動指的是與高等教育知識生產相關的勞動,勞動內容從純腦力活動、設計實驗、修理校準儀器、上山下鄉跑田野、作訪談、發問卷、圖書館搬運書籍、掃描檔案、以及不同情境下相應的情緒勞動。學術勞動又可以簡單分為有薪與無薪二種。有薪學術勞動者就是在高教機構或研究機構任教的學術工作者,從事的事務以「教學」、「研究」、「服務」三項為主。
目前「學術媽媽」相關的學術研究或非學術分享,多以有薪的學術媽媽為多數,這篇芭樂文,以我的學術和育兒勞動經驗,補充無薪學術媽媽的經驗,也許也可以擴充對於不同階段學術媽媽勞動情形的討論。學術勞動關乎知識的生產與傳遞,也因此勞動內容和特定學科的當代知識生產密切相關。像我這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工作者,沒有日日進實驗室報到的壓力,也沒有明顯的老闆與同事,我們的學術勞動條件和環境因此更沒有固定的形式與明顯的時空限制。好像似乎只要帶著筆電平板、甚至只要紙和筆,就可以不受限的閱讀與寫作。
不過,在看似瀟灑、自主的勞動環境下,人文社會學領域的學術工作者大多承受著極大的身心壓力。大多數人都有午夜夢迴無法入睡,或是破曉時分仍然在工作,所以工作—生活的界線也因此模糊不清。我們很難有個可以好好休息,關機的時間。如何在勞動密集、上工下工之間界線模糊或不存在的環境下避免過勞,也是我們共同面對學術勞動文化時最大的功課。林昱瑄(2019)的研究指出,學術媽媽發展出一套「智性母職」的整合策略,整合有薪的勞動與無薪的親職勞動。她的研究,以在大學任教的人文社會領域的媽媽們作為訪談對象,探討這些媽媽如何運用協商策略來回應彈性工作下的建制困境,並在協商過程中促成「智性母職」的轉化性意義。
學術勞動中的「彈性」陷阱: 學術工作的責任制與階層
為了寫這篇文章,這一陣子,我回顧了從懷上小孩至今9年多的生活。我在讀博士期間生小孩,不是在準備好、計劃中的懷孕;在當時的學術人際網絡中算是極少數已為人母的博士生,也是博班同學中第一個當父母的人。在國外讀博士要付出的學術勞動倒也單純,包括上課、讀書、交作業、聽演講、準備資格考、找獎學金、寫論文、參加研討會、跑田野等。得知懷孕時,是我準備回學校上課前的新年連假,返美機票已訂好、新學期已註冊、獎學金已啟動、學籍連著簽證也已經不適合休學了。相較於其他非學術非勞力工作的媽媽而言,我的生活相對平穩可以預測,(無薪)工作有很大的彈性。對於不愁育兒支出或配偶已擔負著家中生計的準媽媽而言,博士生時期生小孩或許是個兼顧學業和育兒的不錯選項,畢竟全職學生的工作負荷量和工時似乎遠低於一個職業婦女,請產假育嬰假等也比較沒有來自主管或同事的壓力。更何況學生有寒暑假,可攻可守,可以依照學習計畫、和指導教授的關係等而有些調整,看起來很自由。
學術勞動的「彈性」源自可以自主安排事務的權力,而無薪低階的學術勞動者所能享有的「彈性」主要來自於自己的和伴侶的收入、伴侶的職業身份、指導教授或單位主管的關係。我聽過一個可怕的傳說,一位學姊在懷孕時被自己的指導教授大罵怎麼可以在這時候懷孕,而指責的指導教授本身也是看起來非常開明的學術媽媽。幸運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很支持我,所以我沒有承受來自上頭的情緒和壓力。我初期的育兒難題倒也很單純:我需要獎學金。家庭增加一個胎兒,但請一個學期的產假與育嬰假視同休學,拿不到本來預計可以拿到的獎學金,加上簽證和獎學金是綁在一起的,還有醫療保險等,光是協調這幾件事情就花掉我大部分的力氣,當時也沒有機會選擇留在台灣生產。我的指導教授在得知我懷孕初期就大力鼓勵我,也在我覺得困頓時給予我需要的支持,不多也不少,她用她的方式間接教導我不卑不亢協調這些不同的勞動,並且冷靜爭取所需的資源。我請她幫我寫了好幾個聲明,有關於學籍休學復學、簽證、醫療保險、獎學金申請等,寄給各個不同的單位包括產科醫生、國際學生處等等,協助我在生產的那學期請假、延後獎學金發放、申請校內的家長獎學金等等。在這些安排下,我期待可以安心作一個好媽媽迎接寶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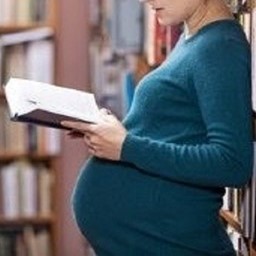
育兒勞動中的「母職」角色設定陷阱: 「妳是一位好媽媽」
除了學業、歡迎零歲新成員加入外,「作媽媽」的勞動在小孩在胎兒時期已開始:妳的身體不是妳的身體,例行性的檢查和良好的自我照顧也是勞動的一部分。不能像懷孕前那樣吃垃圾食物、熬夜虐待自己的身體,因為這不是妳自己的身體,也不能過勞或讓自己壓力太大,懷孕時體重上升太快也不好,胖不少表示著準媽媽吃得不夠營養。這些關懷都是善意的提醒,保障胎兒和母親的基本要求,只是這些要求和相關的勞動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也是另一種壓力來源。當時懷孕初期身體不適,醒著的時候不斷乾嘔,卻異常嗜睡,嚴重影響我的課業。我獨居而且財務窘困,胎兒雖然不用特別花心力另外照顧,但是在身體不適加上課業壓力大的情況下,我也沒有心力去準備營養均衡的三餐,如果在餐廳吃,一頓比較「健康」的餐點吃下去加小費20美元左右。另外臺灣親友也會傳「養胎」或「瘦孕」等相關資訊給我,這些是當時臺灣流行的準媽媽守則,臺灣準媽媽的懷胎經驗也自動漂過了太平洋出現在我的生活對話中。胎兒還沒出來時我每天都在自責,覺得我沒有給寶寶夠好的照顧。我看著愈來愈不熟悉的身體認真害怕起來: 我這樣生小孩和讀博士都沒問題嗎? 如果沒讀完博士我是不是要把已經拿到的獎學金還回去? 我要怎麼還? 小孩身體還好嗎? 我突然不知道自己和胎兒該何去何從? 不過這一切的焦慮隨著中後期身體穩定和學期結束,心情才漸漸平緩下來,終於享受到一段平靜休養時段。
小孩出生後就是進入無法睡覺的地獄,加上親餵,所以這段時段非常疲累,但是小孩大致健康,看著他每天長大就是最快樂的事情。帶小孩回診時醫生看著睡眼惺忪的我說:妳是個好媽媽,因為妳照顧小孩沒有睡飽。我也記得小孩出生四個月後我復學的那個學期,我已恢復正常上課,再加上當一門課的助教。小孩是個不易入睡,白天也不太會小睡的小孩,整體的睡眠時間很短。入睡前的哄睡大多時間要抱著他一小時左右他才會入睡。通常是晚上九點準備哄睡,大約10點半左右會睡著,我會去洗澡然後念書改學生作業,然後12點半到1點半他會醒來喝奶一次,餵完奶放他睡覺,我再回到書桌前工作,然後我也去睡,寶寶3點半左右會再醒一次,再餵奶,然後6點左右他就醒來了,開始了他新的一天。我記得我帶著擠奶器去學校的哺乳室趁下課時間擠奶,校園內有好幾間哺乳室,分散在學校不同的大樓裡,我的系館沒有哺乳室,我申請隔壁棟的,帶著學校發配的密碼解鎖。常常趕到那裡時已經有3-5位媽媽們在排隊。我得趕著上課,無法等待,最後往往只能帶著擠奶器到廁所。真正在哺乳室擠奶成功的機率大約50%。
這樣的母職安排是很常見的,也是現代母職勞動的特性 「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勞動的強度極高,需要完整陪伴小孩,而盡心盡力、無怨無悔付出這樣品質的勞動,這樣的媽媽才會是個「好媽媽」。所以媽媽在學校或職場也持續進行母職的實踐。梁莉芳(2014)在巷仔口社會學中的小文裡引用Rich 的觀點,提出母職對於女人可以是種壓迫,但也可以是種培力。而母職對女人的壓迫來於父權社會期待女人作一個「好媽媽」,付出無私的愛並順從聽話,善盡份內責任,且不被鼓勵說出照顧小孩的挫折與疲乏。
我想,在各種不成文的規範和實踐中,我終究成為了「好媽媽」,但是「好媽媽」的標準攸關個人經驗,自己的成長與童年經驗、創傷、遺憾有關,親職分工狀態、與伴侶的關係、伴侶和他的家人的關係等有很大的關係。因此這種單一、對於母職扁平化的想像和認知顯然阻礙了媽媽們的自我培力,特別是那些與多數好媽媽有著不同經驗的母親。
貪心的學術媽媽: 小孩子才作選擇,博士學位和小孩我都要
一個朋友看到我當時的慘狀,安慰我:我知道的學術媽媽都會遇到生小孩的困境。一種就是像妳一樣,年輕時生小孩但是沒有錢; 一種就是找到終身職,有了錢,但是已經生不出來。即使這種道理顯而易見,即使大部分的圈內人知道這些現實,但學術媽媽一方面要表現「專業」,一方面又被期待有「與生俱來」的母性,似乎更因為工作時間相對的容易調整,也理所當然作為主要照顧者。
小孩從出生到學齡前的階段我是主要照顧者,當時還在讀書,這樣的「彈性」和缺少穩定收入的狀態,所以我在美國、台灣婆家、台灣娘家、台灣自己的住處、小孩爸爸工作的城市全職照顧小孩。勞動的內容包括全職顧小孩、買菜洗衣等家務工作、小孩的醫療照護(包括打疫苗、小孩手術開刀住院陪伴等)。這些年來習慣了打包搬家、多地移動、租房簽約,帶上小孩說走就走。小孩淺眠,睡眠時間不多,我總是在他睡著後開始寫論文、處理學校事務、申請各種獎學金、準備求職資料等。我的研究和論文也在這段時期裡大幅停擺,但我一直沒有真正停下來,我擔心一停下來就無法再次前進。
我記得有一次小孩的爸爸參加學術活動,我帶著年幼的小孩在會場外等待會議結束。小孩的爸爸和其他與會的朋友出來邊走邊聊,他們聊著會議和相關的辯論,其他未婚未生育小孩的朋友和產後不久的我閒聊,他們很關心我的近況,自然也問起我和寶寶的事情。當時的我覺得我離他們好遠,也覺得好害怕,會不會有一天我就這樣自然而然離開學術圈? 或是被逐出學術圈? 會不會都市傳說都是真的呢? 直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那種像是從惡夢中驚醒的恐懼感,也算是我奇特的產後創傷經驗。不過現在只要看到大型國際會議中有提供on-site child care服務,這個創傷就痊癒一些些。
曾聽過一個都市傳說: 女博士生生完小孩後畢業永遠遙遙無期,或是平均生一胎會晚一到二年畢業。主要原因就是育兒的新生活和家庭生活財務無法允許無薪學術媽媽育兒和學業同步進行,為了家庭整體考量只好配合半放棄自己的學業。另一種原因是當媽媽當得太開心,這些媽媽在育兒勞動上得到安慰,想想讀博士摧殘身心,從無薪學術勞動者跳到有尊嚴的有薪學術勞動感也愈來愈難,於是決定頭也不回遠離學術江湖,說不定還打算再生幾個小孩。這個傳說是個可怕的鬼故事,所以在小孩上幼兒園前幾年,我為了準備資格考、跑田野、不定時的研討會或演講、準備畢業,曾經多次請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媽媽協助照顧小孩。也就是這樣一點一滴把論文寫完,終於畢了業。
公共化「媽媽經」
現在終究撐過那一段母職與學術勞動難以協調的日子,那時的我沒有方法「智性」地「整合」學術勞動和親職勞動,是一個相較之下自我培力失敗的媽媽。我在忙學術工作跑田野時自責沒有辦法好好陪小孩,我掉進了「作個好媽媽」的陷阱; 陪伴小孩時腦子裡日夜組織著學術工作,我掉進「學術勞動彈性」的陷阱裡,怎麼作都不對。
幸好,近年來,我在小孩就學的生活圈裡認識了很多家長,無一例外的是媽媽作為親師交流、家長間交流的主要家庭代表。而我在職場上也偶遇了很多和我一樣的學術媽媽,她們也有很多不同的策略,關於自己升遷、研究、教學等和育兒實踐的安排。這些非正式的母職經驗交流讓我發現,即使每位媽媽的育兒故事各有不同,但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和這些母職勞動陷阱衝突、對峙、妥協、投降的成分。
走筆至此,儘管還沒談到求職過程中的惶恐不安,我還是想說:身為學術媽媽,很切身地感受到:當這個社會用「媽媽經」、「育兒經」來描述母職勞動知識時,往往強化了母職知識傳遞和母職經驗的一般特性,而弱化了每一個媽媽的親職經驗──「學術媽媽」又因為學術彈性勞動的責任制與高度自我要求,更顯得孤立。經歷了博士生媽媽曾經身處的暗夜,也受益於媽媽朋友們的交流支持,我很期待:更多媽媽能在育兒的實踐中得以自我培力,反思自己的親職經驗並與朋友分享,將自己的經驗逐漸提升到公共層次,「媽媽經」才能納入更多元的勞動內容、家庭結構與分工、價值系統等視角,回應目前臺灣親職勞動的性別偏誤。我也期待:與我處境類似的學術媽媽們,能開始與朋友分享妳們的「媽媽經」。
*若你想進一步認識學術媽媽的困境,可以讀:
- 林昱瑄(2019) 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臺灣社會學刊,頁125-180。
- Adrienne Rich. (1995).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Norton.
- Tania Lombrozo (Mar. 2017) A Day In The Life Of An Academic Mom. NPR OPINION COSMOS AND CULTURE
- 沈秀華(2016.4.8) 美化母職,卻忽略母親的勞動, 報導者。
- 梁莉芳(2014) 為母則強:母職作為改變社會的場域。巷仔口社會學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蔡書瑋 學術媽媽的多重勞動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84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