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與時間
停止、啟動與同步的疫病日常
講了一通很久的電話,電話那頭是在密西根大學的好友。她在那個全城封鎖的城市,我在這個看似正常的城市,日常很快地成為我們談話的主軸,瑣碎的生活細節,總是圍繞著自身所在的時間,展開一個接著一個的話題。
因為「超前部署」,台灣避免了一場病毒入侵的災難。沈浸在超前部署的話語情境下,我也不自覺的用一種「超前部署」的敘事方式,分享自己能夠在邊境加強檢疫之前從墨爾本即時返台的經驗,慶幸自己用一張機票的價格換得不用居家隔離禁足兩個星期的行動自由。聽完我的「超前部署」,在「全境封鎖」的密西根州已經度過數個星期禁足生活的友人,用一貫平靜的語氣若有所思的說:「這一個多月來,我們好像每天都處在一種追趕病毒時間的混亂狀態,不斷地做決定、用很快的速度調整生活與工作的方式,努力的想要 make up the time(意指彌補一月和二月逝去的部署時間)。」 一時之間,我有些困惑:在全境封鎖的城市裡,少了人的活動,城市的時間不也變得緩慢,為什麼要追趕變得「緩慢的時間」呢?很會說故事的友人開始用平靜的語調,敘說這幾個星期以來追趕病毒時間的疫病日常。
掛上電話,回頭看看隨手寫上的通話筆記。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都在與病毒時間同步的過程中學習另一種經驗日常的方式,“make up the time” 與「超前部署」的鮮明對比,似乎總結了兩個城市與病毒同步的不同時間經驗,呈現兩種不同的疫病日常。

「停止」的任務
3月11日密西根州出現確診首例,當天州長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隔天關閉所有公立學校,3月13日取消大型集會,三月中底特律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幾天之中,出現幾千位確診個案,密西根成了全美僅次於紐約的疫病重災區,底特律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醫療系統負載過重,幾近崩潰邊緣。緊接而來的全城封鎖更是讓人措手不及,3月24日州長發佈全州居家禁足令(stay-at-home order),那個曾經是如此熟悉的日常,竟然轉眼之間就消失不見。
突如其來的封鎖,讓「停止」變成一項完全無法預期的混亂任務,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被置於必須不斷做出停止的「決定」的迫切狀態,關鍵在於:此一迫切狀態下的「決定」是為了協調人類活動和非人類的病毒活動,如果「決定」所反映的是主動時間測定的結果,那麼「停止」則意味著人類活動從日常時間撤退,接下來可能就是由病毒來接管日常時間。封城前的那幾天所有的訊息都很不確定,每個小時都有變化,Ann Arbor 有二十萬左右的居民,密西根大學有師生十萬左右,城市封鎖學校也要完全淨空,這也意味著:放完春假才剛回到校園兩三天的學生被要求立即離開;正在進行的實驗,不論是有機還是無機、機械還是生物,不論是會動的還是不會動的、天上的還是地下的,不論實驗有多麼艱難、或者有多麼重大的發現,基於安全理由都得停止;圖書館、教室、辦公室、大樓等等,所有公共設施和校產全數關閉禁止任何人進入;電腦、中央空調、電燈、冰箱等等,會動的機器都要關閉避免電線走火;廁所、飲水機、垃圾桶等等衛生設施都要清理淨空。沒有人知道要關閉多久,任何一點點的微小疏失都有可能在十天半個月後釀成重大災難。
在生物實驗室工作的Thomas,只有不到24個小時的時間中止實驗室的運作,過去十年來這裡未曾有一天沒有任何人進出。在實驗大樓裡,每個人都用最快的速度移動、用最快的速度判斷做一個決定、用最快的速度處理有生命的實驗物。這天之前又有誰意料到那些曾經被精心呵護的生命,不僅沒能夠成為「為科學犧牲」的烈士,反倒成了「全城封鎖」的祭品。當疫病時間以一種得勝者之姿佔領日常之時,全速煞車的「停止」任務也就是為了彌補「消失的兩個月」不斷地追趕,諷刺的是,不管曾經多麼抗拒,漫不經心的人們終究也只能夠以獻祭的方式「把時間補回來」(make up the time)。
被病毒綁架的日常
靜止之後再要重新啟動日常,卻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時間已經被病毒綁架,啟動日常也就免不了必須與病毒協商,這也意味著人必須要做很多以前沒有做過的決定,儘管「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決定」;因為對病毒的時間表與計畫一無所知,也就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啟動日常的方案,「總是要試了才知道可不可行」。在全城封鎖中啟動日常,是在各種嘗試與錯誤的決定中學習與病毒同步,重新適應一種被病毒綁架的時間節奏。
(1)從社區時間到面對面時間
社區時間被突如其來的病毒吃掉了。從全城封鎖開始的懷疑、拒絕到接受,人們很快地躲進屋子裡,少了每週固定時間的社區聚餐、家庭日的親子活動、小朋友的共學、社區特色的學習班,社區彷彿進入「沒有時間」的靜止狀態。從事監獄人權改革的 Mary King大概是最早察覺到不對勁的人,一種要把「時間」帶回社區的責任感,在大家都還躲在屋裡不知所措的時候,鼓動社區成立「緊急委員會」,在她的奔走下委員會任命公衛學院的Sharon Kardia 為科學顧問,在3月14日開始運作,只不過要把被病毒綁架的社區時間找來回,就像在異時空被重新啟動的同步計時器,運轉起來十分混亂。
最初委員會想要延續社區聚餐,畢竟這是社區行之有年的傳統,也是最能夠凝聚社區意識的活動,恢復社區聚餐是找回過去時間,對社區日常的復甦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委員會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和規劃如何進行,問題是被病毒綁架的行動實在難以被計劃,從帶口罩的效用、社交距離的管理、參加人數的限制、人流動線的規劃、交談和飲食的規定、環境衛生和空間消毒等等,都使得簡單的聚餐活動變成一項不可能任務,經過幾次討論,委員會最終還是放棄恢復社區聚餐活動的規劃。聚餐活動的取消,似乎預示著過去那種能夠「象徵」社區的共同時間已經一去不復返,重新啟動的社區時間註定是「零散破碎」的多義且不穩定的異質符號,如何能夠確定每個人都跟上了呢?與社區時間的同步成為一種節點與節點的連結,點對點、個人對個人、家戶對家戶的互助合作網絡,一個拉一個直到所有人都跟上了。
在社區時間因病毒綁架而支離破碎之後,社區不再只有一個「同步時間」,參與社區活動的精力全都用在為了時間同步的協商與重組之中。實驗室關閉之後,Thomas的時間從實驗室的黑洞解放,像流水一樣的流進不同的家戶和個人,與獨居老夫婦的醫療時間交會、與猶太媽媽的採買時間交會、與實驗室成員的線上交會、與Lea朋友的玩伴時間交會。有人將這流水般的時間擋在門外,卻也更多人願意將時間化身為流水,開展更多交會的管道,時間之流也就這麼漫進越來越多的家戶、抵達越來越遠的角落,人也就慢慢地跟上了。同步時間的重組也帶來關係的重組。失去學校時間的 Lea 和猶太媽媽的兩姐妹組成學習和玩樂的小夥伴,一天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一起,猶太媽媽為幾位小夥伴安排課程時間,Thomas 以採買時間交換。異質的同步時間促成了超越家戶的關係重組,每一個重組都是協商的結果,共同生活的倫理計畫在一連串關於時間的決定當中實現。
(2)異化時間的神聖化與虛擬化
將時間轉換成商品進入市場,大概是資本主義最偉大的發明,從勞動力到服務到時間表,時間越來越抽象,時間的異化也越來越嚴重。看似無窮無盡地供應的勞動力,將時間的價值從供給的限制中解放,在金融市場裡,時間的價值完全獨立於商品的生產與再生產,時間表(schedule)成為一種商品,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的消費時間商品,失去時間主權的人又能通過消費重新宣示對時間的所有權,這是資本主義對被時間商品異化的人所提供的救贖方案。
病毒的活動切斷了時間商品的供給,時間因病毒的吞噬而變得模糊不清,結果似乎產生兩種現象。第一種現象是異化時間的神聖化:越死板固定的時間,也就越容易產生一種穩定的幻覺( fantasy),好像追趕那麼一個剛性(rigid)時間就可以遠離病毒,也就可以緩解支離破碎的恐懼,而時間表(schedule)似乎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在病毒肆虐過後還留下來的時間表,以一種更強硬的方式支配著全城封鎖的日常。比如說:因為不能進超市購物,就得在網路上預訂各家超市的停車取物服務,各家超市每個星期釋出的時段有限,通常剛釋出幾個小時之內就會額滿,為了搶時段,每週總要那麼一天要全天候的掛在線上搶時段,然後再有那麼一天要安排取物行程,在預訂的時間連跑數家超市取回購買商品。當時間表成為商品市場裡的缺稀商品,救贖成為一項殘酷的競爭,不能協商的時間表,錯過了也就錯過了,只能重新再來,同步也就只是一種異化的手段,保留也就只能是一種特權。
第二種現象是異化時間的虛擬化:在全城封鎖的窘境底下,能夠從病毒權柄中脫逃的時間,除了像流水一樣面對面時間,還有在開機/關機、啟動/靜止、連線/斷線中同步的線上虛擬時間。虛擬時間雖然不是假造的,卻是由各種「等待」的空白時段所串連起來的不連續時間——等待表訂時間的到來、等待那個人上線、等待得到回覆、等待最新消息等等。日常的空白時段(如找停車位,跑教室趕場,接送小孩後和其他家長寒暄)被開機/關機的虛擬時間取代,不連續的虛擬時間、不連續的本體,破碎的時間經驗甚至挑戰本體的真實性。
不管是神聖化還是虛擬化,都意味著異化時間的符號地位受到來自病毒性的挑戰,時間的價值可以不再受到商品化邏輯的制約,如何在病毒性的相互觀照中,推進日常的時間主權進而重建日常的主體,將會是一個重新學習「過生活」的過程。
(3)重啟制度時間的日常?
如果說靜止是制度時間的自我閹割,靜止任務有多大的混亂,重新啟動就有多少的騷動。維繫Ann Arbor 城市命脈的密西根大學也是緊緊繫住每個人「生命線」的制度時間,自3月12日關閉以來,學校已經停擺數個星期,這段期間校園只是極低限度對教職員工開放。剛開始的時候,有些系所曾經企圖通過出入管理為系所空間解禁,很快地一些嘗試解禁的措施,在病毒的不受控制下又都停止。被病毒綁架的制度時間呈現一種荒廢的狀態,失去前進的動力連維繫都顯得軟弱無力。制度穩定的前提是時間的連續,重啟制度時間涉及到的也就不只是從停止狀態到運轉狀態的「恢復」而已,還涉及到那些被病毒吃掉的時間能不能補得回來的延續性的問題,當制度時間再度啟動,被病毒綁架前與後的不連續性,已經注定制度時間必然要在斷裂的前提下重構議程(agenda reforming)。
4月14日這一天,密西根大學的校務行政主管主持了一個線上的「市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全校的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教職員工等等,只要是參與學校這個制度的相關人士,都有參加市民大會的資格,三千多人同時上線的巨型會議,在密西根大學應該也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這種市民大會性質的會議本來就不是要做決定的會議,通過參與而達到同步才是會議的目的,會議中同步開放 google sheet,作為參與者的發言平台,各種提問和建議一條一條的增加,反映學校裡各種身份和處境的成員所關心的不同話題和正在面對的不同挑戰。時間是大家共同的焦慮,研究計畫的執行時間、畢業和修業年限、升等與續聘的時間、授課與工作的時數等等,被病毒吃掉的時間能夠補上嗎?又該如何補上呢?又或者應該補上嗎?
當病毒與制度看不見彼此,制度時間與病毒時間展開的是一場競奪主體的戰爭。前者將時間的運轉建立在一套用質的評估與量的累積來審定時間的使用效能的制度之上,審定的結果轉化成考績與薪水的數字,做為制度宣示時間主權的象徵,以及客體化行動主體的時間指標;後者將時間的運轉建立在病毒的移動軌跡與速度,病毒向制度的時間主權宣戰,從制度手中俘虜主體、摧毀指標。病毒的存在顯示制度的脆弱,重啟制度時間的議程重構將會是個冗長和繁瑣的過程,但是如果制度只是想要不顧一切的強勢回歸,如果這個過程只是為了有一個方案補上被病毒吃掉的制度時間,重啟制度時間也只是回到那個被指標化的機械式的日常,制度和病毒還是看不見彼此,回到這樣的制度時間是我們期待的嗎?對於制度時間我們能夠有其他的想像嗎?看見病毒的制度會不會更加溫柔、更加人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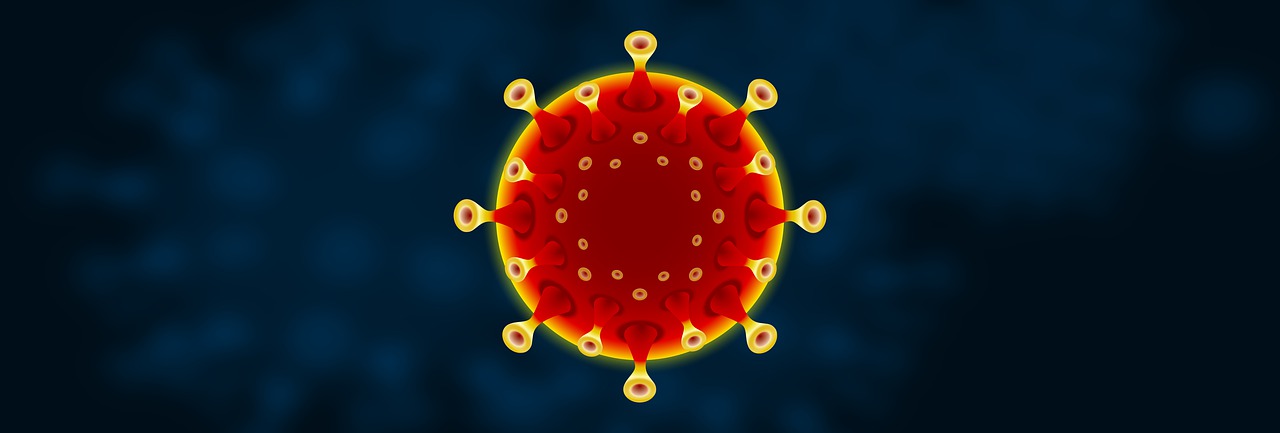
與病毒同步的疫病時間
3月初開始,白宮草坪上的防疫記者會就成了與川普疫病時間同步的媒介。在川普的疫病時間裡,病毒的軌跡有一個超越疫病的政治計畫,隱身在與中國對抗的時間表當中。先是指名中國病毒、批評中國隱瞞病毒軌跡、指責世衛失職、又是攻擊中國將病毒帶到全世界、指控病毒是中國製造的實驗室病毒等等,然而,與中國對抗的政治計畫對病毒而言無關痛癢,川普的疫病時間非但沒有讓人與病毒同步,反倒掩蓋病毒的意圖,輕忽病毒的移動能力。每天節節上升的確診人數依舊看不到高點,病毒像火山爆發的岩漿流竄到全美各地,地圖上染上病毒顏色的州越來越多、顏色也越來越深,直到填滿地圖的每個角落、取代地圖原本的顏色。地圖上顏色的變化宣告著病毒時間的勝利,掩藏不住的是對川普時間的訕笑。
在台灣許多人在時中的疫病時間裡找到與病毒同步的安全感,那是一種可以被計畫的病毒時間,允許人們能在同步當中重新佈署疫病中的日常。從1月20日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以來,每天下午兩點準時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中央防疫記者會,彷彿回到三十年前新聞聯播的那個年代,只不過這回不是播報新聞,而是宣告防疫委員會每一天的新「決定」。一個決定帶來一個改變,從取消中國旅行團的入境簽證、自主健康管理的防疫措施、隔離檢疫的執行辦法、寒假延長開學延後、取消入境航班邊境封鎖、擴充口罩產線、調整口罩購買限額、禁止防疫物資出口、社交距離管理規定等等,一天一點的小改變、一點一點的小改變累積成更大的改變,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日常已經和疫病時間同步,出門前記得戴口罩、進入室內量體溫、用酒精消毒、減少外出和多人聚會、不再追逐排隊餐廳,病毒顯然已經成為共同生活中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我們努力地在病毒路徑和活動空間之間編織起一面保護網,在疫病時間中熟悉的日常依舊緩慢前進,小心地不打擾病毒,深怕一不小心病毒會衝破脆弱的保護網。4月17日連續兩天無確診病例,舉國歡騰,圓山飯店外牆打上ZERO的燈光秀,記者會上的時中指揮官仍舊不忘提醒國人:疫情嚴峻,防疫不能鬆懈!
中央防疫記者會,一天一會、每天至少一個小時,已經持續一百多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在每天下午兩點守著螢幕看記者會,至少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守著時中記者會的人,比守著股市開盤的人還多。時中指揮官條理分明的報告、幽默風趣的回應、果斷謙虛的發言,好的政治語言令人愉悅,跟隨著時中部長掌握確診人數、追蹤病毒軌跡、爭議口罩的分配數、猜測旅遊景點的出遊人數等等。數字成為一種比真實更加真實的符號,人人都成了數字專家,在數字的智識活動中發展出一種防疫指標,彷彿病毒令人害怕的感染力,都可以通過數字來掌握。
病毒的移動速度決定了疫病時間的速度,疫病時間的速度成為日常的壓力。在正常與崩潰、行動與靜止之間維持一種物理平衡,這是在「臨界點」的倫理生活,小心謹慎的呵護著脆弱的日常與隨時可能被取消的行動自由。四月初春假的移動人潮,擾動島內時間速度與日常壓力的物理平衡,社交距離與移動速度顯然重新定義了在疫病時間下的日常倫理。
春假第二天,社群媒體上的幾張照片炸開島民的集體焦慮,墾丁大街、花蓮夜市滿滿人潮,連假第三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緊急公吿十二處人潮過多的旅遊景點,呼籲民眾加強自我管理旅遊足跡。春假最後一天的晚上,大台北地區的家長群組,因為各種來自醫師的建議和醫院內部消息引起不小的騷動,開學當天不少家長幫小孩請假,視疫情狀況再做是否回學校的決定。還記得那天早上,聽說兒子學校有不少學生連假在墾丁和花東出沒,就一直無法決定是否應該幫兒子請假,七點半小孩坐上校車,八點鐘我和平常差不多時間出門,出門後卻無法決定要往哪一個方向前進:是到學校接回小孩?還是到辦公室啟動連假後的日常?我在前往學校與前往辦公室的交叉路口把車停下來,坐在車內等待十點鐘防疫指揮中心的臨時記者會,打開收音機聽到時中部長說:建議連假期間曾經前往人潮較多地點的民眾,執行自主健康管理。聽到這幾句話,我突然懂了,很放心的用一個「倫理」的理由,做了以「信任」為前提的決定:相信那些在春假期間全家出遊的學生和家長,會留在家中自主健康管理。春假結束的兩週之後,令人擔心的「破口」並沒有出現,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度過一次的危機,並不代表不會有下一次的危機。事實上,在零確診的兩天之後,海軍敦睦艦隊爆發疫病以來最嚴重的群聚感染,三十多位確診、七百多位隔離檢疫,病毒的足跡遍佈全台,二十多萬人可能曾經暴露在病毒之中。在與病毒同步的疫病日常裡,看不見病毒並不表示病毒不在場:我們會與病毒協調旅行的時間表,預留14天的隔離檢疫時間;會跟隨著確診者的足跡回溯,重新組織自身的時間經驗;也會根據1968專線的人潮監控系統,決定何時出發、前往何處;在收到細胞簡訊之後,考慮要不要取消接下來的社交活動;甚至還得要在規劃會議之前,參考WHO的全球疫情預測。我們從「看見病毒」開始學習共同生活,在時間測定的決定中,調節病毒的生命節奏與行動韻律。
對日常時間性的再思考
這篇文章從與病毒同步的過程來展開疫病日常中的時間經驗,材料和論證都不嚴謹,只能算是研究日常中的隨思雜記,如果真要說出一個問題意識,我想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疫病日常的時間性會以什麼方式成為意識的對象呢?在探索日常時間性的背後,是對現代性的困惑:如果作為一種時間經驗的現代性的結束已經開始,那麼「病毒」是否可以是海德格用來定義日常時間性的「首先」與「通常」?或者更明確的說,如果病毒已經正在接管「日常」重新定義時間性,那麼疫病日常中的時間經驗是否預示著現代性及其體制將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呢?當然這些假設性的問題,都不會有明確的答案,而是作為思考疫病日常與現代性對話的起點。
我用了很長的篇幅描述與病毒同步的過程,對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而言同步即時間本身,時間是「將兩個或多個在事件過程中持續運動的位置或段落『置入關係當中』」的同步手段(p34),能夠在社會世界裡定位人類活動,調節共同生活(p25)。 這是將時間視為一種「符號現實」(semiotic reality),由於事件的過程本身就是可感知的,「關係」所呈現的是認知者對這些感知的加工或者標準化的結果,在可溝通的社會象徵中被表達,應用在事件流中,就成了確定社會活動的位置或其間的手段。Norbert Elias 所說的「定位」是以人群為中心的符號現實,在病毒的肆虐下,這樣的符號現實卻顯得不堪一擊,與病毒同步的時間經驗顯示,協調人類活動和非人類病毒活動的時間符號,並不總是朝向同質、抽象與制度的異化時間演進,異化時間或許是能夠支持資本主義的時間經驗,卻也任由符號任意性褻瀆主體或他者的時間主權。
對於時間的闡釋,除了將客體化視為一種異化過程的典範以外,另一種客體化是觀照或者體察經驗結構的現象學典範。1927年海德格出版了他的曠世巨作《存在與時間》,這本書有一個遠大的計畫是通過對時間的闡釋具體探討存在的問題,現象學的取徑將時間經驗視為此在的展開狀態。對海德格而言,時間性使此在的存在成為可能,此在在各種存在狀態中展開自身,在領會、情緒、沉淪和言談等存在結構中組裝經驗,時間將經驗組合成連續序列在地平線上綻放進入空間,自身因而在時空中有了一個寓居之所。然而,這麼一個建立在「此在」的存在主義哲學卻是敵視日常的。儘管海德格的確清楚的認識到所有能夠描述此在存在方式的那些結構都得被回收到時間性之中,海德格對日常狀態的描述卻是「單調」,「單調」是一種對日常時間性的領會,能夠「把無論這一日帶來的什麼事情都當作變化」(頁485),儘管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慢,但還是沒有能夠記得時間的樣貌,日常狀態就像是一則沒有英雄的平凡故事、沒有signature的言談、沒有歇斯底里的情緒、甚至是沒有痛感的沉淪,而這一切都指向日常時間性的「未思」,反映出此在對「他者」的漠然。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這本書裡的慣性鬼打牆,經常會對時間性與日常發出一些驚人之語。在這個與病毒時間「同步」的疫病日常裡,我思索著海德格對「日常」的敵視到底說的是一個存在主義哲學上的結論,或者是海德格對日常狀態的領會?1920年代的歐洲是個充滿驚奇彷彿所有不幸都說好了一起降臨的動盪時代,正值盛年的海德格卻迎來了許多人一生夢寐以求的日常狀態。1923年他開始擔任馬爾堡大學哲學教授,在托特瑙堡營造了他自己的別墅(the Hütte),並開始專注寫作《存在與時間》的第一稿。他的教學出眾,獲得許多榮譽,他的神學家同事也都是一時之選,使他在思索存在主義的問題上有長足的進展,1926年他把自己隱居在他的別墅,用很短的時間完成《存在與時間》初稿。然而,對一個歧視猶太人的德意志主義狂熱者,在德國正面對生死存亡之際,享受或者說是寓居於夢寐以求的日常狀態,或許是令人難堪的。想像他隱居在別墅裡,享受著不被打擾的寫作時光,思索著存在主義的大問題,在柏林正在發生的大規模失業潮、四面楚歌的共和政府搖搖欲墜,歐洲政局每日都有新的變化,所有的擔憂與焦慮都被禁錮在一個「單調」的日常狀態之中。或許對海德格而言,真實生活中的日常是令人尷尬也是令人沮喪的存在狀態,日常時間性像是有一種魔力,把一切所有的不穩定甚至應該是驚天動地的變化,變得平凡甚至成為一種自帶某種節奏的慣性(routine),這個無法被逃離的狀態,竟然也就成了「從時間性闡釋此在」的難點,就連海德格自己也不諱言地指出,「只有在對一般存在的意義及其種種可能的演變的原則性討論的框架內才可能充分地從概念上界說日常狀態」(頁487)。海德格「從時間性闡釋此在」的哲學計畫終究永遠沒有能夠完成。原本計劃寫作二部共六篇的《存在與時間》僅僅完成了二篇的導論部分,其餘的寫作計畫也無疾而終,甚至在1936年以後,海德格的哲學思考全面轉向詩意。
病毒綁架了日常狀態,也修改了日常的「時間性」。如果說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用世故與狡狤的眼光看待日常,那麼在病毒的肆虐下,海德格筆下那個「單調的」日常時間,顯然不可能也不應該存在。海德格對日常的敵視乃至對他者的漠然,就如列維納斯對海德格的批評,過度高舉此在的倫理學反倒讓人無視主體對他者的暴虐,海德格的存在主義精準的捕捉了現代性體制的暴力,而病毒性卻能夠以一種輕巧的方式摧毀現代性的體制,這不是病毒的反抗也不是意識形態的操作,病毒就只是存在而已,它的存在顯示對他者的無視衍然就是現代性體制的缺陷,這樣的缺陷可能導致體制的全面崩潰。同樣的,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班雅明在《柏林童年》中用天真與欣賞的眼光看待日常,在病毒的肆虐下,班雅明筆下那個「進步的」日常時間,也許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在《拱廊街研究計畫》裡,城市漫遊者生動活潑的進步日常,或許精準的捕捉現代性的創造力,病毒卻使得這一切的行動都變成是危險的,危險帶來道德上的疑慮,病毒的存在直指現代生活的倫理缺陷。
如果說現代性的時間經驗讓每一個人都成為存在主義的哲學家,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期待,疫病日常的時間經驗,讓每一個人都成為規劃共同生活的倫理學家?雖然說現代意識的起源總是被回溯到啟蒙時代,作為一種時間經驗的「現代性」卻是時間性成為意識對象的近代現實,反映的是「日常」被問題化的一種存在狀態。十九世紀以來新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在戰爭和瘟疫的襲擊下幾近崩潰邊緣,就此拉開後帝國主義時代的序幕,去殖民運動和自由主義定義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秩序,工業化、全球化和金融化成為現代性不可逆轉的趨勢。各種快速變化的現實挑戰讓日常的穩定狀態,被動時間經驗被任意性所佔據,無法迴避的日常需要一種新的時間觀來駕馭不確定的和不可預測的變化,安置在日常狀態下主動的時間經驗。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那些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突然之間失去前進的動能,崩潰會取代進化重新定義後瘟疫時代不可逆轉的變化趨勢嗎?瘟疫之後的人類世體制如何規劃共同生活,對病毒性的觀照帶來倫理生活的可能,對於這樣的可能性我們樂觀以待。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黃淑莉 病毒與時間:停止、啟動與同步的疫病日常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825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