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蟲化身的吟遊詩人
修・萊佛士(Hugh Raffles)的「一昆蟲一世界」
昆蟲作為知識
「人類學家為什麼書寫昆蟲,而不讓『專業的』昆蟲學家來就好了呢?」初次閱讀《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的讀者,也許會產生這樣對人類學者「跨界」處理「專業」議題的質問。如同對於研究人類生活世界裡的民族植物,宗教儀式, 經濟活動,甚至傳統慣習人類學的質疑,為什麼不讓植物學者,宗教學者,經濟學者,法律學者來就好呢?
「當然不同!」人類學家如此回答。除了強調「文化差異」觀點反映從主流或者科學性研究的單向思考之外,人類學研究所呈現的不只是知識內容,還包括知識生產過程的社會情境與歷史背景,以及透過該知識所反射出的人類思維特質。最後還會再進一步考量,專家(不論是科學家或者是在地達人)建構該知識的同時,所展現的權力與倫理觀點,並且反省如何透過該研究對象呈現特殊的生命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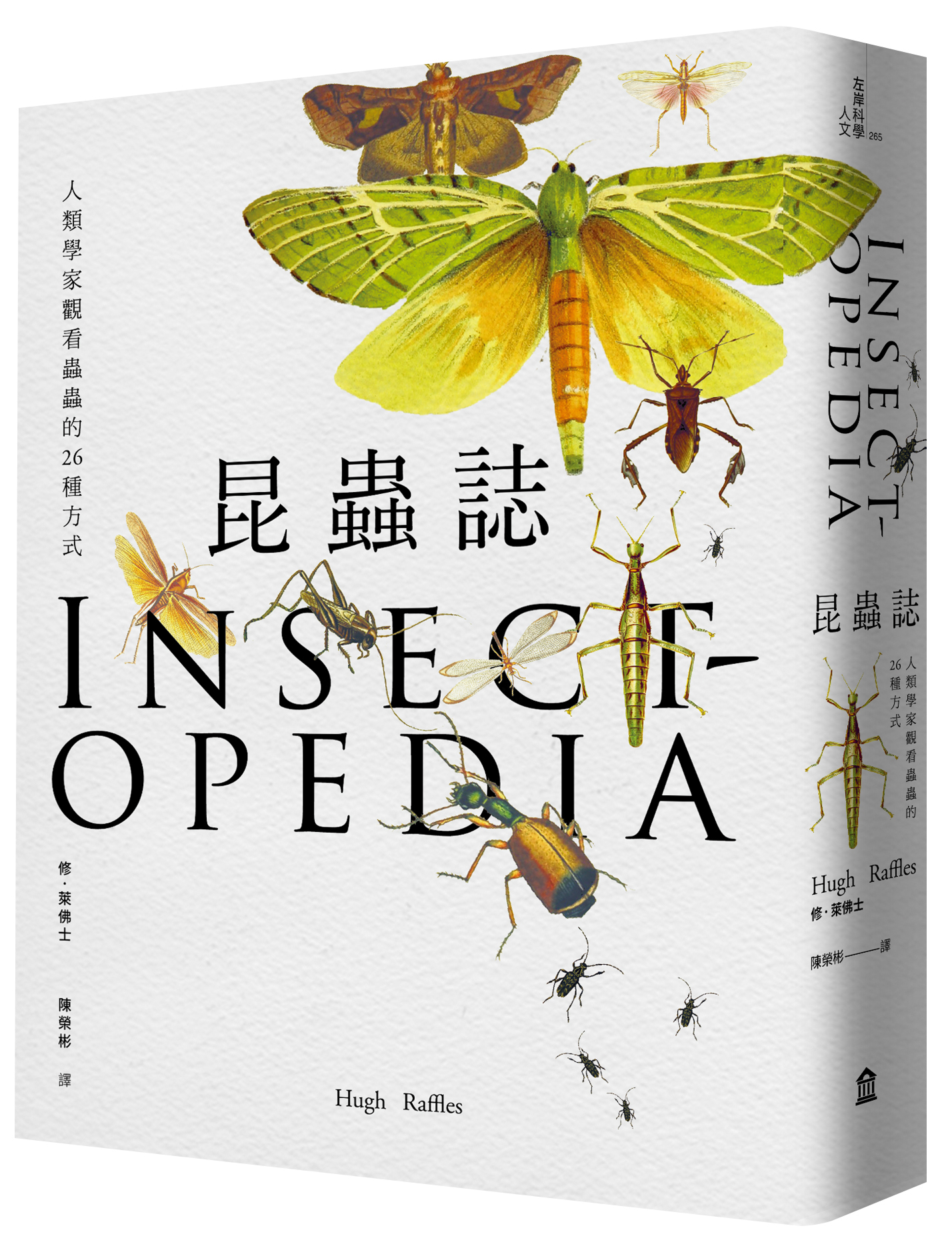
舉例來說,當研究工廠對海岸產生污染問題的時候,人類學家不只要跟漁民一起出海瞭解海洋污染的情境,學習漁民如何辨識或者避免污染海產的能力,還要出席科學家與地方官員向地方漁民說明污染的公聽會,瞭解政府官員處理(或者不處理)污染問題的策略;也要呈現科學家所提供的污染研究數據與方法,與科學家一起採集「科學證據」並且學習如何辨識證據,更包括污染知識如何從實驗室的建構過程回到日常生活的解釋;最後還要瞭解與分析工廠與漁民的關係(比如工廠與漁民並非決然對立而可能有僱傭需求),瞭解工廠在當地進行的生產以及其政治經濟效應,並且分析因工廠設立對「非人物種」(比如潮間生物)以及歷史地景(比如養殖漁業環境)的衝擊等等。
就這個案例看來,人類學家在處理問題時不能只是以學科分類來羅列知識與排列觀點,還需要對比各種知識生產情境所產生的意圖與非意圖後果,以及各類組織對該議題所進行的回應與行動。這些是人類學家在做「科學性題材」研究時,和「專業學科」學者不同之所在。即便使用不同取向的知識體系以及對話來面處理跨學科議題,人類學家仍然面對知識所呈現出來的「倫理議題」:以專家語言呈現該學科議題的內在邏輯,如何與常民活動運作時的生活或生命層次互相關聯,甚至產生政策性或者價值性的判斷?
「物化」自我
《昆蟲誌》所呈現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人類學知識觀點:除了陳述昆蟲與人類的關係(包括對昆蟲的科學研究與日常運用)之外,更深入這些「物種知識」所產生出來的倫理關係以及歷史脈絡。作者修・萊佛士(Hugh Raffles) 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在倫敦成長,二十四歲移居紐約。學術訓練背景為耶魯大學森林與環境研究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人類學系。作為人類學者前曾經當過計程車司機,清潔工,還有無數的文字工作活動。他的第一本書是In Amazonia,這本由博士論文章節延展又改寫的書籍(其中有一篇關於蝴蝶的收藏史曾經先發表在《美國民族學家》期刊裡,據說原來有一百頁!),為他贏得美國人類學會人文分會的Victor Turner書獎。而《昆蟲誌》出版後更是佳評如潮, 贏得4S學會(國際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的Ludwick Fleck 書獎,紐約時報年度選書,「獵戶座」Orion人文書獎,以及2010年懷丁(Whiting) 寫作獎;這些都不是人類學者平常有機會取得的獎項,而是給予文字表達具獨特性以及反思研究領域具重要貢獻者。與其說萊佛士是以人類學者的身分做昆蟲研究,還不如說他討論的是人透過與昆蟲的連結過程中,感官的多樣性表現,對人類處境與昆蟲處境的對比/類比,這一連串思維所創造出來的「親密性知識」(intimate knowledge,這也是他先前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人類系任教時提出的論文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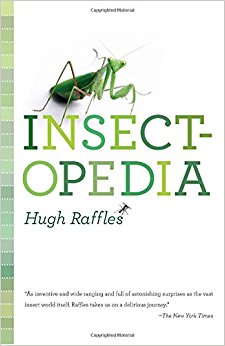
他還研究「收集」在人類學的意義,反思「時間」與人類知識之間的關係,這個研究旨趣引導他走向關於「石頭」的反思。他收集不同的石頭,也收集石頭收藏家的故事,同時還思考文化的「範疇」和「規模」如何透過石頭展現出來。《昆蟲誌》的書寫裡面也討論許多關於「種類」、「觀察」、「意義」、「存在」等等議題。而在討論石頭的脈絡裡,這些問題的時間性更加延伸,但思維對象的共同存有性卻和昆蟲完全不同:石頭的基本狀態是恆定、冷漠、完全非生命。他參與杜克大學舉行的《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出版二十五週年的研討會時,嘗試詢問,對於書寫對象為「族群文化」的人類學者來說, 「石頭民族誌」的挑戰為何?在探索石頭的普同性和特殊性之間,他發現石頭與人的關係,就是「讓我著迷的對象同時也占據了我」(what preoccupied me occupies me)。思考石頭是漫長時間軸下人類對於存在狀態的自我質問。
這樣的觀點在昆蟲的描述中也同樣出現。在關於昆蟲〈視覺〉的討論中, 昆蟲愛好者或研究者,設法透過各種觀察方式和研究器材,模擬或者拆解昆蟲身體以及行動路徑等方式。萊佛士以此細緻地描繪「透過觀察客體使我成為該對象」的想像和慾望過程。這個想法和人類學常使用的另一個意義化概念「體現」(embodiment)相似,但對於主體與思考對象的觀點卻有截然不同的想法。「體現」指的是讓體驗者作為意向主體,將外在的環境狀態以及客觀物質的運作,透過身體經驗的方式,產生可以解釋意義的身體技術。而昆蟲研究者、觀察者,或甚至是那些踩爛昆蟲以達到性高潮的特殊癖好者(不奇怪,請見本書〈性〉),其實是透過「進入」或「穿戴」的過程,讓昆蟲的感官或者是行動方式「占據」我之後,才得以完成「想要進入另一個自我體內,但又無法被滿足的強烈渴望」(見〈視覺〉第三節)。看起來是「被物化」的操作,卻恰恰使得自我得以在「物化」過程中發現特殊的主體經驗。
對比與規模
物化自我的認識論在本書中還有其他精彩案例。例如〈G:慷慨招待(歡樂時光)〉和〈P:升天節的卡斯齊內公園〉同時談到的蟋蟀文化,前者是中國傳統昆蟲比鬥在現代化操作下的「感受分類」以及蟋蟀性格特質裡的「五德」,後者是南義大利地區在春天升天節日時,城市居民在公園裡聆聽吊掛在籠子裡的蟋蟀聲音感受季節到來。在〈P:升天節的卡斯齊內公園〉,萊佛士話鋒一轉,提到佛羅倫斯出產的童話「木偶奇遇記」以及其中的蟋蟀,但蟋蟀卻是被道德化的童話故事裡面勸說小木偶的「良心使者」。這個物化自我的表現形式讓昆蟲也成為得以被思考甚至被模仿的意義化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從催促紡織的「織娘」到珍惜時光的「知了」,都透過模仿人類而成了意義訊息的使者。

對昆蟲生命短促的感受投射,以及勤奮的蜜蜂活動等等提醒人類的「道德行為」,展現出思考昆蟲時的另一層次:「對比與規模」。 我們常說「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從微小畫面的觀點來看,昆蟲提供小宇宙層次的觀點。在〈車諾比〉,萊佛士特別以受車諾比核災影響的突變昆蟲為例,告訴我們一個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昆蟲拍攝與繪圖藝術家,如何長時間追尋核災後歐洲各地盲蝽或者果蠅的微小體型差異,並表現出特別的畸形樣式。這名藝術家在尋找畸形盲蝽的過程中,竟被醫師以畫圖的方式告知自己懷胎的嬰兒(因為核災?)也是畸形。這是從物化自我擴展出來的平行主體,但同時讓人類的尺度與昆蟲的渺小得到等同的對比。
但昆蟲也可以很大,尤其是數量所聚集起來的「龐大」。萊佛士的書寫旁徵博引又漫步在細節之中,讓閱讀者在昆蟲以及他們所形成的空間內外不斷來回跳耀。昆蟲此時成為「異類」與「我族」的兩種共時比喻:昆蟲的形體/質地/外型之種種,都讓人類感到與自己差異極大,而將其型態投射在所謂「異形」的模樣想像上。
然而昆蟲的行為規則、集體活動、生活模式等等,看來卻又與人類的社會性極為相似,這種綜合性提供恰如人類生存關係的矛盾。在〈馬哈瑪內正開車穿越尼阿美〉的章節裡面,作者提到蝗蟲與非洲尼日居民在吃與被吃之間的差別。平常蝗蟲是市場上販賣的美味,甚至還有特殊的調味風格以及飲食饗宴的共食節日(中國集體抓蟋蟀是為了投資與比賽,尼日集體抓蝗蟲則為了販賣與宴客)。但是在氣候或者生存資源變動的情境下,蝗蟲會「變形」成為大型飛翔除草機,從可以駕馭的食材變成遮天蓋地的蝗災。這個對比關係也暗示了殖民經驗下的主奴性質轉換;萊佛士引用非洲文學家奇奴瓦・阿契貝(Chinua Achebe)的比喻說到:「我忘了跟你說,神諭還提到一件事。神諭說,其他白人也要來了。他們跟蝗蟲一樣,第一個白人只是來探路的,被派來勘查土地,所以他們殺了他」(O〈馬哈瑪內正開車穿越尼阿美〉,第一節)。殖民與被殖民、吃與被吃、物化模擬以及主體經驗;這些對比不斷出現在人與昆蟲的關係裡,也因為規模的不同產生差異極大的結果。
昆蟲是好的思維對象?
在〈P升天節的卡斯齊內公園〉提到:「當歐洲人於十九世紀初挺身為動物爭取福祉時,剛好廢奴運動(Abolitionist movement)也在同一時期崛起。這兩種運動往往共享組織資源,也有許多人同時參加兩種運動,而且他們跟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者一樣,也相信人類的存在具有優越性,因此也要承擔家長一般的責任。」廢奴運動與動物福祉運動的同時出現,卻標示著對於特定類別的動物較為關切(尤其是擁有與人類溝通能力的那類動物),進而反映在人種關係的差異區辨,轉而對非我族類的人予以排斥甚至屠殺:書中非常鮮明而駭人的案例就是把猶太人比喻為蝨子, 除去猶太人就如同為社會進行身體清潔。此時讓我們回到前面談到作為知識對象的昆蟲。萊佛士提到海德格論述存有狀態不同層級的差異:「石頭是『無世界的』(worldless),動物是『貧乏於世界的』(poor in world),而人則是『建構這個世界』(world-framing)。」這段話似乎能對照出我們與當代的原住民狩獵權益以及動保團體的對話:當代社會試圖以「是否能夠對於傳統領域取得建構世界的觀點」(也就是誰是土地上的「人」,而人類的道德感勝過與動物的互為主體關係),來決定該知識主體是否能夠作為繼續狩獵與使用土地的依據。但原住民所持的狩獵觀點可能因為對於領域上的其他物種以「過於互為主體」(也就是,打獵使得雙方可能都會受傷甚至死亡)的方式來互動,以至於被認為比「豢養宰殺」要為野蠻,也需要被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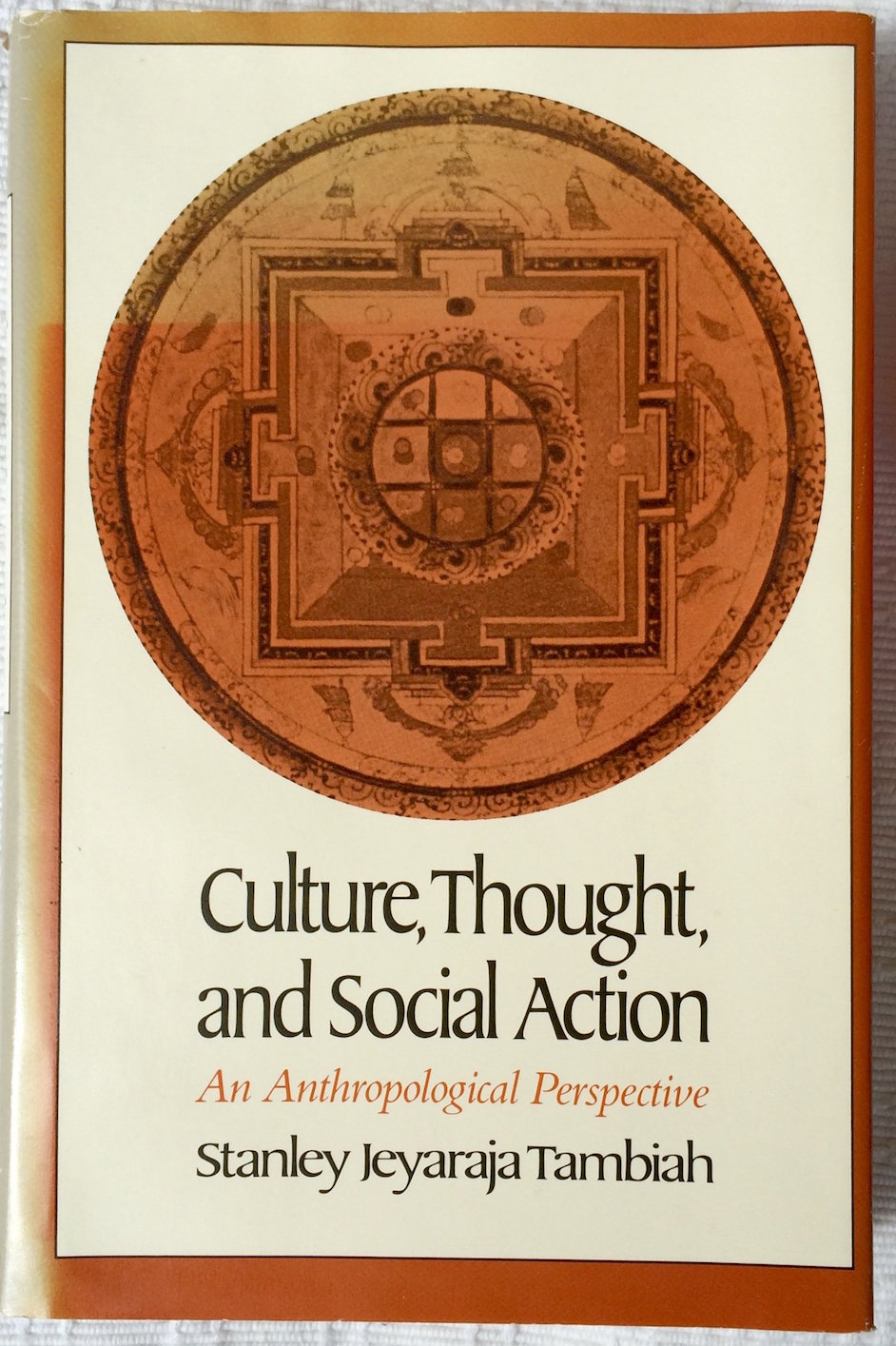
"Animals are good to think and good to prohibit"
如果你是人類學同行,可能會想到另外兩位人類學者有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論述:李維史陀說「動物是好的思維對象」,因為動物代表了人對自然物種的對立與使用狀態,也反映結構主義把人的思維建構在物種關係的操作上。而湯拜亞(Stanley Tambiah)模仿李維史陀的說法,提到「動物是好的思維對象,也是好的『禁止對象』」則結合了思考動物作為象徵以及文化脈絡(運用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潔淨與危險」中的對比)。如果從台灣當代原住民狩獵議題再來看這兩個論述,可以發現以象徵和思維結構產生的道德論述,並沒有帶給我們解決問題的路線,反而落入將文化本質化的運用。
萊佛士從昆蟲科學研究的論述提醒:「我們面對一個兩難的處境:一方面總是無可避免把對自己的理解硬套在其他生物身上,但另一方面還是會意識到自己與其他生物基本上並不相同。」(T〈誘惑〉,第五節)。這個提醒雖然是來自在昆蟲研究中揣測「生物世界的意圖與真實性」(T〈誘惑〉中提到的昆蟲學者用詞),我們也可以回頭詢問反對原住民狩獵方式的人,對於在地族群生存的意圖與狩獵情境真實性的理解,是不是在現代想像中,都被可替換的功能性觀點(例如蛋白質需求或者市場買賣)所取代了呢?當動物透過圖騰成為結構意識下的分類,昆蟲卻未列名其中,不是因為他們無法分類,而是昆蟲在受到觀察者所反映的情緒與使用意圖時,就反映出人在思考時不自覺出現的階層性。當昆蟲研究者都可能誤認生物真實行動的意圖時,我們如何宣稱理性與道德觀點比原住民知識更優於看待動物的狩獵關係?
從多物種民族誌與本體論轉向出發
人類學研究近年發展的兩個取向,都強調從「非人類」觀點來呈現人類學議題的衝擊與反思,其一是「多物種民族誌」,另一個是「本體論轉向」的人類學研究。多物種民族誌的立場在於,從「人類發言中心」的書寫與觀察位置產生的「部分真實」(partial truth),轉換為由其他物種為觀察起點時,可能相互發現的「另類現實」(alternative realities)。而人類學的「本體論轉向」,則反思知識論研究如何呈現唯一的現實世界的問題,轉而重視多重世界(multiple worlds)的存在。因此本體論反對人類中心的單一文化觀點,強調現實(realities) 與世界(worlds)的複數型態。引用人類學家愛德華多・科恩(Eduardo Kohn)的說法,多物種民族誌關切人類與其他「活生生的自我們」(Living Selves,這裡不把「自我」當作人類獨有的觀點)互相交纏下的「生命人類學」整體,同時關注多重的有機體之間如何透過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互相形塑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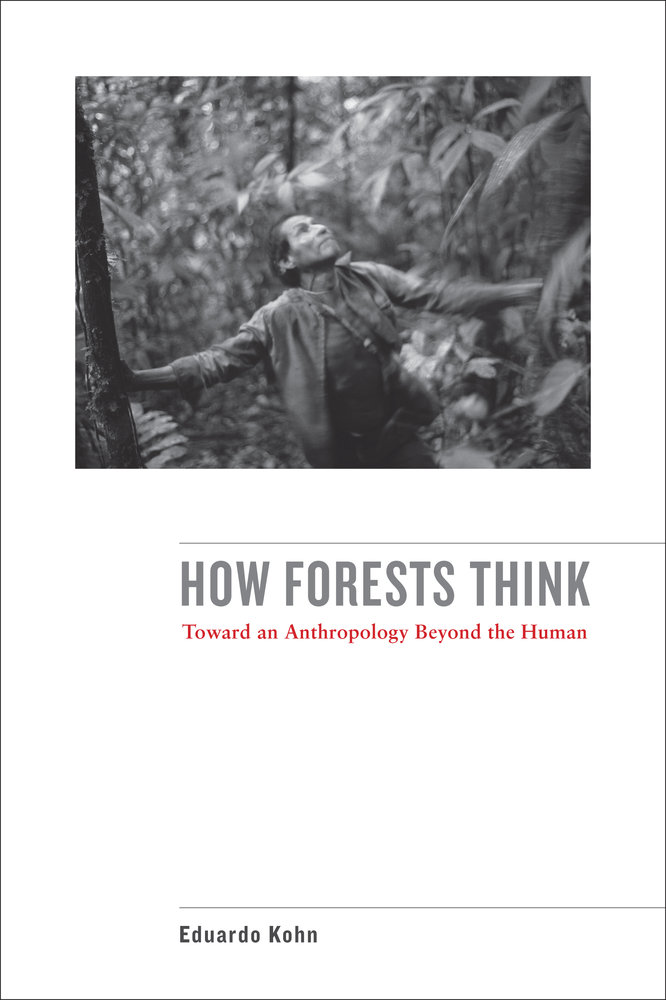
這兩個論述的實踐同時出現在《昆蟲誌》這本書裡。「多物種民族誌」取向上,我們看到物種與人類世界的交會成為瞭解該物種以及人類自身活動的必要方式。從萊佛士有興趣的研究題材來看,他的取向和「新文化史」的物質生命史考察接近,都關注到非人物質如何引發並且呈現出文化或族群的特殊活動。不同的是,他並不以昆蟲使用與交易等等人類為主動的行動層面上進行討論,而是針對如何思考昆蟲、觀察昆蟲、使用昆蟲一直到被昆蟲影響的人類災難,當作相關的整體,也因此呈現出與「新文化史」不同取向的觀點。
更進一步從「本體論轉向」的書寫看來,萊佛士透過行動網絡內的多重行動者對照,甚至包括「技術擴增真實/實境」(technology-aid realities)來呈現人如何看到、聽到、感受到昆蟲的世界。在接近書末的〈W全球暖化的聲音〉裡,萊佛士為我們描述了研究者透過聆聽樹木內昆蟲活動的聲音,而發現到昆蟲的行動不只是早先版本的費洛蒙生態觀點,而可能是音景生態觀(soundscape ecology)。想要「聆聽」這樣的生態必須有特別的器材,因此收集昆蟲與樹木交互聲音的研究者不斷思考「松樹世界之物質性」,如何能夠以不同的導電變壓材質,來當作聆聽樹木聲音的介質。在過程中,「科技能夠幫助我們更接近這個世界……(能夠)近距離體驗其他生命形式的感官經驗,還有牠們對於環境的特有敏感度。」
從昆蟲與樹木的聲音生態學、昆蟲視覺的功能分類為線索,到生物哲學家所思考以生物感官與時空經驗才能出現的「周遭世界」,在《昆蟲誌》這本模擬百科全書來向昆蟲致敬的書裡面,萊佛士協助我們看到昆蟲和人類之間展現出來的交互主體,甚至是人類透過昆蟲的能力才得以延伸出去的感官世界。就讓我們透過作者帶領的閱讀和觀察,跟著書中所描述的昆蟲一起:從空中到地底,從蜜蜂發現食物的舞蹈到舞虻求偶的送禮方式,徹底改變我們作為人類身體的邊界,並且享受「甲蟲」卡夫卡未曾設想過的多重真實世界。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李宜澤 昆蟲化身的吟遊詩人:修・萊佛士(Hugh Raffles)的「一昆蟲一世界」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39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