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彼岸思考氣候變遷與原住民主權
洄游芭樂
去年九月開始,我們展開全家在西雅圖流浪一年的生活。雖然可以暫時離開台灣的教學責任,探索不同的學術環境;但是來到全新的環境當中,再加上西雅圖因為近年高科技產業進駐,疫情後生活費高漲,在國外的生活也只能省吃儉用簡單度過。不過作為Fulbright訪問學者,在另一個學術環境裡體驗和參與不同的議題,正是此行的重要回饋。雖然是以華盛頓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為我的接待單位,不過因為研究的議題關係,我積極地和美國印地安與原住民學系(American Indi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的成員聯繫,也因為台灣學界好友的介紹,我很快地跟兩三位在AIIS任教的朋友熟識起來。其中包括剛剛出版一本關於本身Osage族群歷史的Dr. Jean Dennison(Osage族即是電影「花月殺手」中因為傳統領域挖到石油,出現一連串被白人社會所謀害的主角族群);另一位是回歸自身族群在鮭魚迴游與環境變遷議題上反應家族關係的Dr. Charlotte Cote(是Tseshaht/ Nuu-chah-nulth族人);以及多年來在阿拉斯加北極圈地區,與伊努特人一起了解其生活環境受到氣候影響的Dr. Paul Griffin(非原住民族)。雖然不全然是原住民族群的自身成員,這幾位AIS的研究者都討論當代原民社區與氣候變遷與環境資源的問題。
我在課堂上或者課堂外,跟這幾位學者有不同機會的交流。從他們的研究專長以及近來的原住民環境議題,可以發現氣候變遷問題對原住民社區以及相關影響的議題,有三個不同層次:第一層次的議題是,如何將原住民自身的生態觀點與整體社群歷史變遷的關係,透過經歷的轉譯而連結起來,例如觀察自身家族採摘野菜的路徑與捕捉鮭魚的傳統再現;第二層次的議題,則是在政府治理與環境變遷的資源分配下,解構治理與環境學科之間的糾纏關係,例如與族人共同行動去翻轉寄宿學校歷史或是組成合作環境調查團隊;第三個層次,則是進入到原住民主權對資源使用的重新認識,以及針對殖民抵抗與權利返還的行動,案例則是以不同主權觀點盤點食物來源,生存所需的「溫度」,或者碳排放等等當代議題。透過我在華盛頓大學原住民學程所參與的課堂討論,演講系列,以及特定社區活動,深深感受到原住民學者與社區在面對環境資源生存抗爭以及氣候議題時,經歷過不同時期與需求的轉變。以下從幾個場合說明我在太平洋彼岸所看到的氣候變遷與原住民主權議題實況與討論。
第一個場合是在2024年10月14日西雅圖辦理的第十屆原住民日(ʔaciɬtalbixʷ tiʔəʔ sləx̌il, Indigenous People’s Day)遊行;這個活動是為了取代惡名昭彰的「哥倫布日」而來的自主活動。活動訊息透過華盛頓大學“indigenous_studies” 電子信件系統聯繫的。名稱上看起來好像只是校內的原住民研究公告信件欄,但是這個電子信件群組卻包含了許多在大西雅圖地區的族群領袖以及NGO團體。因此在原住民日的活動之前,信件上有許多邀請擔任志工以及說明當天活動進程的討論。今年度的原住民日主題是「水資源與歷史」,因此從金恩廣場到市中心的遊行當中,有許多與水有關的標語和行動劇,包括要求當時還正在尋求勝選的兩黨總統候選人注意原住民受到能源與礦業開採所受到的水污染問題。在遊行當中不同團隊以水煙和藥草作為工具,向空中揮灑水霧;也特別繞行西雅圖有名的水岸商業區(Pier 61, Waterfront area),讓在路上逛街的行人都注意到這個綿長的隊伍;同時也以口號宣告這次的主題:

What we care? Water is Life!
What we want? Land and Water back!
以原住民成員為主的遊行在星期一的上班日看似沒有多少人注目,但是當隊伍聚集在「西湖廣場」(Westlake Park)時,仍然有上百人參與。此時在華盛頓大學任教的Dr. Charlotte Cote以及Duwamish 部族議會領袖Ken Workman,都上台發表演說;並且由散文詩集「河流在我的血脈裡」(River in My Veins)的作者Kara Briggs透過朗讀來頌讚祖先,表達對於將要來到的選舉以及連帶對於水資源的大量開發的憂慮。尤其才在華盛頓州商業部通過的CCA(Climate Commitment Act),似乎會因為川普表態將裁撤「針對特定族群所進行的環境補貼」而改變,當次的遊行更具有選戰前哨戰的意義。遊行在台灣不少見,不過西雅圖以原住民日為主的遊行活動,特別把社區青少年樂團以及家庭幼兒成員都帶到街頭上,讓下一代一起參與爭取權益以及公眾關注的活動;另一方面,這次的遊行除了連結水資源主題,進一步邀請關注巴勒斯坦的行動者舉起標語一起行走,並且在行走到終點時發表他們在遠方戰區中看到醫療需求與婦孺群體,同樣受到水資源不足威脅的經驗。這次的街頭經驗,是在美國第一次感受到北美原住民社區團結性Solidarity的重要經歷。

氣候變遷的問題不只是在街頭上回應,更多是在課堂上透過閱讀而討論的多重觀點。在華大的第一個學期,我選擇Dr. Paul Griffin教授的「原住民生態與氣候變遷」這門課參與旁聽。這門課是高等大學部的課程,因此大概有四位研究生和十位大學部學生一起上課。讓我意外的是,雖然課堂的先修課程是北美原住民概論,但大概有七八位同學並非原住民背景也一起來參與課程。我詢問了幾位參與的非原住民背景同學(透過每週都有隨機分組討論的機會),為什麼他們選擇來上這門課。有主修環境科學(以環境工程為主的「硬科學」學程)的學生,認為這堂課可以提供與自然科學不同觀點並且邀請自己多傾聽原住民族聲音的需求;有主修政治學的學生,認為從原住民社群組織自己的模式,可以看到與美國現行民主體制不同但「同源」(來自於Iroquois易洛魁族群所組成的部族聯邦體制)的參考觀點;另外也有考古學研究生希望針對部落的氣候變遷韌性回應方式,來討論特定文化器物的功用是否因外在環境有不同。這樣的多樣背景讓課堂討論變得很有趣,也具有挑戰性。
這個課堂的四份主要讀本都與氣候變遷與部落主權有關係,我稱呼他們為「行動民族誌」(ethnography of action)。第一份讀本是《一手拿鼓,一手拿鮭魚:太平洋西北岸的原住民食物主權故事》(A Drum in One Hand, a Sockeye in the Other: Stories of Indigenous Food Sovereignty from the Northwest Coas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2)。由華盛頓大學學者Charlotte Coté所寫,她本身是Tseshaht/ Nuu-chah-nulth族人。透過回憶過去與祖父母採野莓和河流彎處捕捉洄游大目鮭魚的經驗,描述土地與河川對於族人的意義,以及徹夜守候鮭魚洄游時所體驗的部落族人情誼與環境樣貌。另一章節她並帶領族人回到過去無數族人受折磨的寄宿學校區,將家族親人所留下的可採集植物和野莓重新種回學校空地上,讓荒蕪並且造成創傷的環境上慢慢變為菜園,她說:「我們正在等待祖先的回覆」。讀者可能會認為原住民研究都傾向來自追求自身歷史背景的自我書寫;但這本著作不同的地方在於,Cote很深刻地使用了自我的質疑與反思,回想過去家族曾經走過的路線—不管是在捕鮭魚的位置,或者是曾經被「軟禁」在寄宿學校的親人—並且與當代的選擇重新「和解」。回看目前在台灣所進行的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調查,除了以踏查行動回到歷史事件的場域,仍然以設立碑體或者永久建物為主要的「紀念」方式,反而失去了與歷史「和解」時讓傳統慣習進入紀念空間中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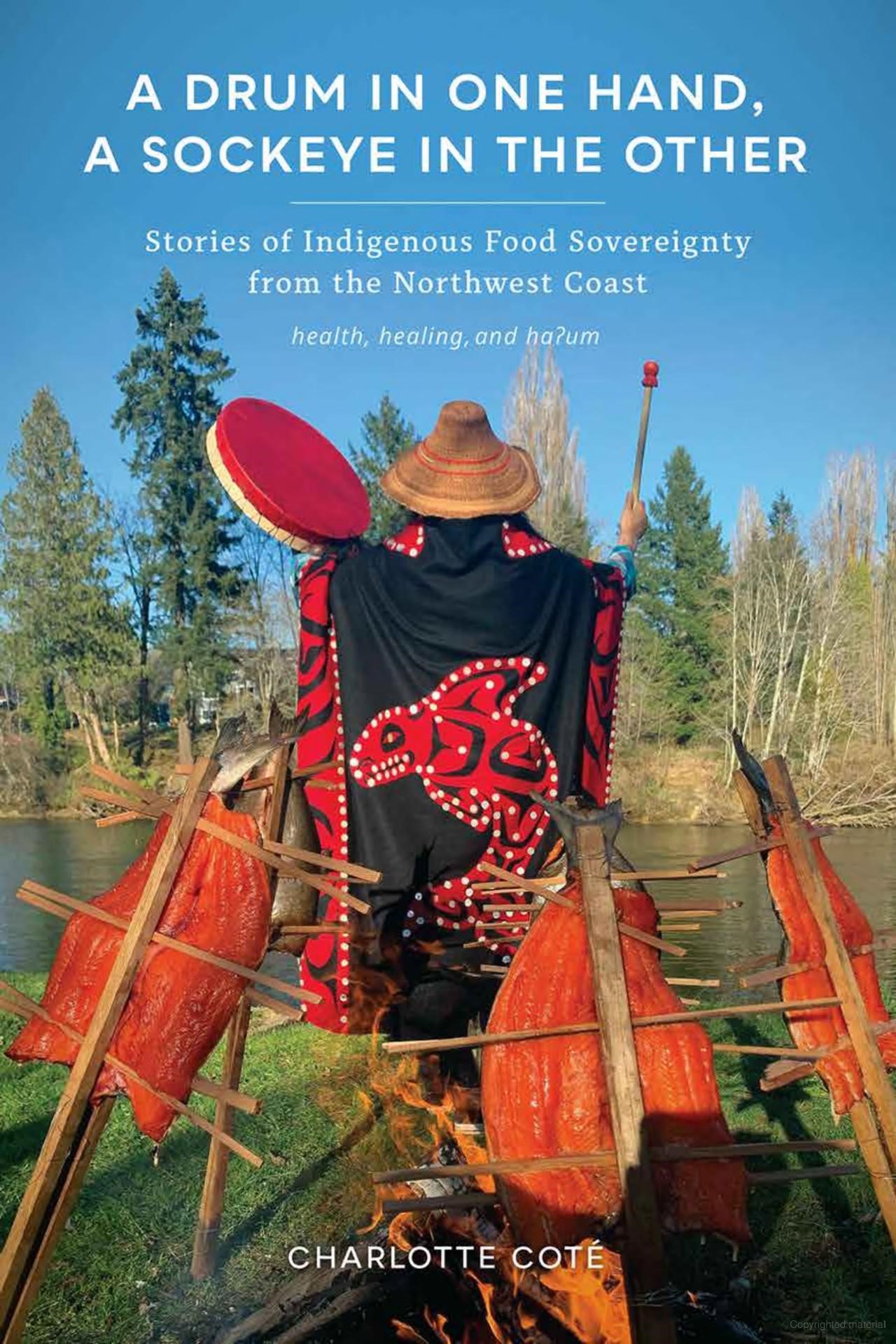
課堂的第二本閱讀是《在沼澤上:爭取原住民環境正義的路》(On the Swamp: Fighting for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Justi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4)。作者是在杜克大學水利工程系任教的Ryan Emanual,是Lumbee族人。這本「行動民族誌」紀錄Lumbee族人因為在美國政府劃設保留區時期被排除在外,因此無法以原住民身份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和採集,甚至受到在沼澤挖掘頁岩油公司的威脅。但也在此同時許多Lumbee族人見證自己祖先回到該地的夢境和意象;例如作者描述,某外來挖掘工人在一次晚上守夜時,看到整個沼澤地突然有無數光點持續不退,當他跟來換班的Lumbee族人提到這個「恐怖經驗」時,族人非常驚訝又感動地說,「祖先終於等待我們回來了」。這份自我民族誌的特殊角度在於,一方面重新檢視歷史檔案說明沼澤地如何從傳統領域變成國家「無主地」而被「開發」,另一方面也不斷引發與紀錄族人們的生命經驗。在結合當代科學檢測模型與族人觀點的同時,Emanual以自己的水利工程專業,分析早先族人從採集活動到農業的歷史轉變,以至於近來將此地作為新能源用地以及氣候變遷時的灰色地帶:要疏濬還是要當作滯洪功能的爭論。但在此同時他也重新招集族人設置測量與規劃的基礎設施公民平台,並且強力遊說政府規劃對該地水文的改變政策。環境正義在此不只是重新回歸族人在地記憶,同時以教導分享外來資源而為抵抗國家殖民而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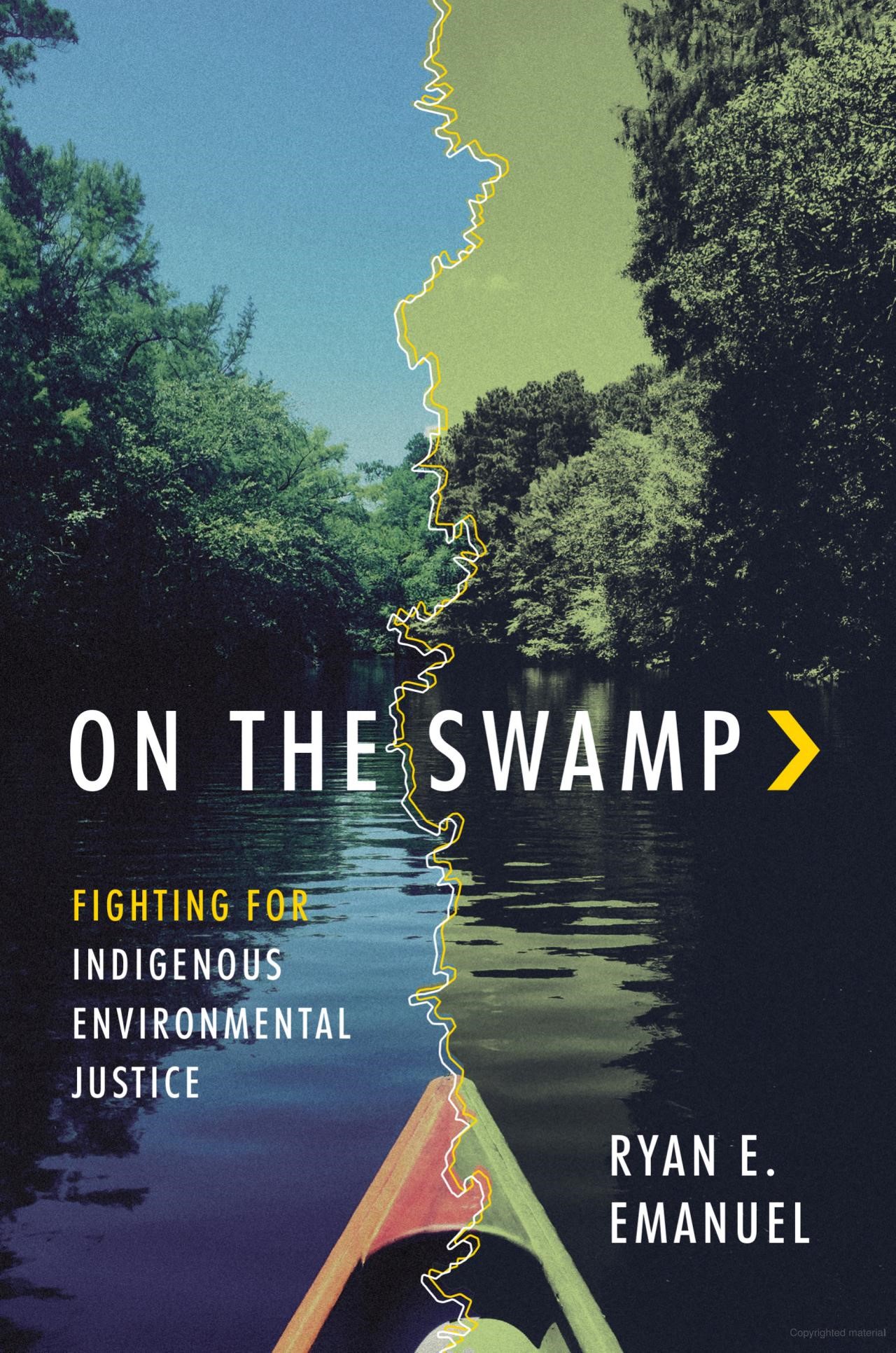
第三本行動民族誌是《寒冷的權利:一位女性為極區以及保護地球受氣候變遷衝擊的奮鬥》(The Right to Be Cold: One Woman's Fight to Protect the Arctic and Save the Planet from Climate Chan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作者是加拿大伊努皮雅族的環境運動者Sheila Watt-Cloutier。她以親身觀察描述在阿拉斯加邊境的村落Kivalina,因為暖化而造成村落水源污染,道路崩壞,以及捕獵鯨魚海豹的困境。寒冷聽起來只是一種溫度的對比,但是在大氣科學裡面地球上其他地方因為燃燒化石燃料而出現的懸浮微粒,最終因為冷熱對流交替會沉澱在南北極區(如同海洋中的大型垃圾聚集區)。這個氣候流動現象會因為暖化而加劇,居住在阿拉斯加極區的伊努皮雅人也因而在物種體內(包含海豹,獵犬,當然還有人類)檢測出超高標準的塑膠微粒等物質;所以當極區的原住民失去狩獵的基本資源時,更進一步成為全球大型氣候垃圾循環系統的受害者。該村落因此進行了第一次集體向美國政府控告Exxon Mobile石油公司的案例,可惜的是2013年最高法院因為沒有「直接證據」最後駁回了這個訴訟。但Watt-Cloutier的重點不在於這個判決,而是仔細描繪當氣候變遷改變了極地社區的海岸線以及基礎設施的時候,日常生活的困境:例如當地唯一的高中在靠近海邊的校區受到冰原融化侵蝕而遷址,當地的伊努皮雅人卻因為狩獵機會降低收入減少,無法負擔讓學生通勤用的巴士(也沒有公路),也影響了學生參與社區其他原住民文化活動的能力;甚至過去親人曾經進行捕獵的領域,現今都因為環境阻礙而無法進入。作者在書中提出「從村落創傷理解人類創傷」(understanding tribal trauma as human trauma),就是從一個村落的在地問題,看待人類全體面對氣候變遷的困境與急迫性。也因此即使寒冷帶來不便,但族人們仍然期待以當前的技術框架重建生活中「寒冷規模」的概念。
最後進入第四本民族誌是Andrew Curley所寫的《碳主權:煤炭、發展與納瓦霍民族的能源轉型》(Carbon Sovereignty: Coal, Development,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Navajo N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23)。Curley 的核心論點圍繞「碳主權」這一概念,討論第內(Dine, Navajo的正式族語名稱)族人如何在殖民背景下,透過煤炭經濟確立其主權和自治性。他認為煤炭經濟既是一種賦權的工具,也是一種殖民剝削的產物。書中分析了第內族如何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壓力下,面臨能源轉型的挑戰,以及如何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維護和爭取其土地與資源的主權。從歷史角度來看煤炭工業如何在納瓦霍地區成形,並分析煤炭產業如何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Curley 指出,殖民主義背景下,煤炭開採既為第內人帶來了有限的經濟收益,也讓他們陷入對外部經濟體系的依賴;特別是在公共基礎設施(如學校、醫療設施)和就業機會方面。煤炭產業成為第內民族自治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同時也使其被綁定於一個碳密集的經濟結構。但也呈現第內人與毗鄰的霍皮(Hopi)民族在煤炭資源開採上的矛盾,揭示了殖民主義在原住民土地分配上的長期影響。Curley延伸土地主權的概念來闡述能源主權,並討論土地治理在第內民族主權中的重要性。他批判當前的能源轉型敘事的「洗綠效應」(greenwash),指出這些敘事經常忽略原住民族的觀點,並未充分考慮他們對土地與資源的依賴以及文化連結。碳主權延伸自土地主權以及環境資源主權,是進一步對於主流社會覬覦的啟動資源重新定義的主權領域觀點。當代的能源轉型出現的機會仍然可能延續殖民設置的傷害:以太陽能與風能計劃為例,清潔能源轉型雖然帶來了新的機會,但未能有效替代煤炭經濟對當地的支撐作用,這些計劃經常忽視原民文化和土地使用的複雜性。Curley 討論煤炭在第內文化中的象徵意義時詳細分析文化與經濟之間的張力。他認為煤炭不僅是經濟資源,也是社會身份的象徵。第內民族的經驗揭示了殖民遺緒在能源轉型中的深遠影響,並且以原住民煤炭工人組織與文化活動的連結來建議重新思考能源政策,將原住民族的需求與視角納入主流討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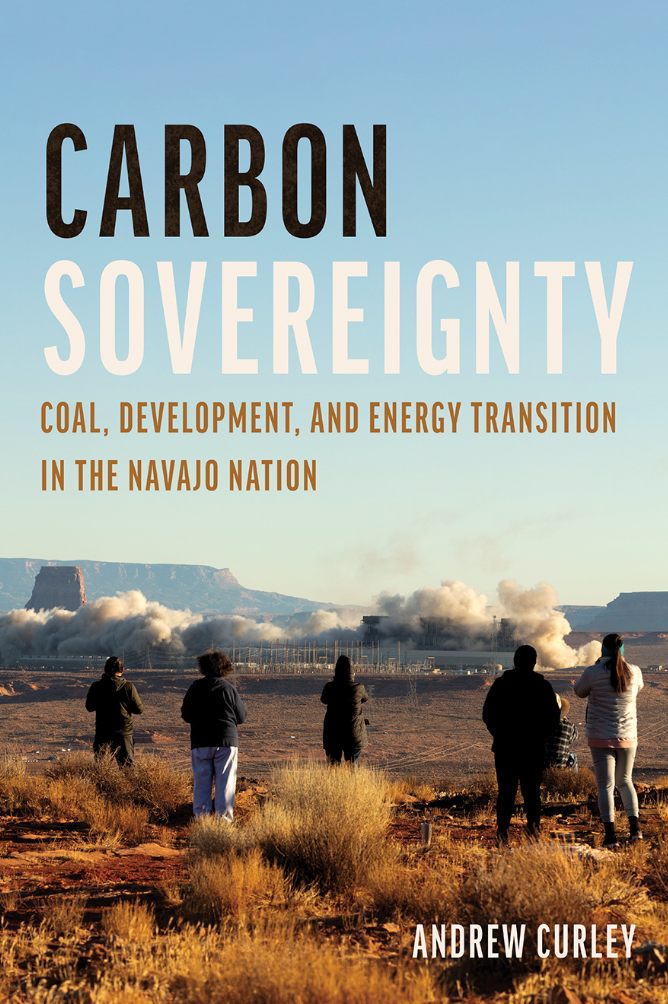
以上這些討論都在課堂中進行,但是除了閱讀之外,許多行動也在實際情境中發生。例如在電子郵件群組中,社區工作者會邀請學生參與環境變遷工作坊,包括鄰近西雅圖的Snoqualmie保留區鮭魚洄游季時擔任志工,或者在大學裡的原住民聚會所intellectual house參與新的環境紀錄片討論等等。最後要介紹的氣候與原民主權議題場合,就是關於西雅圖原住民爭取自己食物(以及文化)主權的《鮭魚戰爭》(Fish War)這部影片。
鮭魚對華盛頓州的原住民社區而言是生命的命脈。1855年華盛頓領區的長官Isaac Stevens 與原住民之間的Stevens Treaty裡面寫道,原住民將土地讓渡給美國政府,但仍保有本身文化與捕魚狩獵權利。但是在真正執行的過程卻一直受到許多阻撓。尤其在二戰之後美國開始進行強勢執法,讓許多原住民在基本的魚網捕魚活動都被視為違法而當場被拘捕或沒收漁具(紀錄片中採訪到,當年放學的原住民小孩甚至在家並不知道父母已經被捕了)。在1974年,原住民族決定上法庭控告州政府違反權益(US vs. Washington 1974, Boldt decision)。紀錄片中提到訴訟中透過Quinalt湖畔地區的原住民加入整體的法律戰,讓他們的權益更明確地被看到:因為Quinault地區的原住民幾乎家家都以捕魚為生,也有更豐富地現代漁業知識可以在法庭上攻防對比。在開明派法官Boldt的判決下,原住民族看似得到了勝利。但這不是最終,白人開始上街抗議,堵住漁港海域,認為原住民剝奪了他們一半以上的捕魚權益(是不是很像先前在台灣看到屏東漁民到蘭嶼抗議飛魚季禁捕的新聞?)。這個案例後來上溯到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仍然讓原住民得到了勝利。但此時原住民意識到不能只以兩邊的對立來僵持這個問題,因此八〇年代開始與州政府討論「共管」,由兩邊的委員會成員針對捕魚數量方式進行詳細討論。另一方面,兩方也開始聘請生物與生態學者提供科學層面的論述,作為法律工具。1980後期左右發現鮭魚數量大量下降,也開啟了讓原住民族以孵化區Hatchery作為管理的方式。由原住民從孵化區裡面取得魚苗後,移置到文化活動中常有的鮭魚迴游區來流放,慢慢地形成文化與自然循環的新平衡狀況。

鮭魚戰爭的劇照與連結
在西北條約部族的支持下,紀錄片《鮭魚戰爭》利用檔案影像以及抗爭前線活動家的見解,追溯這場戰鬥從1960年代的起源至今,同時探討在氣候危機與人類干預的背景下,對華盛頓州原住民族所保障的捕魚權真正的意義在哪裡。影片更介紹了原住民耆老Billy Frank Jr.以他在不同委員會裡面以及大眾媒體上侃侃而談的領袖能力,帶領大眾了解原住民的現況。紀錄片中某次與柯林頓總統的會談,只見柯林頓原來下巴抬高的姿態,慢慢轉變成為仔細聆聽,最後對於Frank Jr. 的論述給予完全肯定的掌聲,也是一種很奇妙的媒體運用觀點。放映後的問題聽了兩個:一個是幾位年輕的鮭魚生態學研究生,詢問科學知識與原住民的知識是否有對立不同之處?與談的Billy Frank III(耆老的兒子)提到,我們正需要不同觀點的知識,也需要深入的對話,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看到鮭魚在不同地方都可以洄游並且與族人共享。另一個是身為族人的高中生,詢問目前在教育環境是否已經有足夠的鮭魚文化權益的教育內容?這讓我聯想到我們在台灣正近行的原住民轉型正義與知識體系教育,不應該只是傳統知識的收集和紀錄,更應該加入現代的技術論述以及法律觀點在教育體制內,才能夠將知識體系作為有生命的整體,不斷延伸下去。
以當前台灣來看,我們有許多文化主權復返的爭取案例,也有關於氣候變遷下社區安全,能源主權,以及與不同層級政府單位合作共管關係的例子。在太平洋的兩岸,不同文化源頭的原住民族,都為著環境、領域、食物與能源等主權議題在不同情境下為自己發聲。希望透過在太平洋彼岸的見聞,給我在台灣朋友們傳遞團結與新使命的觀點。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馬上瘋檳榔 在太平洋彼岸思考氣候變遷與原住民主權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7072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