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南方
她者亦是共同體
曾有人說過,所有的社會學都是南方社會學,因為社會學必然論及不平等,而關照了不平等,就形同關照了南方。如果這種說法成立,追求一個「南方的」社會學,將只會是畫蛇添足。但果真如此嗎?從台灣的南方出發,我們希望指出,上述觀點忽略了「南方」社會學出現的脈絡,也並未理解「南方」概念與近年來常用的學術語彙「全球南方」,如何有著關鍵性的區別。與此同樣重要的是,這種說法低估了近年來社會學與其他親緣學科之間的協作共生,尤其是從人類學而來的,處理差異與培養同理的滋養。這套書的作者群檔案呼應著對「南方」問題的多聲道叩問。除了文化研究學者、人口學家、文學評論家、哲學家與法律學家之外,本書作者群中有十八位為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帶著不同的訓練與概念齊聚一堂,我們串連彼此的關懷並將其展開,探問「南方」在具體人生與抽象理論之間的可能意涵。
南方的真諦
當舊的冷戰秩序褪去、現代化理論失靈,「全球南方」概念的興起,誓言要正視世界的發展失衡與資源的分配不均。[1]乍看之下,「全球南方」意味著,我們將不再以政治系統(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貧窮程度(已開發、開發中)來分類國度。取而代之的,我們將強調受害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後進者之間的共通性,[2]而這些共通性,大部分由地理上相對於歐美為「南方」的複數區域所繼承。
過去十年間,「全球南方」逐漸成為另一個不證自明的通用語彙。只是,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忍不住反躬自問,比起「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全球南方」是否更有洞察力?我們所欲提倡的「南方」,與這個「全球南方」有什麼實質上的差別?
在回應這些疑惑以前,或許我們必須先釐清兩個問題。首先,全球南方在哪裡?「全球南方」在語境中涉及一種空間的指涉,但在經驗層次上其實無法作為連續的地理區塊。畢竟,南北的內部都是高度異質的。在華盛頓與北京,名牌跑車與貧民共存一地;巴黎實質種族隔離的郊區之生活品質,遠不如雅加達的穆斯林新興豪宅社區;摩洛哥卡薩布蘭加高級住宅區中的花園水池宮廷,當然也遠比槍林彈雨的巴爾的摩街道舒服愜意。換言之,地理北方的內部其實充盈著南方製造,而地理南方的人生勝利組嫁接、挪用,游刃有餘地創造出比北方更北方的生活特權。這些超越國界與區域的社會不平等與其加劇的現象,在在顯示出全球南方本身非地理可解釋。簡言之,無論是「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或「全球南方」,只要是鋪天蓋地的概念,均無法處理區域內部的異質性。

其次,「全球南方」與「開發中國家」的區別是什麼?以經濟發展為地方價值之定奪的基礎預設,與其隱含的以進步為前提的單一線性史觀,並未因全球南方概念的興起而改變。不論是作為原料的提供者、產品的消費者、污染的接收者,或是龐大的經濟體以及快速的經濟成長載體,「全球南方」的語境依然圍繞著經濟至上論打轉。透過「全球南方」的論述,世界/銀行再次打造出一個虛幻的美麗願景:「全球南方有崛起的可能,有燦爛的希望。」在全球南方的許諾下,社會生活與文化抵抗僅僅是無關緊要的雕花裝飾,不是核心的人類價值。換言之,即便我們表面上不再以貧窮程度或政治系統來分類國度,但在「經濟最大」的預設之上,「全球南方」與「開發中國家」在大多時候有可能是兩套換湯不換藥的概念。
著眼於這些限制,我們認為有必要提醒,南方不是一種地理方位,也不是一種開發程度,而是一種真正強調多重交織性,重視內部異質性,並以挑戰普遍理論為己任的碰觸與實踐。在南方的實踐中,我們必須記錄與見證難以被規訓的「不倫不類」,必須反駁「總會等到『已開發』那天」的單一線性史觀,必須訓練積極發掘南方俯拾皆是的能力,必須培養出一種「邊緣觸生」的生活態度。簡言之,南方必須是一種「異文化就在你身邊」的開放同理,並有賴「他/她者亦是共同體」的悔悟與決心。
因此,「所有的社會學都是南方社會學,因為關照了不平等就形同關照了南方」的陳述,是無法令人滿足的。南方的社會學在新的時代中更強調內部的異質性,以更多元的方式來反對經濟至上的論點,也更堅持體悟多重交織性之下的,南方之中的南方。當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將此「南方的南方」視為己任時,我們相信,雙方彼此的互補交融,將有助於深化各自的初衷。
交融兩種抵抗的顏色
對許多人類學者而言,社會學往往背負太多看不見的歐美包袱,同時又太少異文化的震撼洗禮。(當然,有顯而易見的反例,比如布赫迪厄的柏柏爾田野與階級秀異論彼此貫穿。)同樣是談論「公民運動」,當社會學的參照對象是歐美日韓的「國民」或「公民」時,人類學卻會忍不住考慮後進國家內部的「宗派」或「族裔」,比如貝魯特郊區的什葉派慈善團體,或是馬達加斯加島上的斐索人。同時,人類學者對於以國家為單位的論述以及權利語言的力量,也更常抱持懷疑態度。[3]於是,當社會學家處理許多火熱議題卻直接繞過「文化差異」時,人類學者可能會下意識地感覺到:這根本不夠「南方」。
確實,就異文化感知力的掌握而言,人類學可能比社會學更為「南方」;只是一旦來到執行批判與推動改革的層面,社會學卻可能比人類學更為「南方」。在此,南方不只代表著被宰制與非主流,更有反抗的行動意味。(當然,我們依舊有顯而易見的反例,如發起占領華爾街運動領袖之一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當澳洲學者康乃爾(Raewyn Connell)推廣她的「南方理論」時,即反映出一種特殊的政治企圖:抵抗當前狀態,尤其是抵抗「發展中國家」或「發展」等語彙所掩蓋的不義。簡言之,「南方理論」重申並重新定義了抵抗的必要性。
因而,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南方的著力點:抵抗。

平平是「抵抗」,人類學版本與社會學版本,非常不同。九○年代,英語人類學界盛行「權力為萬物之母」之際,人類學家往往很自在地將日常生活的種種當成「弱者的武器」。鬧鬼是抵抗、神靈附身是抵抗、穿垮褲是抵抗、加入幫派是抵抗、在森林吟唱是抵抗、戴伊斯蘭頭巾是抵抗、參加新興宗教聚會也是抵抗。雖然這些研究幫助了我們理解底層人民的能動性,但當萬事萬物、花草樹木都可以是抵抗時,抵抗也近乎喪失了它的內涵。
相較而言,社會學著作對於抵抗有較為穩定而清晰的主軸,抵抗的變形也相對較有節制。面對金融資本主義的掠奪、國家公權力的壓迫、主流社會的歧視,以及各種現代形式的不平等,社會學家的控訴與解方的提供,都是相對清楚的。當然,這些解方有一大部分源自相信「個人自由」,但「個人自由」對人類學者而言,卻算是一種被現代性過譽的觀念。除此之外,相較於人類學者更常關注族群政治、宗教儀式、實質經濟、文化混合,以及語言變遷,社會學者可能更常研究社會運動、勞權、污名、政治社會,與政策評估,因而更有能力提供可以操作與改進的對話平台。
當然,上述兩者間相對的差異,並不是絕對的。而且,不論我們體認與否,我們仍是歐美帝國主義遺產影響下學院知識分工結構的逆女孽子。[4]人類學者因為其研究社群本身就已經十足「南方」,因此在議題上,似乎也就不需要再如社會學者那般刻意的「南方」。「社會問題」是北方社會的特權;南方社會的一切都是「社會問題」。但正因為如此,我們相信,與其更念茲在茲地劃清界線,還不如突破重圍、相濡以沫地彼此滋養。是而,這本書將以坦然的姿態面對社會學與人類學各自的優缺,期盼兩者的並置,足以激盪出南方的南方的多種路徑。
在這樣的抱負下,「南方的社會學」可以是一種更願意執行改變的人類學,同時也是一種更關照深層差異的社會學。在向各種南方的社群學習時,我們將預設所有社會面向均有文化差異。同時,我們相信社會結構中非主流行動者的文化生命,曾在歷史中與主流系統協商,而協商的歷史所構成的新社會網絡,長期而言可能撼動權力結構。如此卑微但堅毅的「南方」立場與方法,深知文化與社會作為意義之流與行動的匯集,可以孕育扎根、灌溉創新,但也能反叛挑戰,樹立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永遠必須重新體悟到南方之中總有南方,南方也必須捍衛南方的南方。

一言以蔽之,南方是一種與差異同在的靈魂,也是一種肩負批判各種資源分布不均的任務。在南方的南方取徑中,社會學從人類學獲取更多洞察差異與同理的細膩,人類學從社會學展開更多批判與實踐的魄力。我們相信,這樣的集結,在這個時代──這個美國醫療資本主義失靈、歐洲民主的危機與右派興起、中國言論自由的箝制與天災人禍、各國對中國的膚淺認識所鋪陳的全球瘟疫,以及人畜共通疾病盛行的多災難時代──將更趨重要。在民主的脆弱與民粹的喧囂之際,我們堅持肯認異文化就在我們身邊,並嚴肅地追溯遙遠的異國如何是我們也深涉其中的不平等外包。正因為知道南方之中總還有南方,邊緣之中也還有邊緣,北方與南方的相對概念在益發多元分歧的社會中,有助於我們揚棄對東方與西方之間浪漫與理智差距的誇大,並轉而培養更謙卑的行動與同理。
從他者到她者
行動與同理是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社會對南方—遑論南方的南方—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在生活中,台灣社會充滿對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外籍配偶與勞工的歧視,更時常以恩人自居,以一種傲慢態度籠罩並掩飾剝削的事實;在國際新聞裡,我們對歐美的一切文化風情與科技發展歌功頌德,但對於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歐美少數族裔在帝國強權殖民遺緒下的遭遇置若罔聞。不論是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的印尼穆斯林移工、在漢人為主的社會求存的原住民、或是遠在敘利亞內戰中家破人亡乃至在地中海上飄零或溺死的難民,這些人,都是不同主流社會乃至全球社會中的他者。他者是一種沒有特權可以挑三揀四生活風格的人們,是隨時準備要逃亡或被遺棄的生命。
但,這樣的「他者」,往往也在刻板印象中,被奪走了發聲權與能動性。其中一項重要卻較少被討論的剝奪,也來自於我們對「他者」這個詞彙的去性別化。他者(Other)原來的翻譯是「異己」,但學術界因各種歷史因素的約定俗成,當年曾一度被視為「洋腔洋調」的「他者」一詞,如今儼然已成為標準的翻譯選擇。所謂的他者,指的是非我族類的人們,他們源自不同的階級、種族、國族、宗教、政治意識型態,以及性傾向等等。「他者」代表了所有「他者」與「她者」。而「她者」,則永遠是被標記的主體。
在本文進行「南方的南方」宣言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我們仍會遭受使用中文漢字的種種侷限。為什麼是這個她?一般而言,「他者」,不是都用他嗎?我們一定非她不可嗎?
語言人類學者一百多年來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我們的思考如何由語言深刻地中介,儘管並非完全地決定。近年來,最依賴萬事萬物均有陰陽性的幾種歐洲語言,如德語及法語,也開始字詞性別的改革,如發明「無性字彙」,辯論是否該繼續以陽性當成人事物的原型及代表。至於「自然性別語言」(即人稱代名詞有性別,但大部分詞語無性別差異的語言。當然,這個詞其實本身就帶有某種二元性別觀的偏見),如英語及瑞典語,也陸續朝往語言的性平化方向前進,比如第三人稱單數不再以男性的他為主。事實上,即使是無性別語言,如印尼語及土耳其語,還是能依靠字詞組裝而構築以男性為優先主體的語言。回到我們熟悉的華語及台語,口語上較少性別的差異,但在具有深層累積性與超強複製性的現代書寫中,中文的「她」是一種專屬於少數「他者」的指涉標籤。她必定只能是一位生理女、跨性別,頂多是一個國家、一種大自然或某個星球。她是被標記的主體,既無法作為全人類的代表,亦無法代表「他者」。
這篇導論的最後一個作用,即打破這種對於「她者」的禁錮。是什麼阻止了「她們」來代表全部的「他們」?是什麼讓「她者」代表所有「他者」的正當性受到了質疑?是否因為我們心中與筆下總有約定俗成的概念與實現,使得那人字旁的他可以代表了普同的人類與一個特定的男人;而她,即便在現代中文後才出現,卻永遠只能依存於女體、女心,或某種他人可以為之情緒高昂、開發與征服的客體?為何男人與普遍的人之間在字面上足以等值互換,女人就只是特定而絕非普遍的主體?
只要稍加端倪,很難不去發現漢字系統中以女字部來施加「他者化」作用的傾向。在女字部的負面化能力中,「妒」與「嫌」都是一種加了女字部就成了負面道德指標的字,而「姦」更是將絕大部分為男性所犯下的性暴力開脫成女色污染男性道德的造字法則。在他者化的領域裡,「奴」與「妖」更是一種女性即為他者的說明。[5]5奴是被宰制、被壓迫,與被決定的「他者」,其本質為一種肩負照顧責任的「她者」。至於妖,則是常的悖論,是所有正統、正常、普遍,與具有正當性的一切之叛逆的「她者」。因而,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一套妖書,從中,我們想解放各種奴性(菸~)。
在此,南方的南方作為一種取徑,由於體悟到南方中還有南方,且南方必須捍衛南方的南方,「她者」因而代表了所有受到不平等對待的「他者」之中的「更南方」。她是士兵的母親,是戰場上的照護者,是悲涼時期的領導者,是衰退時期的復興者,是勞工回家後發怒的對象,是逃亡者之所以可以逃亡的定錨。因為擁抱了南方的南方,「她者」不但可以代表所有的「他者」,更應該被去污名化,成為一種光榮而期待的、與所有受難者、受傷者一起,感其所感,痛其所痛的符碼,以及靈光。
她者亦是共同體
據此,「她者亦是共同體」意味著以一種策略性選擇女字部的她,來指涉所有的他者,無論他們是漢人主體社會中的原住民、現代社會的民間宗教實踐者、台灣認同下的客家、相對於北客的南客、人數極少的穆斯林、非異性戀者、同性家庭、跨國婚姻、第三性,或是馬來亞時代的華人、中緬邊境走私者、流亡印度的藏人、印度與中國的媒工、台塑越鋼受災戶、阿根廷「沒有老闆的工廠」、有年金改革需求的勞動者,以及追求呼吸平權的高雄人。這些她者在我們的兩冊四部曲中,將以各自的旋律,呼應著南方的南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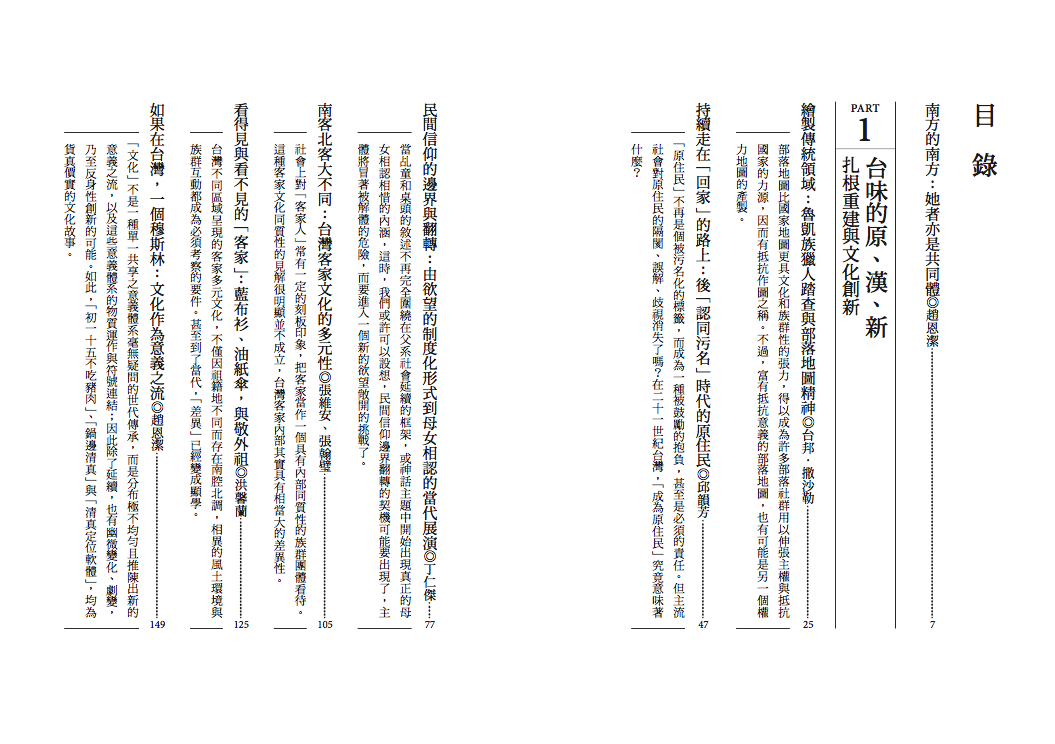
上冊以台灣的多元身世拉開首部曲。「台味的原、漢、新」首先來到台邦.撒沙勒的〈繪製傳統領域〉。從加拿大到台灣,部落地圖是一種文化性的知識,也是一種文化性的抵抗。結合獵人的知識、記憶傳述及GPS等科技,部落地圖有潛力幫助族人拿回在土地上生存的尊嚴,並進一步掌握河川、小溪及湖泊被主流社會污染的路徑。原住民一方面學習新的科技,另一方面更深耕原民獨有的知識形構,將森林與萬物她者視如己出,同時視己如出。
延續原住民尋回尊嚴的文化復振運動,邱韻芳的〈持續走在「回家」的路上〉細數了好幾位原住民族青年返鄉,試圖從頭學起並重新定義傳統技藝的故事。從太魯閣青年的復耕、泰雅織女的練習、排灣族送情柴的復振,再到布農族重返舊社行動,乃至與人事更新後的林務局重新協商山林守護的原則等歷練,原民從原本被污名化的弱勢她者,如今捲土重來,成為挑戰文化流失不可逆論、反對汲汲營營平地生存模式的創造性她者。
在領會原民的扎根與流動之後,迎接我們的,是漢人文化領域最柔軟的一塊:深埋在父權身體裡,被壓抑與被掏空的母女之情。在〈民間信仰的邊界與翻轉〉裡,丁仁傑帶領我們進入那個長期被打壓為「不理性」的怪力亂神之地,以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獨特視角,呈現出台灣會靈山運動中史詩般的母女神話。在會眾重演神話的儀式中,信徒對女神──王母、金母、地母、九天玄女、準提佛母──表達了濃稠而撕裂的依戀關係,而母女相認的劇烈情緒逼使我們重新思考將自我昇華為另一種「她者」──女兒──的特殊精神意義。
無獨有偶地,當我們來到了客家領域,我們將再度發現「她者」亦是共同體。張維安與張翰璧的〈南客北客大不同〉將為我們系統性地梳理南北客家的大異其趣,而洪馨蘭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客家」〉則透過六堆客家的敬外祖習俗來討論客家的崇母意識。確實,在刻板印象中,勤儉持家的「細妹恁靚」代表的是一種經典的族群她者。幸而,透過上述這兩篇客家的章節,我們將以更流動與更深層的探討來理解「感念母方祖先」如何成為一種將她者接納為共同體的實際行動。
在首部曲的最後,趙恩潔以台灣穆斯林的古今社群為例,以本質上難以共享、必然分布不均的「文化」概念,作為正面理解少數族群所經歷之認同與文化變遷的取徑。當「文化」是一種河流時,一般本質主義預設下的「文化流失」現象,將瞬間還原為貨真價實的文化本身。同時,不同於國際主流媒體裡永遠受害的穆斯林女性「她者」,〈如果在台灣,一個穆斯林〉給予了所有穆斯林行動者應得的能動性,描繪他們作為足以應變、融入、照護,與幫助的啟蒙她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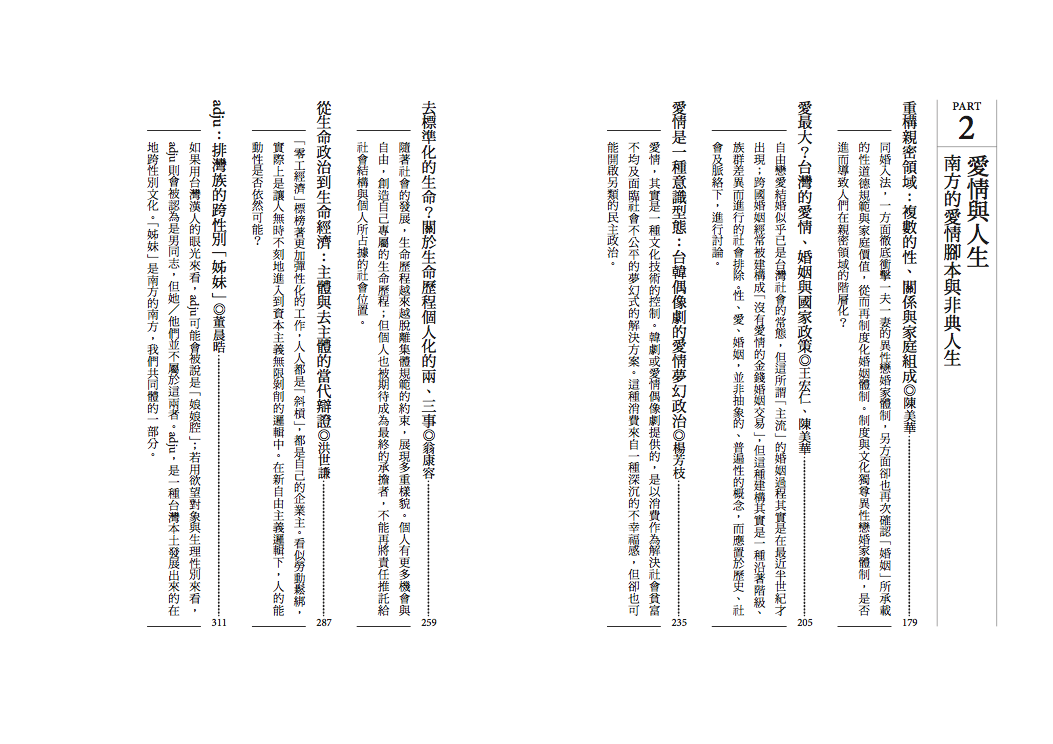
第二部曲「愛情與人生」側重在南方的愛情腳本與非典人生。陳美華的〈重構親密領域〉系統性地分析常規以外的愛情腳本如何在霸權的異性戀體制底下蠢蠢欲動卻仍具污名。種種表面上由中性稱呼代言的社會現象──諸如「晚婚」、「不婚」,與「少子」──其實每一項都預設了異性戀婚姻與傳宗接代是最自然與最理想安排的人生藍圖。因而,在「南方的南方」使命中,我們除了要提倡非異性戀與非典人生的尊嚴,也要將異性戀與婚姻去自然化,還原未被標記的主體──「正常」異性戀結婚生子者──本身的不自然性。
王宏仁與陳美華的文章〈愛最大?〉以台灣過去三十年的跨國婚姻現象為核心議題,透析自由戀愛的論述如何被選擇性地挪用成為國家控制與種族化的邊境措施。「沒有愛情的婚姻」不只是過去相親制度的常態,亦存在於後來婚姻仲介的媒妁婚約,以及目前仍是進行式的現代門當戶對的隱形內婚制度。婚姻與愛情的不重疊在古今眾多社會中均非意外,因為婚姻往往有政治、經濟或階級的考量。是以,當社會以「用錢買來的外籍配偶」的名義來質疑跨國婚姻的正當性時,該質疑本身很可能不過是以自由戀愛為名的種族歧視,而這正是無法將她者視為共同體的表徵。
接續質疑愛情作為一種治理術的母題,楊芳枝在〈愛情是一種意識型態〉一文中,以偶像劇常有的貧窮女與富帥男相愛為題,指出用愛情治癒階級鴻溝的後果,可能使得女性觀眾成為去政治化的「她者」。當愛情是一種意識型態,各種階級的對立就能被化約為私人恩怨情仇,而階級的傷口也因此得以被真愛癒合。以這種主旋律為基調的偶像劇製造出正義與勤奮的女主角,並將其餘女性妖魔化,使其成為妒忌、貪戀權貴與愚昧的她者。不論是在愛情中獲得向上流動機會的女主角,或其他被醜化的她者,始終都依照著資本主義邏輯活著,卻被包裝為個人特質的善惡果報,使得女性文類被去政治化的同時,也更加深了女性對愛情的嚮往,使得愛情成了一種治理的技術。
然而,這並不表示實質的抵抗與變遷是毫無可能的。事實上,從量化的生命歷程角度來看,翁康容的章節展示台灣人的人生正在「去典型化」當中。當然,我們必須小心翼翼,不去低估過去社會的多元性,只是在此,我們策略性地以理想型作為破除迷思的基礎。在〈去標準化的生命?〉中,當代社會中個體的生命歷程不再絕對地依附在既有社會類屬上,而是產生出更多的社會角色劇本,也更少依賴性別刻板印象。從量化研究的觀點出發,我們看到人的生命歷程更少依照被給定的劇本走,更加不可預測,也更可能由個人來創造專屬於自己的人生。愛情與人生在此,便開始了更多迎向多元她者的軌跡。

是而,即使是一般認定新自由主義經濟作為鋪天蓋地的經濟預設,在人的價值被深刻地市場化的世界秩序之下,人們仍然可能在在主體與「去主體」之間,形成真實的自我。洪世謙的〈從生命政治到生命經濟〉,思考的恰好就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非資本主義主體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說傅柯的生命政治之終極論證是新自由主義對主體的治理術在於生產的而非禁制的,那麼對拉扎拉托而言,「生命經濟」概念的提出更進一步地利用了「負債之人」概括所有以關懷為名、而將主體帶入終生奴役體系的社會過程。幸而,在生命經濟的框架中,仍有出口,因為協作可能讓人掌握主體而集體逃脫。透過協作,我們可以構成不穩定而充滿變化的「她者」,正如這本書實驗性的協作那般。
最後,我們呈現性少數、族群少數、宗教少數三者集於一身的排灣adju(阿督),以一場融合非典、非二元的性別革命與文化變遷的正在進行式,作為本書的結尾。董晨晧〈adju:排灣族的跨性別「姊妹」〉,正好是本書宣言「真正強調多重交織性,重視內部異質性,並以挑戰普遍理論為己任的碰觸與實踐」的身體力行。adju深刻地集結了性別與族群的意涵,而更為糾結的是,「排灣文化」與教會勢力同時是打壓姊妹,卻又是匯集姊妹生活的場所。從排灣族的姊妹出發,我們得以見證正在發生的傳統,接觸正在誕生的她者。
從「台味的原、漢、新」到「愛情與人生」,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用「她者」來涵蓋所有次人的、污名的,與邊緣的他者的途徑,搭建了一座展演台灣生命的舞台。我們也交融了兩種抵抗的顏色,在追尋差異與批判實踐中,學習捍衛南方的南方。透過台灣歧異的眾生相,我們試圖異中求異,為的不是各自分立,而是去探索更堅實的共同體。為此,我們期待「她者亦是共同體」的那天,將不斷地到來。
[1] 「全球南方」一詞至少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出現,九○年代稍常見,但要等到二十一世紀的頭一個十年後,才變成慣用詞彙。請見Pagel, Heike, Karen Ranke, Fabian Hempel, and Jonas Köhler. “The Use of the Concept Global South” in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25 (2014): 13-9.
[2] What’s Wrong With The Global North And The Global South? Thomas Hylland Eriksen. https://web.archive.org/ web/20160923171120/http://gssc.uni-koeln.de/node/454.
[3] 這種傾向的差異,有其學科系譜,肇因於某種歐洲早期社會科學分工的「原罪」:左手把「現代西方社會」交給社會學、右手把「原始非西方社會」交給人類學。儘管這種粗糙的劃分早已過時,這份原罪卻在學科的精神樣態上遺存下來。
[4] Wallerstein, Immanuel et al.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奴」為會意字,女指女奴,又指用手掠奪之;一說又指女奴從事勞動。而形聲字的「妖」,《康熙字典》解釋為「豔也,媚也,異也,孽也」,《左傳》則言「人棄常則妖興」。所謂「常」,是指主流人事物,非主流族裔因而是妖,非典人生因而也是妖。簡言之,即使有「安」、「好」、「妙」這類女字部的正面語彙,但平安來自「家」的屋簷,而美好來自將人「子」性別化,且美妙是青春年「少」。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恩潔 南方的南方:她者亦是共同體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38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