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民族誌與俗民紀錄片
除了「再現」、「主體性」之外
研究者可以研究自己嗎?
人類學家以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有學術價值嗎?以自我為主角的民族誌合理嗎?如何維持客觀、判斷真實性、證明可信度?微觀角度下呈現的研究發現,和其他人有何關係?是否具足夠公共性而能論證其存在意義?這些提問背後有著對於學術研究過程與成果之想像與預設。例如,認為有機會、且應該完全客觀中立、全然不受個人價值觀影響。又如,認定「他者」或包含自我、但尺度大於個體的單位—「文化」、「社會」、「社群」等—才能啟發有學術意義的討論。
本文目的並非就上述提問給出決斷答案,而是談談個人/個別群體觀點之「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為將討論具體化,聚焦「自我民族誌」、「俗民紀錄片」。兩個概念皆是回應被研究者「主體性」(subjectivity)之反思,也共同面對「再現」(representation)產生的問題,此為並列兩者之基礎。但關於主體性、再現議題現已累積豐富文獻,此文不再重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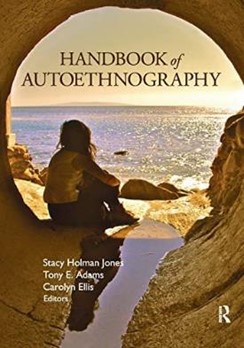
2013. Handbook of Auto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
1980年代前,學術研究對象被認定只能是外在客體,「自我」不能作為研究核心。此想法直至後現代思潮、反思文化概念與文化書寫形式運動興起才被鬆動,開始意識到,對於「事實」的「客觀」描述,難免受再現情境、工具影響,因此權威而必定為真的論述只能是幻想、誤會。不只作者具能動性與主體性,文本、讀者也可能作為染劑或調味料,使得作者、文本、讀者三者互動生產出多元、難以預測的結果。文本(民族誌或廣義的研究成果)從生產到接收過程中,滿載主觀詮釋與意圖,訴說的不是「真相」,而是作者、讀者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活著的故事。
進入二十一世紀,關於「自我民族誌」(或稱「自傳式民族誌」)之探討越來越多。Ellis、Adams、Bochner(2011)將其定義為:透過描述個人經驗,經系統性分析後,理解當事者文化經驗,如此不只呈現研究成果,也表述民族誌生產過程。自傳式民族誌與由他人書寫的民族誌,同樣皆透過觀察、分析、理解、詮釋、再現而生產。相較於他人執筆,自我民族誌得以獲得近身、第一手、細節豐滿的資訊,或許能提供更細膩、深入之描述與分析。然而,自我民族誌並非容易書寫的文體,其不只關乎吾人如何認知世界,更關乎如何存在—如何以覺察、反思、有七情六慾的姿態活著(Carolyn Ellis(2013),收錄於Ortiz-Vilarelle(2021)之評述)。意即,要寫出自我民族誌,除了認知表層生活樣態,例如每日行程,更需體察自身如何思考、感受、行動。多位學者因此進一步闡釋(Ellis & Bochner 2006;Méndez 2013),此取徑得以透過述說個人生命經驗,增加同理、共情、體驗他人經驗之能力。
然而,上述優點卻也為自我民族誌招來批評:它如何能為他人接受,而不只是「自我耽溺、自我滿足、自戀的、過於內省與個體化、有可能基於虛構而非現實卻無法求證」的幻想(例如Méndez(2013)文章中引用Atkinson(1997)、 Coffey(1999)、Walford(2004)等學者之批判)?首先,民族誌內容為作者第一人稱生命經驗,審查人、讀者等皆無從驗證。再者,如此獲取的資料恐怕只與自身有關,而與整個文化脫節(可參閱Méndez 2013)。但Méndez(ibid.)也提及,Bochner 與 Ellis(1996)其實已處理了此問題,他們認為,若吾人相信文化對所有個體皆有影響,那麼自我民族誌描寫之個體亦不能自外於此。若是如此,「個體」與「群體」/「社會」/「文化」之界線不再清晰絕對,個體甚至是群體之縮影,得以見微知著,也提供比較基礎。由此,僅屬於個人或微小尺度之田野資料便有了公共性、普遍性。紀錄片工作面臨類似提問,且情況更具體、生動,以下援引紀錄片實例,尋找進一步解方。

俗民紀錄片(folkloric film)
本文「俗民紀錄片」(或稱「民俗學電影」)中的「俗民」概念並非指涉業餘或未受過專業訓練者,而是採用Sharon R. Sherman 所著Documenting Ourselves: Film, Video, and Culture一書定義之「folkloric film/folkloristic film/folklore documentary」,與「民族誌電影」(ethnographic film)有所區別:「ethnographic film」泛指具人類學、民族誌觀點之影像紀錄與創作,傾向(並非全然)呈現「他者」;「folkloric film」則強調第一人稱視角或在地人掌鏡,將創作者視為獨特個體,而非僅以影像工作者、文化載體等集合性名詞分類,消彌了個體性。此觀點下,影像成為創作主體溝通創作動機、選題意識、情節鋪排的管道,但也同時視影像為文本,不可避免地揭露了創作者面目與意向。
若以民族誌類比,「俗民紀錄片」與「自我民族誌」皆被賦予「主體性」,但也因此難脫主觀意識。以下以The Kayapo: Out of the Forest紀錄片,及其被歸屬之分類「原住民族媒體」[1]討論。此處「原住民族媒體」指涉「indigenous media」,此概念1980年代中期後逐漸廣為人知並付諸實踐,非泛指原住民族相關題材作品,而是由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影視工作者主責拍攝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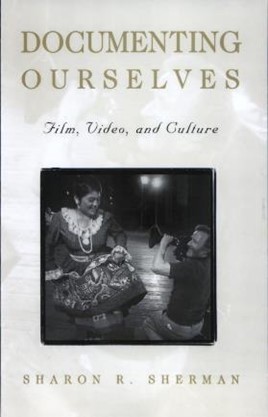
時間回到1989年,地點是巴西中部,Kayapo族人正召集附近聚落成員共同於Altamira舉行會議。Altamira位於新古河(River Xingu)流域,當地將建造巨型水力發電水壩,洪水將淹沒大部分新古河流域村落。會議前幾日,卻有重要幹部因內部衝突而負傷,面臨入醫院接受治療或堅守前線的抉擇。由於政治意涵厚重,這場集會吸引了國際媒體注意。The Kayapo: Out of the Forest記錄了The Kayapo這部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呈現Kayapo族人藉由媒體工具對外介紹自己,並向國際社會發表訴求。
此拍攝計畫由Kayapo族人發起,1987年進行到1989年,為達一明確訴求:紀錄當地文化,並區別過去外界所看到的Kayapo影像紀錄、敘事;回應原住民族於國家與國際權力、資源競逐場域中之再現政治、文化真實性、社會認同想像。往日,通常由歐美專家學者或媒體從業人員申請經費至當地拍攝,再回傳畫面並向全世界播送。當地人認為,如此一來,Kayapo被描述的方式難脫西方文化脈絡,而族人吸收此類敘事後,可能影響自我認同。有鑑於此,想製播由Kayapo族人掌鏡的紀錄片,以圖呈現在地人觀點。外來團隊僅從旁提供建議與器材、技術支援。外來團隊包括芝加哥大學人類學者Terence Turner,及多位自1985年便在此地與Kayapo族人合作之巴西籍人類學者、紀錄片工作者。
影片刻意呈現被視為延續了傳統的當代生活面貌,涵蓋儀式、頭人演說、造訪其他Kayapo聚落過程、甚至與巴西非原住民族群體之衝突。目的是扭轉、甚至匡正我族在外部影視工作者作品中的樣貌,並於長者離去前紀錄下口傳歷史、傳說、生態知識,保存讓後代子孫理解其意涵。更多製片細節與分析可參考Terence Turner所撰The Kayapo Video Project: A Progress Report一文。
Terence Turner另一專文Defiant Images: The Kayapo Appropriation of Video,特寫了遠離村落樹林中的Mebiok(為小男孩命名的儀式),由一位17歲青年Tamok擔綱導演。一開始,搖擺的鏡頭拍出儀式參與者整齊劃一舞步與合諧曲調。下一個分鏡,描繪眾人從樹林前往村落中心廣場完成儀式途中情況:歌曲、手勢、舞步與儀式前半部相同,但舞者穿戴更多裝飾,小男孩們上一代與上兩代親屬也加入跳舞行列,其中有人帶著小男孩共舞。尾聲,場景在村落中心廣場,舞步與歌曲不變,但眾人身著全套儀式用服,包括Kayapo社會中最有價值的華麗羽毛頭飾。
Turner說明,Kayapo族人認為與他人協力進行連綿不斷的「自然」表現模式,例如抒發性靈或模仿大自然歌唱與舞蹈,是Kayapo社會存在的根本,也是組成其「文化」之要素。族人認為,精確重複的儀式環節具體化了Kayapo最上層的價值觀—社會上、道德上、美學上對「美」的追求。這裡所說的「美」意指「完整」、「完美」,經由不斷重複同一模式、順序,每次演示都整合了既有與額外元素,愈臻完熟,因此也不斷提高其社會價值。此為導演Tamok想呈現之重點,故透過運鏡使閱聽者注視儀式過程重覆性,甚至將鏡頭聚焦追蹤一頂不斷以相同方式移動的華麗頭飾。頭飾在此脈絡下不僅是儀式物件,更成為認同載體。導演以頭飾代稱傳統服飾,並突顯不斷重複的儀式流程,強調將「重複」視為「美」的文化價值觀,創造出了具象我族文化精髓的框架。
針對此部紀錄片之評論,多篇指出,美中不足的是,因攝影機終究只掌握於少數人手中,作品多大程度呈現出「真實」,並顧及群體內部異質性,仍有辯論空間。評論者指出,當地人熟悉並活用媒體科技、技術後,透過自身視角對現況、文化、社會組織創作出一套視覺再現形式;這套形式再由具動機與社會資本、科技能力的創作者傳播、強化、清晰化、再形塑。過程中,特定創作者有機會透過製播媒體來展示其個人認知的部落生活與文化,影像作品或許摒除了外部觀點可能隱含的偏見與曲解,但是否呈現「完整」、「具代表性」之在地觀點,是面面俱到或一家之言,卻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回到上述紀錄片案例,掌鏡者不僅扮演攝影角色,同時具導演、編劇、製片身分,正好整合了Kayapo社會成為領袖的要件:有名望,並能透過政治、媒體、文化交流與西方社會連結。因此,出乎意料地,有政治抱負的年輕人紛紛爭取掌鏡者角色,許多有望擔當部落頭人者成為領導人前,都曾擔任掌鏡者。

個體的「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
影像反映出的故事遠多於畫面呈現:內容如何被創作者篩選、剪接、翻譯、詮釋?什麼細節被突顯?什麼細節被壓抑?什麼樣的敘事手法穿插其中?拍攝者與被拍攝者間坐落於何種關係脈絡?掌鏡者如何經由畫面編排與閱聽人對話?一切看似具有公共性與普遍性,但仍難脫主觀視角。觀看「俗民紀錄片」時,若僅著眼其記錄的物質表現、動作、流程、知識、文化體系,其實假定了創作者的缺席,未考量其身分、背景、意圖。如是假定,似乎從根本上違反了反思誰掌鏡、誰敘事的初衷。
Kayapo族人親自參與攝影工作有幾項深意:對內傳承部落歷史,對外宣揚部落文化;更是訴求社會改革的揚聲器,爭取在主流社會、國家結構中的地位。即便可能被質疑「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卻不減「俗民紀錄片」作為批判專業霸權、菁英主義、殖民遺緒的典範之一,此行動本身就有意義,且因其獨特視角而揭示的內容,重要性或許高於「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層次。但不可諱言,上述意義或重要性,必須建立在創作者、閱聽人、評論人多方皆對於影像作品採取後設思考批判、而非全盤接收的前提之上。
同樣地,「自我民族誌」內容是否真的發生過?作者詮釋與記憶是否正確?「自己的故事自己講」一定較不可信嗎?或其實更接近真實?自己的故事讓別人講,就是讓渡了主體性嗎?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不是自我民族誌文體/範式最重要的價值。在並未「蓄意」扭曲、欺騙、操弄前提下(筆者自身都無法覺察則不在此列,那是關於文本為何不可能百分之百客觀、民族誌內容為何無法宣稱絕對權威的討論,可參考文章開頭提及之反思文化與書寫過程的論辯),民族誌內容引起具相似經驗者共鳴,或給予有不同生命經驗者多元思考角度,那麼,一則記錄了人類社會生存軌跡,一則開啟了理論對話空間。若有此用途,對於內容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之質疑,恐怕不足以否定自我民族誌存在意義。更有甚者,人生活於社會之中、是生活環境的產物,任何個體經歷勢必連結到更大脈絡,各種議題透過單一個體向外輻射、縱橫交錯,演示出多層次、大尺度之資訊、圖像。因此自傳式民族誌雖以一人為中心,說的卻是群體的故事。
然而,無論「俗民紀錄片」或「自我民族誌」,都面臨知情同意原則倫理困境。影像創作與田野工作皆須獲得參與者個別知情同意與群體諮商同意,但在某些情況,例如多人參與、現場人流來來去去的公開場合,一一尋求可能出現在畫面或田野筆記中人物之首肯,基本上做不到。Wall(2008)反思其自我民族誌的文章中提及,打算以自己領養孩子、擔任親職的生命經驗為材料撰寫民族誌,發表前先徵詢了一位學界資深前輩意見。她得到以下回饋(p.46,筆者根據英文原文翻譯與修改):前輩說,「這是一個美好的禮物,我開始看之後就停不下來,而且對我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幫助。我不認為我有資格要妳做任何修改,這是妳的故事,以一種優美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妳卻從中點出了我們直覺的盲點,揪出被廣為接受的刻板印象。」
儘管得到積極回覆,Wall(ibid.)在文章中闡明此研究投稿時遇到的學術倫理質疑。原先認為就現有規範,以「自身」為研究對象,已從本質上繞過了對「他人」產生潛在影響而需格外小心的顧慮。然而,論文審查人點出,記述內容除了作者自身,因作者是孩子的照顧者,孩子自然而然成了故事中一角,若明言論文是作者對自我生命的書寫,則孩子的匿名無法做到;另一方面,孩子處於親職養育權力關係中,不可能拒絕參與研究,難以實施有意義的知情同意。但話又說回來,知情同意倫理「困境」究竟是真實存在或矯枉過正,或許還未有共識,且需考量個別案例確切脈絡,方能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推薦延伸閱讀
Ellis, C., Adams, T. E., & Bochner, A. P. 2011. 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6 (4): 273–290.
Méndez, Mariza. 2013. Autoethn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Advantages, limitations and criticisms. Colombian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15 (2): 279–287.
Wall, S. 2008. Easier Said than Done: Writing an Auto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38–53.
Ortiz-Vilarelle, Lisa. 2021. Autoethnography and Beyond: Genealogy, Memory, Media, Witness, Life Writing, 18 (4): 475–482.
Ellis, Carolyn, & Arthur P. Bochner, 2006. Analyzing analytic autoethnography: An autops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 (4): 429–449.
Ellis, Carolyn. 2013. Preface: Carrying the Torch for Autoethnography. In Stacy Homan Jones, Tony Adams, & Carolyn Ellis (Eds.), Handbook of Autoethnography, 9–12. London: Routledge.
Bochner, A. P., & Ellis, C. (1996). Talking over ethnography.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13–45.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1] 可參考Turner, T. (1992). Defiant Images: The Kayapo Appropriation of Video. Anthropology Today, 8(6), 5–16. https://doi.org/10.2307/2783265.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雪裡紅 自我民族誌與俗民紀錄片:除了「再現」、「主體性」之外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7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