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文是流量密碼,長輩照護文也可以嗎?
社群媒體上,育兒日常總被溫柔包裝、廣泛分享、獲得同理,照顧長者的經驗卻多半壓抑在沉默與孤單中。大眾想像中,長輩照護是一定年紀後才需面臨的挑戰,且屆時家庭、事業穩定,也有足夠積蓄。但事實是,不少人因為生命的偶然,被迫早早接受考驗。筆者有二十出頭歲的學生,在那本應為賦新詞強說愁、追求學業、夢想的年紀,卻必須長期守在醫院,事後又得扛起家庭經濟責任、張羅家中長照設備設置、聘僱看護,在其他同學焦慮考試、報告、抱怨父母管太多時,細細品嚐著擔任一家之主的滋味。提早上工的照護者,還沒來得及釐清與父母的愛恨情仇,心理尚未完成對長輩的認同與釋懷,就開始面對臥床、失智、失能、甚至身後事衝擊。此種親職責任的轉換劇烈而沉重,卻往往缺乏無論精神上或物質上的社會支持。

圖片來源:筆者使用ChatGPT繪製。
當代,「親職」概念幾乎都與孩子連結,從國家機構到民間組織,提供兒童養育一套相對完善的機制。與此對照的,是照護的「年齡歧視」(Saif-Ur-Rahman et al. 2021)及代際資源競爭且優先分配給孩童(Gál et al. 2016、Zhong & Peng 2024)。長者與嬰幼兒同樣由於身體狀況與心智能力而需協助,照顧長者其實與照顧嬰幼兒極其相似:協助如廁、餵食、陪伴、看病,幾乎是相同勞務,且牽涉更多重大決策及與相關人員協調的情緒與勞務,但社會普遍展現出對待方式的「不對稱性」(asymmetry,Anton 2012),包容孩童無法自理,但譴責、誤解、忽視年長者。此種「兒童優先」原則,已長期造成長者照護的政策缺口(Humber & Almeder 2003)。
臺灣對於嬰幼兒照顧給予諸多彈性與補助,例如育嬰假、托育補助、彈性工時、親子空間、早療資源,這些制度是重要的進步,反映出社會對親職責任的重視。但當照護對象變成年邁父母,情況截然不同。民眾傾向將兒童照護在家中由家庭成員親自完成,但長者照護則期待政府或非營利組織介入(葉崇揚等,2020)。我們似乎認為照顧小孩和照顧長輩的辛苦不一樣,照顧小孩每一天都是有希望的,會看到他們長大,事情越來越好,對於孩子未來懷有期待、很快樂、願意投入;照顧長輩的晚年卻覺得看不到希望,面對家人身體一天比一天差,越來越傷心絕望,每一天都離終點更近,只剩焦慮、甚至回避。
缺乏輿論意識使制度留下缺口,社福制度針對長者照護的措施遠不及兒童,倡議也相對微弱,經常可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等舉辦慈善義賣或街頭募款;但為失能或弱勢長者發聲的團體卻屈指可數,彷彿社會對「值得照顧」的對象已做出選擇。此情況導致對非正式、低薪勞動力的依賴,並使承擔責任的家庭成員承受經濟與身心巨大壓力(Weiss 2024)。許多在職照護者面臨父母失能時,必須靠請事假、特休、甚至離職來應對(Kim 2023)。有薪假可大幅滿足年邁家庭成員照護需求,但全球超過半數國家未提供此類制度(Heymann et al. 2024)。照顧者承受長期身心壓力之餘,還可能遭遇職場不諒解與經濟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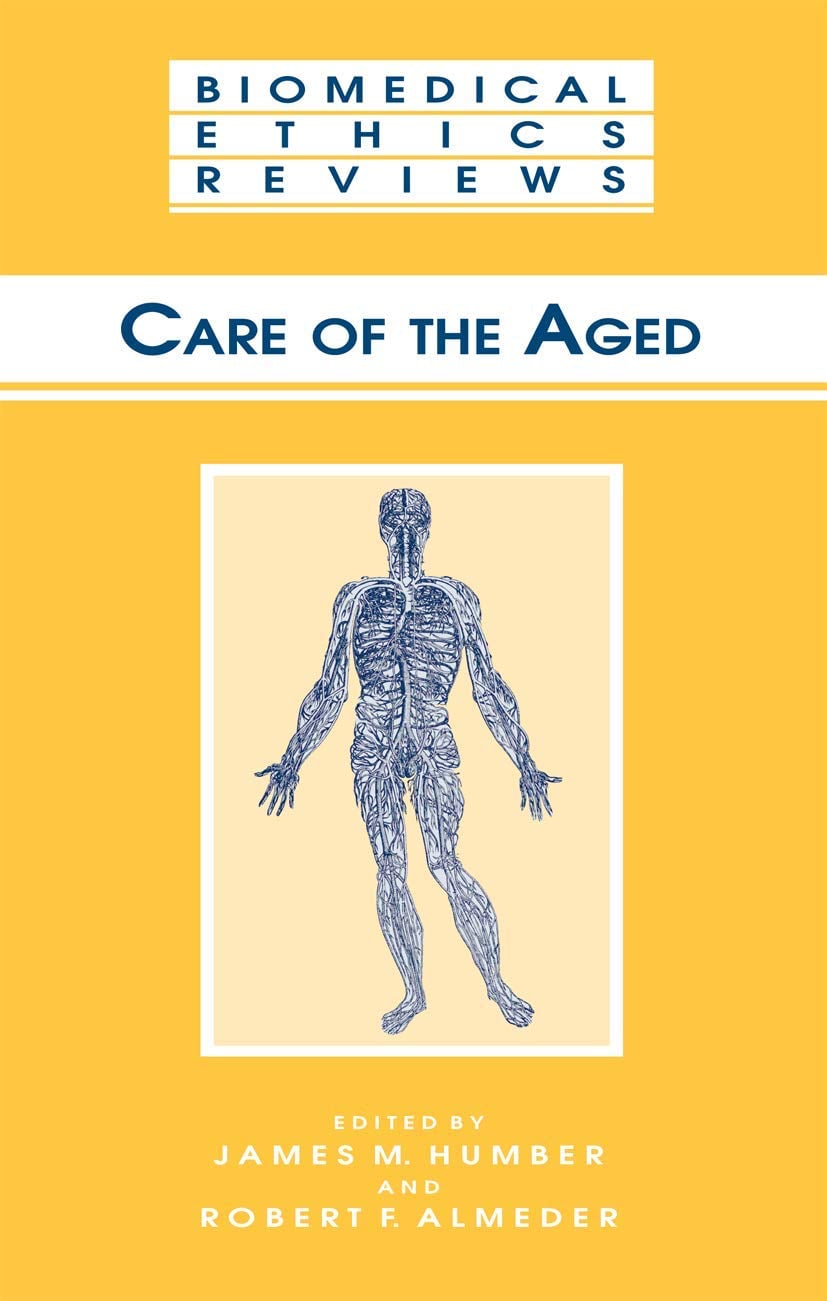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de/-/en/James-M-Humber/dp/1588292401
民族誌中常見不同文化長者具有崇高社會地位,被視為智慧與歷史守護者。然而在我們所處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實在找不到更精確的描述),經常以「生產力」、「產值」來評價一個人的價值。嬰幼兒被視為「潛在生產者」,因此值得投資;長者則被視為「資源消耗者」,因此被邊緣化。此種價值判斷滲透到日常對話與行為之中:對孩童的失誤總是無限寬容,認為他們還小、還不懂事;對長者因老化或疾病產生的失能、失控、無法回應,卻感到煩躁不解。我們總在孩子的塗鴉前駐足微笑,卻難以在長輩的呼求中保持耐心。
對於上述觀點常見的質疑,是認為背後隱含保守的家庭意識形態、「孝道」倫理。類似概念在中、外文化中都經常與權威、壓迫、犧牲連結——長輩不容質疑,子女無條件服從。但Anton(2012)提出「成人尊嚴」(adult dignity)概念,強調即便心智受損或身體機能退化使長者無法表現出好相處、有生產力、具社會功能狀態,仍不足以摧毀一個人一生累積的價值,這種價值並不指向偉大成就,而是在活到老年的悠長歲月中,獲得的經驗、做過的事、說過的話、幫過的人,這種尊嚴不來自於他人的「尊重」,而是必然(ontological),因此年長者的尊嚴並不隨風華而退卻。
相比對高齡社會持負面態度的看法,有不少研究致力提醒高齡社會優點,例如指出高齡化其實是一個群體走向成熟、社會成員享有更高福祉的象徵(Nyce & Schieber 2005);而銀髮族並非不事生產,仍然為社會帶來各種助益,從經濟成長、家庭勞務、家戶或公共照護,到社會參與、終身學習、教導與養育下一代(Brink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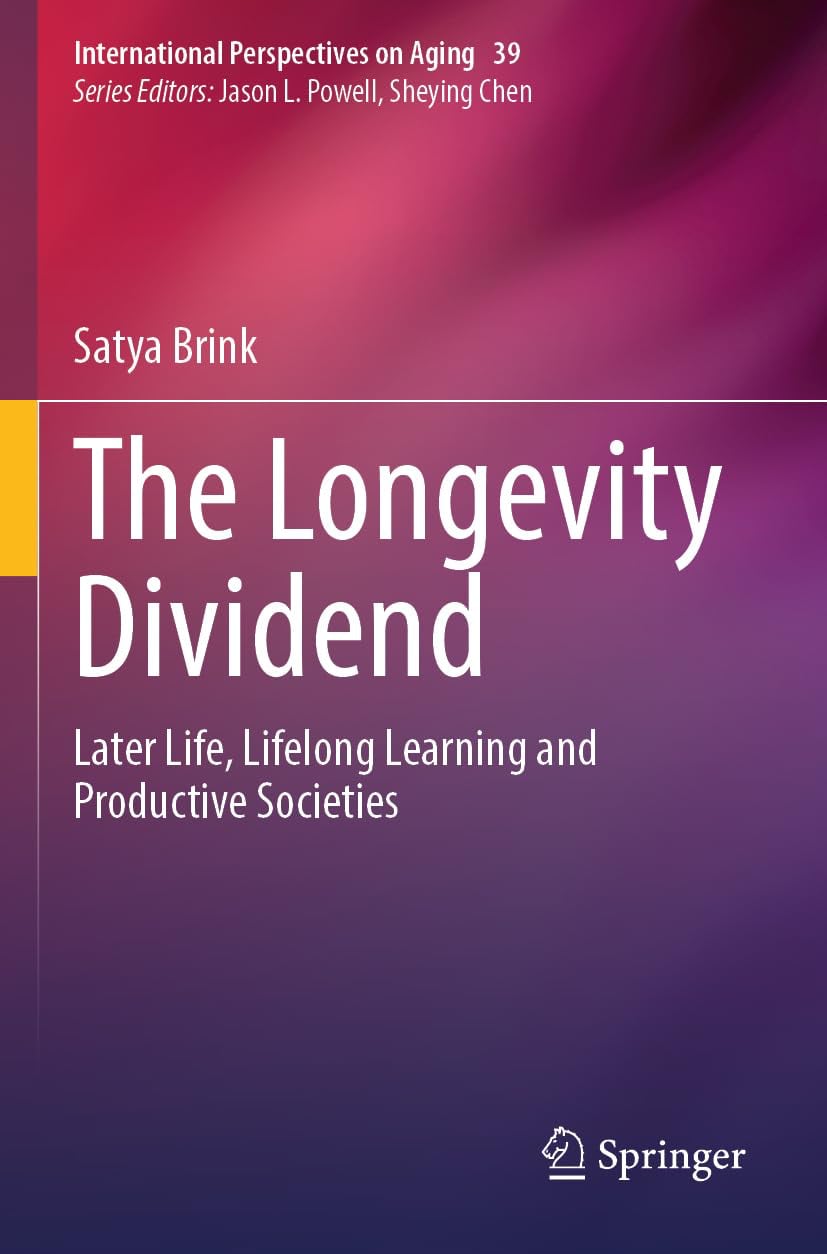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de/-/en/Longevity-Dividend-Productive-International-…
由此,「只有(未來)能創造價值者才值得被照顧」的邏輯很難站住腳。「照顧長輩」與其說是單向、階序性的道德律令,不如重新定義為對關係的回應,基於人與人之間交流所自然衍生的情感與責任感,而非強制的義務。說到底,就如許多父母承認生小孩是為了自己,帶著兩、三歲還沒有記憶的孩童出遊也是為了自己的回憶,照顧長輩何嘗不是,陪伴時間終有盡頭,「卸下重擔」後,是照顧者能少一些遺憾,留下珍貴的相處回憶。這亦是一種生命循環的覺察與生命歷程的對話,曾經弱小無助的被照顧者,在自己的照顧者年老後提供照顧,也理解有一日自己也會步入老年。
社群媒體上,相較於分享育兒喜悅,較少分享照顧年邁長輩或生病家人的歷程。但或許很多人正經歷著,只是不向外人道。照顧者所處的這個生命階段,只是她/他整本生命之書裡的一個篇章,終究會翻篇、會有新的明天。但也因此,很多事當下沒做,就再也沒有機會做;而那個當下雖然只是一個章節,但內容沒寫好,會影響整本書。照顧新生命和照顧生命漸漸走向終點的家人,或許意義是一樣的,表面上是回應被照護者的脆弱與依賴,深層卻是對照護者自身生命的滋養。過程中,獲得陪伴珍視之人的滿足感、豐富的喜怒哀樂體驗、克服問題的經驗、智慧和心智強度、理解他人與自己情緒情感的能力、盡了心力而能盡量免除懊悔的平靜。反而是走過一段看似辛苦、傷心、絕望的旅程,生命才更加完滿厚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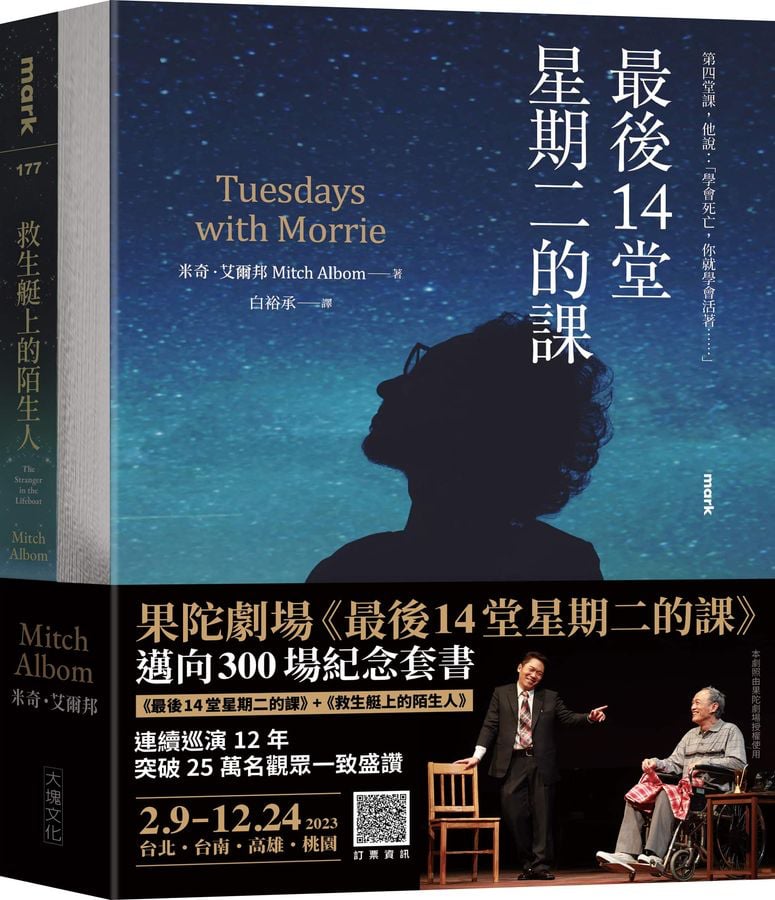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29722682340744004?srsltid=AfmBOorFm…
如果有看到這篇文的照顧者覺得自己正行過絕望幽谷,其實妳/你或許正處於一段很神奇、豐盛、受祝福、有獨特緣分、轉化的時刻。是不是聽起來像垃圾話?但很多垃圾話,會不會才是對真實更精確的描述?《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説:「學會死亡,我們才學會活著。」能否延伸一下:「學會陪伴他人走向生命終點,我們才學會開創自己生命的起點。」當被照顧者(這一回合)生命的盡頭就在眼前,似乎一切都要結束了,但其實,他們的生命將在那些最後時光中陪伴一旁的下一個世代身上延續,無論是血緣上的下一代、生活互動上的下一代、或職涯上的下一代,都是被照顧者精神的見證與體現。因此,辛苦了一段時間的照顧著啊,現在更要照顧好自己,做讓自己快樂、對世界有益的事。無形的不只更長久,而且更真實。很想念的時候,當作長輩只是買了一張機票先起飛,等時機到時,都會再見面的。而在團聚之前,在世的人要好好做完這一生的功課,過得精彩、過得盡興、過得對得起自己和所愛的人,下次見面時,才可以了無遺憾地說:「我把功課交好了才來的!」
參考書目:
葉崇揚、周怡君、楊佑萱。(2020)。家庭主義的分歧?台灣民眾對兒童及老人照顧的福利態度分析。《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41, 1–56。
Anton, A. L. (2012). Respecting one's elders: In search of an ontolog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asymmetry between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dependent adults and children. Philosophical Papers, 41(3), 397–419.
Brink, S. (2023). The Longevity Dividend: Later Life,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ductive Societies. Berlin: Springer.
Gál, R. I., Vanhuysse, P., & Vargha, L. (2016). Pro-elderly welfare states within pro-child societies: Incorporating family cash and time into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alysis (Center for Economic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6-6).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eymann, J., Raub, A., Waisath, W., Earle, A., Stek, P., & Sprague, A. (2024). Paid leave to meet the health needs of aging family members in 193 countries.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36(4), 508–531.
Humber, J. M., & Almeder, R. F. (Eds.). (2003). Care of the Aged. Totowa, NJ: Humana Press.
Kim, S. (2023). Access to employer-provided paid leave and eldercare provision for older worker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26(3), 285–291.
Nyce S. A., & Schieber S. J. (2005).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ging Societies: The Costs of 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f-Ur-Rahman, K. M., Mamun, R., Eriksson, E., He, Y., & Hirakawa, Y. (2021).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elderly in health-care services: A systematic review. Psychogeriatrics, 21(3), 418–429.
Weiss, H. (2024). Family ideology: Uneasy entanglements of eldercare in German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30(3), 555–570.
Zhong, X., & Peng, M. (2024). Eldercare or childcare: Intergenerational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facing care deficit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11, 20.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雪裡紅 育兒文是流量密碼,長輩照護文也可以嗎?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708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