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ble is with us late and s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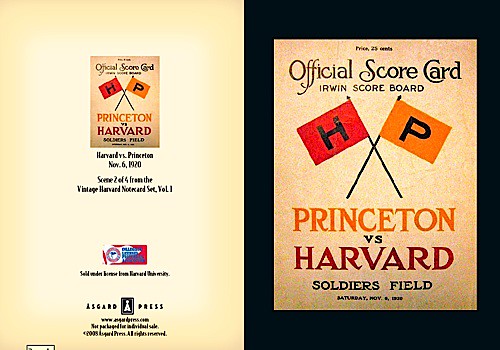

2010年,頂著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逐漸消退的光芒(如果有的話),以及一個位於窮鄉僻壤卻顯得躍躍欲試的年輕大學擔任了五年助理教授的資歷——正因為這兩項調性確實並不一致,讓我很陶醉在一種唐突且帶有古典人類學況味的奇妙氛圍——我透過一些重量級卻因此額外顯得行禮如儀的推薦函之後,取得Fulbright「資深學者」獎學金。再次地,這又是一次令人感到名不符實的困窘標籤。那年的夏天,我隻身前往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訪問。在同年度,與我共同前往亞洲中心共有四人:我、一位歐洲A咖漢學家、一位身任大學副校長且認真修課的中國經濟學家,外加一位喜馬拉雅山登頂兩次的中國億萬富翁。


一同前往劍橋的(何其幸運地!)還有一位台大考古學教授。這名燕京學社聘任的教授在未來將會目睹我一篇投稿到人類學期刊,後來遭編輯委員會以「涉及刑事誹謗罪」退稿的一切過程。他總是用訕笑的姿態鼓勵我,恐怕注定了二人未來以男性獨特的情誼方式,渡過各自互不相干卻又彼此嘲弄的人生。(我感謝他!)經過總共六審的過程——與審查委員們論戰超過40,000字數——這篇三年來以馬拉松式修改超過500遍的論文,最終卻相當意外地以「獲得刊登」迅速收場。「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季,一位書寫者」用後現代意境來表達這篇論文「一粒麥子不死」的際遇,頗具超現實震慄。在這一年的東岸生活裡,我完成了近十萬字的中文書寫,分別刊登在四份屬性不盡相同的台灣期刊中(其中三篇是TSSCI;其中兩篇正是先前答覆審查人意見的40,000字內容)。某種程度上,我發現自己頗能忍受,甚至相當安分於這種杜斯托也夫斯基筆下主人公的孤獨生活。以一種事過境遷(後事實追尋?)的心態回顧此一過程,這種書寫過程總帶來一份不確定的樂趣。


我並不清楚這種「不確定」是否帶有冒險、自信,外加些許頇愚成份的總和。我前往麻州劍橋前,尚未安排居住處所;台灣Fulbirght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好心地警告我:「你最好趕緊找到住所,我們不願意你凍死在街頭。」(接著她們提供劍橋地區同學會的聯絡方式。)抵達波士頓當天,我直接前往亞洲中心報到,領了學生證(哈佛行政大樓的安檢設施簡直媲美海關一般令人歎為觀止),和一間兩人共用的迷你研究室。(當下我發現「睡在研究室」這個想法已是一種幻覺。)
這間狹小且沒有窗戶的密閉研究室在二星期後來了一位德國籍漢學家,在往後兩個月的相處中,老先生持續問我去過燕京圖書館沒?我總是急忙回答「還沒還沒!我會去的,只是現在有點忙⋯⋯」老教授以中文調侃我:「你今晚打電話給你媽媽(懺悔):『媽!我到現在還沒去燕京圖書館。』」當時我正苦惱於另一篇期刊論文的改寫,在老先生叨念的那兩個月內追讀了近三千頁的民族誌資料⋯⋯(寫到這兒,腦袋裡突然間傳來周董的歌:「你打我媽,我叫你爸,這樣對嗎?」⋯⋯)


總之,我先借住在先前這位考古學教授的客廳,一星期後幸運地在craigslist上頭找到一間極其便宜的公寓,與一位上海復旦大學的副教授數學家共享了未來十個月的半穴居生活(圖中窗戶即是地面高度;右圖是除夕夜自己做的料理)。這種生活與哈佛大學Fulbright訪問學者此一光環構成一項「金絮其外」的最佳寫照:「既平行又高對比」正是人類學調查的特色,這是一種生活在小心維護、隨時有意外的不確定處境;也正因為如此,它形塑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學科樂趣——在那兒開始了我的「地下室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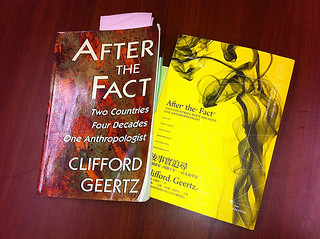

對我來說,人類學生命總是在反諷的處境中發現自己的唐突與無助:聲望與身分、頭銜與實力、野心與能力、改變與安置、不穩定與不知從何而來的好運。以葛茲的自嘲說法:「不知是我到得太晚還是來得太早?」;或者按李維史陀的話語來描述,這是一種垂直閱讀下和諧音與不和諧音的堆疊理解;或者依Appadurai的觀點:「動盪不安也許是活在無所不在的現代性裡最令人興奮的收穫」。這般的人類學生命,不管在田野生活、進修訪問,還是論文書寫,甚至三者根本雜亂成堆(jumble)捆在一塊兒,因此使得自己掉入一個「混亂的多重歷史」旋渦之中(或者按我的話語:「反諷使我們得以更看清楚事物的本質,而因此讓自己戰戰兢兢地生活」)。我用了葛茲生前最後幾篇文章中的最後一句話「Jumble is with us late and soon.」作為這篇短文的標題,期待自己可以學習欣賞這種「不確定」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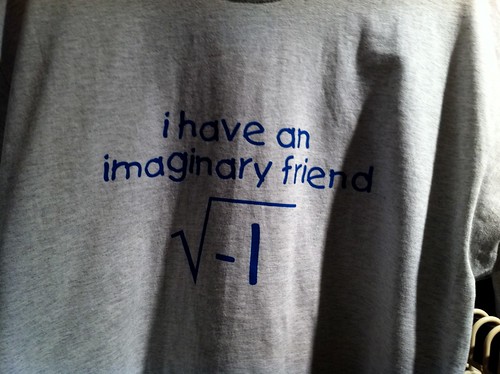
或許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的確,「不確定」讓人感到不安;但是,「安定」是否會因此削弱了一個人的想像能力?在一場例行的導生聚會中,一名大一導生因為自己僑生的身分(父親香港人,母親台灣人)向我詢問公職的報考資格:「我想畢業之後取得公職,然後到山地鄉鎮服務原住民!」我為這孩子的志向因而就讀原住民學院感到無比驕傲又帶有一絲難過。又或者,在上週末在台大社會學系舉辦的全國高中生「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習營」口試中,一位接著一位的高中一年級學生斬釘截鐵並帶有自信地向口試老師表示:「我富有正義感,嫉惡如仇,因此我喜歡法律。我希望將來成為法官或檢察官。」基於一種濃鬱的情感、成人世界的運作規則、學院知識的教育職責,以及身為一位人類學家的特殊經歷,我想告訴她們:「孩子,你的將來有無限種可能性。」
現今這個更為廣泛的世界正朝向片斷、分散、多樣、拆解而移動著,這使得事物現象具備更多元的特質,或是自身成為持續多元化的內容。人類學家因此將在更不具秩序、不勻稱,或是無法預期的處境下工作。[⋯⋯] 而人類學生命正處在如此富饒趣意的時代,以及這項多變不定的專業之中:我羨慕這些即將承接此一時代的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An Inconstant Profession〉,2002)
我總喜歡在課堂裡與學生們分享這段想法:「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信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都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葛茲如是說(中譯本《後事實追尋》2009:227)。當今世界的秩序,按照他的說法,正像是一場突發式地方風暴或是嘈雜的攤販市集;也就是說,此一秩序完全不具任何韻律。在如此的大環境下,事物的發展似乎顯得既紛亂且令人感到無所適從。但是,借自並且翻轉Robert Darnton的話語,或許可以適切地期許此一維特根斯坦式的處境:「在探索的途中,那些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恐怕正是最讓人寄予厚望之處」(《貓的大屠殺》,1984:262)。我知道,這些令自己感到不安的時刻,都將成為日後我最懷念的細節所在。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小林尊 jumble is with us late and soon...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275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