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下)
這次要談的是暗黑,是前兩篇文章(第一篇談傷心,第二篇談善與幸福)約略觸及但沒有細談的部分。
Sherry Ortner於2016年發表的「暗黑人類學及其他者」(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中所陳述的暗黑現實──一言以蔽之,是新自由主義及其效應所塑造而成的當下世界。Ortner發揮她寫作「1960年代以來的人類學理論」(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之學史回顧功力,整理了1980年代以來的人類學發展。秉持她的一貫關懷,回顧主軸仍集中於抵抗、權力,與不平等;因此,她著重馬克思以及傅柯,作為聯繫這兩篇學史性質回顧文章的橋接點──「馬克思與傅柯可謂定義了人類學的『暗黑』轉向,要求讀者以權力、剝削,以及長期的不平等觀點來理解世界」(頁50)。依照Ortner的界定,暗黑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新自由主義及其效應──除了結構世界的不平等,更具備成為理解「他者」之框架的作用,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在暗黑理論崛起之幕後,也在其前台。」 針對暗黑人類學的研究對象,Ortner界定了兩條取徑:新自由主義既是一種特定的經濟體系,加劇了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分化,也是一種治理性的特定形式,在不同歷史地理脈絡中展現各種變貌。(關於新自由主義如何具備意識形態作用,形塑研究觀點視角,很可惜Ortner沒有著墨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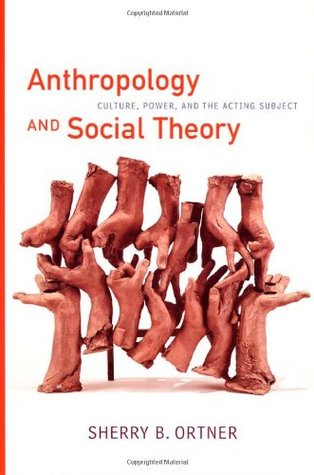
Ortner以「暗黑人類學」指陳1980年代以來的人類學,著重於普遍存在的權力宰制與不平等現象,以及指陳關於經濟不安和懲罰性治理的民族誌研究。但是關於暗黑人類學轉向並不是沒有挑戰的,芭樂人類學刊載的「在《幸福路上》遇到人類學家」就回顧了人類學中的「幸福討論」。如Joel Robbins (2013)的文章就指出:生活於苦難、貧窮之中,或者身處於暴力與壓迫之中的受苦主體,往往是人類學的研究核心。Robbins想建立「關於善的人類學」(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著重於價值、道德性、well-being、imagination、同情共感、關愛、禮物、希望、時間與變遷。
被Ortner歸類於與「關於善的人類學」同一陣營的,還有人類學的倫理學轉向──以Michael Lambek所編的Ordinary Ethics為例。Michael Lambek提到:民族誌工作者察覺到人們不斷努力地嘗試進行著他們認為正確、美善之事,其行為也受到該社會中「正確」或「善」的價值判斷所評價,更日復一日身處於「什麼是好的」之日常生活倫理辯論折衝之中,但是人類學理論卻多半著重分析結構、權力、利益,而忽視這些日常生活的倫理學。因此,Lambek所列舉出人類學家亦可關注的分析主題包括(不少是Robbins所提出的重疊):自由、判斷、責任、尊嚴、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關懷、同情共感、人格、美德(virtue)、真理、論理(reasoning)、正義、好的生活(good life of huma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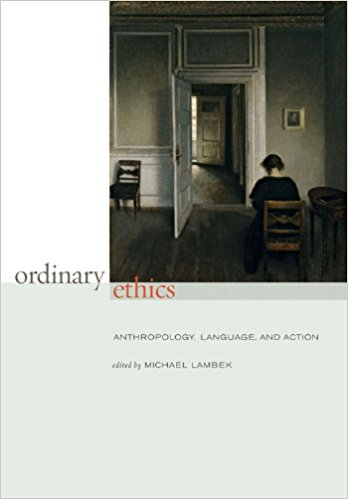
Ortner並不反對Robbins與Lambek。她同意:討論人們如何賦予生活/生命以方向感與目的,或者如何在敵意環伺的艱困環境中奮力尋求好的生活方式,確實十分關鍵。這股潮流在強調新自由主義壓迫與治理性箝制的一片暗黑氣氛當中,閃現了不少出路可能。她也同意:如果無法想像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與更好的未來,那麼我們還能站在什麼基礎來對抗新自由主義?但是,她還是驚訝於「幸福轉向」過於強調信念價值的光明面而相對忽視有關權力宰制與不平等的現實黑暗面。對Ortner而言,討論幸福與倫理學轉向,和關於暴力、不平等、權力的作品,兩者之間似乎有無法跨越的鴻溝。因此,Ortner提出了一種不同的「關於善的人類學」──特別關注批判、抵抗與行動的人類學。比如David Graeber的民族誌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2009)──針對以紐約為基地的運動組織Direct Action Network反對2001四月於加拿大魁北克召開有關美洲自由貿易區之美洲高峰會的詳實記述。或者Appadurai於The Future as Cultural Fact (2013)所揭櫫:以孟買貧民窟為基地的「貧民窟居民國際」(Shack/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研究。這類強調行動的人類學,研究者自身往往涉入運動。人類學家對佔領華爾街運動與另類經濟想像的發言即為一例。Appadurai的「貧民窟居民國際」亦為行動人類學的例子:藉由安置這群資本主義的底層賤民並訓練他們基本的研究與記錄技法,Appadurai提出:或然率的倫理學(ethics of probability)與可能性的倫理學(ethics of possibility)──前者對應到暗黑人類學的現狀分析描述,後者對應到「關於希望的人類學」──研究對象如何思考、感受、行動,以增廣其希望的生活視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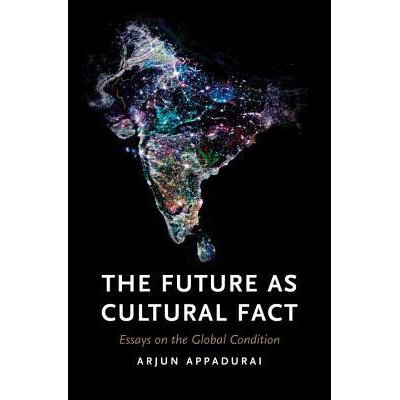
讀到這裡,我想人類學與非人類學的學生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非人類學訓練的學生,可能覺得:的確,人類學應該更政治化一些,更涉入現實衝突一些,更「行動」一些,更弄髒手一些,而不是以研究上的客觀主義將自己封鎖於現實政治圈之外。但是人類學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可能挑眉質疑:「行動涉入」對於開拓與細緻化人類學知識,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新議題,從而回答先前的研究累積所無能處理的問題?或者只是另一個誘拐並不比當地人或社工專業者在行的人類學訓練者陷入現實政治鬥爭,犧牲學術勞動時間精力,乃至以人類學科最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知識特性為祭品,導致人類學的消失?
針對人類學系的學生會問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學科知識的開展問題,Ortner所標舉的「批判、抵抗、行動」似乎又走回了1980年代抵抗研究的老路,而呈現出理論上的倒退。Ortner針對這一點,提出了一個學史外部的原因:抵抗研究曾盛行於1980年代,但於1990年代中期由「鋪天蓋地全無出路」的傅柯式治理性討論取而代之。這固然其有知識史嬗進之故──治理性理論能更有效面對權力的細緻滲透與做工(特指主體形塑)。但亦不可忽視學史外部的原因,也是知識社會學的範疇:1990年代的現實世界已經更加黑暗(依照Ortner的定調,即為更被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滲透架構),1960與1970年代乍似可以改變現狀的社會運動許諾也逐漸淡出,1960年代與1970年代出生的人開始經驗到美國夢的瓦解,「抵抗」顯得空泛不切實際,更加細緻的治理性概念看起來似乎更為貼近於真實世界的實際狀況。她認為,1990年代興起的後現代論述與大敘事之終結(伴隨著抵抗與革命之終結)也可以在這個脈絡下檢視。
人類學訓練的學生,很難被學史外部的原因完全說服。「暗黑人類學及其他者」刊出後,下期(2016年Hau雜誌6(2)期)刊出的幾位著名人類學家回應也一樣。Rutherford與Laidlaw顯然沒有被說服,而Appadurai與Graeber則採取比較同情(但期望概念能更細緻而議題能更開展)的立場。他們的回應,我就不在此細摘了。

最後,關於傷心的人類學
看倌還記得這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談的是「傷心」,是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的易受傷性。問題意識起源於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我將「傷心」置於「暗黑」背景中,試圖將Sherry Ortner的「暗黑人類學」與Ruth Behar的「傷心人類學」結合起來──其實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common sense了。我只是借用兩位作者的大作賦之以喻:
認識到時代的性質就是黑暗,不可能不傷心;然而與選擇其麻木與虛偽,還不如傷心。經過深度反思與高度節制的易感性往往具備撼人的力量。但是同時,如果傷心流露出淺薄廉價,問題可能不在脆弱易感,而在於……(下回或下下回分解)。(本系列第一篇)
各位知道答案在哪裡嗎?是什麼會讓部分研究者將訴諸苦難的民族誌視角稱為一種(旁觀他人之苦難)「偷窺式的三級片視角」(”voyeuristic quasi-pornography”)(Kelly 2013,轉引自Ortner 2016這篇文章)呢?是什麼又讓Ruth Behar尖刻地批評:那些將自己的脆弱性與個人經驗刻意隱藏,將研究中的「情感」因素隱而不提,實乃藉由隱藏自己的立場實則上演學院獵頭劇碼的弒父者呢?(註)
我認為,是立場角度的問題。是研究者願不願意客體化自己的參與,以及客體化的同時正視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脆弱性。情感上的脆弱性,也意味著「同情共感」程度上的開放性。

我確實不認為Robbins的「關於善的人類學」,或者常常舉出他的名字來代表的幸福人類學陣營,與Ortner所命名的暗黑人類學相互對立。而我也的確覺得Ortner大刀闊斧式的學史分析的確已經不太相契於當下講求細緻理路的概念定義。我更不認為Behar所說的「易受傷的觀察者」與暗黑人類學較為親合,而與幸福人類學關係較遠。並不。民族誌工作者在田野中是開放的,因此也是脆弱易受傷的。他可能因為目睹暗黑沉重的現實而脆弱,但也可能因為目睹人們在暗黑中的努力而感到些許振奮。作為民族誌書寫者,他的易受傷性會直接傳達給讀者--這是田野工作者與田野中的人的同情共感,也是讀者與民族誌書寫者的同情共感。是不同層次的同情共感。
有時我會遇見在田野中研究尖銳議題而遍體鱗傷的朋友,或者經歷運動傷害(和永無休止的自我懷疑)的朋友。有的人凝視過尼采所說的深淵(彷彿也正在毫無辦法地變成深淵)。他們好像從來不知道,在田野中所受的(心理的)傷害如何療癒。我不認為療癒可以制度化,至少這並不是目前台灣的人類學教育可以負擔的。很多時候他們得仰賴著各種(多半是)非正式的療癒管道──媽祖、筊杯、聖母、耶穌、十字架、符水、濟公、收驚效勞生──或者咖啡、茶、基隆鹿港北港知名糕餅舖的點心。換言之,是研究者的福德、業與命。但這可能是人類學教育(不只是台灣,北美也是)的黑箱。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在談「暗黑」之前,還不是開啟「傷心」的時機。但就算約略簡單談了暗黑,也覺得,田野工作者的「傷心」,目前還是很難仔細去談論。我們的語言還不夠,準備也還不夠。
但是,有一篇芭樂文,我想推薦各位(主要是我)回去重讀:用聆聽與行動療癒創傷:給反課綱運動同學及其他大人的一席話。
這篇談論療癒的文章,雖然主體並不是田野工作者,卻很接近我心中的「傷心人類學」。
三部曲還是得先打住。於是我暫時寫到這裡。
註:特指兩位後輩評論者評論Renato Rosaldo "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 (1984)過於訴諸個人經驗,其情感主義可溯源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文化。Behar認為這兩位評論者刻意忽視Rosaldo的觀察者立場,在脆弱性(的同情共感上)完全封閉。詳見《傷心人類學》第六章。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bricoleur 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52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遍體鱗傷(窩又錯字了......)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