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二二八
擴大「我們」的邊界,向起而抵抗的靈魂致意
今年真的 … 還要 … 再寫二二八嗎?雖說芭樂讀者之中,看到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字眼就躁動的人應該是少數,但每年都談這個主題,讀者會不會膩啊?(顯示為焦慮)再說,近日大家的注意力,應該都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萬一阿共攻打台灣美國會不會出兵攻佔了,75年前在台政權發動的血腥軍事鎮壓,以及後續四十年中對至少兩萬名真實的、潛在的、被誤認的、被公報私仇誣陷的異議者荼毒迫害的歷史,對於21世紀居住在台灣的人們來說,是否覺得有些遙不可及?或者,歷史場景中的人事物,反而突然變得鮮明起來?
為了避免少數芭樂讀者誤以為這些事情很遙遠,為了維持民主健康體質,還是來做一下基本衛教。在威權統治時期(aka KMT一黨專政的黨國時期,那些覺得為什麼只針對K黨的人,建議可以先讀這篇),掌權者傾國安、情治、軍隊、警察、教育、外交等公務體系之力壓迫人民的眾多政治案件,雖然發生距今75到30年不等,但中間經歷了長達40年的噤聲期(i.e.如今天在香港或其他PRC境內城市,只要預備紀念六四就會遭到當局逮捕),真正能在公開場合談論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不過30年。禁忌之所以能逐步打開,需要感謝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鄭南榕先生等多位民主先行者,在威權煙硝仍未散去的1989年初,便開始極力爭取紀念二二八。只是,解除四十年累積的心理防衛慣性的速度,不見得跟得上體制變革的速度。至今仍有許多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心靈長久被恐懼籠罩而畏於啟齒。
反覆出現是意義的抵達,或是抗拒引發的重複衝動?
可能有人會說,如今三十多個年頭過去,政權三度輪替,從李登輝開始,歷任執政者反覆在紀念儀式上代表國家表達歉意,二二八也已成為國定紀念日,擁有專屬國家紀念館、紀念公園,已被寫進教科書,每年有愈來愈多人加入民間發起的二二八紀念遊行,由關切人權議題的青年們舉辦的共生音樂節也邁入第十屆,相關口述歷史見證、學術專著、藝術創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表面上看來,二二八作為歷史事件的名詞,已經在公共空間反覆出現了無數次,我們是否還需要談二二八?
歷史學家們可能會說(抱歉僭越了):當然需要談!君不見許多關鍵政治檔案才剛出土,須留待研究者細細爬梳。何況大部分民眾對二二八的印象只停留在大稻埕查緝私菸,天馬茶房,林江邁,陳文溪,包圍長官公署,全島抗爭,軍隊鎮壓或「綏靖」(看你站在人民或政權的角度),至於這些人事地物之間的因果關係及時序細節為何?哪些握有決策權的體制參與者在哪些環節做了什麼?導致何種後果?以「反共抗俄」為名施加的侵害人權作為是否合乎當時的法律?諸多尚待考察的來龍去脈,涉及戰後史觀的重構,國家合法性、法律正當性的重要探問。然而,按照與我交流過的多位線上教師的說法:倘若教科書裡沒寫,考試不考,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也就船過水無痕。
總是想太多的精神分析學家則可能會換個角度問:當一個名詞反覆出現,究竟是因為它欲指向的真實已為大眾所知悉?還是這樣的反覆出現本身,恰好說明著它欲傳達的訊息尚未抵達他者,被適切地接收?抑或是,類似某些反覆出現的精神症狀,某個未成形、被噤聲的經驗,在與意義藴生的符指鍊扣連的嘗試中,因著主、客體各種因素交織影響下失之交臂,只能墮入無止盡的重複循環?

自我形貌在談論二二八時彰顯
為了探問歷史創傷記憶何以如此之難,這一次就讓我直接進入心理動力的領域,邀請讀者一起來思考,一段重大政治暴力創傷歷史,如果真的已成為歷史,為什麼光是談論它,就會引發這麼豐沛的情緒,甚至是壓制、攻擊的行為?(例如,近日南部某大學諮商相關科系邀請促轉會成員及政治受難家屬共同主講政治暴力創傷與療癒主題,貼在校園公佈欄的宣傳海報遭到毀損)為什麼了解、記得二二八的邀請,會被快速連結到「撕裂」、「提款機」的政治動員陰謀論?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記憶,真的能夠有效地轉譯成政黨政治角力的槓桿嗎?而反二二八的言論,是否不存在政治動員的成分?我想,談論二二八,不只是涉及歷史與記憶的爬梳(重建歷史真相),甚至不只是政治價值的選擇(確立及捍衛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是作為一個人,我們是否終究有勇氣直面形塑自身身份認同(以及不知不覺中選擇站立的位置)的各種力線,檢視維繫自己及自認歸屬的群體形象的情感需求?
無論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被捲進這段創傷史,在其中真實與想像的歷史位置為何,是否願意訴說、聆聽、承載,或是逃避、否認、蔑視,實際上與形塑個人和集體身份認同的心理狀態密不可分。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談論或避談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擁護或斥責某些談論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方式,很大程度取決於我們選擇以何種姿態、距離,與這段歷史發生關係。因此,談論「二二八」(當然,「二二八」可代換成人類歷史上、或眼前正發生的各種強勢對弱勢的欺壓,以及弱勢對強勢的抵抗)的同時,恰好彰顯了我們自己的形貌。儘管身份認同這個概念在賽伯格時代聽起來像是個過時老舊的容器,但是不妨礙在真實的心理及社會生活中,它依然扎扎實實地影響著不同層次的人際關係動力,並形塑著區域政治與地緣政治。
一次預料之外的對話場景
2021年11月底,應「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邀請,我在堂體內(也就是那一尊超過六米高的大銅像底下)舉辦了一場「我身上的威權印記」探索工作坊。可能是我的文案寫得不夠吸引人,原本網路報名人數僅29位,當天天氣濕冷,實際出席的人數不到一半。有研究所學生、歷史老師、助人工作者,也有一位剛滿18歲的白恐三代,平均年齡25歲左右。他們對白色恐怖歷史認識程度不一,十分有興趣探索威權遺緒以何種形式潛藏在當前社會大眾的認知、思想、行為慣性中,甚至遺存在對威權的辨認能力,以及與各種形式的權威應對的方式裡。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現場另外來了十多位年長參與者,人數甚至超過了網路報名者。後來得知,她/他們是中正紀念堂的導覽志工,平均年齡70左右,全是藍營死忠支持者(這是可以想見的,如果不是,大概很難導覽常設展中把蔣公奉為民族救星的史觀)。在我說明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如何以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的手段對異議者進行壓迫,又對社會各層面進行嚴密控制,並以經濟發展作為障眼法,隔絕民眾對壓迫真相的認識時,志工們在底下嘰嘰喳喳,顯然十分不以為然。

若回憶帶來撕裂,撕裂的不是關係,而是過度理想化的自我認同
我接著做了一些自我揭露:我年輕時就是黨國教育下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人,深信官方媒體傳播的版本,包括污衊政治良心犯為暴徒的指控。於是,我曾經以自己的無知和錯認,間接捍衛了威權統治體制,助長了對民主抗爭前輩們的鎮壓及社會污名。睜開眼看見自己的錯誤,發現自以為正義,原來卻是站在公義的對立面,的確會引發羞愧和痛苦。但作為一名願意相信悔改是救贖之道的天主教基督徒,我認為真正的原罪是拒絕看見他人處境。
嘈雜聲漸緩,我看見一雙雙狐疑不信任的眼神。我進一步解釋:輿論上經常把促轉會委員們稱為「綠營打手」、「塔綠班」,甚至非人化的「綠蛆」。但我從來不是民進黨員,唯一曾經被慫恿加入的政黨其實是國民黨。實際上,我的政治立場其實既紅又綠,在曾經擁有法國國籍時,我支持過法國共產黨,我的綠是環保綠,在許多環境議題上,經常跟DPP唱反調。我不贊成K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說法,但是K黨作為四十年威權統治時期唯一執政政黨的繼承者,必須要直視自己在黨國時期令成千上萬個家庭家破人亡的事實。非常重要的是,雖然在二二八期間,死傷的絕大多數是所謂的本省人,但在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之中45%是所謂的外省人。所以重點從來不是省籍衝突,而是國家以合法外貌包裝非法手段,大規模侵害人民基本人權。而我認為外省受害者更辛苦,處境非常類似家暴受害者,寧可犧牲自己,不敢聲張,以免背負破壞家庭和諧的罪名。可是,若要受害者、受難家屬,以及社會大眾相信KMT性質已經改變,不再是支持威權統治者侵害人權的政黨,就必須從現在起就一起參與修復式轉型正義的工作,而不是一味地否認,把修復個人、家庭、集體創傷和不同群體成員間社會信任的責任,丟給現在及未來的世代,彷彿事不關己。
接下來,四位擔任分組討論桌長的心理工作者,亦一一分享他們自己意識到作用在自己身上各種政治力線,或簡化的說,政治「啟蒙」的歷程。其中一位是八零年代出生,其他三位均是九零後。前者出生在本省籍家庭,卻被刻意送進專門為外省權貴子弟設置的菁英中學,希望未來能躋身「上流」社會。說字正腔圓的國語,消抹原生家庭文化的痕跡,成為王道。她的分享讓我想起自己小學時經常被老師嘲笑客家C音,因而奮發圖強每天聽中廣相聲糾正口音的童年。
三位九零後工作者,是開始能在校園中接觸到台灣鄉土教育的一代。其中兩位成長於深藍外省家庭,最顯著的政治啟蒙時刻要算是三一八公民運動,為此和家裡發生或顯或隱的衝突。其後發現,家族成員中儘管是擁有高學歷和豐富社會歷練者,經常無差別地激烈批評綠營政治人物,在line群組裡轉傳內容農場生產的假消息。也有在其他面向上謙恭溫和待人者,一旦談起綠營執政相關議題,幾乎像是變了一個人,無法理性討論。第三位九零後則生長於深綠家庭,家族因曾有土地被強制徵收的過往而痛恨國民黨,從小經常看著家人對著電視痛罵,也聽聞許多兩蔣戕害政治思想犯的故事,可理解長輩的憤怒,但也覺得容易陷入偏激、無法思考的狀態中,期待能帶著理解長出自己的判斷。
幾位主持者做完自我探索示範後,進入分組討論時間。我原以為年長志工們會紛紛走避,不願入席,但是他們留下來了。(聽說是因為志工有必須完成進修課程點數的壓力,真是辛苦了!)討論的一開始,人數佔優勢的志工長輩們,幾乎主導每一組的話語權,對於由心理師擔任的桌長事先說好的發話規則視為無物。想必是前面一小時的聽講,累積了不少憤怒需要發洩。志工長輩們紛紛表示,到政黨輪替以前,她/他們從來沒有感受到任何一絲威權或獨裁的氛圍,他們帶著感慨回憶著當時台灣的經濟繁榮,民生富庶,社會安定,什麼問題都沒有!他們說:現在,才真正是威權統治!蔡英文才是真正的獨裁者!
四位擔任桌長的心理工作者很鎮定,並沒有企圖反駁,很盡責地幫忙摘要他們的發言,確認他們的立場被同桌組員理解無誤。我巡桌時,也只提醒時間有限,需要讓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機會。有些年輕參與者低頭不語,看起來很悲傷,有幾位等待可以說話的縫隙,講著自己所認識的台灣史和政治受難前輩的遭遇,有些分享在深藍家庭長大的辛酸和衝突。那一位白恐三代青年,很率直地表達了國民黨必須要為迫害他阿公、剝奪了他人生24年的歲月負起責任。被迫聆聽年輕人想法的長者們,逐漸轉為沈默。然後,有這麼一兩位,開始淡淡地,緩慢地回憶起,當年他們沒有辦法直接與在對岸家鄉的親人聯繫,連寄一封家書都得輾轉曲折,必須先寄到日本,香港,或其他第三國,免得被告發「通匪」,置自己和在台家人於險境。
你可能會說,連最基本的親情聯繫都會被懷疑是通匪,這不就是白色恐怖的日常嗎?這些外省長輩的父母輩,當年在戰亂中被迫逃亡離散,想必極度思念家鄉,卻只能戰戰兢兢想方設法與對岸的家人聯繫。明明親身體驗過威權統治下的驚惶,卻被患了被迫害妄想症的獨裁者情勒,逼迫大家都要跟他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連生命安危受到脅迫都可以忍受,還繼續認同、擁護加害者,這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嗎?!
心理分析師分身在此提醒大家:請大家暫時懸置輕易的診斷標籤,避免把疾病診斷當成貶抑人格的工具。作為心理工作者,即使面對昧於現實的荒謬行徑,甚至做出蔑視他人人權和尊嚴罪行的犯罪者,專業訓練要求我們在面對面地對待接應中,暫時懸置道德評價(請注意:並不是不做評價),以便讓出心理空間,理解眼前的這個人,為何選擇了一個拒絕看見他人或自己受苦狀態的視框?為何看不見施暴者的不義?
選擇性創傷、集體退行、理想化自我與毀滅衝動
國際對話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Dialogue Initiative)創辦人,兼具精神科醫師身份的督導級資深精神分析師Vamik Volkan,自吉米・卡特時代起,便開始在全球發生激烈政治或武裝衝突的地區,推動對峙群體成員之間的非官方對話平台。根據自己作為賽普勒斯土耳其裔的親身體驗,以及累積超過三十年的獨特臨床經驗,Volkan發表了大量圍繞著歷史創傷、群體間衝突、大群體身份認同等議題的精神分析取向深度心理學著作(2019年出版的科普著作Large-group identity, who are we now? leader-follower relationship and societal-political divisions,中譯本已由心靈工坊出版,書名為《我們為何彼此撕裂?:從大團體心理學踏出和解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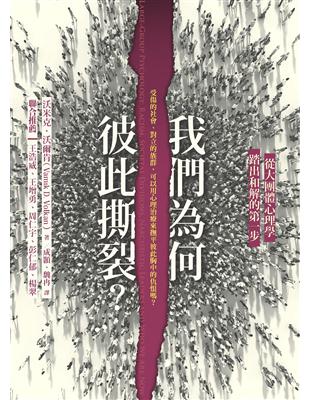
在我看來,Volkan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不僅是將精神分析對於個體的深層心理動力認識,運用在大群體成員的情緒、思維及行為模式的理解上,更在於他指出當大群體身份認同建立在選擇性創傷(chosen trauma)和選擇性榮耀(chosen glory)時,將大幅提高對他群的敵意,並可能在集體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防衛機制影響下,將自身的恐懼、仇恨、攻擊衝動,投射在敵視群體成員的身上,將他者想像成威脅自身性命的惡意存在。倘若面對想像或真實衝突的大群體成員,遇上一名自戀型領袖人物,則群體成員極可能發生退行狀態,過度理想化該名領袖,把他視為比父母更偉大的保護者,並在強烈依附需求催生的幻想中把自己和領袖融為一體。自此,被高舉為至善至美至聖的大群體領袖,若號召眾成員將敵意投射到被非人化的他群成員身上,一切消滅他群成員的殘酷暴行,都將被合理化成自我防禦、甚至是正義的光榮行動。
打開異質對話空間
Volkan的大群體心理學,的確在相當程度上為全球歷史上及正在進行中的由擁抱大XX思想的政治領導人發起的戰爭和屠殺的心理成因,提供了一個解釋的理論框架。需要特別提醒的是,選擇性創傷的概念完全不否定真實的創傷經驗。我自己的解讀是,選擇性創傷反而是選擇逃避直面、轉化真實創傷經驗的結果,以至於面貌模糊的創傷記憶碎片可被有心的政治領導者操弄,以抽象意識形態取代真實創傷經驗,並將它凝鍊成對於非我族類的濃烈恨意。所幸,大群體的「大帳篷」(Volkan提出的隱喻)並非只護佑著高同質性的成員,同溫層中仍存在有能力容忍異質性,有意願冒險朝向他者開放的人們。和平對話的契機就是從這些人們開始。透過第三方(通常是受過訓練的心理專業工作者)的折衝,衝突中群體成員有機會緩慢地了解彼此的經驗感受和現實處境,在相互認納的前提下,共同建立和平共處的準則與規範。不過,在今年初心靈工坊為華語讀者舉辦的線上座談中,Volkan坦承,在他超過30年引導和平對話的經驗中,每一次的對話協商過程都極為困難,而且經常以失敗作收。但是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只要衝突群體成員不放棄持續對話,關係修復與和解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
回觀威權印記探索工作坊的經驗,很可惜的是,我們就只有一次機會。工作坊結束時,長者與年輕人們,並沒有戲劇性地出現彼此接納的感人場景,但也未發生激烈的衝突。橫跨三個世代的參與者們,可能帶著第三類接觸(還有人知道這個梗嗎?)的魔幻感離開現場,回到各自的同溫層去。我原本擔心白恐三代在表白自己身份以後,仍舊聽到這麼多國民黨支持者的言論,會難過受傷。沒想到他的回應無比輕盈:「還好耶,以前只是聽說有這一種人,今天第一次現場碰到,我覺得很新奇!」(大媽融化~)
抵抗者的集結拓展「我們」的邊界
眼前烏克蘭,與不久前的香港,都遭遇與台灣二二八時類似的軍警暴力。而對他群發動戰爭的政權,對於己群內抗議成員遂行的壓迫與威嚇,亦與台灣經歷的白色恐怖相去不遠。普丁舉著「回復」蘇聯榮光的大旗,習近平聲稱要「收回」台灣以成就統一大業。兩人都以「解救」受苦受難的弟兄、同胞,重現國族榮耀之名,試圖摧毀已享有民主自由的社會,也都同時低估了人民抵抗的意志。這兩位自戀型人格領導者主導下的大規模暴力不僅無情無理,尚且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然而,也就和當年的台灣一樣,許多俄羅斯和中國人民,活在政權刻意製造出的平行時空,看不見、也不想看見國家製造的恐怖正四處蔓延,扼殺有志者對自由、民主、平等、公義的追尋。偏執的獨裁者練就了魅惑擁戴者的雄辯術,假借解放進步的論述,混淆了威權與民主、迫害與自由的定義與分野,掏空字詞的意涵。
當普丁下令射擊的砲彈落在烏克蘭城市,摧毀無數家庭的生活,我腦中浮現國民黨軍隊從基隆和高雄港上岸,射殺遊行抗議者的畫面,耳中響起港警對年輕手足發射上千枚催淚彈、橡膠彈的聲音。儘管仍有部分地球人相信,威權強人以武力撐起的排他自我認同,才是群體存續的依歸,但不論是昨日的台灣,今日的香港和烏克蘭,已有無數個勇於為自由起而抵抗的靈魂,證明著有一種群體自我認同不須倚靠消滅異己而存活。有一種「我們」由愛與信念而生,這頂跨越族群邊界的廣大「帳篷」,足以容納每一個願意進來的人。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彭仁郁 紀念二二八: 擴大「我們」的邊界,向起而抵抗的靈魂致意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18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