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
在兩種[真實]之間
九月新竹交清教授組成的竹風社包場賽德克‧巴萊上集的太陽旗,我和親朋好友以及同學一起觀賞,席間還有主辦者邀請的新竹縣尖石附近部落的朋友。觀賞到一半,還有小孩在旁大哭,很有[全民]電影的感覺,儼然一部屬於大家的電影。

過不了兩周,我和幾位台灣學術界的同行,一起參加了法國外交部在日本舉行的半官方研討會。台灣學者去了6位,很巧的其中4位的研究都和台灣認同有關,因此大會就把我們4位組成一個名為「台灣認同」的panel。加上引言人是長期研究台灣的法籍學者,因此我們這組就在大家都沒事先講好的情況下,台味十足起來。引言人從台灣的地理政治和歷史變遷切入後,四位同仁個別從我們自己的研究角度談論,我自己從社區運動的歷史背景切入,一位政治系的同仁直接訴諸台灣認同的民調數字,以及台灣在國際上被拒絕的事實,並且認為這是這些號稱老牌民主國家的偽善和恥辱。
panel的評論人正好是法國學術界兩位重要人物,他們似乎被政治系同仁直接的聲討震住了。是的,這樣的指控直接而不容逃避。因此他們在評論時似乎完全遺忘那些拗口的學術用語,直接回應「台灣問題」。其中那位歷史學者的評論大致說,可以理解作為台灣人的辛苦和用心,但是政治上的局勢是如此,言下之意是你們可以有甚麼做法呢?聽起來不大像論文評論,我們四位仍然必須回應。
輪到我時我心想,天啊!是的,我必須承認國際現實就是這樣,我這個獨立主義者要怎麼在一個半官方的場合接受這件事?我只好誠實地說(是的,誠實才能找到解藥):
我們理解我們的未來是這麼的不可掌握,但是…(是的,我不服輸,台灣這麼多年來都如此妾身不明了,還會更糟嗎?就在這時,賽德克‧巴萊在我腦海冒出來)就像最近台灣最紅的一部片,賽德克‧巴萊,我們的現實是這麼不可預測,但是我們懂得找,並且不會停止找一種精神,那是[真正的人]。不管現實如何,我們不會放棄找一種真正的人的精神,那才是我們的價值和資產。
說完之後,我自己似乎也得到一種解放。原來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塊台獨的招牌(也許那會生鏽),而是懂得誠實地找[甚麼是真正的人]。真是感謝賽德克‧巴萊,在那不能認輸的一刻,它也讓我自己「頓悟」。多年來我自己的研究不願直接以台灣為尺度,寧願在地方社群著墨,也是期望自己找到藏匿在底層的動力。原來我們和他們如果有不一樣的地方是在這裏,我們不是在追求一個不動的神主牌,而是懂得尋找:[我是誰?甚麼是真正的人],是這個精神在支撐我們,而不是一種[要求]或[指責]要成為甚麼?也是這個問號,讓我們的社會得以維持動力和生命力。正如那位歷史學家說的,他竟然在這裏碰到一個正面的民族主義。我們費了許多唇舌想告訴那些懼怕民族主義如蛇蠍的人,台灣民族主義是這麼不一樣,答案在這裡。會後一位在聽眾席的台灣同仁和我說,秀幸,我很喜歡你的發表,那不是枝末細節的分析,而是一種力量。我心裏想是最後回應的賽德克‧巴萊,讓我們大家都有力起來。

回來以後,接著下集上映,我們幾位好友約了一起去看,那天是在新竹遠百的樓上。我們幾個人坐在最前兩排,因為看得人實在太多,買不到後排。下集看完後,我從上集共享的勇氣感,瞬間頓入了羞愧感。在上集我們看到的是勇士們奮勇出征,在下集我們看到的卻是勇士們為他們的英勇如何[承擔]的過程。當他們決定反抗時,求得只是如何死得有價而已。換言之,在那個漫長的森林戰役中,賽德克族求的不是贏,因為知道完全沒有贏面,而是死得有價。然而那個死卻不是一了百了,而是遭受飢餓與恐懼,歷盡艱難折磨。
當霧社起事之後,他們退往山上守,日本人的飛機就在天上飛,年輕人往天上鳴槍,莫那魯道說:「你們那麼害怕嗎?」。下集正是精神淬煉的開始,這些人要為他們的勇氣負責。彩虹橋呈現的並不只是賽德克族的善戰而已,更是一場藉由戰鬥呈現肉體和意志結合的過程。當日軍以飛機,砲彈等強攻猛打時,賽德克族只有身體、意志和熟悉的山林。他們像風在森林中的迅速和機警迎戰,然而身體卻有它的極限。少年巴萬在吃不飽睡不夠時,央求莫那魯道早點和日人正面迎戰,以求早日一死把義務盡完。然而他們還是小心翼翼地戰到最後一刻、戰到一無所有,善用了他們所擁有的一切:身體、意志和山林。
當莫那魯道知道自己已經用完他能夠用的一切時,他還有最後的義務:不讓敵人找到他的身體並得以羞辱他。他和兒子道別,和兒子說,以後由他自己決定要怎麼做,受降還是繼續抵抗。但是他要去盡他最後的義務,把自己的身體藏起來。一位戰士雖然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卻無處容身,身體的去處也必須靠意志事先妥善安排。

我們在此看到的不是誇耀的勇氣,就像到處爭論的是不是英雄,而是一個深刻的「犧牲」的過程,如何把肉體奉獻出去的過程:那不是一了百了的自盡,而是把身體的能力用到極致,善用了部落的智慧和教誨。過程中族人的煎熬,沒有食物,男人們餓到發昏,婦女以死來相讓食物。突然憶起年輕時看過某位蘇俄名導的[犧牲],除了巴哈的音樂,以及一個不斷燃燒的房子之外,狀似矯揉造作,我實在絲毫感受不到犧牲的深刻。(這部片還得了大獎,文化差異?還是名氣作祟?)
我當場為自己的貪吃和懶散感到羞愧,想想我們用到我們身體多少?我們沒有善用過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腳是拿來踩油門的,我們的手只拿來敲鍵盤,自從有了平板電腦之後,一指神功代替了四指神功。當代人一方面缺乏身體的實踐,一方面卻發瘋似地受身體的制約(想想多少減肥藥),也因此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犧牲」吧!在這部片裡身體是一個高度強調的主題,不管是騁馳在山林裏獵鹿,或是面對文明的敵人時唯一的武器,到彈盡糧絕時,對身體的實踐的透徹,恰恰得到對身體的主宰和解放。對身體的善用讓敵人喪膽,完成價值的締造,意志和身體如此地緊密合作,獲得最後的尊嚴。
當我看完電影走出戲院,一層一層地離開那間百貨公司時,感到當代人的枯絕和任性。我們的熟練表現在刷卡、簽名和吃。一股羞愧感襲來,如此殘缺卻自大。我們離我們的身體這麼遠,意志不是和身體合作,而是對地球遠方的物資的濫用。喪失意志的真意的人,敵人來時可知道堅持?

我在看完彩虹橋一個月後,又有一個研討會,處理的主題是社會事件的文化面。我把賽德克‧巴萊的內容和社會迴響直接放進論文裡的一段,談論的是insider和outsider。在這篇論文裡,我說台灣歷史帶給我們最深的創傷、焦慮和文化性,就是對外來的侵略者的感受,雖然每個歷史時期的outsider和 insider不一樣,因為過去的outsider也有可能變成今日的insider,而這部片恰恰是對這個歷史創傷的重新詮釋,那麼誰是今日的outsider?
評論人是一位優秀認真的日本人類學家,作為知識的守門員,他的專業反應和大部分人類學家一樣,他提到獵首(headhunting),提到Rosaldo,當然,就是懷疑獵首的詮釋。這次我有備而來,因為這事我早已想過多遍。我回他說,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理解獵首,包括當代的族人,但是就是因為它難以理解,所以這個討論如此地有力。「你是人類學家,你應該知道象徵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深不可測,所以它帶來想像和力量,當然這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編織在脈絡中的想像。」這位東京大學的人類學家點了頭。在我看來魏導並沒有把獵首說死,就如戴立忍導演的評論所言,他以情境來呈現,避開了作為他者的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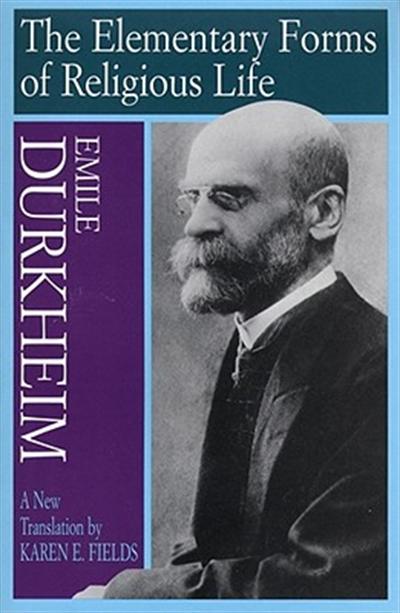
開完會回到課堂,今年我有一門社會經典的課,這門課大概只能在馬涂韋三位伯伯中選一到兩位來讀,我今年選了涂爾幹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型式。為了對抗同學們的離心力,我提高聲調喊著:各位同學,涂爾幹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告訴我們,象徵必須和社會形式結合起來談論。譬如……。我心裏想如果和他們說北港朝天宮的媽祖婆和你們村子的媽祖婆就是不一樣的話,這些少年ㄟ肯定沒有感覺。於是我又只好求援賽德克‧巴萊:
[各位,就像賽德克‧巴萊裡的獵首,過去在部落裡的獵首,和當代一部台灣電影裡的獵首會是同一件事嗎?涂爾幹告訴我們,不一樣。]
賽德克‧巴萊出現之後,從部落角度出發的聲音,形成另一種對立的聲音,當然,是否需要[對立]是可以談論的空間。最典型被引用的一句話是郭明正老師說的:魏導缺乏在部落裡生活的經驗。就是這裏,賽德克‧巴萊恰恰處於國家和族群之間的張力。魏導是站在哪個位置說故事?郭老師是站在哪個角度講話?恰恰是對話或對立的來源。
那一場有關台灣認同的論文發表會上,賽德克‧巴萊幫助我在那個意志和現實的落差中,給了我一個空間,進行了一場真真實實的文化建構。一部作品可以是一個社會空間嗎?作為在地研究者最擔心的是部落或村子的[真實]在一個[大尺度]的場域裡被簡化,這簡直就是人類學家的夢靨。
但是人類學家不是一直意圖要把研究場域擴大到區域和國家嗎?一部作品,一個話語當然不會是部落裡人的實踐,但是兩者沒有任何橋樑可以互通嗎?這樣的矛盾Gellner在Nations and Nationalism裡頭有過很好的論述。話語是不是如此地罪大惡極?在犁變成筆時(再借Gellner語),人類的命運就一直朝這個方向移動了。我們這些提筆的似乎沒有比拿攝影機有少冒一些簡化的危險。如果一部作品可以開闢一個社會空間,它可以促成多層次,從國家到部落的各種實踐,是宿命也是機會。到底賽片有沒有給出這個空間?是一個需要判斷的問題,也不是短暫的現象可以完全定論,需要更長期的觀察。截至目前為止,導演給出的空間算是寬闊的。
如果一千零一夜令人想到「芝麻」,涂爾幹就是「圖騰」。這讓我想起一個多年的故事和上課同學分享。多年前我在一場研討會場合,有原住民朋友在聽眾席發言,提到[圖騰]兩字,當場被一位資深人類學家糾正圖騰用錯了用法。我和同學們講,如果你指責一位一般聽眾用錯學術名詞,那你可能不是稱職的社會學家。你應該問的是,他為甚麼這麼用,而且好多人都這麼[誤用]時(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誤在那裏?難道不能轉用,我們不是一天到晚在講譬喻轉喻嗎?),這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了。我今天回想這件事,場景剛好倒轉,一個漢人導演被指責沒有把部落的[獵頭]的真意詮釋出來,但是手指來自於同一個地方。有趣的對比。

我看完上集太陽旗時,到處寄信要朋友去看,覺得好像是自己的榮耀。看完下集後,我也不覺得導演阻礙了我們繼續尋求[歷史真相]的動機和努力。那天我獨自開車在眼前平坦又白晃晃的柏油路上,想到這部電影導演本身的探索,他帶來的全台的討論和探索,我突然想到湯湘竹導演的兩部電影的名稱:[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我只看了前一部,後一部還沒有看。但是對照到賽德克巴萊的探索,是阿,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我流下淚來。台灣,你的探索,是我們的未來。歷史,可以是過去,可以是未來。
我又在課堂上嘔心瀝血地對抗離心力:同學,歷史是里程碑堆出來的(雖然近年來我們都在注意日常生活),沒有事件就沒有歷史,沒有傑出的作品就沒有地形擠壓出來的摺痕,我們只能看到光凸凸的柏油路。如果我們不探索,不用盡全力擠出作品,那將是光凸凸地一片。這時候我心裏向賽德克巴萊的所有貢獻者輕聲說了謝謝。

後記:交清的竹風社贊助也主辦了多項校園活動,包括第一部太陽旗的包場,其中清大楊克峻教授向來出資最力,卻不欲為人知。我這個周末剛參加了他的喪禮,在此謝謝他請我們大家看電影。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秀幸 賽德克‧巴萊:在兩種[真實]之間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2266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to 韻芳
還好,我應該不是震撼,大概沒有比我的電腦中毒更令我震撼的(前兩天),這個才震撼。
我想我只是把這部片的位置點出來,當然是從我的觀點。任何作品都有它的位置,這是我們得清楚的。就算是我們的論文,也有我們的位置,這是我們首先必須具備的前提,才能進入一部作品,否則只會是不斷地詰問。當然,我認為你所知道的部落看法當然要可以提出來,不過那和這部「作品」關連性有多強?換言之,有點像郭老師那本書,那是另一個作品,和這部電影有關,但是多有關?可以討論。也許不大影響這部片的主旨。
也許吧,和我做的田野有關,但是我也有村落經驗阿。這句話的目的不是在「我」,而是如何儘量消減待在部落的人類學家和其他人的界線。我的意思是文化有時候並不全然是對「型態」的掌握,譬如如果我多知道些漢人儀式的禁忌,並不大能表示我多了多少理解。有時候是對尺度的掌握,和語氣、氛圍、態度有關,否則我們很難跨越界線去理解。我的意思是不少對這部片的詰問是和部落的禁忌不一樣,但是我們很難說禁忌是文化的全部(當然它也很重要),但是文化有其他的面向,也許導演的鏡頭比我們的筆多做了些也不一定。歷史恩怨亦然,很重要,但不是全部。換言之,我們如何看一部電影?禁忌,歷史恩怨,這些可以補充,也可以要求導演儘量要顧到這些。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對異文化的探索,導演和我們的位置沒有相差多少,同樣地都是帶著當代的關懷,從某一個面向進入,那種進入永遠是一個探險,每個人成就不一。譬如,導演把獵首凸顯得這麼刺目,對謹慎的人類學家來說,很刺耳。但是沒有一個導演會笨到不懂得討好觀眾,他只要減少這部分的突兀,把出草的一方塑造得「無辜」一點,可以大大降低各方質疑,甚至增加一些票房(不少「人頭滿天飛」的耳語嚇跑一些觀眾)。他為何這麼笨,勿寧是說,這是他的重要的「點」:獵首是他探險的方向之一,就好像常看到的色情藝術之爭一樣,藉由對色情禁忌的防線的試探,藝術家總想要冒險一番。我相信後人除了獵首禁忌和規矩之外大概很難說多懂了什麼?當導演笨到去踩紅線時,我們不妨去體會一下藝術表現手法。難道我們寫論文沒有冒險之旅的成分?說這些不是要justify製片團隊什麼,而是要提醒「看電影」和「看論文」有它的相似處也有它的相異處。
所以我不大認為這是熟悉部落的人和一般觀眾的差別?前者也活在現代生活裡,後者也有他的社群經驗,不可能沒有對話。也許把個別位置點出來,把每個人進入的取徑釐清會比較清楚,而不是熟悉不熟悉部落的二分法。也許這樣才能將人類學的特權解放。
我很高興自己是第一個回應這篇文章的人。因為在幾個星期前我就同一部電影,從很不一樣的角度,寫了另一篇芭樂文:〈在眾『巴萊』之間沈思〉,這就是芭樂人類學的精神,歡迎、鼓勵眾聲喧嘩。
作為《賽德克巴萊》的觀眾和評論者,我和秀幸是站在很不同的位置在感受與發言。我作原住民,包括賽德克族的研究;秀幸研究的是漢人。我想這個差別可能就是秀幸可以從一個純然觀眾角度的立場去聆聽、感受魏導的用心;但我卻因知道太多有關霧社事件不同於主流敘事的部落口述,以及賽德克族不同支族間因此造成的長年傷痕,以致看這部片時心情非常錯綜複雜。
不過,仔細閱讀秀幸的文章,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真的受到這部片很大的感動和震撼(這大概是她有史以來最長最嚴肅的芭樂文吧!),也說服我相信的確魏導非常努力地在這部片裡傳達「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的精神,而且的確讓不少觀眾為之動容震撼,雖然他所詮釋「真正的人」之意涵和賽德克族人有了一些出入,加進了一些他對原住民浪漫的想像。但,或許這就是秀幸文章副標題所說的:在兩種「真實」之間,也是她下述引文想表達的(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
「賽德克‧巴萊出現之後,從部落角度出發的聲音,形成另一種對立的聲音,當然,是否需要[對立]是可以談論的空間。最典型被引用的一句話是郭明正老師說的:魏導缺乏在部落裡生活的經驗。就是這裏,賽德克‧巴萊恰恰處於國家和族群之間的張力。魏導是站在哪個位置說故事?郭老師是站在哪個角度講話?恰恰是對話或對立的來源。」
在我看來,我們需要的是從不同角度的「對話」,而非黑白分明孰是孰非的「對立」。我的那篇文章從來沒有如某位讀者留言所說,有要「批鬥」魏導的意思,我只是想讓族人和像我這樣生命已和族人糾葛不清的觀眾心聲也能被聽見。
謝謝秀幸這篇文章,它讓我可以暫時拋開族人一下下,從更多不同層面的角度和心情再次去感受、思索這部電影。
韻芳搶到頭香啦~
我對你們的回應(很間接的啦), as promised, 快要寫好了,非常長
所以下週芭樂另起一篇刊登,現在只是來預告 :)
哇,這下熱鬧了,成芭樂三部曲了,還是之後會有人繼續手癢,變成連續劇......
留個跟賽德克巴萊無關的言。那個俄國導演叫做塔科夫斯基,偏不巧我還蠻喜歡那部叫犧牲的電影。看電影時喜不喜歡或感不感動或能不能感到empowered,與個人觀影的生命史與觀影慣行密不可分。我很喜歡你將觀影經驗與個人終極關懷與學術志業時時連結並且相互辯證的分享。
不過,當我讀到你對事件與歷史間關係的說法,心頭浮現出英雄史詩般磅礡氣勢的歷史。但是,無法成為英雄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盡心所做的小事,難道有一天不會成為創造歷史的力量嗎?傑出作品的確可以創造歷史(但許多歷史定位與里程碑是後代的人給的,因這些傑出作品往往不見容於同時代),盡力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或許終有一天也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打造新的歷史與時代。我想,在日常生活中盡力地並反思地生活著的人,或許有別你所批判的那種毫無反思地生活的空洞的人?
來個題外話,大學時修了紀錄片的課,正好也看了湯湘竹導演的《山有多高?》。
文中提到此片勾起了回憶,也好想看看耳聞尚未一見的《海有多深?》
to L.Y.
你知道湯導演還有第三部曲《路有多長》嗎?內容是有關一些都蘭阿美族當年被國民黨派去大陸打仗,戰死或滯留在對岸多年後才得以歸鄉的故事。
原來還有第三部片啊~哈哈這部片在我畢業後完成的,結果沒Follow到最新消息!(當然要去找來看囉~)
我們的作者去哪了?很想看到秀幸的回應。
Kaka,
完全同意,我所謂的作品包括我們日常的潛伏的「做工」,雖然不馬上亮麗,但是總會有開花的一天,也許開在自己身上,也許開在別人身上,譬如受到你的影響,但是藉由另一媒材表現的他人的作品。我們處在一個共振的時空裡,每個做工都互為牽連,作品有時並非單一作者。譬如韻芳勇敢地拋出反問語氣,我也六親不認地反問了學術圈,如果佩宜再丟出一篇,不少作品就衍生下去。
感謝秀幸的分享,雖然沒有特別提出與賽德克‧巴萊相關的討論
但我相當喜歡秀幸文章中的這段:
「多年前我在一場研討會場合,有原住民朋友在聽眾席發言,提到[圖騰]兩字,當場被一位資深人類學家糾正圖騰用錯了用法。我和同學們講,如果你指責一位一般聽眾用錯學術名詞,那你可能不是稱職的社會學家。你應該問的是,他為甚麼這麼用,而且好多人都這麼[誤用]時(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誤在那裏?難道不能轉用,我們不是一天到晚在講譬喻轉喻嗎?)」
因為這段話讓我聯想到敘事的研究,即某位人類學者進入中國的某工廠對其中的女性做訪談,並將其所言放入更大的時代脈絡探究,並進一步探討為甚麼她們會擁有某些特定的敘事能力,最後其人發現此能力竟很有可能地是當代國家所賦予,賦予一套會說故事的能力。語言、詞彙的用法常是顯現其人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與發展脈絡,而若拘泥於字句、詞彙的定義做討論,也許就喪失的更多有趣討論的可能。而秀幸深入淺出的比喻真是讓人佩服。
小傍陂,
很有意思的分享。我們常常忘記「當代性」,因為當代性是最難以捉摸的,需要一些冒險的探測性和想像力,也需要對「脈絡」一直保持敏感。有些事情因為事涉敏感,如霧社事件和獵首,因此容易造成知識界立即的守門反應,我也可以理解。只是提供一些不同想像的版本來為「文化」增添未來性和動態性,是我的意圖。
很喜歡本文作者的深度分享,與本人看完「賽德克.巴萊」後,心裏的感想大部分相同
上面有位「韻芳」的作者,她對「賽德克.巴萊」的為文本人恰好也看過,對她文章的內容,本人有許多與她不同的看法,或許實在太多的不同了,以致於實在不想回應,尤其看了她文章下面的網友回應後,更加明白:「在以相當主觀而嚴厲的文字評判他人與己之不同觀點時,完全建構不了彼此溝通的最大值」。
這大概也是自認為對於學術研究投入很多心力的學者們無法令「一般人」想多靠近你們的田野研究一點點的原因吧。
恰巧,
謝謝回應。
我們還是要互相同理對方,也可以試著理解韻芳在部落裡承受較多部落的立即反應,試著把他們的聲音傳遞出來。雖然我覺得沈澱一陣子後,也許也會有不同的聲音,但是立即的傳遞也有他的效應。何不把它當作一種現象,如果不幫忙傳遞,也許悶在那裡也不太好。從這樣的觀點看,韻芳做了一個很好的報導。反正網路上言論是開放的,誰也沒有獨佔發言台,都不錯。(最後一句話很像小時候作文的「早日解救『大陸』同胞」
to「hh」:
很喜歡您溫暖的回應和勸說,覺得這是很好的溝通方式。
不過,不喜歡那篇文章之處,除了觀點上的不同,更有該作者的嚴厲用詞及非常明顯的本位主義觀點吧。我也看過郭明正老師的「真相.巴萊」,雖然有很多與電影不同的觀點及看法,但並不令人覺得反感或不想接受,反倒會想再深入了解並多思考霧社事件的各面相,也許這就是每個人表達方式之不同所帶來的不同效應吧!
謝謝您的回應!
贊成上述鄉民的文.表達方式帶來不同的效應.
感謝版主好文分享.
是中午看道您這篇文章,
我頭皮發麻了許久許久,
謝謝您用精準的文字說出了我心中的感受
(轉發給其他朋友,他們也都直點頭啊)
其實,有時後會以為自己可以對一些觀念妥協或充耳不聞,
但在搞不清楚狀況的外國人面前,或是面對張牙舞爪的其它人,
才會在那一瞬間明白,自己有多麼的"微不足道",
卻同時更清楚的知道,很多自己堅持的信念和價值觀,
是絕對不可能蒙混過去,或被否定的。
(好像也就是在那一瞬間,頭腦瞬間很清晰,非母語的語言頓時無比流暢,
能夠完整對外人說出自己的想法)
這算不算是"賽德克巴萊"呢?
算不算是"老鬼"呢?
"他們不會瞭解,老鬼、老槍,不是個人,而是一種精神、一種信仰......"
電影帶給台灣人對於自身族群過往的追尋和認知,
以及改變對原住民刻板的印象,
該是最美好的禮物,如同天邊的彩虹。
以下是我看了邱韻芳老師的評論後給她的回饋,作為學運時代就學期曾與民族學擦身而過的中年人,讓我在這年代看見賽德克巴萊片,不禁回想起年少時代的文藝熱情與抉擇感探。
邱韻芳老師:
快下片了,還好有林秀幸的評論,否則無法平衡您對本片的批評對我心靈造成的傷害,您很難想像我對本片的崇敬。相反地,魏導的片子予我如是感動,我也想不到對您與特別是春陽部落遺老卻是種傷害。如果您的研究對象是清流部落,是否也會寫出這樣一篇文章?
我認為魏導的片子應該改名回"靈魂的權重The Weight of Soul",我理解下的本片是探討賽德克族各人物,特別是魏導偏愛的莫那魯道,對於個人與族群生命面對轉折時的抉擇。魏導敘述的故事中:反抗六部落(或者五部落)族人選擇給予靈魂在生命中更高的價值權重,我可以聽見魏導在盛讚:尋找根源並認識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是的,我認為魏導偏心,在儘可能客觀處理歷史恩怨當中,他還是偏袒莫那魯道。我也贊同了他。
正像三國演義改寫真史,羅貫中讓我們都偏袒蜀國人物。
三國演義是失敗作品嗎?荷馬史詩符合事實嗎?坦白說這部片子隱含著寓言,我們來看這部片子的人要能跳脫人類學與真史,真史很重要,但是看穿說故事者的含意是另一重點。魏導有很多故事可以拍 -- 為什麼,為什麼要拍賽德克巴萊?因為這個故事有魏導想說的隱喻。
賽德克族與三國後代的觀點很重要,但是看穿說故事者的觀點更重要,不然創作者留下的只是考古展示。創作要藉著一個故事告訴你一些觀點想法,至於傷害曹操後代或部份人,作者只好另外補救。
這部片子即使來自完全虛構的小說,也有一定的寓意與震撼力,因為故事人物對於族群與自身命運的抉擇都是習於庸庸碌碌者不懂或不敢面對的,但是真的有那麼一天時,我們自問又會如何抉擇?
當下的台灣各族群互相爭奪,哪天台灣又被外來者統治了,大家輪流與統治者生活後,不會重演「反抗番」與「親權番」嗎?後代看我們的恩怨,也是沒有對錯,只是不同族群價值觀的選擇?你以為魏導講希望本片促進族群和諧就只限於賽德克族各亞群嗎?
不要談國家前途,個人對於自己認為對的生命態度,難道妥協就是唯一出路?妥協要到哪個限度?巴蘭社的瓦力斯布尼的價值真的優於莫那魯道的抉擇?今天的Toda年輕人不能有不同於祖先的選擇?不能批判自己祖先的選擇?即便回到當初,Toda族內真沒有暗暗贊成反抗的人?
即使魏導這麼偏心,我也這樣認同,回想我在進戲院看彩虹橋時,鄰座的漢族老太太在孫女的劇情解說下仍然不時提出評論:「看這個番人頭目害死多少人隨他而死。」這真是價值觀的不同啊!
魏導說這場事件是信仰的衝突,我自己會說是價值觀的抉擇與衝突。對於將報復、利益、求存、靈魂之間的權重拿捏,80年前困擾著賽德克族人的祖先,今天也還持續困擾著當代的賽德克人與他們週遭的我們。
樓上的jhu022,
實在太同意您說的話了。
『邱韻芳老師:快下片了,還好有林秀幸的評論,否則無法平衡您對本片的批評對我心靈造成的傷害,您很難想像我對本片的崇敬。相反地,魏導的片子予我如是感動,我也想不到對您與特別是春陽部落遺老卻是種傷害。如果您的研究對象是清流部落,是否也會寫出這樣一篇文章?』
怎麼可能有一部電影能夠滿足所有觀眾,
照顧到所有觀點,
本來每個作者就是有立場的,只能盡力做到圓融。
導演未免也承載背負了過多莫名奇妙的批判,
好像所有的努力和苦心,在這些人眼中是如此的不值,
那麼,何不自己拍一部?
用自己的觀點去影響世人的看法,
再看清流部落的遺族們 會怎麼想?
「她」帶著不爽的成見去看這部電影,怎麼看,「她」總能挑出不滿的地方(或是春陽部落不滿的地方),但事實是,如果不是這部魏德盛的「賽德克巴萊」撞擊世人的內心,「她」的文章也只能在「高尚的學術小圈圈」彼此流傳而已,我們這般庸俗之人應該不會想多看一眼。
ps 現在的「春陽部落」是以前荷歌社族人的家吧 (這句話的含意就自己去想吧)......
to 恰巧看到好文的鄉民,alex和jhu022
你們對我的批評指教我剛剛在我那篇文的留言版裡,針對jhu022 的留言有做出回應了,你們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p.s.我從來不覺得學術圈高尚,而且那篇文章也並不學術。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