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到資本主義這部巨型機器中,並成為一個「人」?
《便利店人間》的閱讀隨想
第155屆芥川賞《便利店人間》是一部有關那些不願意也無法融入社會規範的人,如何從底層勞動工作所建立的生活節奏與秩序感中,找到了保全其微小自由並確認其做為人的意義之作品。
對一個研究當代的工作與資本主義的人而言,這本小說帶給我的驚豔,不在於如何巧妙地運用各種前衛理論或菁英視角,來誇飾底層工作者的面貌,而在於小說自身具備了以民族誌回應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經濟主體與社會對人的集體規範之間衝突與張力的理論潛力。更重要地,作者指出了一種新人觀的誕生:一個在社會規範中被邊緣化的人,以自認為生物(非人)的視角,在從事彈性勞動的過程中,從模仿他人(同事與朋友)的行為舉止、品味與情感反應等,意識地掩飾自己的生物性,好使自己「看起來像個社會人」,最終被觸發而產生了主動「成為人」的欲望。在我看來,這為資本主義這個機器的主體化過程及其打造之主體性,提供了一個細膩、發人深省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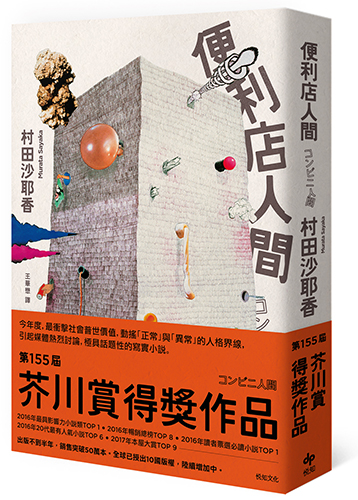
作者村田沙耶香長期在便利店從事兼職工作,她以相當細膩的超商工作細節,描繪了一個在便利超商兼職十八年的三十六歲單身女性古倉惠子,如何從模仿店員工作的錄影帶、標準化的工作程序、個人形象的自我管理、周遭他人說話的語調、食物、品味乃至於情感表達等,來建立自己成為他人眼中的「人」,她藉由模仿與納入廣泛的他性(alterity),逐漸構成了惠子做為一個社會人的內在與外在,使自身能融入集體所欲的社會人形象之中。這是惠子回應家人希望她能「治好」的努力。
那麼,惠子是怎麼壞掉的?為什麼一個人無法展現出合乎社會規範的情緒表達與互動方式,被認為是壞掉的,因此需要透過各種手段去修復?如果無法被修復或無法被治好,這樣的人該如何在社會中生活下來?
作者用三個插曲呈現惠子的「異常」。其一,在公園發現死掉的小鳥時,惠子想到的是燒烤小鳥讓家人分享,因為難得是牠自己死亡,而非如眾人預期,應當為可愛小鳥失去生命感到悲傷,並舉行葬禮。其二,當男同學發生爭執扭打時,旁人高喊誰來制止時,惠子找出鏟子擊打其中一名男同學的頭,以求有效快速地制止暴力。其三,當女教師在課間歇斯底里而所有學生束手無策時,惠子用力扯下老師的裙子與內褲,只因她曾從電視上播映的電影中看過這個「能立刻讓女性安靜」的方式。即使父母聽從心理諮商師,盡量給予惠子關愛,但終究沒能治好她。惠子的青少年時光就在沈默少語和模仿他人之中度過。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既不著墨於惠子是否經歷童年創傷而「壞掉」,也沒有訴諸重建與家人的關係(特別是訴諸子女與母親間的阿闍世情結)來矯治惠子,使其成為一個符合家庭與社會規範的人。相反地,惠子是從他人的反應,選擇了「自我正常化」的手段,成為集體的一部分,或者說,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被集體意識到是「異物」。
年過三十,惠子開始以無傷大雅的謊言(如健康欠佳、照顧父母)來迴避周遭不斷投射出各種有關性別與角色的規範,以及他人以關心或勸誡為名的柔性壓迫。為了逃離這些柔性壓迫,惠子無意間收留了曾是同事的三十五歲無業男白羽。對雙方而言,住在同一屋簷下只是單純的利益交換,毫無涉入任何情思愛慾:惠子因為與男人同住一個屋簷下,順利成章地擺脫了周遭質疑,白羽則希望能從身邊遇見的人都自認有資格直接干預他人生命的殘暴中隱藏起來。與惠子同樣不願輕易融入既有性別與人觀規範的白羽,曾在走投無路時去便利店打工,大力抨擊日本社會強調有正職者、有婚姻家庭與後代才是對有所貢獻社會,根本是階級壓迫。矛盾的是,他同時又以職業階序所構築的充滿階級敵視與輕蔑的語言,辱罵便利店店員及其工作。同樣地,他高聲批評既有性別規範,卻又矛盾地希望在便利店找到婚姻對象,擺脫他人的目光與評價。猶有進之,白羽被惠子收留後,竟傲慢地認為自己能讓惠子快速履行了社會對女性的評價與規範,以交換寄生於惠子的正當性,仿擬女性對男人的寄生。
但當惠子辭去便利店兼職工作以利尋找正職後,過去十八年來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與節奏,徹底崩壞。在繭居過程中,便利店的各種聲音,成為她深切渴望逃離當下一無所有的追尋。面試新職當天,惠子路過便利店並進入,便忍不住動手調整起貨架上的商品擺設,讓商品成為能夠被顧客所看見,並從這種被顧客所注意與消費的短暫過程中,清楚確認了便利店店員的生活之於自己的意義,進而從白羽近似弱弱相殘的寄生中掙脫出來。

作者將主角在前述過程中經歷與面對的,定性為一個關乎社會人的正常與異常之辨,同時質疑:個人主義的普及,並未讓那些偏離了多數人習以為常的性別身份與相應生命歷程的少數人,獲得真正的解放。此一意識與質疑令人想起Foucault對異常(the abnormal)的討論,以及個人的正常化是藉各種社會建制與權力關係而得以被確立的歷史過程。不過,小說中提到公園小鳥的例子,讓我想起《異鄉人》中的莫梭,因無法在母親喪禮上公開表達悲傷,使其被法庭建構為法律主體的過程中,成為他人質疑莫梭是否具備人性的證據之一,進而觸發了卡繆對個人存在意義的反思。當然,惠子不是莫梭,她並不是在被建構為法律主體的過程中,才受到他人對其是否具備人性的質疑,而是從一開始就掉落在日本社會集體所認定的「人性」限閾之外。因此,惠子自年幼起就經常面對自己總是異於他人的處境,因而必須時時思考「什麼是人?」這個問題。
自認為是社會異物的惠子,將自己當成生物(動物)來看待,以動物的眼光來看待周遭的生物,而人只是眾多生物中相當獨特的一類。進入便利店工作的惠子,先經歷了一段藉與他人互動以及食用類似食物而改變自身動物性的「社會化」過程,並以生物或動物之姿來扮演「人」。但惠子的社會化過程尚不完整,偶爾會被他人意料之外的舉止或反應所驚訝,產生了「啊!這就是人!」的感受。在作者筆下,做為生物的惠子,並不是我們常識中對動物的預設,即,完全被本能與原始欲望所驅動而產生行為能力的生物。事實上,惠子這種生物是被時代的經濟條件所造就的:她以幾乎無需烹飪技術的食物維生,並稱之為飼料,她藉模仿其他生物的行為、品味、美感、生活習慣來「社會化」,但惠子這種生物卻沒有出自本能的欲望,既沒有性慾或性的衝動,更沒有性經驗。特別是,當從惠子問白羽的弟妹,自己是否應該(就像白羽口中繩文時代的女人一樣)交配以繁衍後代,好能為社會/村落有所貢獻時,卻被羞辱,斥責惠子與白羽這些底層的人,根本不應將基因留在人間。這段話讓惠子決計日後要盡量避免那些能產生後代的行為。對惠子而言,被預設為本能的欲望,不只從未實現過,只有那些被視為是「人」的生物,才有資格去實現性交與生育這類被分類為社會人的本能和欲望,特別是只有擁有正式職位的人(会社人)的欲望。換言之,階級不僅決定了人的位階高低,更關乎欲望是否具備被實現的價值。
顯然,這有別於常識對於原始慾望(滿足肉體的各種功能運作)乃是生物(動物)本能的動物觀。從行文來看,作者是將人與動物的階序之別,視為社會人與無法達成社會規範與價值的邊緣人之間的隱喻。惠子這類自外於集體規範的生物人,除了成為便利店店員與模仿他人好讓自己看起來像人,同時還可能滿足於自己有效發揮(資本主義)機器之零件的功能,此外,她再沒有其他更社會性的欲望與情慾。更重要地,便利店店員的欲望生產(即,以「不使欲望展現」的形式出現),並不是來自集體的欲望結構(如,阿闍世情結),而是與資本主義機器密不可分,特別是,類似惠子的「領悟世代」(悟世代),看破了總體經濟結構對人設下了限制,擺脫了物質欲望或累積財富的欲望,甚至放棄了企圖心與希望。對世間與人間的欲望低下甚至欠缺,才是惠子這類生物人的欲望之性質。

事實上,便利店這個資本主義機器,更提供了形塑店員這種經濟主體的各種符號:工作程序變成自身治理(如經常修剪指甲、不染髮並保持整潔、留意工作應對時聲音質地、音量與情感表現、定時就寢),自我治理更被解釋為店員時薪的一部分。換言之,勞動價值不僅來自勞動,更關乎自工作者的自我治理。這些自我技藝建立了惠子的生活節奏與秩序感,更使惠子這種生物能夠轉變其動物性,成功扮演社會可接受的人這種主體形象。就此,自我技藝與自我治理打造了便利店店員這種勞動主體,這些技藝甚至被認為是工資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工資不僅購買了店員的時間,更介入了其做為勞動主體的打造:只有被資本主義機器所欲的主體形象,才是價值的來源。此外,成為這般勞動主體的意義,進一步呈現在惠子的存在感:在離職後喪失了時間感,生活節奏的崩壞,全然放棄自我治理的各項技藝之後,惠子這種生物就只剩下醒了就吃、累了就睡這類最低限度的維生活動。
儘管便利店店員給予惠子這種生物正常化的身份,卻無法讓她成為一個主流的或正常的社會人,即,與正職身份(会社人)產生某種連結的人(成為一員,或成為会社人的妻子)。多數日本人堅持著「人必須透過工作或結婚來與社會產生連結」的信念,認為所有人在相近年歲時,均會走上相似的生命階段,與大家都一樣滿足於「普通標準」,人人都有成為平均人的欲望。弔詭的是,便利店店員的工作支持了会社人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節奏,但打算長期兼職的店員,不被認為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甚至是一種註定被集體所卑賤的社會類別,一如賤民之於印度卡斯特體系。不同的是,便利店店員這種社會類別是不穩定的、流動的、過渡的。便利店店員當然是一個階級化的社會類別,然而,進入這個類別中的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彼此間沒有形成集體或群體的基礎;他們共有的只是工作時相似的情緒反應,以及評斷他人的一致準則。
惠子的動物視角讓我想起卡夫卡《變形記》的男主角格里高爾・薩姆莎:他一方面要學習以甲蟲的身體存活下來,另一方面卻始終以人的眼光、思維與情感來看待與對待公司、工作、家人與家庭生活。事實上,薩姆莎的孤獨是建立現代性主體的一項預設上:身體做為人類主體的最重要媒介,因身體係語言、情感與思維等人性的不可或缺之基礎。由此,動物的身體自然無法承載「人之所以為人」的屬性:即使隱藏在動物身體下那些屬於人類的思維與情感並未喪失,薩姆莎卻無法被家人視為人。另一個顯現薩姆莎仍保有人性則是:即使他因動物身體的本能而培養出某些移動與飲食的特徵,但那些動物本能是他透過人類習得生活技能的意識所發展出來,而非自然而然的。但這無法做為其具有人性的證據。更重要地,對薩姆莎的家人而言,因為身體的變化而無法準時搭上火車去工作的格里高爾,最先喪失的就是做為一個資本主義勞動者的身份,這個身份及其收入,建立與維繫了他提供家人生活所需與未來夢想的經濟基礎,甚至是一個社會人的基礎。當薩姆莎失去身體時,也失去了可用性,不僅引來旁人的反感,最後只能被拋棄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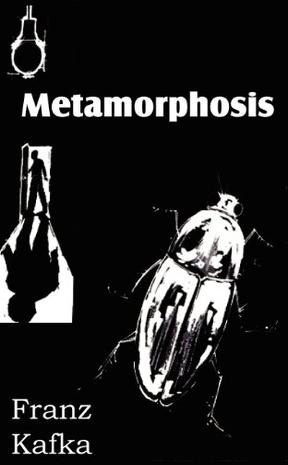
在家中,變成動物的薩姆莎宛若跨物種的怪物,成為the uncanny的來源,他的現身引發了家人前所未有的恐懼與恐慌。共同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家人對他不由自主的厭惡往往勝過家人之愛,呈現出恐懼與家人之愛的正負情愫交融,唯一願意接近他的是擔任臨時幫傭的年長女性。儘管如此,毫無攻擊他人能力的薩姆莎,最後還是被父親以蘋果攻擊而重傷。失去工作的薩姆莎,讓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無以為繼的家人只得將空房間出租。原本薩姆莎的房間變成了棄置無用家具的儲物室,只為討好房客。此舉讓家人最初還試圖為薩姆莎保留一個可以歸去之所的意圖,正在逐漸削減中。在薩姆莎受到妹妹的提琴聲所吸引而逐步靠近她時,他的現身卻驚嚇了房客與所有在場的人,房客盛怒下立刻退租,甚至威脅要以此對一家三口提告。這是家人徹底將薩姆莎視為失去人性的純粹動物之時刻,即使臨終前的薩姆莎還對家人特別是妹妹有所顧念。這是薩姆莎家人對格里高爾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斷裂。這個斷裂,以幫傭清掃動物屍體作結,同時也終結了此一充滿the uncanny的家庭生活。存活下來的一家三口決定搬離他處。最後,在薩姆莎父母意識到身體日漸美好豐潤的妹妹是該進入婚姻的玫瑰色想像時,這家人看似邁向全新未來的希望。就此,卡夫卡筆下現代性人類主體的前提是身體,這是承載與表現人之所以為人的本體論基礎,包含思考方式、情緒、情感、空間分化、互動方式以及關係樣態。如果擁有相同身體的單一人類種屬被認為思考方式彼此有別的多元文化論,是西方對自然與文化的預設,那麼,不具備人類身體的動物,不僅是對文化與人性有所威脅的自然,更是the uncanny的客體化。在卡夫卡的筆下,自然與文化的對立,不僅是哲學人類學的範疇,更深入了人的無意識。
藉對照上述現代性主體,我們可以追問:便利店店員惠子的主體性,是如何在資本主義機器中生產出來的?作者提到,惠子所食用的食物、衣著風格與情緒反應方式,都是模仿他人以裝扮自己成為「人」的符號,這些符號會隨著惠子在不同時間與場所所遇見並一起工作的人,而有所不同。換言之,這些指向社會人形象的符號,會隨著關係強度的改變而被置換,甚至消失。事實上,便利店各種聲音不只是這本書的關鍵象徵,更是深深嵌入惠子皮膚之下、身體之內的無意指符號(asignifying signs)。這些做為符號的聲音,在惠子經年累月的工作中,與他的身體慣行巧妙地組裝,構連成她(自認為)變成「正常人」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利店聲音這類符號,在個人之下(infra-individual)這個層面,與分裂的人(dividual,即,從做為主體的人之中分裂出的部分),彼此結合,構成了惠子的主體性。這鮮活展現了金融資本主義下機器式臣屬(machinic subjugation)這種主體化樣態。更重要地,這種不可分割的關係的意義,在惠子辭去工作後更為明顯,因其是關乎她存在論的基礎。當惠子放棄新工作的面試,想重新成為便利店店員時,那個決定是出自惠子想要成為人的欲望,是她真正的欲望。儘管在他人(包括敵視社會規範的白羽)眼中,便利店店員根本是當代的「人間失格」,那卻是惠子可以「成為人」的憑藉,是她存在的意義。這一點完美展現了Maurizio Lazzarato認為金融資本主義下「存在是機器屬性的」(existence is machinic)。甚至,在附錄的那封給便利店的情書中,我們看到便利店更成了店員(或作者?)約會的對象,是觸發與表達愛慾的對象,更是能與店員(或作者)建立某種獨佔情感關係的主體。這已經不是人與機器人談戀愛或二次元戀愛,與那部賦予人存在論意義的巨型機器互有好感,與資本主義巨型機器的設置之間產生了互為主體的欲望。能讓便利店店員惠子「成為人」、生活有秩序且感到被人所需要的巨型機器,就是愛慾的來處與去向:唯有在這個愛人的懷抱裡,惠子才能感覺到自己成為人。正如這部小說展現的新人觀所帶來的訝異,這般愛慾的對象與性質同樣讓人瞠目結舌,唯一不變的愛戀中或溫柔或嬌嗔或是微微嫉妒的纏綿情意。

如果「工作對人的意義為何?」是我們不斷自問的生命課題,這本小說揭示了當代情境中經濟主體性之生成、資本主義機器下的主體化樣態,以及工作對人的存在論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本小說指出了一個有別於仰賴符號資本(Semiocapital)的數位知識勞動者之主體性的另類面貌。Franco Berardi認為,數位勞動及其特性,在以下幾個面向有別於工業資本主義。其一,個人負責工作的部分是分開獨立進行,且工作程序不受限於生產線設定的時間,個人因而能從工作場所的空間與固定工時中解放出來。其二,數位勞動強調心智勞動,讓工作者不受限於體能限制,因而能延長工時。然而這卻造成了資本只對工人的有用勞動時間感到興趣,進而將無法有所產出的時間,視為沒有商品價值的時間。其三,工作者從數位勞動中獲得認同與自我實現,進一步將個人從工會組織的集體性中解放出來。其四,相較於福特主義的工廠體制具備明確的權力中心與階序關係,電腦化產業則是藉行動電話來整合那些分散於個人負責的工作片段,使組織更加扁平、去中心化。其五,相較於體力勞動者的剝削是聚焦在工人的身體,造成工人與勞動成果異化(alienation),電腦產業的剝削對象是個人靈魂、情緒和慾望,造成了原子化的工人情緒上的疏離(estrangement)。其六,相較於體力勞動者藉由組織集體行動以抵抗資本的剝削,電腦科技產業員工則使用鎮靜劑與抗憂鬱劑來對抗恐慌、焦慮與沮喪這些資本剝削的後果。Berardi認為,人們使用鎮靜劑與抗憂鬱劑來對抗精神失序如恐慌、焦慮與沮喪的現象,體現了新自由主義下的工作對主體性的雙重束縛:工作是個人自我實現的所在,心智勞動會讓人誤以為可以超越身體體能的限制,不斷將精力投注於工作。一旦在工作中過度投入生命力與性慾(libidinal overinvestment),人的生命能量將大量耗損,甚至陷入恐慌與沮喪,最後只能以鎮靜劑與抗憂鬱藥物來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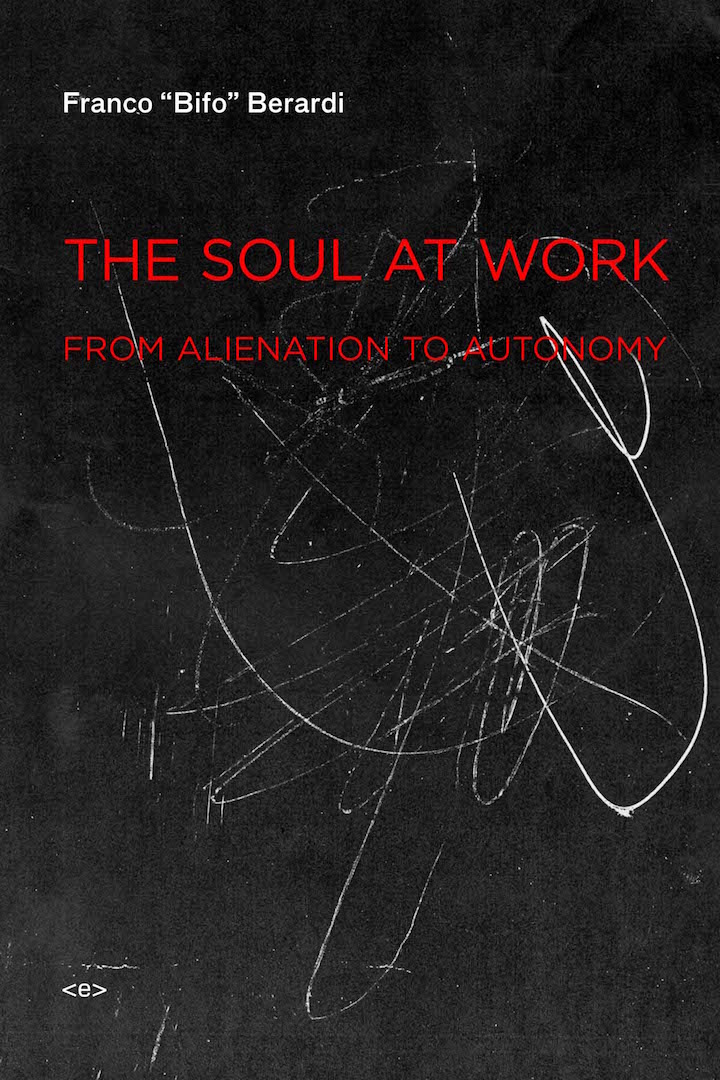
的確,便利店不被認為是能夠實現自我的工作或有靈魂的工作,甚至成為便利店店員這種「人」,幾乎很被賦予任何意義上的超越性救贖。在這部小說中,便利店店員讓那些難以成為社會人的人,變成資本主義機器所需的零件,進而確保了那些無視社會互動與情感表達規範的異物,經由工作規訓過程,逐漸將社會樂於接受的形象、關係與互動規範等,嵌入自己的日常習慣中,為那些偏離或不願服膺社會規範的人,提供了逃離主流社會對性別、婚姻與家庭等特定階級價值的避難所,不讓「主流他者」獨斷地干預個人的生命。為一般社會人提供全年無休服務的便利店,弔詭地創造了這些異物得以立身並寓居世界的存在之域(existence territory)。進而言之,藉結合資本主義的無意指符號,分裂的人展現了分子組成(molecular)的主體性,更以此從主流社會不斷鞏固之群聚的(molar)性別身份中逃逸出去。必須留意的是,血汗便利店並非什麼烏托邦,卻是讓某些人得以逃離主流社會與性別規範的壓迫,甚至是寓居於世的所在。

當然,讀者大可透過結構視角與批判理論的角度,指稱這種店員以便利店做為個人的棲身之所,根本就是商品拜物教的極致或虛假意識,便利店是資本主義的劊子手,必須透過教育讓受壓迫者覺醒,使其團結並發動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正如Berardi所述,當代資本主義的特性之一是工人從工會身份或工人集體性當中解放出來,這意味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當代原子化勞工的政治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問題。的確,便利店店員無疑是被剝削得最嚴重的勞動者之一,但這部小說指出,壓迫不是只有來自資本主義,各種形式的社會壓迫更是無所不在,弔詭地是,當兼職服務業這類工作被當事人存在化,甚至成為他們擺脫社會壓迫的逃城而非抗爭對象時,研究者必須面對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如果對惠子及其同類而言,「社會」若淪為展現性別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機器,那麼,這些人該往何處尋找容身所在?成為一個符合普通標準的「正常人」,究竟意味什麼?逃離了「社會」及其所喜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我們還能夠做為人,或是成為人?如果不能或無法成為「社會人」,那我們到底是什麼?或者,能成為什麼?如此,我們才能夠更貼近脈絡地去考察、想像或甚至掌握原子化工人將如何展現其政治主體性與能動性。
成為便利店人(間),是對会社人及其生活方式的逃離,藉由讓自己變成一個讓機器運作的有用零件,以證明自己是有用之人(一如会社人之於公司)。更重要地,便利店人(間)在日復一日的生活節奏、秩序感與有用之用,感受到自己真正地存在著。猶有進之,成為便利店人(間)這項作為,就是對那些僵化的(甚至是階級化的)社會規範與人性預設(所謂「傳統」、「主流」)的一種批判。這部小說以貼近人們日常的淺白語言、細節與情節推演,促使我們深思:資本主義機器所帶來的主體化過程及其對人的存在性質與顯現之影響,更重要地,它造就或形構了怎樣的新人觀、欲望以及(經濟的,之後是政治的)主體性。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鄭瑋寧 逃離到資本主義這部巨型機器中,並成為一個「人」?《便利店人間》的閱讀隨想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621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very nice reading and exposition, thanks!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