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松茸》中「聽不見」的臺灣史(上)
近日將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末日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是本奇書。不論就其涉及的空間尺度,欲對話的理論脈絡,還是作者Anna Lowenhaupt Tsing 流暢的文字,都是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少見的佳作。我現在人在美國看檔案及閉關寫書。當我被檔案中無止盡的細節所吸引、終至無法自拔時, 我就會翻上幾頁《末日松茸》(在我出國時,中文版還未出版,我參考的是英文原版),夢想著我可從中吸取一些以簡御繁、在經驗材料與理論間穿梭及跨領域對話的功力。於是,當我看到這本書這麼快就有了中文版,心情是又驚又喜。藉由「芭樂人類學」這個平臺,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在閱讀該書時的一些體會。簡單來說,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末日松茸》的意義不只是一本人類學的名著而已。在該書多維與多重的敘事線中,我試著指出,還有條Tsing未能觸及的、隱而不顯的軸線,聯繫起當前日本的松茸消費者,以及在美國奧勒岡一帶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集松茸的尋菇人。我稱這條軸線是「『聽不見』的臺灣史」。為什麼說這條軸線是「聽不見」?臺灣史跟松茸的採集與消費又有何關係?讓我先從八旗為該書撰寫的介紹開始:
在橫跨日本東京與京都、美國奧勒岡州、中國雲南,以及芬蘭拉普蘭地區的田野調查中,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Anna Lowenhaupt Tsing藉由尋溯一條微小、罕為人知的商品供應鏈,從經濟活動、生態科學和人類學三個面向,追蹤松茸如何在美國廢棄的工業林地悄悄破土而出,經遁入山林尋求自由的瑤族、苗族與東南亞裔尋菇人採集,再由買手憑藉技巧購入,之後累積層層價值「轉譯」進入日本,經中間人穿針引線,化身為帶有強烈象徵意涵的饋贈物件,在成為桌上珍饈前傳達贈禮者不言說的訊息。
在第一章中,Tsing 交代了為何今日日本社會淪落至得向奧勒岡之尋菇人購買松茸的窘境。原來,作為一個得在次生林—或者,更準確地說,天然林經過伐除後,重新長出之以松樹為主的陽性森林—中才能生長的菇類,松茸在日本社會中的流行,乃至於在日本社會文化中的關鍵角色,與江戶時期大規模的伐林與造林、明治時期的殖產興業是分不開的。只是,Tsing寫道,「到了西元一九五○年代中期,情況開始有變」:
小農們的鄉間林地被夷平,改為林木種植場,為城郊發展鋪路,有的林業地直接遭遷居城市的農人棄置。石化燃料取代了木柴和木炭;農民不再利用剩餘林地空間,這些地方於是長成濃密的闊葉雜林。曾被松茸覆蓋的山坡如今過於幽暗,不利松樹生長。遮蔭過多的松樹也被有害的線蟲侵襲致死。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松茸在全日本已寥寥無幾。
即便如此,日本社會對松茸的需求還是有增無減--即在此時, 松茸卻在「美國廢棄的工業林地悄悄破土而出」,開啟了一段跨國、跨族裔以及跨越商品經濟與禮物經濟的旅程。
無疑地,要處理這樣跨國與越界的旅程,研究者得要有不同的理論視野不可。在此,Tsing援引了晚近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廣受討論的分析概念:拼裝(assemblage)。所謂的拼裝,簡單來說,即是強調即便像資本主義這樣貌似無遠弗屆、讓「堅固者終將煙消雲散」的力量,研究者也不能將之視為是滴水不漏、由資本及近代國家悉心籌劃、讓行動者身陷其中難以自拔的掠奪計畫。Tsing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些貌似讓行動者無所遁逃於天地間的「計畫」,往往是研究者的後見之明。一旦我們回到現場,設身處地地觀察那些「被壓迫」、「被宰制」與「被剝削」的人們(例如在奧勒岡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菇的東南亞移民),Tsing表示,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計畫其實是一團無以名狀、充滿間隙、讓行動者得以見縫插針與入室操戈的間隙。Tsing試著以複音音樂(polyphony)來掌握這團無以名狀的「東西」。以她的話來說: 「當我第一次聽見複音音樂時,那是個聽覺上的啟示。我被迫撿起分離與同時的旋律,聆聽這些旋律共同譜出之和諧與不和諧的時刻」(英文版第 23頁)。就任何針對資本主義或其他宏觀結構的研究而言,Tsing主張,關鍵不是為這團拼裝梳理出一套首尾一致、結構縝密、永遠可自圓其說的邏輯—相反的,研究者得關心當中的眾聲喧嘩,乃至於構成這些拼裝之異質元素間的交會與碰撞,到底譜出什麼樣出人意表的樂章。
這也是為什麼我我會稱以下的故事為 「聽不見的臺灣史」。我試著說明,即便Tsing已經聽得如此仔細,在這團將日本、北美與東南亞串起來的「跨界拼裝」(translocal assemblage) 中,還有條更隱晦的旋律。這條旋律訴說著末日松茸的前史,也就是當奧勒岡一帶及日本森林還未淪為資本主義廢墟的時刻。更具體地說,這條旋律回答了以下的問題:奧勒岡的原生森林到底去了那裡、從而讓北美赤松成為當地的優勢物種,並提供了松茸良好的生長環境?還有,如果說松茸在日本的流行與明治時期以降的殖產興業脫不了關係,這些遭到日本資本家反覆伐除、從而讓松茸可生生不息的日本松林又去了那裡?以下我將說明,回答這些問題的樞紐位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或者,更準確地說,位於臺灣中高海拔、被美國植物採集家稱為「東亞最美麗的森林」之中。事實上,當「瑤族、苗族與東南亞裔尋菇人」湧入奧勒岡的國有林中尋求自由,從而提供了太平洋另一端、在經濟衰退中苦苦掙扎之日本人打通關的禮物時,在同一片資本主義造就的廢墟中,我們看到的是反覆遭到林務局驅趕、在「國有林班地」中苦苦種植香菇、以求溫飽的臺灣原住民。總之,我希望說明,閱讀《末日松茸》時,不要忘記,臺灣並未自外在Tsing如此悉心描繪的資本主義體制之外。要了解這套資本主義體制,讓我們先回到二十世紀初期。當時,全球森林資源的快速耗竭,就跟曾經臭氧層的破洞與當前南極冰川的溶解一般,引起了國際的廣泛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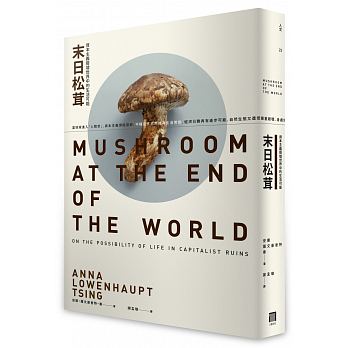
昭代恩澤遍孤島,殖產興業日駸駸
1900年,與巴黎萬國博覽會一併舉行的萬國森林會議認為,自1850年以來,如德、法、英等木材輸出國均轉型為輸入國,且輸入量還逐年遞增。自詡為「森林國」的明治政府並未忽略這樣的趨勢。明治6年已降,明治政府積極以日本林產物參與各萬國博覽會(如明治6年的維也納、9年的費城萬國博覽會等),讓歐美列強得知日本林業的進展。明治15年(1882),在逐漸擺脫歐美於關稅與貿易上的限制後,明治政府更確立以木材輸出為主的貿易政策。經過十餘年的規劃與醞釀,明治32年(1899)的特別經營事業將「木材輸出為目的」的業者納入特賣對象,而北海道與樺太亦分別於明治34與45年納入特賣制的範圍。明治30及40年間,山林局與農商務省更積極派遣林業家前往清國、韓國、滿州、澳洲與南美等地勘查木材輸出的可能性。民間業者如三井物產等,也在政府的鼓勵獎掖下,致力於日本材的輸出工作。明治政府將林業「面向世界」的作法很快地有了成效。明治末年,日本帝國開始躋身重要的木材輸出國之列。大正7年至8年的出超額分別為六百二十萬圓與一千三百三十萬圓,輸入額僅一千萬圓左右。
不過,正積極搶進世界木材市場的日本帝國,並非全無敵手的。尤其是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出產的針葉材,如Pseudotsuga menziesii(美松)、Thuja plicata (美杉)、Chamaecyparis lawsoniana(美檜)等樹種,因物美價廉,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便逐漸掌控歐洲市場。特別是產自華盛頓州、奧瑞岡州與加州北部一帶的美檜, 因其「長大」的特性,更廣受歐陸消費者的歡迎。在如此的背景下,就明治政府而言,臺灣檜木林的發現毋寧有其「戰略意義」。從植物地理學的角度,北美、日本與臺灣是世上僅有的三大檜木產地。儘管日本長野、三重、和歌山、靜岡、奈良、熊本一帶也有生產檜木,惟久經開發,材積難以與美檜抗衡。臺灣「千古以來斧斤未入」的檜木則不然。不僅在材積上較美檜有過之而無不及,材質亦遠比美檜出色。特別是,美檜的色澤會逐漸消褪,且不耐白蟻,臺檜均無此些缺點。簡言之,如果說美檜是讓美國得以稱霸世界木材市場的秘密武器,那麼,放眼世界,唯有領有臺灣的日本帝國能與其「一較長短」。此外,值得一提的,除了放眼世界外,日本林業部門也期待臺灣材能協助內地緩解其日漸浮現的木材供給失衡問題。原來,一次大戰結束後,隨著日本都市化與工業化程度加劇,大量人口湧入都市,衍生糧食與住宅不足、物價急升與生活品質降低等後果。震驚日本國內的「米騷動」(搶米暴動)便是前述問題的體現。顯然的,若不想要類似的騷動發生在木材之上,日本政府得設法找到量多且質優的木材來源不可。阿里山號稱「無盡藏」的檜木資源似乎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個解套之法。
前述「安內攘外」「根植日本、放眼世界」的企圖即反映在總督府林業部門對阿里山林場的設計及規劃上。創業之初,阿里山作業所便以美國西岸的伐木企業為藍本,向美國著名的林業公司Lidgerwood訂購蒸汽動力、集材半徑可達一千公尺的架空式鐵索集材機(cableway skidder)。運材則以海拔三十公尺的嘉義車站為起點,直接銜接兩千公尺餘的伐木地。該所設於嘉義的阿里山製材廠則有「東洋第一」之美譽,其各式製材機不僅可依原木大小進行製材,且自大正初年接收自內地官營製材所退役下來的製材設施後,製材量每日可達四百石。歷經大正2至3年(1913-14)間水災重創鐵路設施、從業者對相關設施仍不熟練等考驗,阿里山作業所得於大正4年(1915)將首批官營材運至內地試售。翌年,當出材更為穩定,作業所得以比照內地官營材的銷售策略,即將木材市場劃定為數個販賣區域,並在每一販賣區域中指定一名指定商。此「販賣區—指定商」制的目的相當明顯,即透過該指定商於該販賣區中的獨占,營林所得避開材商間的競爭、拉高木材市價、降低經營風險及拿捏木材供需間的平衡。幾經協調,自大正6年(1917)起,鈴木商店與東京野澤組同意擔任營林所的指定商,分別負責關東與關西地方的臺灣官營材銷售業務。同年,三井物產也將臺檜運至利物浦試賣。雖說當時日本國內及歐美各國還不了解臺產材(特別是臺灣特有的扁柏)的特色,但以永田正吉的說法,官營林場於臺灣的前途顯然是一片光明。在其《臺灣造林指針(中編)》一書中,總督府技手伊藤貞次郎以如下詩句表達對官營林場的期待:
昭代恩澤遍孤島,殖產興業日駸駸;伐木造林相並進,不知國利年收幾百萬黃金。
的確,隨著理蕃事業的推展,當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檜木資源並非阿里山獨有,諸如大甲溪及宜蘭濁水溪流域也可找到毫不遜色的檜木林時,即便如三井這樣在日本木材貿易、臺灣蕃地拓殖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內地資本,曾向總督府表達經營意願,總督府還是決議直營。除了理蕃的考量外,另一關鍵原因是,草創初期的阿里山屢因風雨導致運輸路線中斷,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日難以運材。受此影響,阿里山林場位於嘉義的製材所不時處在停工狀態。出材不順讓官營材的買主頗感遲疑,對於正欲打開銷路的阿里山作業所實有不利。八仙山與宜蘭濁水溪右岸(即日後的太平山)的檜木林,樹齡與品質均與阿里山相若;三者若能合併經營,將可分擔阿里山經營的風險。
就營林部門而言,將大規模的檜木美林收歸國有、從而打造從生產到流通至消費均在政府管控之下的官營林場,才是理想的林業經營模式。即便官營林場確有與民爭利之嫌,但考慮到森林的公益功能,營林部門還是主張,政府還是森林經營最重要且權威不容挑戰的規劃者及經營者。事實上,證諸二十世紀上半業林業及林學的發展趨勢,我們甚至可以說,臺灣官營林場的設計堪稱當時林業的模範生。就拿被臺灣營林部門視為仿效及取經對象的美國西海岸林業為例。儘管該類型林業的技術密集程度廣受當時林業界注目,但在林業家眼中,其運作是無法永續的。關鍵在於,美國西海岸的林場多為資本家所經營,而這些林業資本關心的只是如何將林木伐倒搬出,對於每年應當砍伐多少才算合理、砍伐量與森林生長量的關係、植伐間該如何取得平衡等至關重要的問題,幾乎是全然置之於度外。於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起,以美國林務署署長 Gifford Pinchot(1865–1946)為首的林業社群開始試著將尚未被資本家圈佔的森林收歸國有。受到德國林業的啟發,這些美國新一代的林學者認為,森林經營絕不能放手讓資本家經營。儘管私有財產權可說是美國社會的基礎,美國林學者主張,考慮到森林的公益功能,政府絕對不能允許讓森林盡成資本的禁臠。於是,約當是營林部門積極規劃阿里山林場的時點,美國林業界也在當時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將大面積的森林收歸國有,並在調查其面積、材積、林木生長量等資訊後,規劃能達到森林之永續收穫的經營計畫。如此由專業的林業官僚為社會大眾規劃森林該如何利用,依其專業判斷來追求森林之多重功能間的平衡,其影響不僅是在林業界,而是貫穿整個「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的精神。以當時的詞彙,這個精神喚做 “conservation”,日文及中文均翻成「保育」。
當我們將全球林業史的脈絡納入考量,不難發現,就營林部門而言,阿里山、八仙山及太平山林場所代表的,不僅是殖民政府想透過殖產興業來開發臺灣此落後、原始及野蠻的「孤島」而已—同等重要的,是以此為樣板,顯示臺灣的殖民林業已可以與美國並列。甚至,考慮到當時美國林業界還只是試著說服社會大眾森林國有及國營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說,至少就林業的觀點,臺灣的官營林場可說是世界林業的楷模,是結合美國技術及德國林學的完美結晶。難怪官營林場會被總督府當成殖民統治之進步、文明開化之成效的展示櫥窗。1920年代,在親身走訪臺灣的官營林場後,著名的植物獵人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在 “A Phyto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Lingneous Flora of Formosa” 一文中盛讚臺灣的針葉林可說是「東亞最美的森林」(the finest forests of eastern Asia)。文末,他則留下如此耐人尋味的句子:「由原住民族群的獵頭習俗而保存下來、免於被功利性的中國人破壞的森林,我誠摯地希望不會被進步的日本人破壞」(Preserved from the utilitarian Chinese by the head-hunting custom of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it is sincerely to be hoped that these forests may not be destroyed by the progressive Japanese)。
伐木造林相並進?不知國利年收幾百萬黃金?
讓我們就來看看所謂「進步的日本人」能否妥善地「保育」這片東亞最美的森林。到底臺灣的官營林場是個立足東亞、放眼世界的嶄新發明還是邯鄲學步?德國林業及美國科技的結合是殖產興業的火車頭,還是個不時瀕臨瓦解的拼裝車?當總督府幾近獨占臺灣寶貴的針葉樹資源,領有臺灣的日本帝國能否如願地與美國木材在世界舞臺上一較長短?營林所作業課長大石浩發表在《臺灣の山林》上的〈本島の官營斫伐事業〉一文讓我們得以回答前述問題。依照大石浩提供的數據,自大正4年(1915)開張以來,八仙山至昭和2年(1927)幾近年年虧損;昭和3年(1928)起雖有獲利跡象,至昭和10年(1935)仍有481705.76圓的虧損。至於阿里山與太平山林場的表現則遠為出色。太平山林場至昭和10年的收益已達4,081,288.26圓,阿里山則達9,421,801.2圓。儘管官營林場以外的指定國有林野的經營成績乏善可陳(大正元年至昭和10年總計有2455394.83圓的虧損),整體而言,營林所還是為國庫帶來總額達10,565,988.87圓的利潤,平均年收益為459390.8圓。
有趣的是,在以數據說明官營林場的經營實績後,大石浩卻要讀者不要對官營林場的永續性過於樂觀。關鍵在於,由於官營林場係以政府預算支付如鐵道、索道等固定設施的興建及維護費用,若計算時未將固定設施的「償却」包括在內, 官營林場為國庫帶來的利潤不免被高估。按此算法,三大林場均面臨入不敷出、勉力維持的困境。就以帳面上獲利最多的阿里山林場為例。由於其創業費達6,087,527.97圓,如每年以三分利計算,要到昭和9年(1934),阿里山林場才勉強將固定設施償却完畢—意即,昭和10年以降的阿里山經營收益才算為國庫帶來淨利。眼見各類號稱「東亞第一」的固定設施有著淪為沈積資本(sunk capital)的危機,大石浩直指官營林場的病灶:生產成本。昭和元年(1926)每立方米官營材的生產成本可達二、三十圓,加上運銷等費用已無利潤可圖。所幸在基礎設施的完備、伐木及製材技術的熟練及本島人雇傭策略的實施等面向的影響下,至昭和10年(1935)三大林場的生產成本已成功地降至原本的六成(阿里山 23.394→18.611;太平山 34.456→17.432;八仙山 31.298→19.033),大石浩還是表示,官營材的銷路若不打開、市價低落又不改善的話,技術改善並不會讓各林場脫離「倒覆之運命」。
讀者也許會質疑大石浩的論點不免失之偏頗且過於官方本位,日本做為臺灣的殖民母國,難道不就是渴望著臺灣的檜木資源嗎?官營材既以檜木爲主軸,怎可能會有「有貨無市」的問題?從後見之明來看,前述迷思的源頭也許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在其1929年出版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一書中, 矢內原將「日本向臺灣買檜木而賣松杉」的貿易規則比擬爲糖米間的關係,也就是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所說的維生部門及出口部門間的關係。但檜木/松杉與糖/米間關係的最大差異是日本並不像需要糖一般地需求檜木—或者,更準確地說,日本並不需要像臺檜這樣的檜木。原來,大正9年(1920),有鑑於住宅及工廠建設、促進針葉材輸入等目標下,原敬內閣決議徹廢一部分的木材關稅,引進外材以緩解日本日益嚴重的都市問題。此舉讓日本急轉為木材輸入國,大正9年的木材年輸入額為兩千兩百五十萬圓,10年達四千三百五十萬圓,11年甚至創下八千四百八十萬圓的鉅額。大正12年,受經濟不況影響,輸入量略有減少,然在同年9月東京大震後,用材需求孔急,外材更湧入日本木材市場。是年9月至12月的四個月間,輸入額達到三百七十四萬石,價值三千八百七十餘萬圓,這讓大正12年的木材輸入額達到九千三百二十餘萬圓。大正13年,木材已躍居輸入品的第三位,僅次於棉花與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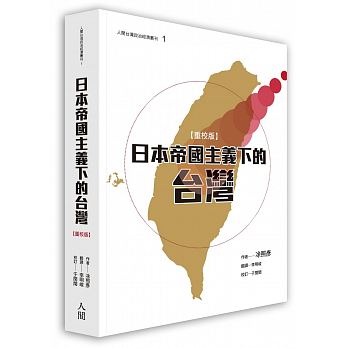
來自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一帶的針葉材在輸入材中佔了極大比重。雖說從林產加工的觀點,美材實有易受蟲蛀、材質欠佳等缺陷,然其材價格便宜、規格統一、量多價廉、能在短時間內大量供給等特點,非常適合做為工業原料與建材。再加上,大正9年(1920)以降,美國正值經濟不景氣,不僅材價急落,日美間的船運費亦甚為便宜。這些因素在在構成美材在內地市場一支獨秀的主因。可以理解,當內地木材市場幾為美材支配,如官營材這樣與美材可相互替代的商品,下場不會太好。的確,當臺灣的營林部門開始穩定供材給內地市場時,卻發現內地材商、製材業者及建築業者等對如此價格高昂、數量稀少的「高級品」興趣缺缺。更雪上加霜的,昭和4年(1929),隨著金輸解禁(即廢除黃金輸出的規定,回歸金本位制)、震災復舊完成及全球的景氣低迷,內地木材市場更難以抵禦北美與南洋材的夾擠而陷入遲滯,臺灣官營材的地位也隨之跌落。不堪虧損,長期擔任臺灣營林部門之指定商的鈴木商店與東京野澤組,決定於大正13年(1924)起不與營林所續約。對於臺灣營林部門來說,這自然是個沈重的打擊。為了讓「販賣區域—指定商」制得以運作,營林部門只得壓低價格,以招募新的指定商。此舉有了成效。臺灣材組合、總木材會社及大臺組應允擔任東京、名古屋及大阪的官營材銷售業務。然而,可能是為了促進官營材的流通,內地營林部門於大正14年(1925)廢除販賣區域制。受此影響,臺灣營林部門之指定商的數目逐漸增加。依據昭和7年(1932)出版的《臺灣材》,東京計有11名、名古屋2名、大阪3名、九州2名等18名指定商。昭和8年(1933)年的〈特種林木扁柏、紅檜の需給及取引に就て〉一文則列東京12名、名古屋3名、大阪4名、京阪4名與九州3名的「本島產扁柏及紅檜取扱店」。單從指定商數目的增加趨勢來看,儘管不時面臨入不敷出的窘境,臺灣的營林部門還是勉強守住了內地這塊木材市場。
但守住內地這塊市場的代價卻是格外高昂。讓我們先來看看官營材於內地及臺灣的銷售成績。大正13年(1924)起,受到木材市況不佳、廢除販賣區域制等影響,銷往內地的材積僅六、七萬石,佔總銷售量的兩成,餘八成盡在「島內消化」。至於銷售策略則維持「高價品移往內地」的模式,扁柏佔了移出量的七成左右。材質略遜的紅檜則佔移出量一成七,松、杉、柏等針葉材的比例則微不足道。換言之,如果說臺灣的營林部門得以守住內地市場的手段在於賤賣,這些遭到「賤賣」的商品不是別的—而是生長緩慢、千百年來方能成就一片美林的臺灣特有種扁柏。
如果說內地市場得靠賤賣臺灣特有的、價值高昂的扁柏方能勉強維持,吸收八成之官營材的本島木材市場又是如何?首先,必須強調的,為了要確保官營材之於本島木材市場的獨占,臺灣的營林部門也引入如內地般的「販賣區域—指定商」制。其次,官營材依加工方式不同可分為製材與丸太兩類。製材方面原由大正5年(1916)成立的臺灣木材共同購買所代理,然大正12年(1923)因臺灣財政衰退,該會社各出資者意見不一而告解散。不數月,臺灣木材共同販賣所(資金六十萬圓)隨即成立,由島內各主要材商出資,負責人為植松材木店臺灣支店主任平戶吉藏。丸太材以往仰賴各木商受營林所木材拂下後自行求售,但大正末年的財政不景氣讓木商陷入「非常之苦境」,總督府基於「整理統一之急務」,於大正15年(1926)輔助業者成立合資會社臺灣丸太共同購買所,代表社員為櫻井組的櫻井貞次郎。但昭和5年(1930)又受財政不況影響,翌年兩社合併為臺灣材友會。依據昭和8年(1933)的統計資料,營林所於西部各州計有九家「拂下指定商」,包括臺北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灣丸太共同購買代表飯田清、臺灣木材共同購買代表平戶吉藏、淡水施合發商行,臺中林金峰、豐原張海浪(協榮木材商行)以及嘉義的邱塔與小野寺舜平、臺南的蘇墩等。
不過,雖說營林部門的初衷是透過「指定商—販賣區域」的設計來穩定或拉抬官營材於臺灣木材市場的市價,這樣的構想卻難以落實。關鍵在於,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在美材等外材的圍攻下難以喘息的內地林業資本,紛紛將其滯銷的針葉材傾銷至臺灣。依據總督府林務課山崎嘉夫於大正12年(1923)發表的〈臺灣に於ける木材需給に就て〉,臺灣的木材市場充斥著廉價的內地針葉材及福州材,一旦官營材出材一有閃失,營林部門將難以與內地材商競爭而被「殺倒」。在如此浮動、不確定且高度競爭的木材市場中,臺灣官營材銷售網絡發展出與內地迥異的型態。如宮瀨浩所觀察到的,當內地的官營材銷售多仰賴少數幾個「卸問屋」(即批發商)為「取引機構」,臺灣的官營材銷售多由數量眾多、相互競爭激烈的「小賣業者」擔綱。原來,在自營林部門處取得官營材後,為避免市場波動釀成損失,指定商多將之脫手給在地的製材業者。依據總督府林業官員的觀察,這些製材業者多為本島人經營,資金有限、技術相對原始而規模也不大;在自指定商處取得官營材後,為了在充斥著內地松杉材及福州杉材的市場中尋得一線生機,業者只得賤價出售官營材,以免周轉不靈。換言之,如果說營林部門得以守住內地市場的關鍵是賤價出售臺灣珍貴的扁柏材,在島內「消化」的官營材也同樣遭到賤賣。
就營林部門而言,「賣行不振」另一嚴重的後遺症是損及官營林場的正當性基礎。如前所述,在官營林場設置之初,營林部門之所以能排除內地資本、將臺灣珍貴的檜木林納入直營,關鍵在於,依照當時林學的觀點,惟有國家方能在兼顧公眾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林業的永續收穫。另外,考慮到臺灣千百年來斧今未入的檜木林已過於老熟,營林部門認為,理想的模式是採高強度的皆伐,將森林淨空後予以造林,如此一來,這些老熟林才能恢復活力。從今日環境保育的觀點,這樣的見解或許難以接受—但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保育觀中,如此「皆伐造林林相更新」的作業順序允為最先進的經營模式之一。雖說如此,一旦把官營林場「入不敷出」、「賣行不振」的困境考慮在內,不難發現,前述先進的見解完全沒有在臺灣落實的可能性。關鍵在於,如果說營林部門得賤賣臺灣獨步全球之檜木方能在木材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對於同樣也是臺灣針葉林帶之重要成員的樹種,像是鐵杉或雲杉, 該部門根本不會予以考慮—勉力伐倒搬出的話,只會遭致「有貨無市」的困境。如此「有貨無市」的隱憂讓營林部門無法積極地投入前述林相更新工作,進一步導致官營林場的「植伐失衡」。「植伐失衡」的後果或可用大石浩於〈本島の官營斫伐事業〉中的觀察來說明。在計算固定設施的償卻年限後,大石浩表示,八仙山與太平山的起業較晚,且伐木強度較低,其營運應該還可維持六十年;只是,起業之初堪稱臺灣林業樣板的阿里山林場,由於其固定設施的投入過於龐大,當於昭和10年(1935)勉強開始獲利後,所餘天然林已然有限,在八年內恐會宣告枯竭。
對照總督府開發官營林場時的意氣風發,大石浩的結語實教人遺憾。從「移出內地」、「放眼世界」至「八成官營材得在島內消化」,從「千古以來斧斤未入的森林」到「所餘期限不足十年」,這些激烈變化一方面代表臺灣林業史上最為輝煌及矛盾的一頁;另方面,官營林場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日本林業社群重新省思臺灣林業於帝國中的定位。如臺灣山林會表示的,「臺灣林業有其特殊性,內地林業難以一體適用」。這套按照臺灣之特殊性打造出來的治理體制,我將在下集中說明,不僅提供了當今臺灣林業的基礎架構,同時也是臺灣原住民在大程度上流離失所、「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的主因。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洪廣冀 《末日松茸》中「聽不見」的臺灣史(上)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672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殖民廢墟下早產的《末日松茸》!?
這人的文字一向來都很愛掉書袋,塞資料,很難讀 唉.......
作者將複雜的脈絡爬梳清晰非常不簡單,嚴謹引用史料言之有物,絕非掉書袋塞資料~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