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作為異文化的練習
芭樂電台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鯨老師與我們聊聊一個另類的教學實驗。聽說鯨老師在文化人類學導論課(碩班與大三以上)要求學生寫科幻小說,讓人覺得有點神奇。
左:為什麼要寫科幻小說?為什麼不去訓練寫民族誌?
鯨:因為全貌觀。這是對於全貌觀的訓練。
正規的訓練也有正規的好處,那部分我們也做了不少。但因為學生背景多元,許多對人類學不熟悉,要幾個星期就訓練到可以寫民族誌,我覺得不太可行。
如果在短時間內就要貿然去描述某個社群,在對其政治、經濟、親屬、宗教、性別、階級、族群、國族境況等等以及這些彼此糾結之面向的歷史變遷理解不夠深的情況下,會寫出什麼樣的東西?可能是誤讀的詮釋、去歷史性的描繪,即便你以為你呈現的確實是「當地人/當事人觀點」。
所以我覺得,不妨讓學生去建構一個文化或社會,甚至是宇宙。在這裡你是上帝,你知道一切。你可能不知道一間廠商公司何運作,但若你進去工作,做過每一個位子,包含最高層與最底層,你應該會很理解整個廠商運作的方式,如果你有很認真去思考每個環節是怎麼環環相扣、或是斷裂的話。
所以我希望學生創造一個宇宙,不只當上帝,也當工人,也當秘書,也當戰士,也當保姆。這種練習是要去構思社會的每一個面向,要怎麼樣才會合理、可能、像真的一樣?社會的特色在哪裡?人民的性情氣質是什麼?願望是什麼?哪些地方明顯出問題而需要改正?哪些問題為什麼明明很嚴重,卻改變不了?人們為了什麼而鬥爭、犧牲生命?人們如何評論生命、實作生命?我覺得這是一種很人類學式的全貌觀的訓練。
當然,我希望學生以後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現象,就會去想,這是因為哪些其他存在的制度的設計才導致這樣的發展?能這樣想的話,就不會把一個現象孤立,很簡化地去看待一個問題,或認為凡事都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你總是必須考量不同人群的觀點,不同的處境。
左:確實,我們也有很多有人類學背景(或家學淵源)的優秀科幻小說家,而很多經典的、最偉大的科幻小說也往往受到很多地球上的「異文化」而啟發。不過,聽說為了出這份作業,你自己寫了一篇小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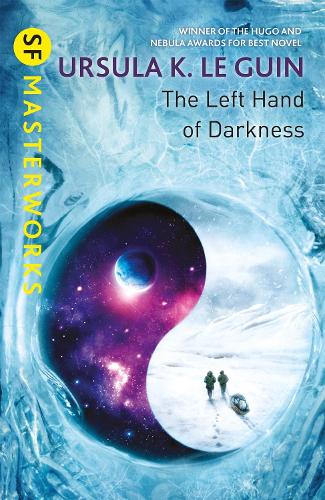
鯨:對,我想更參與其中,當然也想讓平常沒有在讀科幻小說的同學有一個線索,去看大概要做到什麼程度。
左:那你的故事是關於什麼?
鯨:要現在就說嗎?
左:不然我們就直接先聽故事吧。在那之前你有想要提醒聽眾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
鯨:有。我不是小說家,所以以小說家的標準來看,恐怕會覺得拙劣。畢竟是極快速的時間內為了示範給學生看寫出來的。但我希望有達到我的目的。裡頭也有很多不同的經典科幻小說的影子,雖然用法不太一樣。
左:好,接下來我們將聽到鯨老師閱讀她自己的作品,《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她是第一個被帶入蓋亞界域裡的地球人,而那完全是一場意外。
距離地球二十億光年的蓋亞界域,沒有超光速的多次瞬越,就無法抵達的境地。在人類的世界裡是一種從未被實踐的理論,在蓋亞裡卻是一種輕而易舉,卻不常操作的實踐。
克里斯不斷地對她說明關於蓋亞的種種,而他們也在三年內就學會了彼此的語言。
「你們,呃,我的意思是『你』,抱歉,我常常忘記你們有單數第二人稱」,克里斯一手握著一只銀色的琉璃水杯,一手撫摸著她的頭髮。在地球上,她原本從來不喜歡別人摸她的頭髮。但是克里斯是她的情人,她從沒遇過的男人,如果他算「男人」的話。他可以對她做任何事情,因為他做的任何事情永遠使她詫異而驚喜。詫異,但是溫暖,以至於她老早克服了一開始對於蓋亞人外貌的恐懼。他的臉上,跟其他蓋亞人一樣,是密密麻麻的虎紋。他的皮膚有著黑曜石的色澤與頁岩的質地,適應著相對靠近他們的恆星因而演化出耐熱耐曬的生物機能與外貌。而虎紋是完全文化性的。它提醒著已經擁有高科技的蓋亞人接受皮肉之痛,用肉體與心靈去承載蓋亞的重要性。
「你就叫我『主體』吧,我想那相當接近我們地球上「你」的意思。或許這樣你就比較不會叫錯了,」她接著搶過克里斯手中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水。
「主體真的很聰明」,克里斯笑出聲,「但遺忘可能是件美好的事情,尤其是那麼多事情都被記錄下來了。」
「你是說那些蓋亞文明與毀滅博物館的事情?你覺得我應該要回去告訴地球人,讓他們也要蓋這些高科技文明博物館,等到文明毀滅時再回來觀看他們,以免重蹈覆轍?」
「倒也不是,」克里斯若有所思,但沒有立刻接話。他看了窗外遠處將靠近的牧人們,知道是時候跟她攤牌了。
「諾爾,有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選擇讓你來蓋亞界域是有目的的。」
「我知道啊,有地球高層想求助於你們,所以他們決定派了一個『最有同理心』的語言人類學家,可以快速學會當地語言與文化的傢伙,來跟妳們學習——」
「主體先聽我說,」克里斯打斷了她的話,「每三十九年,超光速瞬躍機器才會啟動一次,去到蓋亞界域以外的地方,再折返。三年前,我們還在爭執主體該何時被帶來,但瞬躍機可能有些故障或設定問題,總之突然間就把主體帶來了。主體確實是我們要找的地球人,但時間點比我們想的早了一些。但這是超出我們技術人員能理解的範圍,因此並不影響下次瞬躍機的啟動。總之,下次瞬躍機啟動時,我們要帶一批地球人進來,人數可能相當有限。至於誰可以進來,主體將與我們的互助會一起討論。」

這些話讓諾爾呆住了。最讓她害怕的並不是蓋亞人竟然要她建議誰可以進來。她老早厭惡了那些憑藉著地球最後的資源來鞏固與保護太空船的菁英階層,因此她首要之務一定是建議讓地表船上最脆弱的難民先逃離地球,來到蓋亞。
讓她真正害怕的是,這是她第一次知道瞬躍機只有每三十九年才會啟動一次。從來沒有人告訴她這件事情。換言之,她如果這次不回去,她就要再等三十九年,大約相當於地球的四十五年。她與女兒已經失聯多年,如果她這次不回去,堅持要留在危險海域的地表船上的女兒,是否還能再活四十五年?不,她連女兒現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她甚至不能把女兒列上建議名單上,因為在她來到這裡以前,女兒已經失蹤了兩年。她雖然並不想回地球,卻無法忘記女兒的下落。
她緊張地跑向溫暖的石牆上那以五天為一星期的蓋亞月曆,前後翻閱,卻找不到任何關於三十九年的字樣。
「瞬躍機下次甚麼時候啟動?」她屏息以待克里斯的回答。
克里斯刻意將臉龐別過不去看她的眼睛。他向門外已經抵達的牧人互助會人們舉手打了招呼,同時平靜地說:「再兩個星期,就是三十九年。」
十天,她剩下十天。
*****
五天後,當他們蓋上棺木的時候,諾爾想起在地球上每一個她見過的棺木裏頭,裝的都是年邁的身體。曾經一整個五年,她與其他女修道士們一起照顧無依無靠的老人們。當時新玉山上僅存幾處有電的地方,而圍繞著山的那些海洋與海洋垃圾隨時會沖斷電線桿或電網。也許就是因為在如此偏遠的場所,她們還能勉強不受騷擾地工作。海上過去幾十年幾乎已經沒有盜匪,因為人們存在一種恐怖平衡:誰要是侵犯了他人的疆域,復仇者將引發區域性海水電擊,導致海水中僅存的魚蝦大量死亡,再度引起飢荒。幾次饑荒之後,人們放棄了這一帶的海上掠奪。至於天上來的掠奪,比較有效的抵擋方式是賄賂,以貢獻珍貴的植物來換取和平。但主要有一大部分是靠人脈關係。新玉山上的年輕女人們,多半是有資格進入太空船,卻自願放棄留在地表船上,最後漂流到此的菁英。由於她們多半有親友在天空的另一端,太空船的勒索行為也會稍微有所節制,至少留些情面。
無彩工阿嬤是諾爾在新玉山收容所裏頭第一位埋葬的病人,甚至感覺有點像是親人。因為諾爾生下來是個孤兒,之後被貴族收養,家族裡的人個個身體硬朗,不像太空船裡其他的老頭們,身上插滿了管子,還要定期派部隊到地球上僅存的森林中偷取氧氣。直到成年前,她並未真正參與過任何人的喪禮。
無彩工阿嬤的症狀是不斷重複相同而簡短的話語。她的口頭禪大約只有三個。每每在療程進步到了一個程度,就要突然到完成整堂課程的圖片認知時,她就會自暴自棄地說:「無彩工。」無論誰如何再鼓勵她,接下來好幾個星期,阿嬤總會不屑地別過頭去,咬咬無牙的下巴而後堅定地說:「無彩工。」她過世的前一天,最後跟諾爾說的話仍然是「無彩工」。
諾爾埋葬的第二位病人是一位相信自己是聯合國總理秘書,每天早上五點半一定拿著同一封奇怪信件等待太空船的阿伯。但聯合國阿伯除了幾種食物名稱外,幾乎說不出任何抽象詞彙。照顧他的修士幾乎每天都要被阿伯用各種青菜水果的名稱怒罵一遍。「你簡直地瓜葉海帶芽!什麼番茄橘子!還在香蕉!芭樂真是。芭樂!」
至於第三位,她其實沒有埋葬,因為她把他的骨灰帶在身上。那是她前配偶的骨灰。

兩天前,她就一直帶著骨灰。那是互助會決議完難民收容名單後的隔天,克里斯的兒子約瑟夫剛滿十二歲,臉上的虎紋傷痕仍未完全恢復。
諾爾本想送他一個通過成年禮的禮物,但因為要擬定救難名單與路線,日夜忙碌,來不及準備。反倒是約瑟夫雀躍地寫了一首詩送給她。她認份地笑了笑。她知道,蓋亞人花一輩子的時間作詩與畫畫,只有極少數的人被訓練為電腦計算士與武裝戰士。這是大部分人最擅長做的事情。
年輕詩人臉上的傷提醒著諾爾,蓋亞星球過去的文明曾經有過醫生,但醫生階層已被社會淘汰。現在的人生病時(正確來說,是「修煉」時)會去巫師的房屋長住,病人被稱為修煉士,直到康復,或是死去。紋面並不算是受傷,而是榮耀,根本不必住在巫師家。諾爾武斷地想,許多人並不長壽,或許也是因為如此。但蓋亞人從來不執迷於生命的延展,完全不同於地球人對於長生不老藥的妄想。莉亞如果還在地球上活著——諾爾總覺得她還活著,如果她也可以來到蓋亞星球的話,她一定會因為多了一個難得的詩友而興奮不已。莉亞喜歡的是古老時代的詩歌文學,但身為母親的諾爾喜歡的是結構分析。
我們從不為死亡傷心
因為我存在於每一個角落中
我們不為分別流淚
因為我們是我們祖母的情人
我們擁有她們的記憶
我們一起活著,一起死去
但當我再度復活時
主體會認得我的身體嗎
如今我學會了傷心
但我們畢竟是蓋亞
我們從不為死亡傷心
「謝謝你,約瑟夫。」諾爾讀完詩句,想起克里斯曾經告訴她他是他已經死去的祖母的情人之一的轉世,因為他擁有她的記憶。約瑟夫也是他祖母情人的轉世嗎?但蓋亞人每個人都有許多不分性別的情人,且在肉體上並沒有單獨佔有的關係。
「這首詩有名字嗎,」她問約瑟夫。
「我覺得它的名字是《克里斯的主體》,」約瑟夫回答。
「所以,這首詩是克斯里眼中的我的意思嗎?」
約瑟夫沒有回答。
「再度復活是甚麼意思?」
「克里斯父親即將回歸到祖母地,有一天會再復活。」
她知道在蓋亞文化中,最有智慧的人不是成年人,而是孩子。他們總能創作出意想不到的詩句與畫作。有一幅八歲孩子的畫,去年在宇宙館大廳上被作為常設展。那是一幅巨幅畫像,數個蓋亞人影在海洋深處進行雙手環抱屈膝的水母漂,而屈膝的蓋亞人群阻擋了遠處的海洋垃圾洋流入侵。每個人都是數來個靈魂重疊、甚至數種鯨豚的畫面。
在蓋亞文化裡,諾爾時常分不出哪些是譬喻,哪些是真實。她唯一知道的是她可以盡情問孩子任何問題。她知道回到祖母地就是指死亡的意思,但她必須與約瑟夫再度確認。
「不是死掉,是回歸。他的記憶會被祖母地保留下來,然後我未來的其中一個孩子會繼承他的記憶。」
繼承?要如何繼承?諾爾越聽越困惑。「你的意思是他快要死——我是說,快要回歸祖母地了嗎?但他最近一年多都沒有去過巫師家修煉,感覺也非常」諾爾想說「健康」,但這不是蓋亞人的說法。「他沒有去修煉,感覺身體非常普通,你確定他快要回歸了?」
「回歸是我們的義務。修煉士或普通人若到了時候,都必須回歸。」
「什麼時候你們會知道到了時候?」
「我們三十九歲以前一定要回歸祖母地。克里斯父親再一週就滿三十九歲了。」
她的心緊縮了起來。
突然間,那些人們平均壽命不長的圖像全部都獲取了另外一層的意義。原來不是因為沒有醫生,所以人們平均壽命不長。人們看起來都很年輕,而且也不常去「修煉」,但時常就聽聞會有些人突然間回歸祖母地。人們總是完全投入在自己創作的詩與藝術之中,看來愉悅、浪漫,是因為他們知道很快就要回歸祖母地。怡然自得、自願地回歸。沒有醫療的痛苦,沒有長期照顧的壓力。所有人都在年輕力盛,吟詩作詞,跳舞賞星時回歸。

當他們蓋上棺木的時候,諾爾把她亡夫的骨灰拿了出來,也一起倒了進去。現在,她的亡夫與克里斯葬在一起了。她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做,但那是一股不可遏止的衝動。依照蓋亞星的律法,她不得帶走任何一塊土壤。她想帶著這兩個人的骨灰在身上,但是她無法。或許最好的方式就是都留在這裡。也許這麼一來,她可以用一種全新的心態回到地球。
******
離開蓋亞前的最後一天,諾爾參觀了祖母地的晶片儲存館。她原本想像裏頭會有上百名計算人員進行複雜的數學公式與配對,但整個地方除了濕度溫度控制各種高規格的收藏設計之外,其實更像是一座可以安靜地求神問卜的神社,只有一個負責打掃的男人與一個坐在櫃台上操作電腦的男人。她想起約瑟夫跟她說過,蓋亞人的身體會自動尋找到適合的晶片,承載適合的靈魂與記憶。她覺得這已經超出她的理解範圍,因此不再試圖去了解。
當她經過了歷時地球時間共九天的五次瞬越、五次節點以及五次航行而回到地球時,她在由蓋亞武裝戰士團守衛的基地裏頭,再次沙盤演練如何找到名單上的人。武裝戰士跟她先前認識的蓋亞人都不同,她在蓋亞星上只有偶爾才見過他們。這些人是少數中的少數,由先天身體發展較為殊異的人擔任(在地球上,這些人可能被當作「身障者」)。由於身體殊異,他們與普通人打架或作戰時,更難以捉摸,也更能看穿敵人的弱點。只要加上獨特的裝備,他們被視為難以打倒的戰士。
兩天過去了,這個帶領地球人的「出埃及記」任務涉及越獄、劫走政治犯,困難重重。要不是有她身邊這一群武裝戰士,絕不可能達成。除了從新玉山那類破敗的地方帶走老人不需要動用武力之外,其餘所有在各艘太空船上的政治犯的劫獄,必然導致太空戰。
由於一直有這類棘手的任務在身,所愛之死似乎從未真正擊垮她。她甚至沒有時間流淚。夜晚正準備入睡時,寢室的艙門傳來敲門聲,她打開床燈。這是人類的敲門聲,不是蓋亞人的敲門聲。
人類?能夠進來這裡的人類?她迅速地下床,打開艙門,以為要遇見當初送她去蓋亞星的官員秘書,卻驚訝地看見長髮及膝、膚色黝黑、疲憊卻眼神閃爍著光芒的莉亞。
「莉亞?!!!!莉亞?!」
「媽,我醒了,我全都想起來了。」
「這些年你都到哪裡去了?你、你怎麼進來的?外面有很多,就是,要怎麼跟你解釋,總之就是外星球來的武裝部隊,你要是被發現的話——你等等,我必須先跟他們解釋,你——」
「媽,你等一下,好,主體,主體聽我說。我是克里斯的母親,而主體是克里斯的祖母。」莉亞停下來,看見諾爾皺眉搖頭,她於是接著再用蓋亞星的通用語翻譯了一次這句話。
諾爾聽到了「主體」二字,又聽到蓋亞通用語從女兒口中說出,左手抱住了額頭。
「媽,我們就是蓋亞。爸爸回歸的那天,我就感受到了,但我很混亂,所以我才離開。但現在我全都想起來了,我的晶片完全啟動了,因為克里斯回歸了。」
莉亞對著她說了很多很多,諾爾喝了整個基地營區裡頭最後一包洋甘菊茶。
諾爾感覺到一股憤怒與理解的衝突。如果她自己的母親確實在地球上生下了她、並將她留在地球上,如果她真的是蓋亞人,那麼她又是如何與亡夫生下莉亞的呢?莉亞何時何地獲取晶片?她想起亡夫死在四十五歲,蓋亞年的三十九年。
但為什麼蓋亞人要幫助地球人呢?
「媽,一起回去蓋亞吧,那裡才是我們的家。」莉亞幾乎像一個悟道的智者,溫柔地喚著。
諾爾整整停頓了一夜,沒有說話。
等到凌晨時,她也真的醒了。
她對莉亞說:「我不回去蓋亞。我需要再一個三十九年。」
完

*****
左:三十九年,這個抬頭,是超光速機器運轉的時間,它會把新的少數地球難民帶來,但同時,那也是蓋亞人時候到了、要儀式性自殺的時間。為什麼是三十九年?你一開始是想寫什麼樣的東西?
鯨:構想一開始是想反思「長照問題」、某種生命政治(一直逼人要活下去)。我的問題是:如果人們只有三十九年的壽命,人們的生活會長成什麼樣子?設定這個時間,要夠長、可以繁殖,但又要夠短,短到人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最有意義的決定。
後來長出很多東西,包括背景也是典型的末世場景(海平面上升淹沒大量土地、人人自危,但還是有利他的人)。那些東西也沒有一定要為了主旨而被犧牲掉。反而細節是提供真實很好的素材。
左:蓋亞人的特色是感覺相對原始的與最高科技的結合。也就是說,明明有像記憶晶片跟超光速那樣的東西了,但卻寧可不要醫療制度。這當然是裡頭最具爭議性,但也是最具批判性的一部份了,就是在他們的歷史中,醫生階級曾經存在,但被全部消滅了,取而代之的是傳統療法與青壯年自殺,來控制人口。但我想重點應該不是說,那就讓我們如法炮製、也把醫生都消滅、讓大家都集體自殺,而是換個角度在問說:如果我們都願意會社會做一些事情(比如參與社運)、或者也一直在為國家做某些事情(比如繳稅、選舉),或是從軍等,那是否一旦集體自殺作為死亡事件被當成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該為社群做的事情,其實與其直接譴責,反而應該先去想它是如何被自然化的?或者說,如果我們真的都能好好思考生命苦短、要拿來做最有意義的事情(在蓋亞,是作詩跳舞,甚至是去幫助外星球人?),或許社會真的會比較好?
鯨:但那個「好」也是建立在一種集體暴力之上。最美好的事物都有最暴力的面向在底下支撐。在很多哲學裡頭,死亡是讓人生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人可以一直長生不老的話,那做什麼、是什麼也都沒有意義了,因為不會有後果,之後再做別的試試看就可以了。這話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死亡並不是普同的。在不同的文化宇宙裡,死亡一開始就不是同等的東西。所以「死亡的制度」確實會影響著人類如何生活,但死亡不是同樣的。對死亡的認知、想像、感受、行為,都不一樣。死亡的存在不同。這篇故事確實有一部份在思考死亡的制度。它沒有要提供一個答案的意思,而只是希望大家用一個極端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左:除了這些議題上的討論之外,其實好像也有很多人類學家與報導人的影子在裡頭?當然談戀愛是非常有爭議性、也會被很多人說不倫理的。但戀愛卻也是能更深層同理對方的親密管道。還有,克里斯與諾爾彼此學習對方的語言,語言的設計除了快速有效地增加異文化感之外,也很巧妙地凸顯出蓋亞人那種強烈集體感與個人主體性(「主體」)不必然需要對立而可以共存的可能。
鯨:真實的異文化交流往往是造成雙向的文化震撼的關係,比如克里斯受到諾爾影響,原本是不懂得嫉妒、不懂得佔有慾的,也不懂得為分離悲傷的,結果因為這樣相處下來,不是只有諾爾學習到蓋亞人的文化(當然是漸進式的領悟),克里斯也學到了地球人的文化,包含死亡、分離要悲傷等等。當然他不是直接對她表現,而是隱藏,反而是他兒子約瑟夫的詩詞道出他處於兩個情緒文化之間的矛盾。
左:關於諾爾的身世,可能很多人會有疑問。為什麼諾爾一定要是蓋亞人後代?
鯨:我的想法是,血統在此是個譬喻,就是去到異文化以後,你逐漸領悟很多事情,也很認同,但在最有爭議與最大差異的地方,你開始覺得很不安,不知道你可以認同到什麼程度。這時候你只能麻木。然後下一步是更慘的,你發現所謂的他者本質,其實也在你自己裡面,他們有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你自己也有,只是可能成份不同。所以讓諾爾最後發現自己是蓋亞人,也有點是在逼迫她現在到底比較像地球人還是蓋亞人?但當然她是介於兩者之間,倒不是因為血統(那只是個譬喻,雖然說是很強烈的譬喻),而是因為學習。
這個可以透過跟女兒莉亞比較看出。女兒沒去過蓋亞,除了新增意識以外是徹底的地球人,但女兒似乎想要逼迫母親回鄉從事儀式性自殺嗎,可能是出於對蓋亞有浪漫的想像,但也可能是因為對地表上太幻滅。這部分我們不得而知(我也沒去構想)。諾爾表面上看起來是要留下來繼續救援照顧老人,她真正的部落(因為文化上她仍屬於地球),但她留下來的那個舉動正好就像是她自己不認識的母親要來幫助地球人一樣,具有一種利他的動機。所以她變得更像蓋亞人的方式,是繼續當地球人,或者說當一種雙重文化的混合體。
女兒的存在似乎在功能上是為了把蓋亞人的宇宙觀講得更完整:男人與女人都是祖父母的情人轉世(其實沒有限定同性相戀或異性相戀),簡言之這裡牽涉的是一種循環史觀,而不是線性史觀。
左:但我認為這個故事讀起來,會被記憶晶片搶走風頭,忘記這是為了循環史觀,不是為了不要遺忘。有的人可能會以為記憶晶片是一種讚揚心靈心智精神,貶低肉體的制度,或是一種長生不老藥的「大腦版」而已?
鯨:這個倒是還好,畢竟蓋亞人對身體的重視,與精神是相連的,連選晶片也是身體選的。記憶晶片不是一種線上雲端人人可用,它有一些類似宗教直覺的東西,才能配對成功。所以會把那個儲存晶片的地方寫得像是一座神社,主要就是要暗示宗教性而非數學性的東西。所以說,雖然大腦的晶片常常給我們一種身心二元論的感覺,但在這裡其實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想要試試看改變記憶晶片的意義,改成關於循環、記憶、犧牲,處於淡然與深愛之間的練習。
左:那學生後來都寫了些什麼?
鯨:哇,有的真的很精彩,有一個關於鎢銅鈦三種機器人批判種族主義的故事,還有一個阿法貝塔嘎瑪三階層人批判英雄主義的故事,都寓意深遠,感覺應該收錄在高中課本裡頭。但可能要下次訪談才有機會說了。
左: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期待。再次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節目。
鯨:謝謝讓我有這個機會分享。
{芭樂說文解字}
無彩工 bô-tshái-kang
台語,白費力氣、枉費工夫之意。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左拉 科幻小說作為異文化的練習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63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