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
「練體操與拍電影都是一條困難的道路,如果你下定決心往這條道路走,你就應該要開心地堅持下去,撐到最後就是你的了。」(《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62)
2021年八月八日,東京奧運閉幕。向來是體育門外漢,連一日球迷也當不上的我,卻跟著《翻滾》系列當了一週的夢想迷。四年前在戲院看了《翻滾吧,男人》,趁機補完《翻滾》三部曲。《翻滾吧!男孩》(2005)動人活潑,《翻滾吧!阿信》(2011)感人,《翻滾吧!男人》(2017)則增添了歲月的深度與命運的跌宕。很有趣地,導演林育賢原本對《翻滾吧!男人》的規劃就是拍到2020東京奧運,然而由於2015年秋,由於李智凱有機會爭取2016年里約奧運入場券,在教練的通知下,一切都提前了……《翻滾吧!男人》於2016年九月初拍攝殺青[1],正好是里約奧運結束之後。2017年又增加了八月李智凱於世大運鞍馬單項奪金的重要片段,於十月正式上映。看過影片的同胞們,自然深知其中一切心路歷程與峰迴路轉。
2020年八月一日晚上,李智凱不負眾望拿下台灣史上第一樁奧運鞍馬單項銀牌時,開始有觀眾敲碗下一個翻滾計畫。(或許導演心中會想:果然是命運的安排……)天意似乎意味著還要繼續拍下去。不管是否會繼續翻滾,片中的主角、掌鏡的導演以及觀影的群眾,大概都有種感覺:這一系列影片談的也是你我的故事。在一個訪談節目的結尾,導演提到:
我覺得這個片子表面上是在記錄這兩個人十五年的糾纏的過程,但是其實,某種程度,大家不覺得其實那也是在記錄你跟我十五年的故事?因為看著他們的故事,你一定不斷地會在反饋自己:那我做了什麼,十五年我有沒有完成自己當初的承諾?那我覺得《男人》這個階段完成,對我來說這個事情最重要,也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看他們的過程,回想我們自己。十五年了,我們做了什麼?那如果還沒做,也不要放棄,因為大家都還在翻滾,其實勝負都未定。(https://youtu.be/CQ1kk8WTg7g)(46:54)
實在太激勵人心了。我立刻找來導演寫的《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該書記錄了導演的成長故事與電影夢。一週夢想迷如我恍然大悟:原來翻滾三部曲的真正主角,除了感人至深的選手與教練,兩代體操選手的夢想(可見《報導者》專文),[2]更有記錄著這一切也同時受到激勵的導演、拍攝團隊、演員,以及沿路上啟發他或受到啟發的各路朋友──包括「種樹的男人」盧銘世、看到電影深受刺激的西門町中輟生、轉職作曲的電玩工程師、從四川鄉下為了音樂夢北漂到北京的小吳、醫學院畢業投入影像圈的好友。當然,還有所有觀影群眾的夢想。

人類學有沒有關於夢想的研究呢?(明顯地話鋒一轉)(其實是因為我希望可以盡責地為各位報導一個行業,但由於還沒約訪,就只能先話鋒一轉了。)
有的,在此舉出幾個相近的關鍵字──人類學有研究想望(aspire)、想像(imagine)、希望(hope)、欲望(desire)、未來性(futurity)、奇思妙想(fantasy)……(謎之聲:到底有什麼是人類學沒研究的?)在我有限的所知之內,在這些圍繞著「想望」、「希望」的關鍵字之中,Miyazaki(2004)、Appadurai(2013)、Crapanzano(2004),以及Henrietta Moore(2011)之間,就存在四種不同的談法,其繼承的知識傳統與所援引的理論依據均有差異。再說,芭樂人類學所談的「夢想」案例還少嗎?比如〈用雙手實踐傳統〉、〈對岸異鄉人/二十歲的夏天〉、〈一個關於空地的夢想〉、〈公共夢想空間〉......如同這篇文章〈危機中的「未來」與日常烏托邦〉所提出的:「夢想大概是今天台灣一個滿重要的的關鍵字,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脈絡下,夢想變成很接近一個人的靈魂本質的表徵」。此言不虛。如同我在這短暫的一週之內,彷彿又聽到了村上春樹所說的「從遙遠的時間、遙遠的空間傳來的微弱大鼓聲」,宛如靈魂的召喚一般。
在上述幾條理論路徑中,今天先談最容易理解的。是關於一個我向來好奇的問題:夢想是不是一種資本?誰比較有夢想的能力,誰比較沒有?是什麼讓人不敢夢想?(或者心中有夢想,卻像是蛋一樣經年累月地孵著,使得夢想成為永遠的「尚未」──尚未被實現的狀態?)
今天暫且先用”aspire”(想望)這個詞來趨近「夢想」。
Appadurai在2004發表,2013又收錄在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想望的能力:文化與肯認〉中提到了「想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aspirations)這個概念,這也和文集的名稱《未來做為一種文化事實》密切相關。Appadurai在該文中表示:想望(aspire)牽涉到欲望(wants)、偏好(preferences)、選擇(choices)、計算(calculations),但這些因素(factors)在學科分工內幾乎都是經濟學的主導領域,在分析上被賦予強烈的個人行動者色彩。人類學在學科分工中,就負責處理朝向過去的「文化」(習俗),以及文化被分派到的社會單位:集體。換言之,儘管Appadurai當然意識到人類學的文化定義極為廣泛,但是在社會科學常識中,「文化」一詞常常被認為具有過去性,如「習慣、風俗、遺產、傳統」,而發展總是指向於未來(如「計畫、希望、目標、目的」等等),一如學院內經濟學與人類學的分工(Appadurai 2013[2004]: 179-180)。而Appadurai試圖打破這個分界。福利經濟學家Amartya Sen將自由、尊嚴、道德上的福祉(well-being)帶入福利政治學及經濟學的核心,強調的是capabilities(也就是著重「人可以成為什麼,人可以是什麼」,重視於人將資源轉化為機會的多樣性)。[3]Appadurai則企圖將文化面向帶入,強調:想望(aspiration)是一種強大的文化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能力,可以對抗將貧者排除在外的險惡經濟處境。想望的能力(capacity to aspire),可以說是Sen所提的capabilities的一體兩面。但由於是與人類學界對話,Appadurai更聚焦於「文化」的未來向度(orientation to the fu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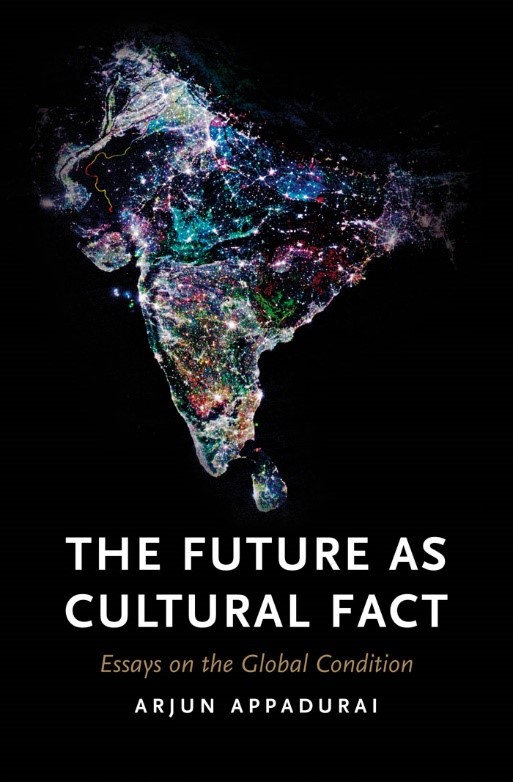
但是這篇文章有一個會令人類學者不安的說法:想望的能力在社會中並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呈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為什麼呢?Appadurai說:因為想望的能力也是一種航行定位的能力(navigational capacity)。權力、尊嚴、物質資源處境愈優渥的人,愈熟悉於各種手段目的之間的關係──在想望和結果之間庫存了豐富的探索、嘗試與收穫經驗。愈貧困的人,因為缺乏機會來練習航行的能力(也因為他們的處境容許更少的實驗,更不容易儲存關於另類未來的多種探索與試誤),想望的邊界(horizon of aspirations)就更脆弱(Appadurai 2013[2004]: 188-189)。[4]如果想望的「地圖」是由層層節點(nodes)和路徑組成,那麼相對貧窮就意味著想望的節點比較少,從具體的欲望、中介的脈絡到一般的規範之間的路徑,也比較稀薄。貧者的確有這些路徑,但是比較僵硬,沒有彈性,策略上比較不可行。這並非因為貧者認知能力不足,而是因為想望的能力,就像任何複雜的文化能力一樣,在實踐、重複、探索、揣摩(conjecture)、拒絕(refutation)之間,茁壯且生存下來。貧窮,意味著相對缺乏此種試誤的機會
我最初看到這一段話的時候,是以自己的田野案例來思考──確實,在我的田野地,西太平洋一個社會階層分明的小島上,我所接觸的人士當中,敢於公開跟決策當局表達對於集體開發案之異見的,都位處於社會中的高階層。階層賦予了他們在公眾場合發言的力量。而我所接觸的中低階層,則都不太願意公開表達意見──我聽過他們表示「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說話」,「在公開場合說話,我感覺好像在傷害自己」。從「敢於表達」、「敢於陳述自己的不同意」到「清楚描述自己的希望」就像是練習說話一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顯然,若依據島嶼的例子,表達「自己想要什麼」的陳述上有著階層的差異。高階層的人可能還不確定自己想要什麼,但是他們敢於公開說出自己不想要什麼。在多次陳述之中,「想要」的藍圖被逼迫著逐漸清晰起來。
但是若回到台灣,顯然並非如此。作為一個常民讀到Appadurai這段陳述,我恐怕會跳起來吧──「這是在告訴我連夢想的能力都不被允許嗎?」而且,常常是環境愈不利,翻身的動力愈大。我始終記得一週夢想迷階段,看到這句話有多麼振奮,簡直想裱框起來:
我為《翻滾吧!阿信》這個故事下了一個標題──「哪怕只有一次機會,我都要用盡全力翻身。」(《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63)
然而,Appadurai這段陳述是否也碰觸到了文化當中的「不可說」?比如,每年的大學入學甄試,就是展現「想望的能力」及其「從手段到目的之間」之實行方式的殘酷舞台。(順道一提,芭樂人類學關於如何協助殘酷舞台不那麼赤裸地反映階級複製,有不少思索,如〈高中生你推甄了沒〉、〈深描自我,或是反思規則?〉、〈鬼滅之刃與你的名字〉。)
儘管如此,我還是同意一點:想望的能力並不是平均分布的。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作夢,但很多人不敢做,或者不敢實行。因此,對我而言有趣的問題反而是:到底是什麼限制了我們的夢想呢?第二個問題就是:究竟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實行夢想的能力呢?
夢想的實行能力並不是平均分布的。在諸多「有夢卻不敢實行」之下有城鄉、性別、年齡、階層、族裔的差別。比如,在我有限的教學經驗中,性別差異會隨著年齡增長,研究所愈高年級的女同學愈害怕自己對文本的陳述是錯誤的,也愈容易將挫折內化,此種傾向常常會發展成謹慎力求不出錯的完美主義,但也常常發展成保守內捲的論述風格。當然,不同的風格有不同的美感。讀者完全可以問:夢想是不是一定飛躍張揚的?在夢想的目的與實現的手段之間,是否有只有著單一的線性軌跡?我在這裡的陳述,是否有將夢想軌道同質化的嫌疑?(「有夢想」是一件好事,「沒有夢想」就顯得可鄙?)這些問題都是該問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很好奇:夢想的分布是不平均的(當然,「平均分布」才是幻想吧),那麼,夢想會沿著何種軌跡來分布呢?是社會學常常舉的的城鄉、性別、年齡、階層、族裔,人類學常常舉的文化,或者大多數人最常說的「個性」?還有,究竟是沒有夢想的問題,還是不敢實行的問題?
小恩說:「你知道嗎?我在這邊學會一個後空翻,比我在教室考一百分還來得高興。」接著,小恩轉頭用手指著我說:「那你呢?你開心嗎?」(《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29)
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你的夢想?這裡面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夢想是什麼的問題,以及如何去達成的問題。兩個問題都非常重要,而且並不是簡單的目的與手段關係而已──常常是:有了實行的能力(比如「說話的能力」),目的才逐漸清晰。自然,也有人是先有目標,然後不斷地精進實現目標的手段。
但無論是對誰,我關心的還是: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你的夢想?
[1] 《翻滾啊!男人,以及喵導》頁191。
[2] 黃銘彰、楊惠君2021/7/23〈林育信、李智凱、黃克強的3個奧運夢──他們翻滾的不只體操、時代,還有自己的人生〉。
[3] 這裡說的能力(capabilities),是一種人達成自己可以做什麼,可以成為什麼的實質自由。
[4]這不是說貧者就不能夠許願(wish)、欲望(want)、需要(need)、規劃(plan)、想望(aspire)。但是貧困的一部分,就是練習(在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路徑)的機會相對缺乏(Appadurai 2013[2004]: 189)。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bricoleur 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83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寫的有夠難讀,不有趣
我覺得點出了很棒的討論議題,關於「敢不敢夢」。
田野中,或是作業放談家中長者的經驗,我們常問:「有沒有有什麼夢想?想做什麼?」他們聽到問題常愣住,對於「夢想」一詞感到尷尬,甚至覺得這是個奇怪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也就是「自我」與「世界」建立在怎樣關係的問題,你/妳勢必要在這個關係中才能活,而這個關係也會要你/妳活不了。
夢想的分布從來不平均,但有沒有可能,並非貧者相對缺乏夢想的能力與機會(預設了一個同樣的夢想路徑),而是貧者擁有不同的夢想?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