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未來」與日常烏托邦
在大學教書常會感受到學生的焦慮與困惑。期末時節,批改學生報告是一種耗費心神的責任,但有時候也是一種privilege,報告好像是一種學生寫給老師的私人信件一樣,總會看到許多「肺腑之言」,學生會藉此隱晦的表達他們對人生與未來的不安與困惑,困惑比較多的是關於未來的方向與生命的「意義」,雖說學人文社會科學本身就是一個處理意義的學科,但也讓他們反覆自我詰問,到底「意義」在被賦予的同時,是否也代表著「意義」的喪失呢?被教導的反抗是不是也是一種順服呢?上了許許多多的課好像覺知了過去,但又好像更加困惑於未來。雖然這種不安常常寫的很輕,是帶著笑意的,可以藏在年輕擺擺頭就輕易甩掉的姿態當中,也好像不好意思給老師添麻煩般的不想透露太多,但終歸能讀出是不安。即使覺得人類學非常有趣,也猶豫著要不要繼續唸書,他們眼見年輕的老師在學術場域中的掙扎與辛苦,這種生活似乎使他們卻步多於鼓舞。他们對未來有許多想像,對於理想也能侃侃而談,但問題在於想要的生活跟現實狀況似乎不能合拍,好像持續陷入一種「有夢,卻找不到路」的窘境。未來、希望、絕望、(設法處理)不確定,這些字眼大概可以用來形容很大一部份大學生的心情。當今他们所面對的社會,改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到底怎樣改變,該怎麼改變,似乎都還是在問號中。
「有夢,卻找不到路」也不是這些學生所獨有的處境,在完全不一樣的脈絡中(階級、教育程度、社會脈絡都有差異)的其他年輕人身上,例如我所研究的青年農民工,也可以觀察到一樣的狀況。人生該如何開展在今天已經完全被「去標準化」,每個人總是要負起責任,自己去找到自己的未來(而不像前一個時代,「x歲前要五子登科」或「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某種普遍的被「標準化的未來」)。這很像很孤單,但其實也不,反映了某種時代的、普遍的、無聲無息的瀰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必然。「不確定」(uncertainty)與「不穩定性」(precarity)再加上insecurity 大概是晚近人類學相當熱門的關鍵字。以前堅不可摧需要拋頭顱灑熱血才能換來的制度改變,在今天似乎是一切都在有形無形或快或慢的崩毀當中,當世界如果不需要革命就正在快速朝向轉變甚至崩毀,那「我們」(不只是學者、研究者,還包括每個要應付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該如何想像跟面對未來?
人類學家與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紛紛注意到了未來的不確定性已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試圖用各自的問題意識、理論框架與方法系統性的去捕捉與描述,找到分析的角度及評估其後果。「未來」既然變成社會概念,那「時間」當然要被重新檢視。人類學家Laura Bear特別指出我們應該更加關注「全球化的時間面向」,主張全球化除了是一種尺度的政治學之外(什麼尺度可以獲得「全球」的稱號),也是一種時間的政治學,全球化是一個「未來」的角力場。「未來」(future)是全球化的一個關鍵字。在全球化下,「時間」等同於「新自由主義時間」,展現時空壓縮的特點,凸顯了「速度文化」,以及「不確定性文化」 ,未來被描述為是特別有問題的:不確定、不存在或是一個懷舊的場域。也就是說,「未來」不再是「現代性」下的樂觀進步,也不再沿著時間自然開展,「未來」成為不確定、甚至衝突的場域:抽象時間與多重的社會時間的衝突、矛盾越發劇烈。Laura Bear呼籲我們注意到若僅強調新型態的、單一的全球時間/新自由主義時間是有問題的,「現代社會時間」需要被進一步探究,我們必須去問:人類學的研究要如何超越這樣的侷限,才能更精準的捕捉當代各種形式的「社會時間」所形成的社會現實(也就是她所謂的「時景」)?多重時間帶來的衝突會如何發生?在何處發生?主宰的時間是什麼?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試圖駕馭多重社會時間的技藝又是什麼?
各個社會如何面對不確定性,顯然也深受其歷史「文化」影響。例如,英國正在面臨脫歐後的不確定,走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時,可以想像英國人會以他们酷愛嘲諷跟崇尚歷史的態度來面對,BBC就做了一個「扯蛋英國史」的仿紀錄片節目,開宗明義說「今日我們收回了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是什麼?我們是誰?又為了什麼?探索英國何去何從最好的方式,是回過頭去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煞有介事的旁白,訪問各種專家學者,彷如一部紀錄片,但主持人又亂入各種無俚頭的問題。法國女星Mélanie Laurent偕同其演藝圈友人拍攝「明日進行曲」紀錄片,走訪世界各地,去拍攝正在替農業(食物)、能源、經濟、民主和教育建構另一種模式的地方小團體,試圖用藝術行動來喚起思考改變世界(類似的還有「最酷的旅伴」(FACES PLACES))。而許多對於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研究,也都一再地證實了變遷引向的「未來」會深受在地歷史文化脈絡的影響,在「不確定性」中,熟悉的東西最容易被拿出來作為策略,能被掌握的也最容易被保留,那些在變遷與不確定發生之前「潛伏」在最底層的、逐漸被淡忘與逝去的「文化」,又再度以新的樣態浮出台面,「新傳統主義」、「韌性」等等的概念都是在描述這種深受過去影響的未來。不管這現象反應的是暫時性的「策略」或是難以撼動的「意義體系」,都帶領我們繼續思考,在快速變遷的政治經濟脈絡中,文化與意義系統如何繼續貫穿在今日當中,而倒底什麼會會隨政治經濟脈絡的改變而改變,而又什麼不會變?為什麼?
眾聲喧嘩的「未來」除了考慮文化因素之外,更可以關注它如何成為政治角力場,「權力」的因素在其中如何運作。「未來的政治性」成為很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未來」誰說了算?誰去勾勒「未來」?未來是誰的美好?誰能在「未來」裡面扮演一個角色,誰又會被排除?「未來」不再是日記裡書寫的個人夢想,不再僅僅只是小女孩對著星空許願的虔誠,這些夢想都將在權力角逐加工操弄勾勒出的未來框架之下去找到實踐之路。如果個體對這個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未來沒有一點意識,遑論理解與掌握,那也難怪會「有夢,卻找不到路」。
談到未來的政治性,國家的角色自然不能忽略。一方面,國家與官僚體系在不穩定、結構的失能崩潰中著試圖去提出能夠彌補斷裂的計畫。不同地方的民族誌研究也指出,國家在推行這些計畫時,通常會嘗試以年輕人「希望、美好、未來的主人翁」的形象,來為出台的計畫代言,使這些計畫的圖像能與「有希望的未來」沾上邊。另方面,國家與官僚體系也提供各種補助,讓未來變成一個個的計畫報告書,透過一個個的官僚機制中的委員會為「未來」評等優劣好壞,讓權力的運作遮掩在看似獎勵創新、創意的補助機制當中。我們今日危機中的「未來」也靠著大量的補助來支撐,補助沒了,未來似乎也沒有了。
但此時此刻,除了國家之外,我們看到更多商業巨頭在引領我們的未來。例如以往都是由知識份子來發動倡議的鄉村教育改革,現在已經由商業鉅子馬雲來主導。馬雲已經成為「鄉村教師代言人」,成為農村教育改革的一個行動者,他在2015年起設置了「鄉村教師獎」,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及六家媒體合作,評優秀鄉村教師,讓得獎老師走上紅毯,變成明星,並給予金錢獎勵。除了給予資源之外,他也下鄉與教師交流,發動各種學習培訓計畫,試圖把他理想中的教育遠景給傳播出去。例如他就邀中國企業家一起探討教育議題,並倡議推動鄉村寄宿學校。企業也常成為是公益活動中的一大行動者,「企業社會責任」讓企業展現出其整合社會與環境的關懷,投入大筆資金資助小農、幫助當地人成家、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協助完成國家啟動的發展計畫,CSR可說是企業給地方的禮物,但人類學家都知道沒有免費的禮物,企業不但把這些都用巨幅廣告轉換成企業「形象」一再宣傳,人類學家更擔心CSR在挑戰傳統企業與政府的分工之際,是否新的社會契約還未形成,足以支撐起結構上的轉換,底層人民可能會在此過程中被擠壓到企業與政府都不企及的真空地帶。
此外,還有無數多的「夢想」。夢想大概是今天台灣一個滿重要的的關鍵字,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脈絡下,夢想變成很接近一個人的靈魂本質的表徵,能說出一個讓人驚艷的夢想就像一張名片一樣,馬上可以在人群當中確立自己的個體性與獨特性,或是可以在各種申請面試那短短的十分鐘之內鎮攝住那些個前一天晚上看了x十份申請書正困擾著如何分辨眼前這些申請者的口試委員。在這個世代整個社會化的過程中,總是有一次次的通過儀式,告訴我們要準備好要隨時告訴別人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一直試圖理解「夢想」這個曾經好像非常個人寫在日記裡小心收藏暗中發誓的概念的轉型,以及其與整個社會「未來」發展之間的關連性。某種程度來說,夢想好像變成時代趨勢,好像變的很政治正確,也越來從私人走向公共。google一下,一直到今天還有各種「築夢計畫」,有公部門舉辦的如內政部移民署的「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教育部「學海築夢」、農委會「農村再生青年回鄉築夢計畫」,也有私人企業舉辦的如「「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若把得獎的名單與計畫全部蒐集起來,做一個研究,大概會是一個有意思的計畫。這些計畫號召也都提出頗激勵人心的口號,如Johnnie walker前五屆的夢想計畫的口號分別是「夢想起飛 成就不凡」、「創意夢想走自己的路」、「小夢想大力量」、「堅持夢想開創未來」、「I have a dream」,據說該團隊制訂這些標語都是有仔細考量當年的社會脈絡,觀察當下的社會趨勢,再決定什麼樣的口號可以號召最多的夢想者參與。
這讓人忍不住想問,把夢想什麼時候變成計畫書了?把夢想給計畫化(projectization)又是一個怎樣的運作機制?這會改變夢想的本質,並淘空夢想徒剩計畫嗎?從他人之手領到「圓夢獎金」,究竟是要來逐誰的夢?夢想作為一整個補助事業,正在「建置化」、「機構化」嗎?夢想正在商業化嗎?這種商業化跟所謂的企業的公益形象與社會責任之間可以直接連結嗎?作為一個有夢想的年輕人把夢想兜售求善價這是沒問題的嗎?企業、公部門又想從這些「夢想」當中得到什麼?這是一種好聽一點的市場行銷術跟政治治理術嗎?當公共之手越來越伸入夢想之中,給予各個夢想排序分等給予獎勵,夢想有了好壞之分、有了高下之別,作夢的人要做好夢,評分的人更困擾,要用很難說的清楚的標準去評出「好的」夢想。當我們說我們有「夢想」時,是否也正在會用這些標準來自我規訓?夢想是否因此分裂成私人的夢想與公共的夢想兩個領域,私人的更走入幽暗之處,公共的則變成公開表演?
當我們學會內化「夢想」的重要性時,也在內化評判夢想好壞的標準嗎?這種看似鼓勵個體化、創意的發夢變成集體的行動與趨勢之後,是否其本質就整個變了呢?像我的小時候還不太流行夢想這一詞,比較流行「志願」,在學校裡被老師要求寫「我的志願」時,就會發現有些志願,它原來就不能算是志願,像夏曼藍波安的想要航海就被老師認為不是個志願。現在是不是有些夢想也不知道是不是夢想?比方說想要集體裸體是不是比起想要發行自己的貨幣更不能算是個夢想?這種透過「夢想」為名,把個人想像的「未來」文字化後評比篩選,留下符合權力擁有者想要的「未來」的整個過程,就活脫脫是一個「未來角力場」。
話說回來,人類學家最擅長挖掘的還是日常生活。關注日常生活的人類學家,除了國家、菁英與掌權者之外,自然還會注意到在「未來」的角力場上,一般人如何感知、經驗、因應,去挖掘他们的行動所具備的任何可能的能動性。許多民族誌的資料不約而同指出,在未來不確定、不存在或是崩毀的狀態中,一般人通常也不會坐以待斃。他们既沒有等待超人拯救,也沒有寄望救世主降臨,即使在最糟糕最邊緣的處境下,一般人還是會在日常生活中找出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自救」、「自助」,好讓日子可以繼續過下去。在研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時,「自助」(self-helping)比起「革命」(revolution)可能是更重要的分析概念。一般人在面對不確定、結構失能時,自助比革命更貼近真實。
人類學家長期累積的「親屬研究」的根基帶我們更容易去看到處於結構劣勢中的人群的「自助行動」常常很大程度的依靠親屬網路,透過非正式的人際網絡來度過難關。不友善的制度之外,人們嘗試與人建立起互惠關係網絡,並透過文化邏輯作為基礎,擴展延伸這樣的網絡。透過這網絡,在結構邊緣或結構之下去「流通」信任感、資源、機會、訊息,達成合作互助,以此來反制正式結構對於他们的壓迫。
但不能不去問的是,這種「自助」行為到底是一種對於結構的妥協,還是具政治力的能動,這似乎很難下定論。「自助」行動往往沒有論述或意識形態的支持,更多是透過實踐的、情感的互動與交換來建立。這種自助是想要讓日子過下去,過的更好,而沒有想要檢討、推翻整個結構。這些「自助」行動通常發生在結構的縫隙當中,具有高度非正式性、個別性,是瑣碎的、突發的、隱微不見的、即興的。自助行動對壓迫他的結構通常不會是高調抗爭,遑論革命,更多是表面順從、暗中顛覆。在分析上,要如何評斷「自助」行為到底有沒有政治性呢?如果是取決於其對於結構能不能造成翻轉的能力的話,我們該說這種「自助行動」僅僅只是一種妥協,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嗎?那其暗中顛覆、暗中鬆動結構的力量又要如何解釋呢?
在此,或許Davina Cooper所使用的「日常烏托邦」的概念可以幫助人類學家去思考日常生活這類瑣碎的、低調的、即興的、隱微的、看似妥協甚至與再生產結構僅有一線之隔的「自助」行動的政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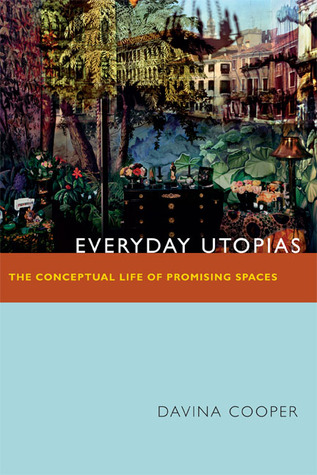
在進到「日常烏托邦」的概念之前,我們先談談烏托邦的概念。許多思想家如Hayek、Karl Popper、Hannah Arendt、Isaiah Berlin都曾經「反烏托邦」,對於他们而言,烏托邦有著本質上的暴力傾向,會帶來獨裁。烏托邦意味著強迫性的理想主義,要全部的人都轉換、丟棄本來的人性,按照構思出來的理想藍圖來生活。人類需求與慾望總是相互矛盾的,同時渴望不能相容的慾望可能就是人性,因此和諧永遠無法企及。烏托邦想要改變無可改變的人性,這種不顧真實社會的複雜性,強加靜態的、理想的、和諧的整體在所有人之上,是一種自大。想要打破這種恆長存在的人類需求的矛盾性,去建立和諧、理想、完美的烏托邦的意圖,本身就是暴力。
Cooper 提出了「日常烏托邦」(everyday utopia)的概念,想要以此概念來指認那些除了激進的、整體的、夢幻的烏托邦實踐之外,另一種烏托邦形式。這種烏托邦是人們努力在日常生活中積極的「活出」或「實現」出的烏托邦願景。「日常」(everyday) 一詞是強調這些烏托邦的實踐者仍然把自己的生活持續「鑲嵌」在主流社會或其他社會機制當中。
雖然Cooper是一位法學家(但根據我與她在研討會之後的談話中,她有提到她不知道為何她當初沒有讀人類學,她覺得人類學家跟她關心的議題更接近一些),但她提出來的這種「鑲嵌式」的、日常生活的、紮根在脈絡中的烏托邦實踐,和人類學家向來有興趣的議題非常接近。我甚至想說,人類學研究的長項與人類學方法論的特點,恰好讓我們可以在未來正處於危機的情況下,好好去關注Cooper提出的這種「日常烏托邦」。這種「日常烏托邦」可能規模很小、不全面、也不太有說服力,只是在亂世中創造一方安身立命的小角落而已,但Cooper肯定了這些行動的重要性,以及其在政治上的潛能。她認為這些行動都是在「重新概念化」當今流通的概念,當這些重新概念化後的概念開始流通之後,可能就可以帶來鬆動現有結構的可能性。
Cooper在這裡對於概念和實踐也做出了新的辯證,她認為概念不需要在行動之前,強調不可言說的經驗的重要性,概念會在這些不可言說的經驗當中得到新的理解。因此Cooper提出了「玩」的概念,就算我們只是「假裝」在另一個世界,就算我們做的這些在別人看來只是在「玩」,那又如何?我們仍然在這過程中,實現了另類可能性,道出另一種存在的狀態。
相對於Cooper的play,人類學家更容易看到get by而忽略play。人類學的訓練讓人類學家家自然看到親屬、宗教的重要性,這些傳統上有別於國家的組織人群的機制,會生出與正式結構對抗的能動性,即使在高度的現代化、個體化的社會中,這些機制也依然存在並發揮功能,讓人們的日子可以過下去(get by)。我把這種研究傾向稱為「get by」的研究傾向。這種get by的研究取向,相較於play顯的有些被動,或許可以與Cooper在「日常烏托邦」中強調的play的研究取向做個相互參照,而讓我們的研究取向能更有主動性。或許我們人類學家可以想想,as if的表演在這些底層人群中發生的可能性,想一想play如何被鑲嵌在社會生活中。在這些親屬、宗教等傳統團結人群的機制中,是否也可能有著一方沃土,正孕育具個人能動性的、玩轉的「日常生活中的翻轉」,能帶來重新概念化的可能性、超越僅僅只是想要get by的掙扎?若有的話,或許我們就看到一個有別於國家制訂的、有別於計畫推動的、非常草根的、本土的、脈絡中的、鑲嵌的、在地觀點的、非僅只是承襲於過往的「危機中的未來」。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方怡潔 危機中的「未來」與日常烏托邦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8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作者后半部分思考的也是我在思考的。什么样的能动性才叫政治的能动性呢?或许可以将政治的定义放大,过好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如果从最早的政治哲学去看的话)。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