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拉回到20世紀末的一個春末夏初的日子,我還依稀記得在我申請推徵人類系研究所碩士班的面試考試時,面對看著我的研究方向不以為然的老考官問道:「妳為什麼不去考舞蹈研究所?」,我心底油然而生地反問:「人類學不能研究舞蹈嗎?」(不過當時我很睿智地沒有讓這個問題脫口而出)。等到了英國唸博士班時,台灣留學生聚會時,每逢有人問起我的研究領域時,我就直說「舞蹈人類學」,身旁的學友想一想簡潔地回一句:我唸的就是人類學,又反倒讓我的自我標籤顯得邊緣。儘管我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舞蹈或藝術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然而一直以來,學科的邊界和內涵的定位問題催逼著我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跨域蜿蜒前進,直至落腳在一所以藝術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

文化一直都是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所有問題的初衷和答案,那藝術呢?人類學家Raymond Firth 回顧藝術(art)一詞的內涵時提到,在希臘化時期,藝術一詞的內涵就是技術,藝術達人是一群與公共社會緊密連結的技術人才(想想那些用在神廟、廳堂的自然主義石雕、以及陶瓶)。在那以後,不論是基督教時代的歐洲、或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都仍然有意識地為社會重大工程或革新效勞。藝術成為狹義的fine art、藝術家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理念,其實是相對晚近且單一地生成於現代、或更精確地說十八世紀的歐洲,源自人文主義高漲後自我主體性確定之必要:the artist as the creator,而美感判斷也被定義成一種(專殊化)理性的實踐。
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麼儘管人類學者針對美感或藝術是否能作為跨文化研究的範疇有不同的看法,但卻不約而同地在各自的研究中嘗試質疑、挑戰或掙脫西方世界制度性的藝術定義。這樣的取向遵循了人類學長久以來慣常地去除族群中心主義、甚至進行自我文化批判的風格。而根據人類學家Daniel Miller 的說法,藝術是在現代化社會零碎化(fragmentation)後探求不可復得的整全(totality),當代的台灣,其實很清楚地顯現零碎化的現代社會特質,人類學、特別是針對藝術所開展的興趣、研究和知識成果,是否如Miller所言,不僅僅是為藝術而藝術,而可以是一種攪動的提醒?

回到台灣後、成為大學教師的十二年來,我面對的學生或群眾並非單一屬性的群體,而是具有不同專業能力、需要不同教育input的多樣化群體,也算是一小群的「大眾」,有鑒於自己曾經不知所屬的經驗,我試圖在使用不同語言、以不同觀點看世界的大眾之間,製造彼此需要的好奇和興趣,而我使用的策略,不外是人類學傳統的比較文化和社會整合意識。呼應郭佩宜在引言中提到的,我的跨域實踐反映了一種個人在人類學定位中的游移與出入,這個歷程說明了或許在大眾人類學的形成以先,人類學者於內必須先確立一種個人人類學(personal anthropology),一種深入關懷對象特殊性的精確視域;於外則需要擴散人類學精神到閱聽大眾,不論所謂的「大眾」是否可用具體的數字計量。前者我透過過去十幾年的教學落實;後者則是在大學外的跨域書寫/轉譯過程中實驗。
「……除非他能夠掌握藝術辨識的『是』,而且將之『組構』成一件藝術品,如果他無法達成這種境界,他就永遠無法欣賞藝術品。……將某物視為藝術,需要某種雙眼無法詆毀的特質,及藝術理論的氛圍、藝術史的知識,也就是藝術世界。」(Arthur Danton,〈藝術即理論〉,頁15-16)
上述Danto對藝術即理論(詮釋)的宣示,其實說明了人類學所提供的詮釋性理論之所以可以在藝術教育科系中佔一席之地的因素。對於理論的渴求或許反映了不同的藝術類別如何建構具體的語言以談論一個「本身不說話的實在」。我十多年的教學經驗面對的多半是非人類學本科系的學生,在不焦急於鞏固人類學疆域的實踐過程中,我觀察到學生對於人類學的嚮往有如對一個略帶神祕感佳人的遠觀,人類學提供了一個藉由他者的藝術理論探求所投射出的理想知識鏡像:在一個仍以西方劇場舞蹈為主流的科系中,人類學的反照價值大於實用價值。

我所參與的第二個實踐場域,則是透過跨文化展演的報導性書寫,也就是召集人引言中的不同的敘說文類,藉助某種既定的舞台,將劇場中作品的意義,進行文化轉譯。11月3、4日的芭樂三週年紀念文說明了箇中原委、也提供了例子。我的書寫或許可以呼應人類學家葛茲關於藝術的技術性言談:「其他言談……的字彙與概念導源自與有關的文化事物,藝術或能效勞、或能反映、或能挑戰、或能描述,但非其本身所創造,這些言談將這些詞彙概念匯聚於藝術的四周,從而將藝術品所蘊含的特殊力量連結到人類經驗的恆常動態。」
以我參與當代劇場舞作之文化書寫或轉譯的經驗,雖然涉及的群眾始終很有限,但是可以感受到文化的視點提供了一種互相理解的語言,讓觀眾可以等同身受地探詢創作者組織意念的型態、進而深入地思考舞作的意義,而不會被舞台上立即顯示的專殊化媒介所引發的感知帶入純然抽象或孤立的經驗。我認為並且試圖說服大眾的是,具有人類學精神的欣賞觀點,激發的是理解舞台上的民族誌客體後,成就與主體之間的深刻對話和反思,讓當下的感知和持續的反芻交疊,可以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於耳的同時,餘思滿盈三日不絕於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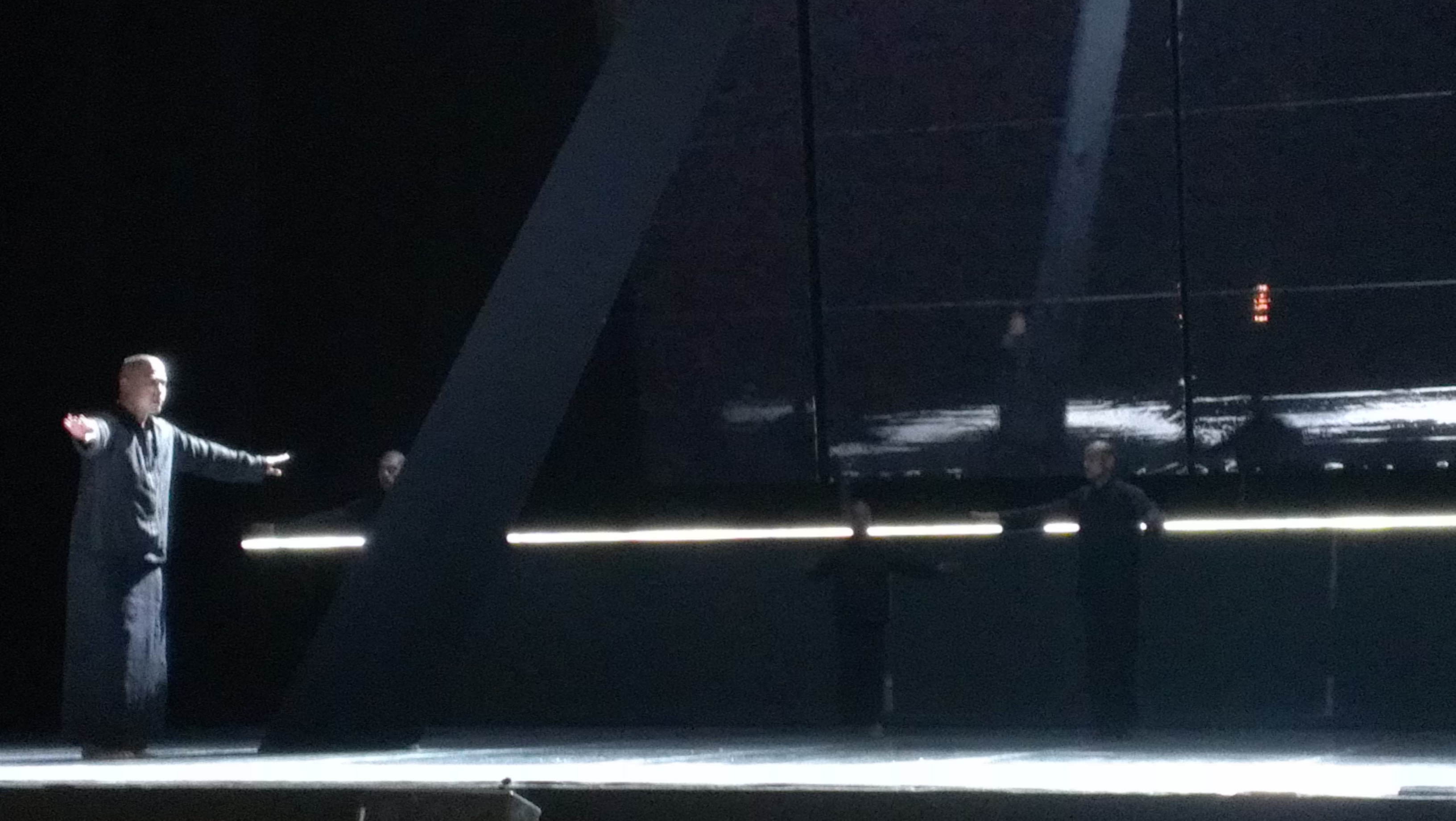
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因為崇尚物質和世俗化、功利化的趨勢,不論是文化或藝術都相對地邊緣化,更別提把這兩者分門別類或階層化背後反映的社會機械觀。人類學研究帶我們到他者的世界繞了一圈後,我們究竟是經歷啟示般地豁然開朗、還是遁逃到更深、更遠的他界?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青原惟信禪師語,典出宋朝釋普濟撰《五燈會元》卷十七)
不能說已經開悟,不過我至今的「修道」過程中,藝術是山、文化是水,依山傍水一路走來,入眼盡是奇景。人類學知識於我有如一位佳人,或轉身面山、或迴身向水,在在映襯出不同的人性景觀。我衷心期盼,這條求道之路,能有更多「大眾」同行,如此佳人才不孤獨。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綺芳 雙面佳人:人類學知識的實踐複象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3645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