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有關「發展」的漁村故事
今天的芭樂人類學,我想要和讀者分享的是我在「文化與發展」這門課教材裡的兩個漁村故事,一個是遠在巴西的阿倫貝皮(Arembepe),另一個則是位於台北關渡平原的下八仙聚落。
遠逝的天堂(assault on paradise):從帆船到機動船(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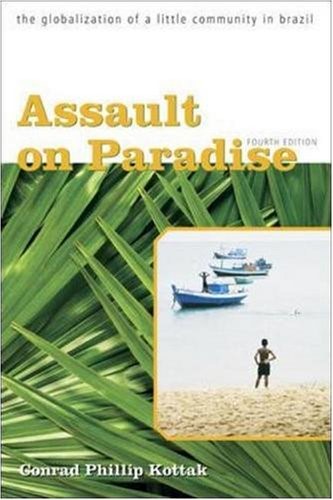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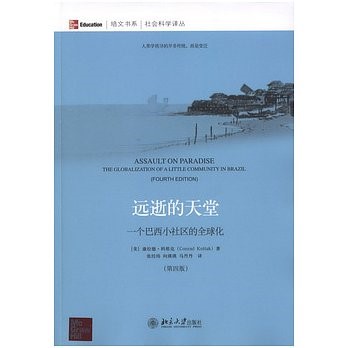
1962夏天,當時還是紐約哥倫比亞學院大學生的Conard Kottak(著名的文化人類學教科書作者)參加了Marvin Harris帶領的田野調查隊,從巴西巴伊亞州首府薩爾瓦多坐了三個小時的吉普車,長途跋涉,顛顛頗頗地來到阿倫貝皮--這個座落於海洋與瀉湖之間的小漁村。
這是一個貧窮的小村落,土地生產力很低,只適合種椰子樹,椰子全年給整個村只帶來5000美元收入;捕魚量也受技術落後所限,當地人使用依賴風力的帆船用魚鉤釣線捕魚(hook-line fishing);此外,當地教育水準低,三分之一成年人不會讀寫,剩下的人勉強會寫自己名字,並且面臨著糟糕的公共衛生,以及較高的嬰兒死亡率。
然而,這樣的阿倫貝皮卻是Kottak心目中的世外桃源,除了優美的自然風光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擁有巴西其他地區之「典型」漁村沒有的經濟自由,與平等的社會結構。上天賜給阿倫貝皮靠近海岸可以捕獲60-360米深各種魚類的的大陸坡(the continental slope,大陸架邊緣處陡降到深海的區域),他們在海上想補多少魚就補多少,沒有人壓價收購,所有魚貨都可在市場上公開販售。這裡的男子74%都從事漁業,擁有開放的經濟等級,只要有志向、工作努力,有卓越的頭腦,很容易從底層爬向高層。
每艘船平均只有四個船員,每天捕魚結束,船主拿走當天漁市銷量25%,剩下由船員平分。船員之間的主要區別是船長和普通船員。船長對船可以全權所有、合夥或受雇。雖然買一條裝備齊全的新船,差不多相當一個普通漁民的全年收入,但買一艘船的錢可以通過在外地從事商業捕魚,也可以給人當一兩年船長,靠合夥的分成購得。

1960年代初期的魚價增長,讓船長買船能力逐漸增長。一艘船在1962年相當於800公斤魚的售價,到了1965年時只需400公斤魚的售價,於是大多數船長逐漸退出與他人的合作關係,以致不捕魚的船主們只能吸引不靠譜的船長和船員,收入自然有限。在這個年代,漁船的價值並不體現在商品,而是體現在充滿熱情的船長和船員之生產方式上。
如此只要努力就可獲致成功的開放經濟,使得阿倫貝皮內部雖然有明顯財富的差別,村民卻堅持:「我們這裡都是平等的。」因著這樣的自信與不斷進取的性格,雖然村人在巴西大社會的「經濟」標準裡屬於下層階級,但面對外人時始終腰桿挺直,無論地主或批發商,進入阿倫貝皮都必須將自身嵌入當地的社會體系之中才能獲得他們想要的。
1964年巴西政變推翻民選總統後,軍政府集中規劃的經濟作法,創造了巴西國民生產總值在1968到1974年間年均增長11%的經濟奇蹟,阿倫貝皮與大城市毗鄰,比其他偏遠地區更早體驗到奇蹟的影響,其中最具體的就是1970年鋪設好的連接阿倫貝皮附近巴西鈦業到薩爾瓦多的公路。
1973年Kottak回到阿倫貝皮,被外來嬉皮、觀光客與污染所帶來的影響所震驚。捕魚仍是當地最普遍的職業,但漁民人口百分比從74%降到53%,其中最關鍵的改變因子是機動船的引入。1960年代,捕魚業最昂貴的物品是值150美元的帆船,1973年,買一艘裝備齊全的汽艇要1700美元,相應的還有汽油、燃料和維修費。過去有志向的漁民皆可透過努力成為船主的常識已經成為神話。

有地產的商人率先買了汽艇,再來則是原先已位居當地經濟高層的船長兼船主們,他們透過漁民合作社低利貸款加裝機動馬達或購船。合作社引進的另一個新設施是讓漁民可以隨時捕魚、隨時冷藏的冰庫。機動化與冰庫相結合,促進了遠距離捕魚,這些「進步」的經濟條件,不僅轉變了原有的漁業模式,同時也造成了魚類收益分配和生產關係的改變。漁船中的社會關係,變得越來越非伙伴,而像是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係。
1980年Kottak再度回到阿倫貝皮時,過去沒有階級的社區,已經出現社會階層,窮人愈窮、富人愈富,而變化最明顯的莫過於漁業。1980年阿倫貝皮男子中只剩下40%從事漁業,船隊規模縮小(1965時31艘,1973時26艘,1980時19艘)、漁船體積變大。十九艘船中除了一艘老式帆船加小馬達,餘為封閉式機動船,有更大的馬達、船載冷藏庫,以及封閉式船艙,價值至少5000美元。
過去,魚是直接擺在海灘上(公共領域),由漁民和船主分配,現在則是直接運到魚舖,放在水泥地上(私人空間)。隨著漁船在不同時間往返,1960年代的日常公共儀式消失了,村民不再在漁船傍晚返航時聚到海灘問候,看著漁民卸貨,討論要賣多少,多少給家人,多少留給邊上貧困的圍觀者。
隨著資本變為維繫成功的重要因素,新漁業模式強調一系列地面活動的投入,因此,最成功的船主成為真正的資本家,不再兼任船長;漁民不再是獨立生產者而是雇工,他們厭惡船長和船主,彼此之間缺乏信任,加上長距離捕魚時不佳的生活條件和風險,越來越多阿倫貝皮人放棄漁業尋找其他工作,留下的空缺,由外來可接受低工資的移民遞補。當地的漁業,已經失去了由風力、當地自產、低消費需求和產品直接消費組成的生產自主性,整個捕魚方式現在都依賴外界供給,如冰塊(從薩爾瓦多來的運冰車)、做為魚餌的小蝦(聖保羅)等,當地撒網行家和漁網織匠的手藝漸漸失傳,沒有年輕人繼承。

阿倫貝皮1973到1980年間的歷史,是巴西同時期普遍發展的地方版本,人們幸運地在經濟奇蹟甫一出現時便享受了繁榮的恩澤。然而,阿倫貝皮乃至整個巴西最窮困的人們,在實際收益增加了幾年後才突然發現,自己在很多地方都要比奇蹟發生前糟糕。1980年普通漁民出售的魚(500公斤)比1965年(600公斤)還少,船長的份額卻增長了八倍。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河口人(Fishermen in city):當百年漁村遇上驕傲都市(註2)
有一個村子,在岸上就看得見台北101,順著潮水就能直通台灣海峽。河海交會的先天條件,滋養了這個百年漁村,但城市與海洋間的矛盾位置,讓河口人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文明造就了城市光鮮的樣貌,卻混淆了河口人對河流的想像,阿公回味著爽口的赤翅仔,爸爸則對烏魚的油味作噁,而孫子卻想把檢來的死魚放生….
聽完遠方機動船帶來的發展變遷,讓我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看看另一個漁村的故事。我想絕大部分的台北人一定和看過《河口人》這部紀錄片之前的我一樣,不知道在台北市裡居然有漁村和漁民,因為他們不會被顯現在繁榮、絢麗的台北圖像當中,但卻是承受了巨大發展代價的一群人。

下八仙聚落位於基隆河末端,與社子島隔著基隆河相望,距離淡水河口只需要五分鐘,河海交會淡鹹各半的水質,有著豐富的漁業資源,加上漁村位於基隆河岸與淡水河交會處,水中浮游生物眾多,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在台北尚未工業化之前,漁民們稱家門前的淡水河為「活寶」。
片中出生於1959年的漁民陳萬益描述小時候的光景時,眼中亮著光芒:
「以前下面那邊, 我們這廟下去差不多150公尺,我們叫深窟仔,潮間帶,以前都是沙地,它陷一個凹,魚蝦貝類很多,真的是很多,不用挖,用撿的就可以。以前我們買菜的那種袋子,提那種袋子下去,差不多半個小時,一袋滿滿的,螃蟹大隻的,從大隻的開始,下去看到都撿,撿到最後就是選大隻的,裡面小隻的就丟了,一直換大隻的,換到最後都提不回來……。」
隨著台北市工商業化,以及升格為院轄市後,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污染,透過河川來到漁人眼前,從前優越的地理位置,如今反而成為下八仙的致命傷。淡水河匯集了大漢溪與新店溪,在關渡與基隆河交會,可以說北部五縣市的廢水,全部來到漁人的家門口。

農曆三月以後,是下八仙漁民撈捕野生文蛤的時節,十多年前,一天最多可抓到兩百多公斤,一個月收入最多可達五、六十萬。而片中,漁民陳萬生從網中一邊撿拾數量少又黑漆漆的文蛤,一邊對導演解釋工業廢水對文蛤的影響:
「若死的原因,就是壞水、被土蓋過去、三月南風動,這三項文蛤才會死……壞水排出來都是鍍錏的硫酸水, 嚴重到沒話講,持續多天就會死,如果說排出來一天,一天就沒了,裡面的潮水會洗啊,那文蛤會鑽下去,所以它不會死,但多天就會死。」
在淡水河污染整治計畫先期工程中,距離下八仙最近的污水處理工程是獅子頭污水處理站,負責將台北市五十萬噸以及台北縣四十萬噸污水先集中,輸送到八里,經處理後再放流到外海。民國九十三年七月的某一天,一場陣雨落雷造成獅子頭污水站抽水機跳電故障,大台北污水處理被迫停擺,台北縣五個截流站也暫停運作,直接將三十八萬噸未經處理的污水排入河川中。
獅子頭污水處理站為台北市管轄,但又位於台北縣境內,共同處理台北縣、市污水,上述污水外洩事件後,縣市政府互踢皮球,不願意承擔責任歸屬。陳萬生無奈地說:
「台北市的屎水排下來,文蛤死,每樣都死。去跟馬英九抗議,剛好馬英九出國,他們的副秘書出來講,一台船要賠三萬,賠到最後也沒了。」
每年九至十月,則是烏魚迴遊入至淡水一帶,並進入淡水河口上溯至台北橋一帶,這時正是烏魚產卵的時期,漁民會捕撈並取其烏魚子,但同樣難逃污染的命運:
「烏仔魚、豆仔魚,那都是壞魚,土味很重,沒人要吃,主要是牠有個土味……人家不知道說是土味,我們說是油味,牠有一層油,因為那油,以前作工程,他們把重機器換油的時候就直接排下來,油沒辦法啊,油沾到,沾到東西就卡住了。烏魚又是底棲魚,吃土的,所以說油味很重。我們這種牛屎烏魚,差不多七成有味道,魚你若把卵起起來曬乾,十串有七串吃有油味…。」

然而,下八仙的漁民們要承受的不只是非他們所造成的污染,以及政府的卸責,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片中主角陳萬生形容為「一條牛剝三層皮」的疏濬工程:
「把河清深一點,它的目的是這樣,結果它那些土都沒載走,它那些土,就是淺的挖去填深的,深的土倒下去,又都流走了沒有效……上游倒下去,流到下游一些文蛤都悶死………」
「你看現在打沙樁這邊,難道沒有問題嗎?這一定合法掩護非法嘛,你說疏濬,我從來沒有看過拖一台廢土出去,都是要沙,現在房地產好,現在沙很缺貨搶手,現在沙搶手,我們這條河沙又讚品質又好……」
「廢土一台出去要給廢土場2000元,我現在沙一台出去,又幾萬塊回來,我兩千省起來,又幾萬塊回來,跟政府標的時候又有錢可以賺,一條牛剛好剝三層皮。」
冬至過後,鰻魚苗會由外海往淡水河上回溯,最遠可到烏來,但由於污染,如今只出現在淡水河口。每年的鰻苗期也正是市政府的疏濬期,疏濬傾倒的棄土,堵塞網具,水流不過去,網裡面還有土,最後重到拉不起來,一張八千元的網就這樣報銷了。
紀錄片的最後,是漁民抗議時找不到人的馬英九市長,在關渡自行車車道落成時舉辦的「2005河濱騎趣百分百:歡慶台北市河濱腳踏車道破百公里」活動中,以宣示勝利的姿態對眾人致詞的畫面:
「你可以從我們景美,沿著新店膝、淡水河,然後基隆河,一直騎到南港…..」

接著馬市長的聲音淡出,淡入的是陳萬生悠悠的感慨:
「我們這裡困難了,我們台北市裡,一條船要維持生活困難了,我小時候要抓什麼都有,所以說小時候,一個人賺錢要養五個家還綽綽有餘,……這條河,一個人可以養五個家,養五個小老婆還很涼快,現在你,一個家,一個都養不起……」
當捕魚不再能養活家人,下八仙的漁民於是去工地綁鋼筋、墓地抬棺木,出賣僅存的勞力生活,再辛苦都希望讓下一代受比較好的教育,目的不是為求向上階層流動,而是擔心他們基本的生存:
「我們的年代,我甘願拿扁擔,甘願做苦工,還有工可以做,你看下一代呢?下一代哪有工可以做?你說要靠抓魚蝦貝類,現在污染成這樣,要去哪裡抓?」
當漁人下一代繼續留在漁村發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預期的,隨著漁業的沒落,紀錄片中陳家兄弟口裡有關這條河的知識也將隨之消逝。
101高樓旁喧鬧的跨年晚會,以及把河流當單純風景與裝飾品的自行車步道,這就是我們僅能想像並且洋洋自得的台北意象嗎?如果說阿倫貝皮的漁民在自身的發展中同時品嚐了甜與澀,下八仙的故事卻似乎只有沈重、令人窒息的污濁(dirt),因為他們所承擔的是別人的發展代價。

發展究竟是發展什麼?
是誰或什麼實際上得到發展?
謀求發展的背後是什麼需求?
這樣的發展如何才能實現?
前面這些問題有什麼政治意涵?
以上是Immanuel Wallerstein 在<發展,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一文中指出的問題,提供給讀者們進一步思考。
註1: 這個標題之下的素材,引用自Conrad Kottak所著的Assault on Paradise一書(中文翻譯本名為《遠逝的天堂:一個巴西小社區的全球化》)。
註2: 這個標題之下的素材,引用自洪淳修導演的紀錄片《河口人》以及同名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碩士論文。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邱韻芳 兩個有關「發展」的漁村故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5758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