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田野,返田野
給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錄
歡迎光臨田野世
二○○六年,《田野的技藝》一書出版。這是台灣第一本由多位人類學與社會學者現身說法的集體田野書。一篇篇或黑色幽默、或跌宕驚險的田野工作實錄,凸顯出不依賴問卷並長期親身參與的「田野技藝」,是如何引領田野工作者突破盲點、走向更曲折的社會真實。十三年過去,物換星移。從高科技產銷到創新社會設計,越來越多領域伸臂擁抱「田野」,期待「田野調查」為相關產業帶來更正確的市場評估、更精準的受眾認識、協助解決更多社會問題。可以說,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不只強調演算法的大數據夯;與大數據精神完全相反,強調「純手工、親體驗」的田野工作,也正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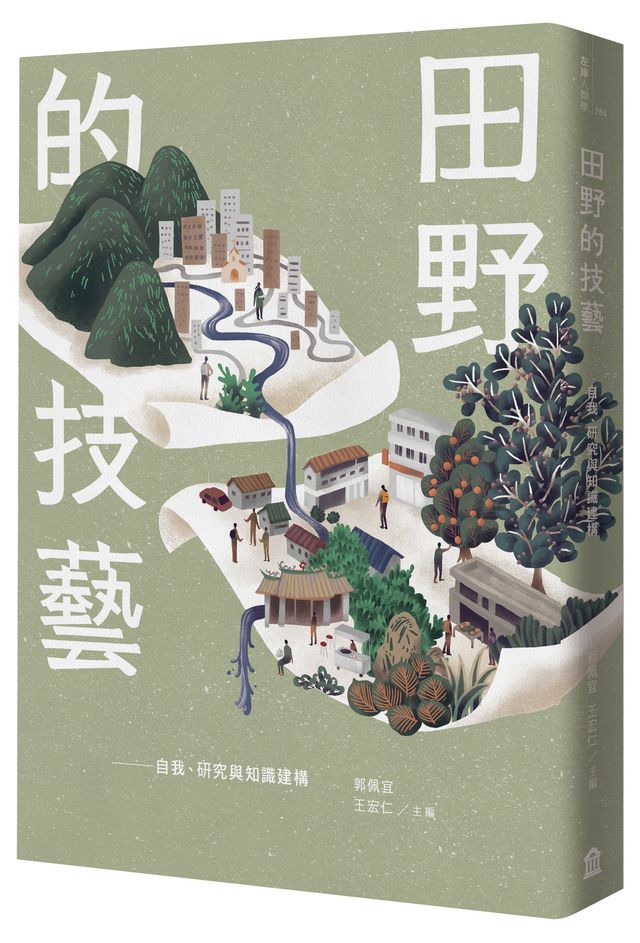
隨著社會遞嬗,今日田野的樣貌變化萬千,田野技藝也隨之轉變。曾有不少人擔心、甚至預言,當所謂的「傳統」消失(姑且不論所謂的「傳統」是否只是一種「現代性」的追求下,被篩選整合起來、甚至「發明」出來的一套東西),人類學將無用武之地。但這個預言失準了,因它小看了田野觸角的延伸力,也錯估了人類學的精神。今日,在更多意想不到的空間,「田野」遍地開花。不論是在紐約華爾街、西方與非西方的科學實驗室、世界各地的電子工廠、醫院診所、爵士酒吧、高空彈跳現場、黑客松、瀕臨絕種的紅毛猩猩棲息地、「第二人生」的線上虛擬遊戲,乃至殘酷的戰場邊緣,都可以找到正在做田野的人類學家。
與此同時,「田野工作」也早已不再只是人類學與最靠近人類學的質性社會學研究的專利。雖然很少有其他學科的人會仿效從事「古典田野」的人類學者那樣,長年專一地「只過他人的生活」,而通常是以相對短期、也可能長年延續的參與及訪談為主;但有越來越多的學科,都加強了其對「田野」方法的倚重。舉凡教育學、地理學、政治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歷史學、國際關係、科技與社會、藝術研究、社會工作、環境資源管理,以及其他越來越多學科開設相關課程教授田野工作,也有高中老師指定學生作業必須根據田野材料而寫成。台灣社會似乎在短短幾年間,就有了各式各樣急速增生的「田野」實踐。
《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這本書,是一群田野工作者對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邀請,與補充。既是錦上添花,也是盛世危言。身為以人類學為職志的田野工作者,我們無意捍衛「田野」不可動搖的最低底線或「正統」。恰恰相反的,我們想延續《田野的技藝》一書的精神,搜羅種種難以寫進田野教科書或工具書的田野歷程,同時更進一步分享,在遇到國家官僚發展計畫與學院管理績效化下重重機關的硬體制時,已經被迫「轉大人」甚至變成「老鳥」的人類學者,該如何選擇田野、也被田野選擇?這些歷程難以被複製、被標準化,或是按表操課,甚至可能是屬於這一輪盛世的特有種經驗,但卻是我們認為「做田野」最迷人、也是最讓我們髮稀齒搖終不悔的理由。
這本書,同時也是一群田野工作者檢視自身田野歷程的直心書寫。說直心,並不是因為我們的田野故事比較激情、勁爆或者十八禁(雖然,那也很值得期待XD),而是因為我們都曾經傻呼呼地土法煉鋼,對田野感到沮喪、挫折,卻仍從田野工作的平凡無奇與日復一日的未知黑暗中,看見了田野之光。藉由此書,我們想為這個田野盛世打開的,是細膩描寫個人經驗,不怕自問,一邊深入直搗田野的種種難題,一邊拒絕被績效控管的另類空間—一個田野異托邦。在這個異托邦,田野狀況無法事先規畫預測、生命體會的成果無法寫入研究報告、最想說的話不會被刊登在期刊、最想做的計畫也不會通過制式的倫理審查。

然而,田野異托邦是寬容而開放的:我們試圖在個人生命經驗與身為「專家」會面臨到的「非菜鳥問題」之間,做同等分量的探索與剖析。因此,相較於給予「定義」,我們鬆動「定義」,但也在鬆動後尋找根基;我們不教導一套標準流程,但我們誓言要讓讀者對「田野」的想像更上一層樓。簡言之,這將是一本讓你感受硬體制與軟生命的田野書。
我們將本書命名為「辶反田野」,一個同時表達「反田野」與「返田野」的多義雙關詞。我們特別選取「辶」部首為字,它有「忽走忽停」與「奔走」的流動意涵,以此指出「反」與「返」之間的時間差,並標示「反」與「返」重疊交錯的可能。因而,「反田野」、「返田野」、「辶反田野」是本書的三大主軸。
「反田野」,代表我們對於古典田野工作範式與大眾想像的不斷反思。在什麼條件下,「古典」的田野範式精神依然足以回應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田野風景,且在被賦予更多工流動的形式與生命之後,與新田野範式們仍有可承接之處?藉由「反田野」,本書的作者們嘗試思索田野範式與時空背景之間的關係。
「返田野」,聚焦的則是我們對田野的一再回返,透過不同田野的對比與反差來探問何謂田野工作。藉由「返田野」,我們努力思考從一個自己愛過或痛過的田野,到下一個新田野之間的斷裂與承接,誠實面對個人生命與學術職涯之間的交織愛恨。
最後,從「反」到「返」的時間差與輪迴性,則提醒我們關注田野的時間質地。慣常的田野想像中,時間是同質與線性的流動:進入田野↓進行田野↓完成田野。然而在成書過程的共同書寫與討論中(請見本文最後附加的精采幕後花絮),最引發眾人共鳴的話題,竟然都不約而同地指向更多異質的田野時間想像,包含倒反的漏斗(從第一田野到第二田野再回到第一田野的旅程)、星軌型輪迴(越年長的田野越意外地回應到年少時的憧憬與陰影)、返土歸田(以土壤孕育植物的多重關係動態想像田野實作的互為主體過程)、潮汐盈缺(體會到碎形田野自身的生命與死亡)等。抱著如此對時間的特定關懷,本書因而有別於過去三十多年來英語系人類學界所發展出的各種新田野概念,諸如「反身性民族誌」(書寫者的權威應被挑戰)、「去地域化的空間」(每個「地方」的固有疆界如何被權力關係生產出來)、「全球組裝」(治理術、技術與倫理的再地域化或在地用法,如生物科技在世界不同角落有著不同的運用),乃至「多點田野」(比如研究移民與難民,其生活流動的本質,要求田野工作者無法蹲點在單一地點)等。我們雖然承接以上這些概念的基本精神,但更強調從空間的反思進入時間的反思,最後迎向非生產性導向的另類時間觀。我們認為,人類學田野工作中許多必要的學習、醞釀,與等待,以及在自身與異文化之間的不斷反覆對照,雖然看似缺乏「效率」與浪費「時間」,其實卻正有助於我們捕捉複雜繽紛的動態真實,甚至還拓展了我們對於「真實」的想像。
以下且讓我們依序說明。

反田野:擁抱碎形與隙縫的當代
「古典」的英美法人類學田野,是一名白人男性或女性,在學院受過民族誌工作與人類學理論的訓練後,隻身一人來到某個異文化,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一住就是一年、兩年不等,習得當地語言、浸淫在當地社會的文化世界中、透過「收養」或其他方式而被當地人接受成為社群的一分子,逐漸懂得當地人的觀點與在地知識,最後能以專業跨文化「比較」的批判視野,描繪出一個社群的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與其他可用數據或圖表傳達的資訊)、肉(各種微觀社會互動的氛圍與肌理,融入政治經濟親屬宗教性別族群國族等脈絡)、靈魂(諸如神話信仰的、美學的、道德的、社群之人的理想性情與對世界的願景),以達到對社群更全貌觀的理解。田野出產的東西叫作民族誌。好的民族誌是骨肉靈魂,不好的民族誌是血肉模糊。
我們「反田野」,首先反對以上古典人類學田野範式中對於「田野」的一套「誰可以研究誰」的正典想像。這套想像預設由白人來研究非白人世界,或由前殖民國的人類學者研究內部與外部殖民地的人民。當一名第三世界的學者也想做田野時,這套想像則預設她或他的最佳選擇會是自己出身的國家、社會與文化。本書反對這種國際田野勞動的分工潛規則。我們相信,如果「田野工作」真是一種好的認識世界、迎向他者的方法,那麼任何人都該有機會學習它。(如何提供做海外田野的政治經濟與語言條件,則是胸懷「新南向」的台灣學界應該認真面對的課題。)與此同時,我們也拒絕這種身分決定論的另一種變形:認為「土著」人類學家「自己人研究自己人」就比較輕鬆。事實上,如同本書第一篇的作者佩宜所言,在地田野往往比海外田野更難抽離自己既有的階級或文化同溫層,也因此必須反覆錘鍊更高的敏感度與反思能力。
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書想做的是繼續拓寬、挖深古典田野範式裡既有的時空想像。在社會生活高度分化、人貨資訊高速流動、網路打造多重時空的年代,「長時間置身某處」的田野古典靜態想像,顯然很難回應當代生活多工、碎形的複雜樣貌。本書作者之一韻芳穿梭在全台各個部落與臉書之間的經驗,很明顯地就是這種碎形田野與網路時空結合的結果。同樣地,佩宜在立法院、法院,與行政院不同單位中的參與觀察,也都不屬於古典的「蹲點田野」,而是跟著開會走的多點田野。邵武在埔里與香港雙邊都研究友善新農,其田野工作模式是間歇式地兩地跑、甚至平行跑。欣怡的「綠電叢林」田野,由於聚焦風力發電機的開發問題,更使得她必須參與決策機關的會議、到西海岸考察民情,乃至參加工作坊,學習鯨豚在海水中若聽見風力發電機打樁會如何反應。無論是研究民主政治體制運作的方式、思索發展計畫如何有感推動、關注土地正義、評估再生能源的設置對居民的影響,更多的人群與課題,都要求田野工作者亦步亦趨隨之移動,也要求田野工作者穿梭於歧異的生活世界之間,學習聆聽不止一種語言,並隨時進行轉譯的工作。如何在碎形化與流動化的異質田野中累積,尋求深入同理的途徑,正是當代田野工作者最需切磋的核心技藝。

正是由於我們重視田野新的開放性所帶來的多樣時空,「反田野」也必然反對只將田野視為一組可以客觀操作、被標準化,甚至可被套餐化的、隨時可用的研究工具。有別於當前種種對於「田野工作」的普遍想像,認為田野工作是以「獲取知識」為目標的一種「研究方法」,我們想強調,其實田野工作本身,就應該是目的。我們並不否認從事田野工作必然有著工具性的考量,但是我們拒絕讓工具性的考量壟斷了對田野工作的所有思考。如果田野工作起始於對「她/他者」深刻的好奇,而且是透過田野工作者的身體力行,深入田野日常,進而成為田野的一部分來對他者展開探問,那麼,田野工作必然在每一個環節與層次都涉及了田野工作者與田野對象之間的心念交錯、言詞互動、聲色相聞,與肢體應對。在這個人我彼此「勾引」而斷續交織的過程中,「他者」無論如何不會只是讓我們獲取書寫材料的「工具」,而是田野工作者必須謙卑討教、努力建立互信、嘗試認真理解與對待的「目的」本身。「田野即目的」的背後,是「迎向她/他者、認納他/她者」的價值選擇與生命倫理實作。
在碎形世界中延續對他者之關懷,使我們相信,當代田野應該更加關注並賦予更多討論的,是人類學向來重視的「日常混亂與隙縫」。在人事物高度流動、幾乎所有田野都必然涉及多點的今日,通過參與觀察日常隙縫、身體力行成為田野一部分的「田野」,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正是由於各種社群與個人都正經歷比從前更快速變動的複雜性與混合性(如欣怡親身介入台灣風力發電的多方爭議與協調、怡潔細說自己如何與中國農民工在工廠與農村之間流動、如珍在香港與菲律賓籍移工一同舉辦選美、恩潔與穆斯林科學家一同探詢伊斯蘭清真戒律如何進入自然科學實驗室),敏銳地關注所有非主流的、缺乏新聞價值而無法被報導的、只能被「哎級論文」與數據過濾掉的生命圖像與聲音,將會是未來田野工作魂得以永續的關鍵。事實上,我們相信這種「以身為度、深入隙縫、在森林中為小草見證,甚至勇於重寫整座森林歷史」的田野魂,將在演算法機器人充斥的未來變得更為重要。
返田野:跟田野一起慢慢變老
這本書的另外一個重點,是我們強調具有時間縱深、重返田野工作所帶來各種不同情感與反思的「返田野」。這裡的時間長度,長達十年、二十年,中間的關卡魔王,包含了工作、績效、台灣特殊的學官兩棲體制,乃至一位人類學者對自身使命的質疑。我們不斷反芻自己的經驗、挑戰書寫田野可能可以有的多元樣貌,是因為我們想要凸顯田野這回事並不只是按照某種嚴謹的研究計畫、在一段時間內可以有顯而易見之「可見成果」的期待下,就可以完成的一套手續。相反地,隨著身分角色從博士生轉換到學者專家,處在需要跟國家體制打交道的台灣學術環境,甚至背負著田野地人們要求回報的期望與害怕落空,使得田野更充斥著自我懷疑、徬徨躊躇,乃至怨念。這些怨念的出口在什麼地方?本書有許多篇章都針對這個問題做了自身經驗的分享。
對於田野工作的職人來說,田野不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不是獲得資料的工具,而是一而再、再而三遁入不同生活之道的身體練習。在截然不同的異生活競技場中,本書作者們都曾經走過學術田野工作的十八銅人巷:從摸索到擇定一個田野、進行不知道哪天才會頓悟當事人邏輯的田野工作、結束田野、書寫論文,然後等到論文出版的那一天,發現自己和田野一起變老了(菸∼)。那麼,當我們在第一田野之後再開展另一個田野,也就是選擇再次進入「銅人巷」的時候,什麼事情有機會變得不一樣,什麼課題卻似乎永遠不變?換言之,我們認為值得談、但是較少有機會被好好談的,是「老後的田野」、「不再夢幻但依然懵懂的二度田野」、「被迫轉大人的二度田野」,也可統稱為「田野第二春」。

這個問題的開展,與學術人的生命及志業軌跡有著密切關連。當我們在高等教育與學術體制中,從博士班學生變成了專家學者,同時也必須迎接生命中重要他者的到來與離去,這些轉變都將在我們身上加諸強大的限制。用白話文來說,因為要教書、工作與擁有生活,我們的田野再也不可能是博士生時學習的、一個人長住遠方的「古典」人類學田野。而且,當研究者從到處碰壁的菜鳥變成手握國家資源、不時被鄉民鄙夷的「學者專家」後,「被研究的社群」對我們這群田野工作者的期待與互動模式也隨之改變。不只如此,上述的限制與變化還要再加上八○年代以降,全球大學學院越趨管理化的影響之下,學者教授被高教體制不斷要求在短時間內做出「績效」與「應用」的現實(詳見本書邵武的文章)。在這些多重限制下,我們幾乎不可能長時間遠走高飛,拋開自己的生活常軌,花一年以上,以全身五感全開的浸淫式生活,去「田野」過他人的生活。換言之,相較於博士論文田野,我們進入全職教學與研究體制以後的田野都變得零碎,參與也變得更為間斷性。這也是說,田野的「碎形化」過程,不只是時代變遷所賦予當代田野工作者的挑戰(這是「反田野」的主題),而是絕大多數學院裡的田野工作者一直必須面對的職涯挑戰。無需否認,這種「碎形田野」,其實在其他精通於訪談藝術的學科中,老早見怪不怪,甚至是常態;然而,「碎形田野」對情有獨鍾於長期浸淫在某個異文化、以「反向學習」(un-learn)自身偏見為目的、期待「終於學習到」當地觀點的人類學者來說,卻是無比地惱人。如果人類學家也開始做這種碎形田野,那古典田野對於整體田野工作的貢獻還存在嗎?
前述問題其實是「反田野」的「碎形」問題,但在我們親身體驗過的實例中,將會更進一步帶領我們到「返田野」的「公共參與」問題。本書有極高比例的田野第二春(含以上),是環繞著公共參與以及重要社會議題而發出關鍵性的提問: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機器日常是怎麼運作的(佩宜)?西岸沿海居民為什麼不喜歡理應美好的綠能風力發電(欣怡)?平平都是「友善新農」,在香港與埔里會需要面對什麼不同的問題(邵武)?如何保存當前被視為宗教禁忌的阿美儀式傳統(宜澤)?台灣的部落該如何才能「發展」起來(韻芳)?香港菲律賓移工為什麼要辦選美活動(如珍)?影響全球清真食品檢驗的科學化過程是如何在微小的實驗室發生的(恩潔)?農人與福壽螺究竟該如何相處才算和平永續(晏霖)?上述這些高度異質的議題扣緊當代各種運動與訴求,不論是社區發展、移工議題、綠能規畫,或是另類科學知識與農業實作的發展,都要求我們與其他各種專家、不同利益團體與公民團體進行相互對話。問題是,隔行如隔山,真實的(不是剪綵拍照用的)跨界對話其實是很困難的。本書除了交代為什麼我們變老後會變成公共參與「控」之外,也希望嘗試回答:人類學式的田野可以如何幫助釐清當代公共議題與社會文化的創新實踐?
在跨界常為必然的當代複雜政治經濟脈絡下,我們相信,人類學田野中最嫻熟的「反向學習」技藝,最有能耐學習不同陣營所擁護的對立願景。這套技藝要求田野工作者先放下自身所相信的種種教條,即使遇到自己想批判的對象,也試著先同理他們的關懷。這套技藝來自古典田野範式的淬煉,卻足以在多變與多方衝突的今日社會,幫助我們理解任何爭議事件中,更細緻的全貌。

辶反田野:非生產性導向的時間們
如果「反田野」裡的「碎形田野」,是以空間性語言來指認當代田野型態的遞變,而「返田野」是以時間性語言來襯托田野工作者在變老且奸巨猾(大誤)後卻仍視如珍寶的初衷;那麼從「反」到「返」的時間差,則構成本書的第三大主題「辶反田野」:田野的另類時間想像,將如何有助於深化我們對田野工作的理解?本書多位作者不約而同地從時間的角度來切入「非生產性導向」的田野經驗與技藝,重新評價那些在單一、線性的時間觀中,往往被視為是反挫的、干擾的、不具生產力的、浪費掉的,甚至是失敗的研究過程。
如珍的香港菲律賓家務移工田野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因為各自職業的需求,而有許多時間上的限制。此外,如珍似乎一直無法抓住菲律賓移工的生活節拍。為什麼約好了又被放鴿子?為什麼約會時間地點不清不楚也沒關係?從一頭霧水到後來成為移工們的最佳伙伴,如珍是如何體會出另外一種時間觀?為什麼她會說「慢」與「混日子」很重要?這跟「潮汐」與「圓滿」又有什麼關連?同樣是關於等待,晏霖在試圖「找福壽螺拍片」期間,又是如何不斷地被「報導鴨」或「報導螺」拒絕,被迫撤退與等待?但晏霖又如何因此參透出完全不同於進步與績效原則的田野觀:土時間──一種努力關照不同生命節奏,嘗試讓更多不同的人與非人相互調適與共同繁盛的時間觀與倫理觀?
恩潔的跨宗教與科學田野,則是在問另外一個「干擾生產力」的問題:如果所有工作都可能會有職業傷害,那麼田野工作的職業傷害會是什麼?在田野中受傷,是什麼樣的感覺?原本,人類學是恩潔年少時所能找到唯一足以安心收納生活中共存的多種對立宇宙觀的避風港。為什麼在出了田野後,避風港會被捲入更深層的風暴之中?同樣是關於拋開超中趕美地找回初衷或珍視回憶,韻芳在投入部落發展計畫後,雖然離「研究」越來越遠,但卻離「部落」越來越近;而佩宜多年來在所羅門群島的累積,最後與當地知識分子們集體創作出一本關於在島上長大的書,更是一種非單向回饋、強調雙向共做的田野回返: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一同建構後者的記憶與技藝。這些共通的長時間累積、等待、意外、不以功利績效為導向的狀態,也都是某種「另類時間」:拋開績效與成果,讓主體之間慢慢探知彼此習性、熟悉彼此韻律、照顧彼此需求,以等待更好的互為主體時刻的到來。我們認為,正是這些未必學術,或非功利性的田野時間,為田野工作帶來了難以取代的神奇力量與洞見。於是,除了原本辶反田野的問題(田野的另類時間想像,將如何有助於深化我們對田野工作的理解),我們還想追問,究竟這些非線性、非生產性的時間觀所帶來的體悟,其力量來自於何方?當今世界為什麼需要這些力量?

這是本書最具實驗性格的部分:多位作者嘗試透過生命書寫與象徵性的語言,描繪與思考那些神奇的覺曉時刻所發生的條件與情境。或許可以說,相對於古典想像裡有著清楚的起始與結束點的「剛性田野」,作者們看見的是更多以異質田野精神貫穿、在時間上卻越加彈性與柔軟的田野型態,我們稱之為軟田野,或從土時間長出來的田野。土壤之外,還有海洋與潮汐,有屬於田野自有生命的潮起潮落。這些篇章深入田野工作者生命經驗而充滿文學式地糾結自問,從而把社會科學論述、運動宣言,乃至被人文社會科學者視為「硬科學」的知識,都消化成一片拍散自然與文化界線的海洋,給予作者與讀者進入不明海域的自由。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我們相信田野工作是一種好的探問世界、迎向他者的方法,但我們絕不認為這是唯一或最好的方法。田野工作從來不是靈丹妙藥,它有非常特定的條件與相對應的限制。最核心的就是它必須是一個研究者以身心與研究對象在其日常生活中互動的過程,也因此深深受限於日常生活的諸般節奏與有機生命的不確定性。在此特定條件下,田野工作者只能盡力讓自己抱持開放的心態、有耐心地深入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但幾乎無法預期什麼樣的研究作為可以換來什麼「成果」。「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人生鐵律,在此必須被理解為:田野工作者只能默默耕耘。但是究竟如何收穫、收穫什麼,卻非操之在我。然而與其因此而焦慮不安,我們願意相信,是這樣的一種「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才是田野工作給田野工作者的最大祝福。我們求知,因為我們對世界好奇;而能夠勇於航向未知與不明的人是幸福的,即便涉險並不總是帶來幸福。田野工作允許我們認真地等待、允許我們細細品味自己與他人日常生活的艱難與小確幸,而且鼓勵我們認真地與田野中的人事物相遇,把他們都當成是田野工作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在管理主義與績效主義已經滲入所有體制的二十一世紀,這樣的處世與工作態度永遠不會獲得「長官」的青睞,卻很可能正是每個人減少工作與生活的異化,同時更勇於面對當代生活種種災難、危機,與不確定性的人生必備技藝。而在各種民粹政治盛行,多數人遁入社群軟體的同溫層,公共對話越來越難進行的年代,田野工作鼓勵我們迎向他者的開放態度,更是一種必要的提醒:沒有人/社群/物種是一座孤島。而要與更多異質的他者共生,我們就必須練習欣賞更多日常生活中的混亂,學習與周遭的雜質與噪音共存,並且更有耐心地去聆聽彼此。我們相信,這是推廣田野科普化的當代意義。我們不需要人人都變成人類學家,但如果每個人都能嘗試更有技巧與耐心地體察他者的處境,那麼我們或許還來得及讓更多的物種與人類共同繁盛,而非因人類而滅絕。
反返工作坊:沒有最合作,只有更合作
本書從最初的提案開始到出版,除了作者們各自努力閉門寫作,中間還歷經三次比武亂鬥兼內功療傷的工作坊,籌備過程超過一年。一開始的提案是幾位勇士們某年投稿圓桌論壇至台灣人類學年會但出師不利,於是後來以番外形式擴大舉辦。(當時的論壇名稱就是「重返田野的技藝」,而我們的「返田野」,也有重返《田野的技藝》,向十三年前的首部曲致敬之意。)論壇現場氣氛熱絡,一位難求,除了如珍無法從香港前來、恩潔在高雄遠距離連線,其餘全員到齊,此外也特別感謝鄭瑋寧前來問很難的問題(誤),同時已經看到本書未來的書商編輯德齡在一旁敲碗。比較遺憾的是,這次參與的伙伴之一彭仁郁因為有更艱鉅的工作要做,不得不離開本書寫作團。我們祝福大無畏的仁郁。

首次工作坊在新竹交大客家學院開張大吉,參與者除了五位率先發難的佛心發表人(佩宜、欣怡、邵武、韻芳、恩潔)、兩位評論人莊雅仲與林浩立,還有等待心靈救贖(咦?)的研究生們。這次的參與者都不約而同提到了台灣特有官學合作之特色、人類學家或因專長或因使命感驅使,涉入國家各種「發展」或「保存」的計畫之中,因而提高了我們嘗試描繪體制運作、不同領域專家與首當其衝的公民如何各說各話的興趣。另外兩個注目焦點,一個是「向上研究」的趨勢,也就是人類學除了研究底層、弱勢、邊緣化的群體(怡潔、韻芳、宜澤、如珍),也直搗國家機器核心(佩宜、欣怡)、深入技術官僚叢林及高教被管理化績效化的危機(邵武),乃至研究代表現代大寫知識的科學實驗(恩潔)。一切討論都讓人思索在硬體制要求中,又要修煉非古典田野技藝之時,田野工作者必須再度反躬自身的職志認同。另一個焦點則是意外地發現:這個集體討論寫稿出書的機會,似乎也可以讓彼此好好談談田野中的受傷與療傷。同時,主編人選也是在第一場之後逐漸有機浮現(=推坑),而非由任何體制內的組織或機構指派。

第二次工作坊在高雄中山大學社會系,對話人是《田野的技藝》主編之一王宏仁,與高師大人類學者劉正元。這次,「返田野」的主題逐漸浮出,但其座落的海域越來越深。宜澤的箴言「從學會、喜歡,到想念」是一個經典田野練習題,但是想念之餘,若想要保存下來,可就得好好理解阿美族儀式禁忌的變遷了;素玫在峇里島華人圈中局外局內人的主體位置轉換,與她先前在都蘭的經驗,可說是倒著走的田野邏輯;怡潔往返於農村與工廠,發現上次的「古典」田野中她沒機會做到的某個田野功夫,這次在工廠成為她更深層認識工人之間連結的管道。同樣是返回新舊田野之間,如珍從一直碰壁無法順利與菲傭做訪談,到後來決定「混日子」後,為何竟然如魚得水?最後,這次工作坊也是晏霖的新詞彙「土時間」冒出來的時刻,如新芽般,又爆破又青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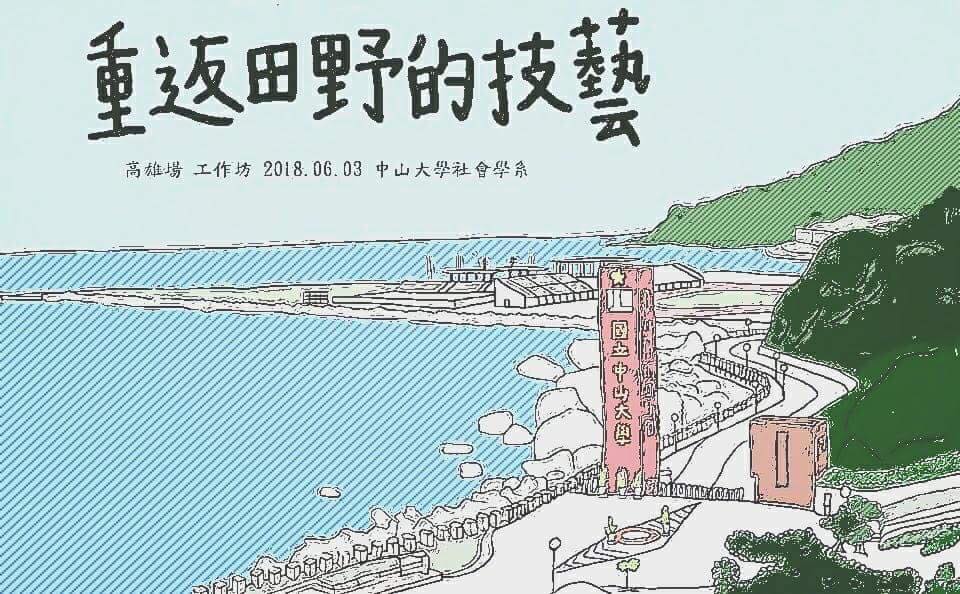
第三場工作坊承續前一本《田野的技藝》的優良傳統:包棟經典民宿,把人類學家們關起來交叉駁火又相互療癒。從兩場初稿發表會,到這場閉門工作會,出版社編輯德齡都是全程參與、筆記、攝影,並以市場角度給予建議,我們戲稱她為「書商」,外人以為她事業做超大。此次閉門工作坊地點在宜蘭壯圍張宅(黃聲遠作品),強迫性親密關禁閉,分下午場、晚上場、晨間場,抽籤決定誰跟誰同房。晚餐吃超美味宜蘭菜,餐後加碼獺祭與啤酒。
閉門工作會裡有人指出本書作者群陰盛陽衰的事實。然而當絕大多數的學術圈都是陽盛陰衰,這種健康的平衡,為什麼不呢?比較有趣的是,除了怡潔在會中提到自己的「未婚」身分常被報導人提問、素玫在文中提及接納自己的阿美年齡組織有著清楚的性別區分,沒有人在文章裡直接談論田野中的性別議題。這是否是因為在「熟女的二度田野」裡,我們比當年更嫻熟於處理田野中種種顯性或隱性的性騷擾、性別歧視,乃至被正面追求等性別課題?但如此老練地安於女性田野工作者身分,是否也暗示著我們接受了性別體制?換個角度看,其實「性別」從來不只是談論特定課題(=某些性別或性身分所帶來的限制或可能),更徹底來說是一種介入世界的姿態,而這是女性主義的禮物。當我們鬆動所有二元化的僵固範疇,細膩追究日常生活的隙縫與光影,掏心掏肺地挖掘人與非人生命的田野,集體創造實驗性的田野話語之時,我們就是在對性別體制的排除進行積極修補,就是在從剛性學術語言中奪回為世界命名的權力,就是在創造新的田野性別。如果我們真能激發更多田野新想像,那是因為我們無分生理性別為何,都共享了「迎向他/她者、認納她/他者」的世界觀。

最後,這本書的寫作與成書,本身也是「非生產性另類時間觀」的體現。這本書無法幫助我們任何一人升等,也不太可能讓我們獲得財富,然而整個成書過程,從年會外的論壇、三場工作坊,到文章修改與導論寫作,所有作者之間的坦誠交鋒與彼此療癒,本身就是最美好的共同創作與互為主體經驗。雖然這些過程在學術體制中毫無「生產力」,但思緒相互啟發與生命會心共振的暢快,恐怕不是任何「績效」可以給予的。
本書特有讀法
這本書雖然作為「一本」紙本/電子的書籍出版,必須有固定的篇章順序,但就內容而言並沒有線性的閱讀邏輯,甚至各篇之間可互相穿插跳讀、對話、吐槽;不同的田野中可能有相似的困擾,一樣的困擾又有不一樣的回應(或是用下一個困擾作為回應)。是以,我們特地在依作者、篇名的編輯方式外,另於書側下了眉標,點出不同作者共同關懷(苦惱)的主題,成為另一種「流動」並與讀者「互為主體」的閱讀線索。不論順著讀、倒著讀、輪迴讀,每篇都有各自的精采,等著讀者們去各自領悟。而在十篇精采的田野故事之後,兩位話很多的主編還提供了後記(也可以視為導論的迴旋曲),邀請讀者再重回我們的主編發酵室,持續將故事們對話、翻攪,再釀造為「繼續深入日常隙縫」、「有練過的二次田野」、「反對進步主義的單一時間」三罈好酒,等待你的品嚐。

可以根據喜好跳著閱讀彼此參照
是購買實體書的讀者才能享有的閱讀福利
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
2019/2 左岸文化出版
反田野,返田野:給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錄/蔡晏霖、趙恩潔
「反做」田野:一個人類學家研究「國家」的難題/郭佩宜
多重倫理交織下的能源困局:穿梭於綠電叢林的田野經驗/呂欣怡
平行的田野,交錯的技藝:我在香港與埔里發現農田的故事/容邵武
從村莊到工廠:田野中的魔幻與隙縫/方怡潔
擺盪於異己之間:來自都蘭和峇里島的田野反思/羅素玫
「跟老人家出發,帶年輕人回來」:記憶復返的村落歷史調查/李宜澤
無處不田野:穿梭在發展計畫和臉書中的人類學家/邱韻芳
田野中的圓滿:你那個研究還沒做完嗎?/陳如珍
療癒的熱帶:一位人類學者跨宗教與科學之旅/趙恩潔
找福壽螺拍片:邁向去人類中心的人類學田野技藝/蔡晏霖
辶反田野後記:迎向更多的開始/蔡晏霖、趙恩潔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蔡晏霖、趙恩潔 反田野,返田野:給這一輪田野盛世的備忘錄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00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田野 = fetish!? especially here in Taiwan!!??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