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新的歷史敘事與檔案技術
朝向「不適者生存」史觀
「不適者生存?」展覽從命名開始即直面「適者生存」這個以達爾文為神祇的科學神諭——將進化觀點限縮在遺傳基因而非生物性的發展。從1970年代起,生物學領域被「基因決定論」、「競爭生存」這樣的新達爾文主義典範所支配,以至於幾乎所有關於生物體之間「合作」「共生」的想法都被認為是浪漫主義式的遐想。對此,美國生物學家琳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2011)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提出了一系列科學論據,主張地球是由「共生」、「互依」演化的,而非達爾文主義的競爭演化。她更曾比喻道:在基因競爭霸權下,你的「未婚的阿姨」就不會是適存者,由此揭示「適者生存」這一概念如何被用來區分種族、性別、年齡等優劣位階。[1]然而已故「女」生物學家與「細菌」[2]為伍,一同被視為是生物演化學領域的「不適者」,亦必須在自身「性別」的競爭弱勢中、經歷早婚離婚再婚磨練著為人妻人母的抗體。
我在2021年3月結束的台北雙年展中遇見琳恩.馬古利斯,接著就迎來「不適者生存?」展;這一連續的看展經驗,刺激著我在不同跨度思考性/別、環境、生物性、生存與共生,而這些思考都是在美術館中發生的。但相較於台北雙年展的星球觀,「不適者生存?」展十分接地氣的鑲嵌在台灣的歷史情境中,深掘歷史向度,也因此更凸顯了「不適者」並非相對單一的整體,而是充滿異質性的集合(assemblage)。這一高度歷史化的傾向,讓我這個藝術外行找到思考的亮光,我進一步將整個展覽視為一種朝向未來的檔案技術與歷史修復,以此叩問「適者」史觀的去殖民、酷兒化,並重構「不適者」的歷史時間與未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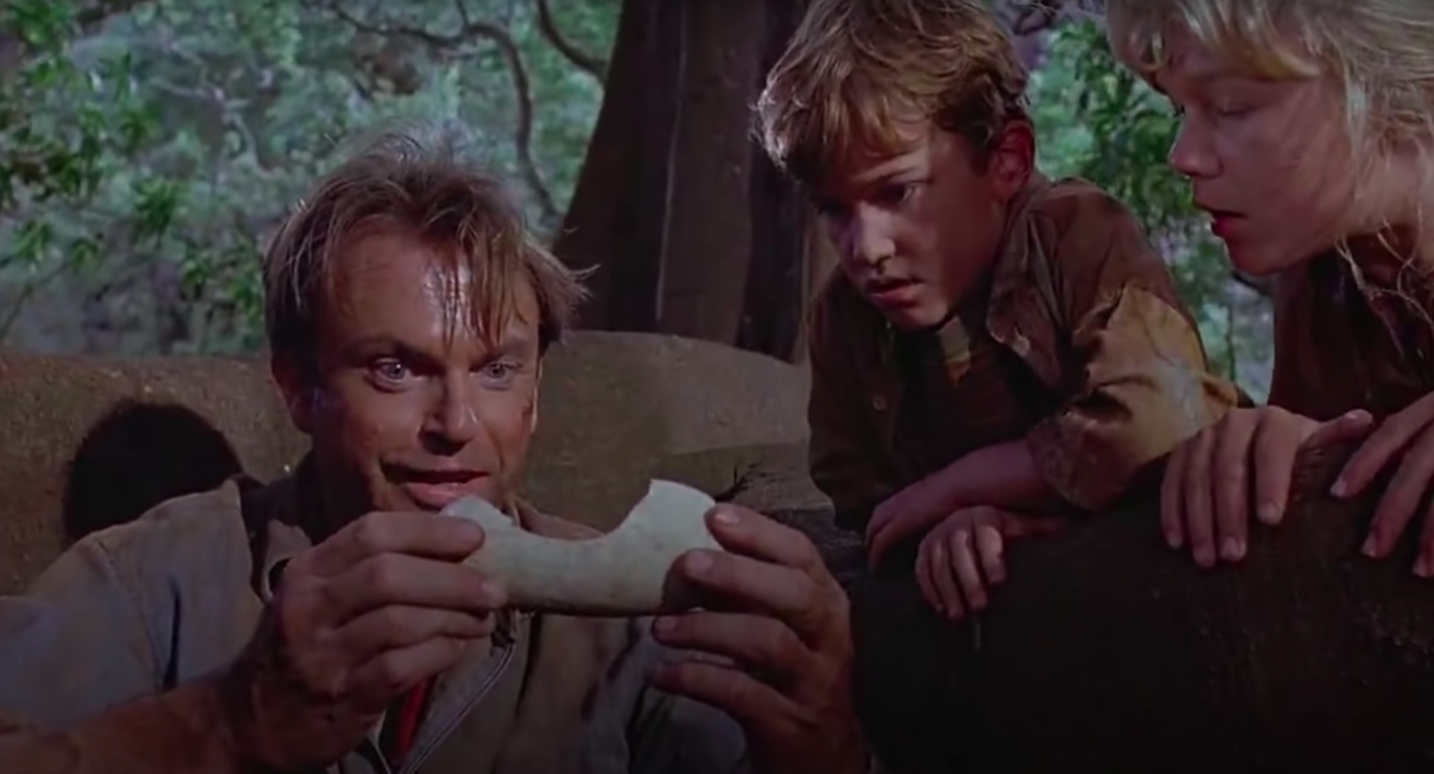
藝術展的檔案意義
美國酷兒文化研究者Ann Cvetkovich曾於《感覺的檔案庫:創傷、性相與女同性戀公共文化》中提出酷兒「創傷史檔案館具有迫切性」(9)[3],但要存檔有關創傷史的記錄通常很困難,因為依舊有許多酷兒或同性戀者在系統性恐同的衣櫃深處,導致其過著秘密的、或雙重生活。Cvetkovich引用了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95)的「檔案熱」(mal d’archive,archive fever)概念,指出「德希達將精神分析推向記憶,得出結論則是檔案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268)「檔案的不可能」(archive impossible)對於德希達來說體現於「無法存檔」的經驗,特別是失去記憶的創傷經驗,即使在無意識中也無法被存檔。[4]但對於Cvetkovich所關心的性少數存在與歷史來說,除了內在創傷的複雜形構,亦要面臨外部歷史的刻意抹除與曲解。
對於主流社會的忽視與排除,歷史學家和檔案員經常得依靠所謂的「瞬息事件」(ephemera)——即經常被歸檔為雜類的物品,可能是隨機出現的出版物和紙質文件、私人物件等,來作為建檔依據。對於內在創傷,Cvetkovich則從藝術作品尋求建檔的可能性,更表明「一些最出色的檔案運動者是藝術家,……透過提醒我們過去的酷兒經驗,提出基進的檔案實踐如何延續酷兒的未來。」[5]「不適者生存?」展則透過重置十九世紀末至今、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檔案,引入當代藝術家的事件詮釋與經驗重構,讓抹除的歷史在場,為創傷賦形。我透過展覽觀察到的檔案技術不在於建檔與封存,而是喚醒檔案的主體與未來性,而這必須將檔案的殖民性梳理清楚才能達至。



共生:檔案的去殖民
而檔案的殖民性就體現在印度性別史研究者Anjali Arondekar(2005、2009)[6]注意到「檔案熱」的另一個形式:檔案的驅力(archive drive)。如德希達所稱,檔案熱(mal d’archive)亦表現在苦於檔案的不足(en mal d’archive)(Derrida, 1995: 142)。Arondekar即注意到印度殖民史研究者競相挖掘史料以證明研究(及其對象)的正當性。雖然挖掘過去不被重視的史料,得以修正性重構被壓抑或扭曲的殖民檔案,也是「酷兒化過去」(queering past)的方法(2005: 11)。然而Arondekar指出一個潛在的問題,即「假定檔案依舊正是能夠理解殖民過去的知識。」(斜體為原文強調;2005: 11)這裡的「檔案」的內涵其實已經有所擴充,不只侷限在官方文件,問題則在於「知識生產的目的論」依舊將我們認知歷史的方式綁定在所能發掘到的事物、資料上,這正是檔案的殖民性。
因此我們必須注意,檔案的構成、形式、以及特定時期的分類和認識論體系,皆反映了殖民政治和國家權力的關鍵特徵。由此反思前述殖民檔案的挖掘,與其說是要將檔案史料等同於性少數主體(或各種「不適者」)之存在,更重要的是檢視檔案史料的建構與詮釋。對此,美國藝術評論與歷史學者Hal Forster在〈檔案的脈動〉[7]一文中更進一步點出,既有的檔案建構傾向維護固有的歷史敍事,但檔案藝術「關注的不是檔案作為單純的資料庫,而是當中的資料具不服從的性質,……它關注的不是檔案的絕對起源,而是其中曖昧的痕跡。
當我以「檔案的不可能」解讀「不適者生存?」展覽作品的檔案技術時,即在於試圖鬆動「檔案」與「不適者主體性」之間的連結。換句話說,需檢視的是檔案自身的建構與詮釋,而非檔案紀錄對象(不適者)之主體性。因此我認為,與其強調在歷史檔案中不適者的生命經驗被沉默和抹除,或試圖將其經驗重新插入國家歷史的既定敘事中,去殖民化的檔案閱讀研究更應朝向尚未考慮的多重連結來找到新的歷史框架,也是展覽提出的「擬態」、「共生」、「晝夜行」與「抗體」這四組關鍵字的內涵。我則將檔案的去殖民視為「共生」的前提,並認為「酷兒化」可以進一步提供維持共生的抗體。



抗體:酷兒化(藝術)檔案
基於上述討論,已有許多酷兒歷史檔案的研究者注意到,我們需要各種新的媒介來重構酷兒歷史與經驗。而正如 Cvetkovich 指出的,電影和影像擴展檔案的方式之一,即是記錄了各種「檔案」[8]。在更多藝術作品或數位媒材成為研究主題之前,「電影」(也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最早被檔案化地處理,以發掘並重新詮釋各種影像中的酷兒身影。如《電影中的同志》(The Celluloid Closet, 1995)追溯了一世紀大眾市場電影中男女同性戀形象的發展,華語電影亦有《關不住的春光:華語同志電影20年》(2012)、《膠卷同志》(2021)等書;而已故酷兒理論家José Esteban Muñoz更專注於有色酷兒(拉丁裔)在電視、攝影、劇場表演等各種媒體中的再現經驗。東亞酷兒文化研究者Chris Berry與Lisa Rofel則藉由「另類檔案」的概念,闡明華語新紀錄片所具有的公共紀錄的社會意義(Berry & Rofel, 2010)。[9]
將酷兒電影檔案化的作法,同時導向酷兒化檔案的思考——即質疑既有檔案本身的美學與意識形態——從病灶中提煉抗體。「不適者生存?」展亦注意到「攝影作為美術館收藏物件,其意涵往往在攝影美學與歷史檔案之間擺盪。」透過重新詮釋既有的攝影作品(如1869〈纏足與天足〉、1936〈吸菸小姐〉、1951〈挽面〉等)中的性別呈現,不僅酷兒化攝影檔案,在主題上也溢出上述以性傾向為主的「酷兒」內涵,讓精神疾病、孝女白琴、愛滋、娼妓、慰安婦等邊緣歷史主體並置在一起。展覽的酷兒化檔案技術,不僅直面污名史,也挑戰美學史;這樣的做法不以既有知識系統為唯一線索,也不另立或強化一套知識權力。因此酷兒化藝術檔案的工作,並非將酷兒史視為比較基進、具反叛性的另類史觀,而是如策展論述提出的,同時觀照「適者或不適者求生頑抗的種種足跡,並思考社會運動、藝術表現和生命記憶共同作為『抗體』的可能性。」在此更重要的是,酷兒檔案呈現的方式與酷兒生存狀態緊密相關,並連結其他不適者群體的歷史。



晝夜行:不適者的歷史時間
而不適者們的歷史,以酷兒為例,就如美國跨性別學者Judith (Jack) Halberstam觀察到的「酷兒時間是一個黑暗夜總會,偏離人生的連貫敘事……」(Dinshaw et al., 2007: 182) Halberstam試圖點出「酷兒的時間性破壞了時間的規範性敘述,[這一規範性敘述]幾乎構成了所有定義人類的基礎。」 (Halberstam 2005: 152) [10]
然而女性主義研究者Anna Clark進一步拆解性行為與性認同之間的聯繫,提醒我們需要好好地理解那些「沒有產生身分認同的性慾、行為或關係。」[11] 她將這些現象稱為「暮光時刻」(Twilight Moments),以彰顯其模糊性和短暫性,並強調,暮光時刻的邊緣狀態並不一定意味著顛覆性,反而經常與統治結構共謀。其中,許多從事「非法」性行為的人不一定會發現自己異常、生病或不自然,但他們不免受各種形式的社會懲罰(例如羞辱)。
無論是黑暗夜總會或暮光時刻,「不適者生存?」展即呈現了各種歷史時間。在單一線性進步史觀內外,有摩登傳統(〈吸菸小姐〉)、有陰性東方(〈中國節日〉);有死亡的青春(《是青春》),也有生猛的悼亡(《醉巡系列之四—孝女白琴》)。在精神、慾望、肉體、信仰等界限間,有著各種渡越主體(liminal subjects)們的不適生活,有快感、羞恥、瘋狂、哀痛、厭世等情感檔案。晝夜分界不是因為生活的兩面性(正常/異常),而是並存共生。生命本該有異常與正常共存。



擬態:朝向不適的未來
過去檔案作為知識、歷史、主體存在的證明,壟斷了生命存在應有的樣態,讓「不適者」必須對嘴跟上,但大多落後脫隊,被封存在過去,沒有未來。這也是大歷史的書寫策略,是為了讓單一同質的整體不斷繁殖演化,讓被殖民者只能如鸚鵡學舌,直到最後吞下自己的舌。
「不適者生存?」展中呈現的多元參照主體,一則反思了社會內部的單一史觀(男性、國族、異性戀中心),與受其排除與扭曲的不適者歷史,以及社群內部不適者間的階序與分斷;二則提供了「變」「態」者聯盟的橫向參照可能,讓被壟斷阻隔的生命經驗並置、連結。前者進一步提出了歷史修正,後者指向新的檔案技術,藝術作品則扮演了重要的媒介,提供了歷史性、物質性、多層次和跨領域的詮釋方式。由此預示了奠基於當下的未來抗體,將以擬態共生,晝夜共行。
[1] 參見:約翰.費爾德曼,《共生地球:琳恩.馬古利斯如何打破常規及開啟科學革命》, 2017,紀錄片,2 小時 27 分。院線與DVD版:John Feldman. Hummingbird Films, 2018.
[2] 馬古利斯在1970年代後期提出證實:構成植物和動物生命基礎的真核細胞是由更簡單、更原始的細菌共生融合而成的,推論我們的祖先就是細菌。
[3] Cvetkovich, Ann. An Archive of Feelings: Trauma, Sexuality, and Lesbian Public Cultures. Durham, NC: Duke UP, 2003.
[4] 具體而言,德希達認為,「缺乏記憶是創傷經歷的最終歸因於……所有記憶的邏輯,即使在無意識中也無法被存檔。」(同上註,頁268)
[5] Cvetkovich, Ann. “The Queer Art of the Counterarchive,” Cruising the Archive: Queer Art and Culture in Los Angeles, 1945-1980, eds. David Frantz and Mia Locks (Los Angeles: ONE 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 2011), pp. 32-35.
[6] Arondekar, Anjali. For the Record: On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Archive in Ind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與〈不見蹤跡:性與殖民檔案〉"Without a Trace: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Archiv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4, no. 1/2 (2005): 10-27.
[7] Foster, Hal. “An Archival Impulse.” October, vol. 110, 2004, pp. 3–22.
[8] 有點巧妙的原文:[o]ne of the ways that documentary film and video expands the archive is by documenting the archive itself.”
[9] Berry, Chris & Rofel, Lisa. (2010). Alternative Archive. In Chris Berry, Xingyu Lu & Lisa Rofel (Eds.), 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pp. 135-15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0] Halberstam, Judith.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Clark, Anna. “Twilight Moment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4, no. 1/2,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p. 139–60, http://www.jstor.org/stable/3704712.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陳佩甄 我們需要新的歷史敘事與檔案技術: 朝向「不適者生存」史觀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12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