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二二八前夕
堅持說下去,因為這一場抗爭也是我們的
許久以前,芭樂現任小編之一NJ女神指(ㄅㄧ)定(ㄆㄛˋ)我要在二二八前夕貢獻一顆芭樂,雖然被各種死線追殺,女神開口,唯命是從。
正義感不是個好題目
起初,我想把這篇文章的標題定為:台灣人究竟有沒有正義感?寫在二二八前夕。這標題有點政治不正確,也不可能有簡單答案。如此切入,需要先定義誰是「台灣人」的認同問題,剖析何謂「正義」及其體現在價值評斷與衍生行動的複雜哲學探問,更須以細膩的民族誌來檢視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多重場域中實踐勢必充滿歧義的「正義感」。這樣的設定不太芭樂,而且寫下來大概需要一本書的篇幅。想到死線們,還是再想想。
先說明為什麼會想質問「台灣人的正義感」。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家可能都觀察到的,正義感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顯然有階序或範疇的差異。比方,網路上常見的鄉民正義,對一般刑事案件義憤填膺、喊打喊殺,非得殺人償命不能罷休,但是對於威權統治者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以情治、軍警、司法等體制力量殘害數萬人民的可怕罪行,卻用「放下」、「向前看」、「過去就讓它過去」等類靈性宗教字眼,企圖開示(a.k.a.二度傷害)受害者及家屬。可見鄉民偵測不同範疇、不同行為人的不義行為的敏感閾限值差異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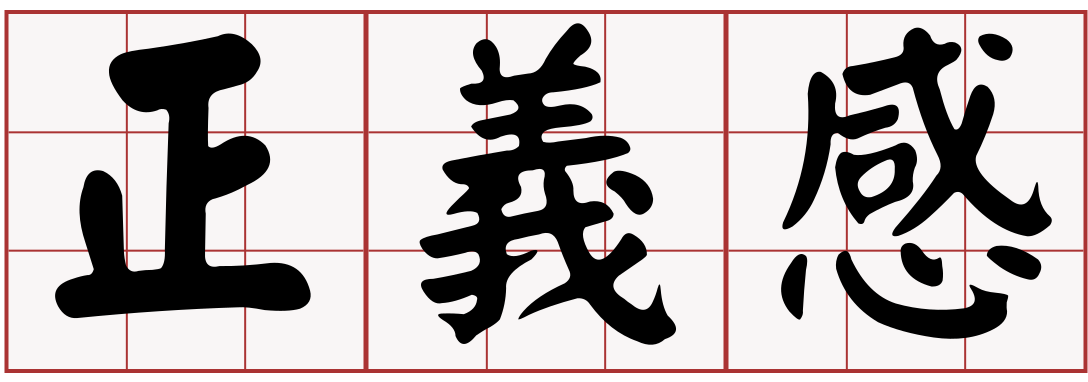
你知道修復式正義在台灣已經11年了嗎?
這裡開個小視窗,鄉民熱烈擁護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式正義,在強調人權、同理的當代社會,是否仍是最適合處理暴力傷害事件的正義觀?而這樣的「素樸」應報正義觀,會不會恰好是阻擋大眾想像轉型正義其實可以是修復式正義的原因?關於修復式正義的定義,法務部委託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黃蘭瑛博士等所做的研究報告《修復式正義理念 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2011)開宗明義便說:「刑事司法制度內的修復式正義實踐是一種強調結合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區共同處理犯罪以及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傷害之機制。」換句話說,當一件暴力犯罪事件發生,需要從被害人、加害人、社區三方著手,而且是「共同處理」,也就是涉事的整體社群都應該參與修復工作。然而,從2010年的「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至今,計畫推動已超過十年,對於應報式正義可能隱含的暴力循環後果,以及修復式正義與和解共生的前提為何,卻遲遲未見充分的社會討論(當然司法人員和社會大眾的觀念改變都很困難,希望法務部不會覺得被針對!)。不過,缺乏內在一致性和經常見風轉舵的正義實踐,當然不是臺灣人的專利。容後敘明。
浮上檯面的真相有多少,攻擊的力道就有多強
在二二八前夕提出正義感與正義實踐的問題,實在是因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與正義之間的關聯,對於現下台灣主流社會而言,並非顯而易見(我剛發現這個現象時,反應有點激烈,大驚小怪,現在比較能平靜以對)。今年是二二八74週年,大部分島民看見「二二八」這幾個字,一般的反應大概是直接略過,開心放假,或心裡冒出類似這樣的OS:「不是都過去很久了,還有必要提這個嗎?」不然就是:「又到了政治提款的時刻了!」更糟的還會加上一句:「夠了沒?錢都拿了,到底有完沒完?!」好奇的朋友們可以去看看歷史科普專門的網路媒體「故事」粉專最近上線的二二八專題底下的留言,便可窺知一二。(順便來推文,歡迎閱讀我在專題中的文章〈關於二二八,誰才是耽溺於過去不願前進的一群?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
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二二八,在一九九零年代以前長期被噤聲,倖存者與家屬敢於公開談論不過是一、二十年來的事,隨著愈來愈多歷史文獻出土,近年圍繞此主題的紀念活動、專題報導、藝文創作逐漸增多,網路社群媒體上攻擊謾罵和扭曲的言論也同步增生。最常出現的扭曲歷史事實、正當化國家暴力的言論不外乎:二二八暴動是共諜發動的,在國共內戰的局勢下,國軍鎮壓叛亂暴民理所當然,再說,若不是國民黨來台,台灣早就被中共血洗云云。
這看起來煞有介事但似是而非的說法,(刻意?)忽略了日本時期老台共與日共的關聯遠大於中共,在殖民情境底下孕生的台灣自治主體意識,亦受到西方左翼反殖思潮的鼓舞(請參閱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老師撰寫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詞條)。但台共組織在1930年代初受到日本政府壓制而幾近瓦解。二戰結束後,許多台籍菁英欣喜殖民者離去,樂見「祖國」來接收,但戰後兩年間,足以讓生計困頓又遭政府無理剝削的人民驚覺,結果到頭來,自己仍是受歧視壓迫的二等公民,這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能在全台引發一連串抗議與抗爭行動的主因。而國府選擇用軍隊血腥鎮壓,拒絕和平談判的手段來處理官民衝突,反而使得原本在台不成氣候的中共地下組織獲得了動能(關於更完整的歷史脈絡,請讀陳翠蓮老師的專書《重構二二八》)。我不是歷史學家,不應亂耍大刀,謹再補充非常重要的一點,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經常被拿來當作近四十年威權統治大規模侵害人民基本人權的藉口,但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中共忙著抗美援朝,美軍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8月再派第十三航空隊駐台,並以大量物資援助囿限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直到1979年斷交為止。換句話說,從1950年中以降,中共攻台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在那之後的五年卻是白色恐怖最血腥的時刻。蔣氏政權不斷延伸戒嚴緊急狀態,以理應受憲法約制的戒嚴令,凍結上位憲法保障人民基本人權的功能,又以全面剷除異聲的恐怖統治手段,其欲達成的主要目標,還是在維繫其掌控下的一黨專政體制。實際上,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中,真正加入地下黨的實為少數,即使是對於真正參加地下組織的抗爭者,威權統治者違反憲法不得以軍法審判人民的規定,以有罪推定酷刑逼供,濫捕濫判又濫殺,不僅嚴重違反比例原則,更違背了當時身為聯合國安理會會員的中華民國理應遵守的國際人權憲章。(愈來愈嚴肅,親愛的讀者你還在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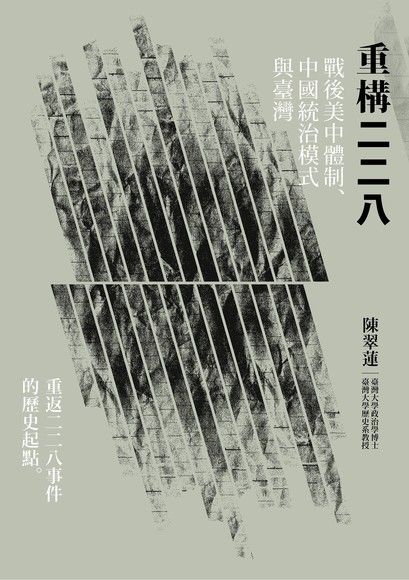
※在這裡補充一下,關於一九五零年代台灣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展與當時政治局勢的交互關係,可參見中山大學社會系林傳凱教授博士論文《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及中研院台史所林正慧教授的〈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 ──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台灣文獻》,第六十卷第一期,2009)。另外,關於二二八事件中特務的角色與作為,可參閱林正慧教授〈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2014。而關於威權壓迫體制的運作方式,促轉會也有許多精彩研究分析,請到官網或粉絲頁搜尋相關文章。
同理共感練習
作為試圖接近人類心靈的臨床田野工作者,還是想邀請大家來做一個同理共享的想像練習。想像你被迫捲入一場不知為何開打的世界大戰,你家鄉的男丁被殖民政府強徵去前線當砲灰,婦女被強徵或誘騙為戰地性奴。戰爭好不容易結束,你送走一個把台灣人視為二等公民的殖民政權,歡喜迎來一個以漢人視角而言同文同種,但終究因你曾受「敵營」統治、新「國語」講得不夠輪轉,而將視你為次級人種的統治者。戰後,你和其他鄉親們的生活拮据難當,個個勒緊褲帶、捉襟見肘,各自想方設法養家活口。初來乍到的統治者壟斷菸酒買賣,不准買賣私菸、釀私酒。再怎麼努力掙錢都趕不上一天連翻好幾倍的通貨膨脹速度,於是有人鋌而走險。接下來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官方查緝私菸時重傷販菸婦女,又失手射殺路人,引爆了人民對腐敗新政權長期積累的怨憤,要求政府為殺人負責的抗議遊行,蔓延成全島的抗爭行動。雖然有零星武裝抗爭企圖,但早有地方選舉經驗的台灣人,大多還是傾向支持透過地方代表跟國軍進行和平談判,提出改善台灣人公民地位的具體要求。不料新的統治者派來大批增援部隊,從基隆、高雄港口登島,以維持秩序之名,恣意濫捕濫殺。上班、上學經過的馬路上,你看見橫躺著一具具抗議者或僅僅是路人的屍體。你聽說有人被法外處決,不知埋在哪個坑洞裡。回到家,親愛的家人消逝無蹤,你急忙四處打聽人被關在哪裡,尋找買通的門路,把稍微值錢的東西通通拿去典當,結果贖人不成,家財卻幾乎散盡。有的家人幸運回來,卻不再是你認識的那個人。有的回家時已是全身布滿彈孔的死屍。知道你家出了事,親友紛紛走避。害怕再次受害,也害怕害到別人,你斬斷各種關係,移居他鄉,隱姓埋名。然而,內心瀰漫的煙硝從未真正散去,家園殘破已成事實。你必須奮力抵擋飄零失根的痛不把自己吞蝕,你對他人、也對自己掩蓋內在時時處於溺斃邊緣的裸命狀態,撐出咬牙活下去的意志。死神不時從暗處跳出來與你肉搏,但你學會讓外表看起來像是無風無波的一般人。
無處不在的指責受害者傾向
跳出入膚式的同理,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噤聲?如果遭到暴力和不正當對待,不是應該勇敢說出來,持續抗爭直到正義彰顯為止嗎?」「為什麼這麼多年都不說?是不是其實根本沒有這麼嚴重?會不會是為了博取同情,才誇大其詞?!」好熟悉的論調對嗎?直到現在,台灣某些食古不化的法官依然會對離不開施暴者的家暴和性侵被害者提出相同的疑問。人們習以為常、難以撼動的不對等權力結構,緊緊掐住受害者的喉嚨,也鼓動沒有能力想像、理解暴力情境,又急著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責怪受害者。
抗爭的條件與代價
二二八發生時,台灣人口約600萬,成千上萬的人親身經驗或目睹二二八,確確實實是一個集體性的極限暴力創傷。但是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應不比現在的人們更勇敢或更懦弱,要不是民不聊生積怨已久,也不可能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反抗,但槍桿子的血淋淋現實,大部分的人是消極妥協了。看看現在鄰居香港的狀況,可想像在當時的台灣,要長期跟蠻橫殘暴程度比今天的港府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政權抗爭,必須付出極大代價,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堅持。但就如今有香港藍絲,昔日亦有台灣本地人積極與當權者協作。從戰後任教於台大哲學系的自由主義哲學家殷海光教授,在1960年撰寫的針砭時事文章,便可見端倪。
1960年5月,雷震、胡適等自由派外省知識份子,與李萬居、郭雨新等本省政治菁英共同籌組中國民主黨,以制衡愈來愈獨裁專制的蔣氏政權(就說省籍情結很多時候是被刻意製造出來分化人民用的)。但這朵民主火苗才剛剛升起就立刻被撲滅。同年九月一日,為組黨行動提供理論基礎的殷海光教授,在〈大江東流擋不住〉這篇社論中,用「唯控制主義」批判了當局剷除有志者的暴行,同時也以利誘控制了一群唯利是圖者。他寫道:
近十幾年來,國民黨權勢核心人物,使出渾身的力量,實行「加緊控制」,他們是否收到什麼效果呢?從一方面看,他們的確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在這個小島上,他們確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唯利是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台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了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台灣一千萬人的身體。
三日後,包括雷震在內的多位組黨領導人物被捕,這些反共自由主義文人被貼上「為匪宣傳、顛覆政府」的罪名。而根據促轉會協助徵集開放的檔案揭露,府方高層對雷震未審先判,他的罪名和刑期,是由蔣中正在總統府內召開的秘密會議上,與14名黨政要人共同沙推決定(請參閱促轉會臉書粉專文)。現在的大家可能很難想像,一小撮文人組個黨,竟然需要國家出動軍法厲器伺候,可見「昨日台灣,今日香港」並非誇大之詞。其後,學界、政界、藝文界、常民百姓,大家都學會了沈默是金,不要碰政治。直到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國際局勢的轉變,逼迫當權者在自己築起的「自由中國」幻象外牆之內,逐步疊上更貼近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真實磚塊。
關心的旁觀者?
相較當年,今天在台灣追求正義通常不再需要以家破人亡為代價。然而,為何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追尋正義平反的道路仍是如此顛簸?許多人愛喊「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彷彿只要讓昔日威權統治繼承者消失,台灣會自動成為閃閃發亮的亞洲民主之光。但一轉頭,看見國民黨仍有近600萬的支持者,許多人感到不解甚至不屑,雙手一攤,繼續回到日常生活。這樣的淺層想像與蒼白抨擊,極可能是缺乏歷史及社會心理分析視角的緣故。作為一個黨國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曾經誓死捍衛秋海棠的人,我想,如果生活在官方名稱為「中華民國台灣」實際統御領土上的公民們,不對作用在自己身上的政治力線進行心靈考古學的解構工作,以便看見自己內裡的他者性與他者的主體性,不可能有機會達成集體創傷修復與和解共生。(這小段看不懂沒有關係,以後有機會再說)
阻抗自我反思的普同性
願意移動位置,從第三方的角度進行自我檢視,承認自己可能以各種形式參與了傷害他人的暴力罪行,甚至繼續維繫容許暴力發生的權力結構,何其困難。來看看國外的例子。自從聯合國創設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著手追訴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賽維奇等重大犯下反人類罪與戰爭罪的國家領導人與軍事指揮官,作為推動轉型正義、締結區域永續和平的主要措施,許多在1990年代發生類似組織型暴力的國家,亦在聯合國的協助下設置了轉型正義國際司法機關。大家可以想像,由於這些地區的重大人權侵害事件,涉及不同文化族群或宗教信仰群體之間複雜的歷史衝突,並非所有的群體成員都樂見聯合國以公正第三方的上位姿態介入。為了提升當地不同群體民眾對國際刑事法庭的支持,許多國際法學者傾向認為須達成幾個重要前提,包括組成法庭成員的選定必須具有公信力,法庭運作必須公開透明,並須透過各種管道對民眾進行宣導。
別來碰我的領導人!
但有位曾經在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擔任助理檢察官,後來去芝加哥John Marshall法律學院教書的白目法律學者史都華・福特(Stuart Ford)教授說,事情不是這樣子的。他分別檢視了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1993年~2017年)、獅子山共和國特別法庭(2002年~2013年)和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1997年迄今)等三個國家針對法庭正當性所做的各項民眾認知調查,指出他的法律同儕們推論有誤。民眾認知調查結果顯示,不管國際刑事法庭多努力提稱自己的正當性,大部分的民眾並沒有興趣知道法庭運作的細節,族群、宗教、政治群體的身份認同歸屬感,仍然是決定法庭正當性認知的最關鍵變項。如果法庭起訴與特定群體成員身份認同有強烈連結的領導人,絕大部分該群體成員會傾向認為法庭不公正。這個結論其實非常接近我們的直覺。如何界定正義?誰才有資格談正義、執行正義?什麼是達成正義的合理手段?永遠跟群體認同和群體內傳布的主流敘事綁在一起。因此,福特教授認為,社會心理學提出的認知偏誤模型,如動機推論(強化原本信念的傾向)、對捷思法的依賴(習於在資訊不完整情況下做判斷)、傾向逃避認知失調引發的不快、確認偏誤(選擇性地回憶有利於己的訊息)等,對於民眾認知法庭正當性的影響因素更具解釋力,這也是轉型正義工作應該費心著墨的面向(關於流言傳布與認知心理學的關聯,可參閱吳謹安的〈為何人們喜歡傳假新聞?假新聞的傳播與心理學〉)。
尾聲:直面自己、朝向他人
沒想到,為了解釋一個被放棄的題目,竟然寫了五千多字啊!(芭樂小編:請快收尾!)但比作者更聰明的讀者,應該很早就明白,這篇文章真正想探問的是:台灣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對於二二八,以及隨後發生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究竟是否可能達成某種認識和感知上的共識,好長出容許差異的寬容空間,找到彼此尊重、共同生活的方法?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某種程度上,我繼承了天主教教廷在十六世紀大規模殘殺新教徒,在二十世紀長久默許、掩蓋眾多神職人員性侵害兒童的罪愆,在得知這些人神共憤的重大暴力真相之後,我該如何自處?我還敢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嗎?我去教堂望彌撒的時候,該如何向天主禱告?在領聖體的時候,我是否還能接納自己藉由領受基督的身體,與全世界天主教徒在想像中融合為一體?而在我身邊,大部分的主內兄弟姊妹至今無法承認兩蔣政權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犯下了不見容於國際人權法律的重大罪行,反倒認為蔣家對台灣功大於過而繼續支持國民黨,我如何與他們共融合一?我承認,許多時刻,這樣的「合一」想像讓我如坐針氈。但我認為,當一個群體內部的異質性跨越某個閾值,反而更能逼問群體內部成員,究竟令你們合一的基礎為何?摸索多年,我目前給自己的答案是:承認人性軟弱,對他者保持開放性,相信在異質的他我之間,存在一個高於我們的共享價值。或許,在當代民主國家,那共享的核心價值會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群體內成員只能努力朝向它,沒有人應該有權力聲稱能夠掌控它、抵達它。以為自己能取代神,掌握真善美的標準,才是真正的原罪。身為這個群體的成員,讓我比其他人都更有責任揭露群體內發生的種種穢行,那是捍衛群體續存的唯一途徑。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花了超過四世紀的時間,才共同創造出對話、和解的機會。希望共同承載台灣歷史暴力傷痕的我們,不需要再等待四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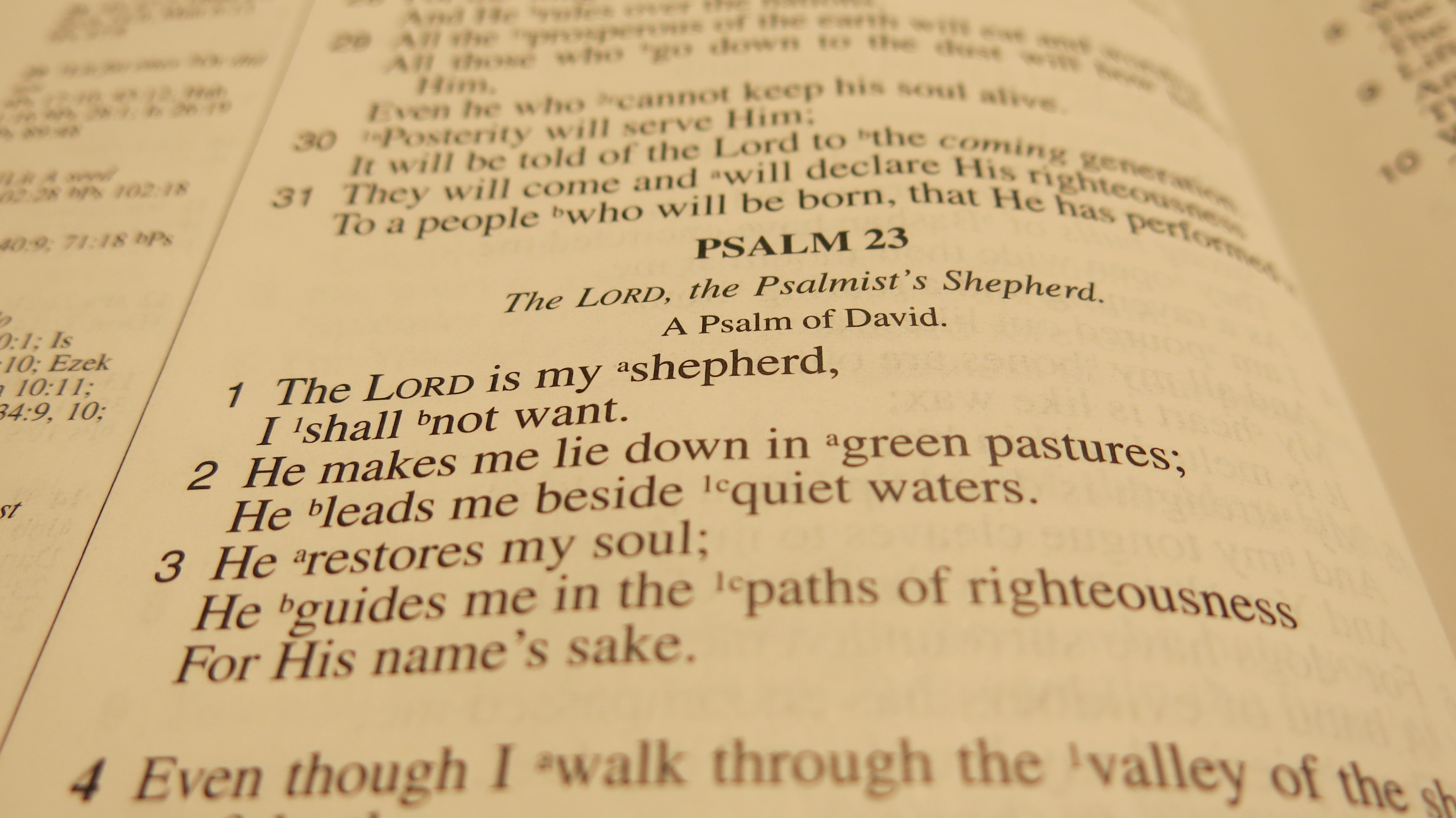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彭仁郁 寫在二二八前夕:堅持說下去,因為這一場抗爭也是我們的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859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台灣政府為釐清二二八真相確實作過一些努力。在李登輝授意下,行政院在1991年1月18日成立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彙整當時國內外的史料,並於次年2月22日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由賴澤涵任總主筆,由吳文星、陳寬政、許雪姬、黃富三、黃秀政等人撰寫,參與者訪談對話者包羅國內臺灣史研究重要學者。
這是我閱讀過的二二八出版品中觀點最多元、立場最超然,因而我最能信任的一套(包括員書坦承:當事人記憶多有出入與相左,史料未及佐證者頗多,仍待後人進一步的研究與釐清)。後來的相關出版往往帶著個人的強烈立場與主觀情緒,使我難以信任。
可惜的是,行政院那一套原始報告印行數量有限,沒有在市面流通(1994年交給時報出版社發行的版本已經大量削減內容)。我是在清大系辦公室裡見到這一套原始報告(模糊的記憶中是三大冊),擱置超過一週而無人翻閱,我徵得系主任同意搬回到自己的研究室去逐頁閱讀。
我因為讀過這三大冊,深知其中事實脈絡極其複雜,絕非單一敘事脈絡或任何學者的個人觀點所能窮盡。其次,我的閱讀經驗讓我相信;認真想要認識二二八的人,都必須去逐頁讀完1992年公布的那一份原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才不會被其他作者的個人觀點、情緒所誤導或左右。
懶惰的人至少要去讀一讀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所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摘要(https://www.228.org.tw/228_overview.php?PID=7),至少有機會感受到要完整還原當時的事件全貌有多困難。
至於其他帶著情緒性的論調,認定(譴責)政府做得不夠多的人,或許應該想一想:進一步的釐清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或者學術界的責任。至少我的觀點是:學術界的集體努力做得不夠多、不夠深,以至於少數個人假借「學術」為名發表立場與觀點的「專書」變成不受學術互評的機制節制,無助於釐清事實反而扭曲了事實;再加上民進黨的炒作,轉型正義委員會自以為是東廠,最後當然會導致社會上有許多人反感。
就事論事,既然二二八的事實還無法進一步釐清,政黨就該先閉嘴,讓學術界積極地發揮 peer rebview 的精神去釐清完整的事實。至於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在提出情緒性的發言(譴責)之前,最好還是先認真地讀完1992年公布的那一份原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吧。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