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聽)研討會發表囉
學術社群的年度儀式與展演
盛夏到紐芬蘭開會,北半球七月中理應是陽光肆無忌憚的季節,但是居北美洲極東一角的聖約翰市(St. John’s),連續幾天低溫、大雨,好不容易陰霾退散,為期一週的ICTM(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雙年會,議程安排得緊湊,我趁著場次和場次之間短暫的休息空檔,提前到一個大會議室找著位子坐下來,準備聽下一場的發表,裡頭有個重量級的學者。

「到目前為止,妳每場都聽了嗎?」「當然沒有!」熟識的學者Andrew挨近我身旁的位置坐了下來,問了我上面這一句,聽到我的回答,似乎露出些微的輕鬆。他隨即引用我們共同的學友所謂的會議參與策略:「Colin說,來開會就是發表文章、露個臉、打打招呼、一起吃飯、喝一杯,我好像應該效法他。我不知道,到現在我還是每場都在趕場,好像有一種,嗯,宗教性。」
聽到這位比我資深的學者如此真誠地剖白,老實說我頗為驚訝,不過仔細想想,頭幾年我不也是如此:每每參與國際會議,總是恭敬地捧著厚厚的議程表,早早就把自己景仰的學者和關連的議題圈了起來,倘若遇到多場次共同進行而感興趣的講者同時段前後出現在不同的場地,哎,心中的掙扎和奔波於不同場地之間的勞頓那就別提了。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變得比較不那麼,嗯,宗教性了呢?套一句Andrew的用語。
約略是自從我發現,國際學術會議中的種種發表,也像是一種儀式語言開始吧。比如說:專題演講。去年於慕尼黑LMU大學舉辦的IFTR/FIRT(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atre Research)研討會,專題演講講員之一的Erika Fischer-Lichte用了「編織」的譬喻,來擘畫全球化時代下跨文化劇場的遠景;今年的會議,主辦單位邀請到Michelle Bigenho 來談原住民的現代性,她則是用了Michael Herzfeld的「文化親密」(cultural intimacy)例證當代民族音樂的跨國流通。簡言之,這些學術儀式中的長老(並不一定是年紀上的senior),不管自己的田野和研究有多麼專精,在此場合,要能善用關鍵字詞,召喚領域的遠景與在場人士的共鳴。
「可是我不喜歡她的態度:用那些很炫的影像,還在舞台上來回踱步……」第二天和一群專精亞洲民族音樂的研究者聚集時,針對前一天的專題演講,大家七嘴八舌,不光光是內容,連演講的話術也都成為眾人議論的焦點。我想起我比較熟悉的台灣原住民和沖繩社會,領袖或長老的話術的確是社會能力中一項不可或缺的指標,這點,現代的學術社群其實也所去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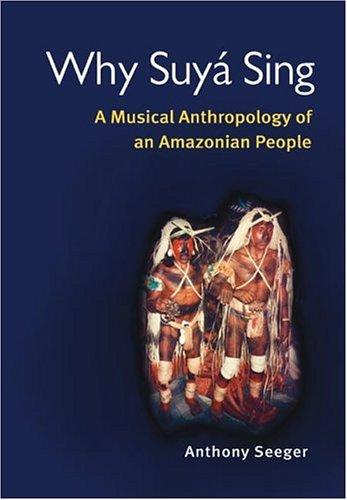
另一類的長老,靠得可就是他們在這個領域為人津津樂道的英雄事蹟和奇特經歷了。拿我文章一開頭提到的那一個場次為例,主講人之ㄧ的美國人類學家Anthony Seeger這位資深學者,早在三十幾年前就開始在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做田野,研究當地原住民的音樂生活與社會關係,出版的Why Suya Sing這本民族誌成了一方經典(以英語系國家的人類學家進行音樂相關的調查而言),歷久不衰。對一位已經在這個領域作出不可磨滅成就、已經有某種程度不可動搖地位的長老而言,他的發表最令人期待的,不是什麼最新的研究發現(相反地,聽眾可能會聽到比較多他的門生們所貢獻出最時下的實例),而是那些一去不復返的、但又十分真實的田野故事:
「Suyá人現在自稱為Kïsêdê,……這群人很有名的就是不喜歡和外人接觸,他們認為認識一個外國人就夠了,(講者語氣平淡但是現場揚起一陣隱微的肅穆)…….前幾年我帶著太太和女兒一起回去看望他們,聽他們說有一個日本的攝影團隊對這個不喜歡和外人接觸的族群很感興趣,特地要跑來做個專題報導,他們還是躲起來了……」
Seeger說話的同時,投影片上呈現的是Kïsêdê人傳統的聚落形式,正如典型的亞馬遜河流域原住民的聚落,人口不多,且圍成一個圓形,透過一條狹宰的通道,穿過蓊鬱的密林才到得了外面的世界,反之亦然。他和Kïsêdê人之間的關係,透過一段輕描淡寫的敘事,在這個投影片聚落空間的襯托下,顯得異常的神聖,且引發眾人的人類學舊時代的懷想,即使是在這場以「原住民的現代性」為主題的會議、即使Kïsêdê人也在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被廣告商欽點入鏡為白人唱歌。
在這場兩年一度的學術盛會中,可以見識到過去一百年來研究世界不同族群音樂和舞蹈的學術社群結構,在研究區域、領域和主題的變遷,正好反映了全球局勢:ICTM原先是以歐洲為最重要的據地發展出來的一個學術社群,原因無他,歐洲在十九世紀末興起了一股在工業化和國族主義共同刺激下的懷舊,開始熱烈地蒐集起自己社會中目不識丁的老百姓(大多是農民)所保留和傳承的民俗文化,其中一個主要的項目就是音樂和舞蹈。這個時期的民族學和民俗學發展與影響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期,歐洲一直都是獨領風騷,成為世界音樂和舞蹈的知識中心,例如:日據時期有名的學者黑澤隆朝將台灣布農族的八部合音錄下來之後,二戰結束後初期就是寄給位於巴黎的IFMC(即ICTM前身)總部。而有關民間舞蹈,學者們更是利用奧匈帝國轄民拉邦Rudolf von Laban發展出獨特的動作紀錄體系(Kinatography Laban),深入民間將一直以來活絡卻又無以名之的民間舞蹈加以記錄,成為二十世紀下半期東歐共產國家共同的學術志業,至今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國家科學院民族音樂學部門之下,仍保存了歐洲最大的民間舞蹈資料庫。
我加入這個學術組織網絡與活動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但是也觀察到過去一向以歐洲為重的網絡甚或研究取向,加入了美洲、甚至亞洲的勢力和影響。其中北美洲的人類學,受惠於鮑亞士本人的獨特興趣,對於藝術、音樂甚至舞蹈都有獨特的關懷(鮑亞士的女兒Franziska Boas本身既是打擊樂演奏者也是舞者),他的第一代弟子也建立了北美民族音樂學的系譜,使得北美洲傳統音樂和舞蹈的研究在民族音樂學和人類學間始終維持緊密的對話,特別是在美洲原住民的樂舞研究上,有其優勢的(當然也很糾葛的)政經與學術支配。

而亞洲的崛起,則是這幾年令人無法忽視的現象。以2004年世界雙年會於福州廣州雙城舉辦為指標來看,中國的民族音樂學者積極地融入這個全球最大的傳統音樂和舞蹈學術研究社群,挾其豐沛的多元文化資源,這個同時兼有著古老的音樂實踐和知識傳統,以及沉重的族群政治之國度,迫切地吸收著也釋放出學術交流的契機。下一屆2013年的雙年會又將移到中國的上海市,由上海音樂學院—中國第一個高等音樂教育機構—主辦,這個不尋常的決定(原有意競爭的馬來西亞因為無法解決是否發給以色列人簽證的疑慮決定放棄),除了印證中國的企圖心,也說明了亞洲勢必在這樣全球性的樂舞研究學術景觀中繼續成為焦點。
回到文章起頭的紐芬蘭,ICTM現任主席、專長舞蹈與大洋洲研究的美國人類學家Adrienne Kaeppler在這次會議的開幕致詞時語帶玩笑地說,加拿大隔了半世紀才再度成為主辦國,然而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的首府聖約翰市卻是一個有著獨特歷史的地方,特別是就歐洲與美洲的文化傳播關係而言。原來聖約翰市是北美洲的第一個城市,最早是由從英格蘭渡過大西洋、遠洋捕魚的季節性移民建立。十七世紀末期之後,受僱於英格蘭人的愛爾蘭僕役隨之而來落戶,並開始建立短期、最終是終身的移民據地與社群,在今天這個島上所謂愛爾蘭圈(The Irish Loop)的區域,見證了愛爾蘭人克服艱困氣候、地理環境和迥別於原鄉生態(在不列顛半島上的農民搖身一變成為北大西洋的漁戶),胼手胝足的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氣候雖然嚴峻,海中資源卻異常豐富,也讓這個靠由捕鯨轉換到捕鱈魚崛起的市鎮,有了穩定的收入,甚至在二戰期間,成為盟軍在北大西洋重要的補給站而名噪一時。近年來,由於石油等天然資源,聖約翰市民享受了相當好的福利,連計程車司機都不忘大力推銷邀請我們這些外來者落戶。
當然前提是你能忍受一年只有兩種季節,而那個不被稱為冬季的季節平均溫度只有十幾度的話。

聖約翰市鬧街上比鄰櫛次的酒吧、繽紛的住屋、以及絕對不會錯認的愛爾蘭移民傳統民俗音樂和舞蹈,在在為這個北美洲極東的城市抹上罕見的色彩,尤其是音樂和舞蹈的蓬勃,印證了表現性文化(expressive)和人群社會生活的緊密連結。除此之外,大會也不忘呈現加拿大境內原住民多元的樂舞生態,包括Inuit女性特殊的喉音唱法、以及其他第一國族的歌聲。當地的協辦者—紀念大學(Memorial University)與加拿大傳統音樂協會—為了擴大這次會議的參與,同時主辦SOUNDshift Festival,讓與會者可以同時一饗紐芬蘭的傳統音樂、加拿大第一國族的特殊歌唱、非洲祖魯人律動的樂舞、葡萄牙女性傳統敘事歌謠Fado掏心掏肺的動人之音、喬治亞男性的悠遠合音等等,這些帶人縱橫世界的樂舞實踐,則是我最期待的活動,也是ICTM研究社群特有的儀式過程:畢竟套句人類學家Bloch的話,沒有音樂沒有舞蹈,那還能叫儀式嗎?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綺芳 來去(聽)研討會發表囉:學術社群的年度儀式與展演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833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嗚嗚,我也想去,只是我的暑假都得待在台中帶學生的實習,已經一個月啦,怎二字羨慕了得 !!!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