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類學,還是公共化人類學
編完最近一期以「公共人類學」為主題的人類學視界,感覺意猶未盡,總覺得最近有關人類學公共參與的討論,似乎少了甚麼。到底人類學家做為人類學學科建制的一部分,如何放進我們現在談的公共性的脈絡裡討論?公共人類學包不包括人類學學科建制的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更精確地問,公共人類學是不是只有在某種公共化人類學的過程中,才能顯露其最大批判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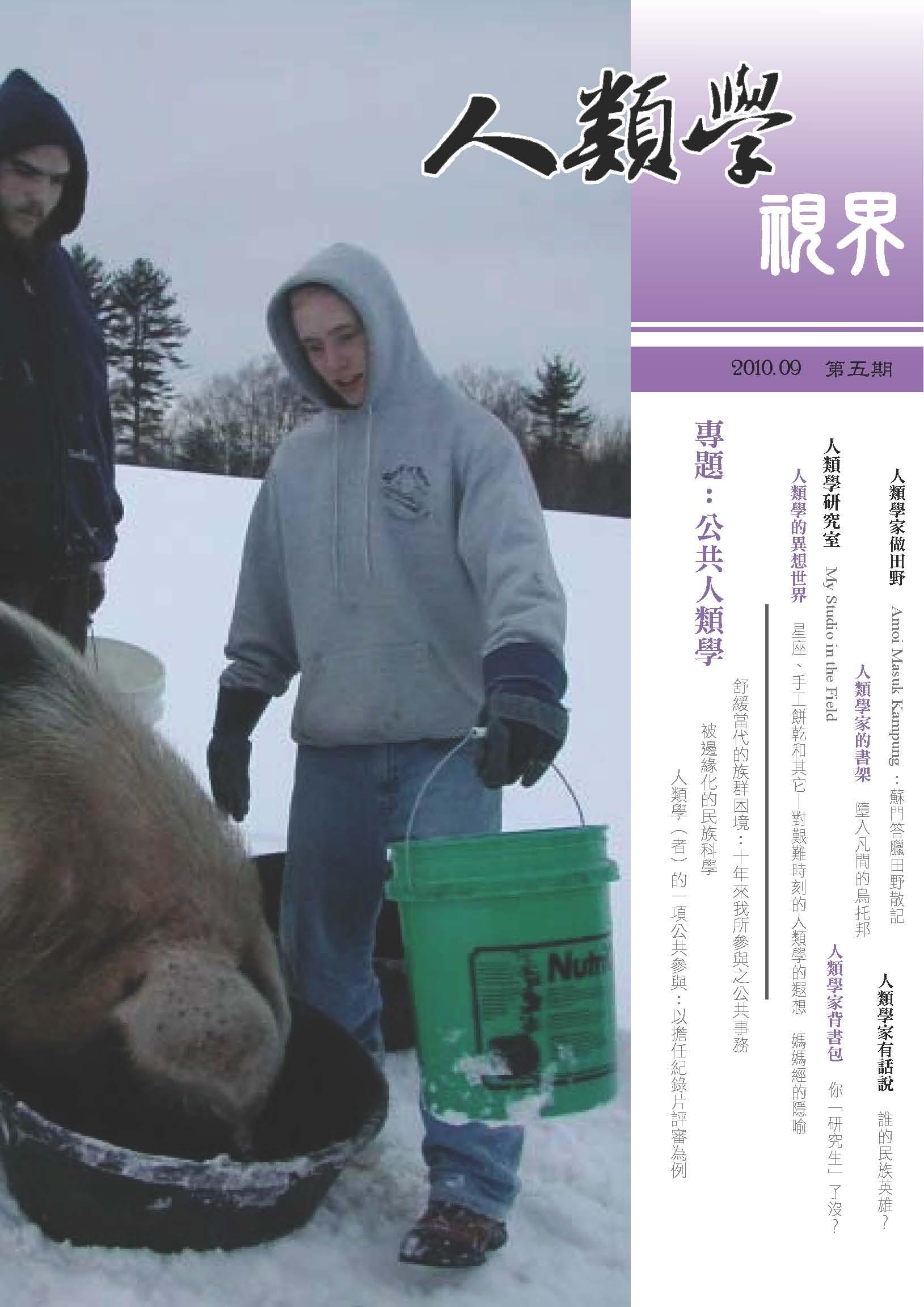
陳奕麟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學院的民主化:邁向理性社會的最後關卡>的文章(社會理論學報,第六卷第一期,2003),雖極具爭議,卻是人類學界唯一一篇有關機構批判的論文。他指出台灣人類學界一直以來和國家權力的緊密關係,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台灣人類學的知識累積方式,學術和社會一直保持著亦步亦趨的關係,雖然這個社會性終究是官方所認定的「社會」。台灣學界從來沒有美國學界因為政學隔離造成的象牙塔現象。
陳奕麟的文章忽略了1980年代末期以來反叛的人類學研究生及其進入學院後的陸續影響,這批學界的生力軍的確改變了人類學對公共事務的定義與介入方式,及其對國家權力的挑戰力道。但是陳奕麟的忽略也許不經意地預言了就算有這群年輕世代學者的衝撞,直至現在,人類學學科建制卻從未真正經歷根本變革。
這個學科慣習比大部分人意識到的還更直接影響我們的學術與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決定了我們的想像力:包括了系所、超組織 (例如教育部、國科會和學會)以及某些學術/社會團體(比如期刊、協會和校友組織)構成人類學場域,透過學術傳統的維持與再發明,相當程度影響內部資源分配、學術審查、人事升遷獎勵與教學養成管道,終極則決定了何為學術理論成就。
陳奕麟文章的爭議之處當然就是在對這個學科傳統生態多所批評,包括殖民主義架構下的本土人類學、單一化師徒制下的唯唯諾諾以及以田野方法論的知識武斷。雖然極具爭議,但最讓我感到不解的則是,這些基本上屬於可受公評範圍的批判,在人類學界卻遭受詭異的沉默以對。
沉默如果來自舊力量的不理不睬,尚還可以理解,但新生代人類學家的沉默 (當然有例外,比如本專欄之前的貼文<一個很低調人類學家之2010年新展望>)則有更深層的制度意涵。陳奕麟在本世紀之初觀察到的學科生態其實已經經過一次的再構造,當教育部與各大學試圖建立一個評量機制,衝衝衝的新生代學者進入一個靈魂探索期。以學術卓越之名,過去以師徒關係為主的學術控制被重新體制化:一方面透過隨意設定的學術標準,大學裡的自然科學及工程勢力伸手進入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另一方面,各個學科內部,年輕研究者們則受困於經費分配、限期升等與獎賞榮譽構成的學術評審大網。重點不是學術評審有甚麼不對,而是新流行的卓越遊戲仍然滲進了舊方法,而且以不那麼容易辨識的學術語言重新包裝,包括了頂尖、國際化、出版等等,但實際上做的事卻很少跟這些詞的原來意義產生關聯。
寫到這裡,也許有人要問本文一開始提的問題,這些學科內省與自批到底和公共參與有甚麼關聯,自我內部再怎麼不堪,怎會影響我們外面的行俠仗義。這個問題讓我想到Susan Sontag的 Regarding the Pains of Others這本書,晚年的Sontag重新反思我們如何看待透過照片傳達的遠在別處的戰爭苦痛,有別於她的早期思想,她認為缺乏了誠意的心,這些視覺的呈現激起不了太多觀看者的同理心,因此也就無法幫助避免這些悲劇的再發生。對我來說,如何將觀看化為見證,正是要同時看到自己和別人身處所在的不公平與殘酷,進而了解這些不同地點的權力暴力與人間苦難其實以某種方式關聯。只有多管齊下,同時挑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不公,真正誠懇的心才有可能生成。正義從來不會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苟且狀態中來到。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莊雅仲 公共人類學,還是公共化人類學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893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雅仲和我預言他要刮刮自己人(包括自己)的鬍子,寫得好。
學術工作本來就是要內外兼治,如何把自我的處境不斷地放進觀看的視野,也才得以不異化學術。照理說,人類學的學科特性要更適合做這工作,因為這個學科本來就是在做自我批評的工作。理想上應該要這樣,但是政治判斷上卻人人殊異。換言之,我們如何可以細緻而大膽,有社會學家的即知即行,膽大妄為,又有人類學家的多愁善感,文化素養。給點處方吧/如何來個近在眼前的民主運功散。
看雅仲講這是編完「人類學視界」專題的感觸,忍不住覺得是在滴咕那個分明高調到不行的「低調人類學家」臨時抽稿,害專欄少了一塊該有的部分?XD(小林尊,出來面對吧~)
然後又覺得「芭樂」其實是某些「衝衝忡」人類學家探索有別於陳奕麟模式的一個嘗試,回頭想想,文章兼具雅仲想串連起來的學科內省和公共參與...(咦,好像提早開始寫芭樂週年慶DM?)
人類學做的總強調深而厚的研究,她對於現前權力結構的辯詰或反叛從來不及社會學立竿見影,但是,對於一個好的人類學者而言,自省絕對也能構成一道深而厚的力量,對自己也對他者或對社會.某師嘗言:容忍,瞭解,欣賞乃人類學的目標.踏進人類學日久,我愈能體味此境.而由新生代人類學者擎起的"人類學視界"或此"芭樂人類學",我倒以為是人類學踩進公共(the public)既鮮明又有趣的一道足跡.無論如何,是個值得擊掌的開端.
我本來以為雅仲本周要寫奶爸經,沒想到推動搖籃的手還是變成了刮鬍子的黑手。
人類學是一個奇怪的學科,以Thomas Ericksen在一本小書Engaging Anthropology(2005) 針對英美人類學,表示人類學大概是最勤於自我批判的。每幾年就有"典範危機",或是"重省人類學"。但是,這些"自我批判"卻似乎從來沒有變成重要的公共議題,弔軌的是,人類學從一開始就是一門經驗學科,而且它的研究對象常常是國家、跨國家情境底下受困的一群。為什麼在英美人類學的"自我批判"走不出象牙塔呢?
台灣人類學的情形呢? 它的確需要系譜學式的分析,探索其中有那些權力、知識、慾望、氣味的糾結?以及有那些比較民主或健康的糾結的可能(沒有沒糾結的機制吧)?
然而,我想到Ericksen的話語彷彿自我實現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台灣人類學的"自我批判"(甚至沒人理睬)終究還是"自我批判",沒能走出象牙塔,因為我們(我們是誰?)還沒證明人類學的"自我批判"是重要的(對誰重要?)。
所以,有可能是公共人類學(以及許多的xx人類學)公共化人類學嗎?
雅仲,寫得好。
最近和幾位比較願意聽年輕人講話的前輩談到類似的問題。他們說,自己年輕時看到這個學科建制化過程的種種問題,立志將來必定進行改革。等到他們進入主管位置試圖進行改革數後年又離開職位後,學科的內部建制仍是問題重重,令他們深感沮喪。
我不是在discourage反省與改革,而是意識到反改革勢力的影武者不斷地製造分身來鞏固霸權。另一方面,我也看過有心改革者,在現有體制中儘管試圖找到對付遊戲規則的戰術,久之也可能接受了遊戲背後的霸權而不自覺。當然,還是有堅持自我批判的理想主義者辛苦地活著。
是否可能找到讓權力結構產生內部矛盾而造成鬆動的機制呢?長期居於底層的Kaka如此妄想著。
藥方早就在那邊,藥引子也有了,就看要不要按帖抓藥了
然後熬碗治病的良藥
2碗水熬至八分滿
雅仲的文章總是學術味道濃厚,還是我們那天年會後巧遇,在公車與捷運上談的議題比較芭樂(還有奶爸的慈父味道)。出去走走的確是必須的(請參考我的部落格:「部落與我」http://blog.gia.ncnu.edu.tw/index.php?blogId=296),這一兩年來,帶學生去參加西拉雅部落夜祭,參與原民會重點部落與原住民國中小資源教室評鑑,跑了許多過去自己作研究時不曾去過的部落,激發了許多有關人類學實踐的想法。
[重點不是學術評審有甚麼不對,而是新流行的卓越遊戲仍然滲進了舊方法,而且以不那麼容易辨識的學術語言重新包裝,包括了頂尖、國際化、出版等等,但實際上做的事卻很少跟這些詞的原來意義產生關聯]
雅仲這段話寫得很深刻,也覆蓋了不少區域。如果我們把它改個詞[重點不是民主有什麼不對,而是新流行的民主遊戲仍然滲進了舊方法,而且以不那麼容易辨識的政治語言重新包裝,包括了依法行政、苦民所苦、人權宣言等等,但實際上做的事卻很少跟這些詞的原來意義產生關聯]。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