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倦的民主
人類學家Arjun Appadurai在2017年寫了一篇〈疲倦的民主〉(Democracy fatigue),收入Heinrich Geiselberger編輯的The Great Regression,以川普的美國、普丁的俄羅斯、莫迪的印度,以及Erdogan的土耳其為主要例子,指出當前有股「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出現,不論是富裕的西方國家或是貧窮的國家都不能倖免,政治菁英都訴諸國家主權遭遇危機,因為民族國家不再能全盤掌握國家經濟,主權不免綁手綁腳。暫且不論國家經濟主權是否為國家主權的唯一基礎,Appadurai說反而不論是掌握國家機器的政客或暗潮洶湧的民間運動都訴諸「文化多數主義」(cultural majoritarianism)、族群民族主義,打壓內部的知識與文化的異議者,反對宗教、性、藝術、文化的自由,並且結合種族主義、排斥移民、獨尊強勢族群的文化 (majoritarianism)。我們可以舉例如川普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強大(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其實是讓美國白人再次強大(make American White great again)。難怪這一波「文化多數主義」常常出現恢復(reclaim)、 拿回(take back)等字眼,似乎宣告著若是無法從幾乎沒有疆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力量中拿回國家經濟主權,至少要能夠鞏固「文化主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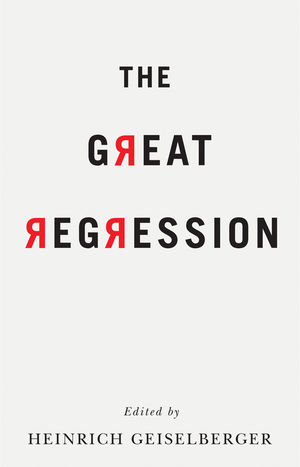
到這裡,Appadurai所描繪的「民粹威權主義」和目前一般認知的世界性的右傾、保守主義當道的狀況相去不遠,所謂的「暗黑人類學」也在處理這種狀況。但是例如英國脫歐(Brexit)以及川普的當選和疲倦的民主有何關係? Appadurai首先引用了美國政治學家Albert Hirschman在經典著作Exit, Voice, Loyalty(中譯:叛離、抗議與忠誠)的概念,作為思考切入點。Hirschman觀察人們面臨了產品、組織、國家提供的服務衰退時,可能會採取的態度,並歸納出三種模式:留下來繼續保持忠誠(我們可以說例如對特定品牌的支持)、離開(例如換個電信業者)、或是發出聲音以求改進。Hirschman進而分析,在甚麼樣的環境下,人們會在這三種態度之間來回,又會花多少時間。當然,21世紀的今天因為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當道,人們表達不滿的方式已遠不同於Hirschman寫作的197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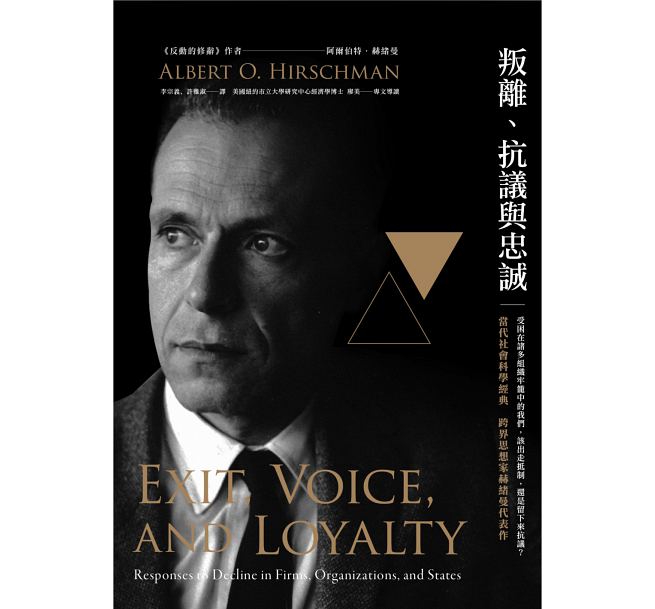
接著,就是〈疲倦的民主〉一文最有趣的部分。Appadurai轉化Hirschman的概念,認為Brexit其實正是是英國民眾發出聲音(Voice),表態要「離開」(Exit)歐盟;Trump的美國、Modi的印度、Erdogan的土耳其也大致如此,正是當地人民以選舉「發出聲音」,表示要「離開」民主。面對代議政治或整個國家失靈,人民參與選舉不再是選擇留在民主政治中發出聲音以求改進的舉動,而是表達對民主政治的「疲倦」而希望脫離。上述這些民粹威權主義的國家都有對民主疲倦的現象,選民票選出的領導者都主張要終結民主政治裡的自由、審議、容納(inclusive)的特徵。Appadurai接著指出,獨裁者利用民主的失敗而崛起,歷史上比比皆是,例如史達林、希特勒等,那麼當代疲倦的民主有何新面向?
Appadurai列出三個新的因素,首先,社群媒體大行其道,創造了網路意見同溫層。其次,民族國家失去國家經濟主權。最後,基本人權的意識形態廣佈全球,使得外國人、陌生人、移民也都能在不友善的國家內引用此一意識形態主張自己的權利,反而造成普世人權和以民族國家為基底的公民權利有所衝突。這三個因素加起來,加深了人們對適當程序、審議理性、政治容忍的不耐煩。與此同時,全球性經濟不平等加劇、社會福利體系崩解、財政金融事業興盛,在這些快速變動的經濟焦慮之下,更讓人們難以容忍民主政治運作的緩慢步調。政治菁英討厭民主,因為民主妨礙他們獨攬權力,而他們的追隨者則是民主疲倦的受害者,以選舉作為離開民主的最好方法。政治菁英對民主的厭惡以及追隨者對民主的精疲力盡卻在文化主權裡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強調種族勝利、族群淨化、「軟」實力的復興。這些所謂的「共同文化立足點」卻遮蔽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之間的重大矛盾,而裙帶資本主義屢屢見諸於這些高舉民粹威權主義的政治菁英裡。
Appadurai上文自己說,歷史上多有民主失敗(靈)、民主倒退,而我們可以說這些狀況的另一面就是民主深化、民主漸進等解決方案,因此可以想見民主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免費禮物,需要時時勤拂拭。同時,每一次民主失敗卻會導致不同種類的民主退步。我自己覺得有趣而且值得演繹的是,為什麼他要用「疲倦的民主」來指稱此次的民主退步呢?
我自己的猜測與衍生詮釋是如此的:過去三十年來,因為資本流動自由而快速,加上科技急遽發展,使得勞動不斷彈性化。也就是說,常態而固定的工作越來越被不斷流竄動的資本放棄;加上產業與科技性質持續更新演化,勞動者對於工作與未來的不確定感越來越強,彷彿自己隨時可能被他人或機器取代。於是,現代人總被鼓勵要發展第二、第三專長,沒有人認為一招半式就可以繼續走跳江湖;君不見大學教育中雙主修、跨領域、短期學程紛紛出現,早已經反應此種趨向與焦慮。新經濟不斷許諾成功屬於多元、活潑、有創造力的人,只要具有靈活創造力,世界便無限寬廣。網路世界似乎是具體而微地展現出無限寬廣的世界,問題是大部分的時候不是我們走向世界,而是世界走向我們,拜行動通訊科技之賜,我們幾乎時時可以被找到,也被期待找到。
當人們受鼓勵與期待發展自己無限的潛力因而必須時時注意各種新創之物的時候,人們的注意力卻總是被各種資訊包圍。人們能夠接觸到理論上無限寬廣的資訊(其實大致上只是被幾個大型蒐尋器的運算法所左右),卻因而常時處於資訊不足的焦慮。人們投入注意力蒐集資訊,注意力卻常被中斷。於是,疲倦(fatigue)、筋疲力盡(burnout)、枯竭(exhaustion),成為形容當代人們的身心狀態的最生動寫實的幾個流行語(catchword)。我們都知道筋疲力盡不只是生理勞累,好像一天辛勞工作後身體不聽使喚,只想好好休息;筋疲力盡大致上指非常投入、積極奉獻的人,經過強烈持續地專注於某個目標之後,卻出現失望、剝落(detachment)的狀態,有時甚至陷入長長的倦怠或喪失信心。以上不是心理學式的描述,雖然心理學絕對有關,但我嘗試社會學式的描述,勾勒人們的疲倦的社會背景。
我推測,也許就是在這個當代情境之下,Appadurai不用民主的失落等來形容這一波的民主倒退。因為這一波的民主困境不是傳統觀察到的公民冷漠、參與度不足等現象;恰恰相反,是因為人們非常投入,甚至帶有基本教義般的狂熱,進入到民主政治,或至少是選舉代議政治,而他們的動機與其效果卻反而終結了民主,或者至少是晚近的多元民主。最後,如同每項診斷都被賦予提出解方的期待,對民主倒退的討論亦然;其實民主理論家大致上也多採取這個「症狀→治療」的論述策略,Appadurai自然也不例外,他以回到歐洲的討論來提出他的解決方案,但我不打算再敘述他的方案,因為我不是民主理論家,難以對這個方案有所評述。我感興趣的,是以疲倦、筋疲力盡、枯竭形容當前政治行動與想像的現象。原因很簡單,我自己作香港研究很難不碰到香港人說自己疲倦、筋疲力盡,無論是指涉不斷攀升的樓價,或是2046年之後何去何從。台灣的後太陽花運動時代是否亦如是?或者總的來說,新經濟的主導是否也讓台灣社會疲倦、筋疲力盡?

我想到人類學家Alberto Corsin Jimenez(2017)的一篇文章卻對筋疲力盡、枯竭(exhaustion)提出完全不同的詮釋。當然,這位激進的人類學家兼政治行動者的說法頗有無政府主義的味道,但是他對於筋疲力盡的論述卻令人耳目一新。Corsin Jimenez借用科學史學者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一本書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中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詮釋觀點,重新演繹耗盡(exhaustion)。也就是,當代政治理論的開山祖師之一Thomas Hobbes(霍布斯)和同時代可說是近代化學的奠基人Robert Boyle(波以耳)在17世紀時關於知識與自然哲學的交鋒。當時,波以耳為了解空氣的各種狀況,常常把試管裡的空氣抽盡(exhausted of air),創造出真空狀態,從而開始各種實驗,後來發現在真空狀態,物質無法燃燒,從而揭示了空氣是燃燒的必要條件。然而對於霍布斯而言,真空或耗盡卻是令人討厭的危險狀態,所有企圖枯竭、抽空重來的行動(或實驗)都造成本體論上的混亂,衍生出各種難以歸類的現象,猶如公然宣揚異端(Shapin and Schaffer對霍布斯此一觀點的重構也惹來許多的批評,但那已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
Corsin Jimenez認為,當代政治基本上建立在對枯竭、耗盡的反對之上,枯竭、耗盡正是混亂的自然狀態互相牽制甚至內戰的結果,Leviathan(巨靈國家)於是興起帶來穩定秩序,政治正好是阻擋人類社會遁入、倒退到枯竭、抽空的狀態的方式。於是,當代科學(化學)企圖從抽盡雜質開展各種實驗開始,當代政治卻從避免枯竭開始,亦即由國家主權(政治)的建立維持秩序開始。Corsin Jimenez以他自己對2011年佔領馬德里的事件的民族誌研究指出,馬德里市民在佔領街道、公共空間的過程中,也面對了各式各樣的筋疲力盡、枯竭,包括因為無政府式的集會、長期的佔領卻看不出效果,所以參與者都表示某種程度的耗盡。然而Corsin Jimenez說,佔領參與者卻因為抽盡的固有的執著或某些政治形式的想像,反而開展出生機蓬勃的實驗(political exhaustion and the experiment of street),蘊育了全新的政治主體的可能。

Puerta del Sol in Madrid during the 2011 Spanish protests, from wiki
Appadurai和Corsin Jimenez所指的政治疲倦或筋疲力盡明顯的有著不同來源、不同形式和規模尺度,但是無論疲倦的民主或政治筋疲力盡都源自於目前代議政治的主導、佔盡我們對政治的想像,於是一個狀況是人民用選舉政治離開代議政治,另一個案例是抽盡、耗盡人們對政治行動的假設,於是有了真空狀態,從而開始各種實驗。前者因為疲倦形成了過去十年民主政治的巨大變動,後者耗盡原有、形成真空,一樣有巨大變動的可能,對個體、對目前代議政治。疲倦遍在,我們有可能淘盡之後重開新的政治嗎?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容邵武 疲倦的民主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5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