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間諜》書評
最愛的人傷我最深?監控檔案中人類學家的間諜分身
如果你得知國家檔案局收藏著關於你的監控檔案,裡面布滿威權統治時期特務和線民為你量身訂製的觀察紀錄,你是否會有勇氣申請閱覽,一窺當年壓迫體制形塑的「你」的樣子?是否會追問曾經有哪些人,在什麼情況下,基於何種理由,選擇與政權合作,做出不利於你的證詞,操弄關於你這個人的「真相」?
以研究東歐社會主義體制著稱的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自1970年代第一次到羅馬尼亞做田野研究起,就受到當時共產獨裁政權秘密警察的嚴密監控。她按照人類學訓練的優良傳統,努力學習異國語言,設法建立友善關係,融入當地社會,蒐集關於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慣習、制度等各方面資訊。孰料,這些從事民族誌田野研究的必備技能,在當局與西方民主陣營對峙及排外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視框下,在在成為強化她就是美國CIA間諜的「證據」。但年輕學者凱薩琳,對這些指控,以及她墮入其中的險境,渾然未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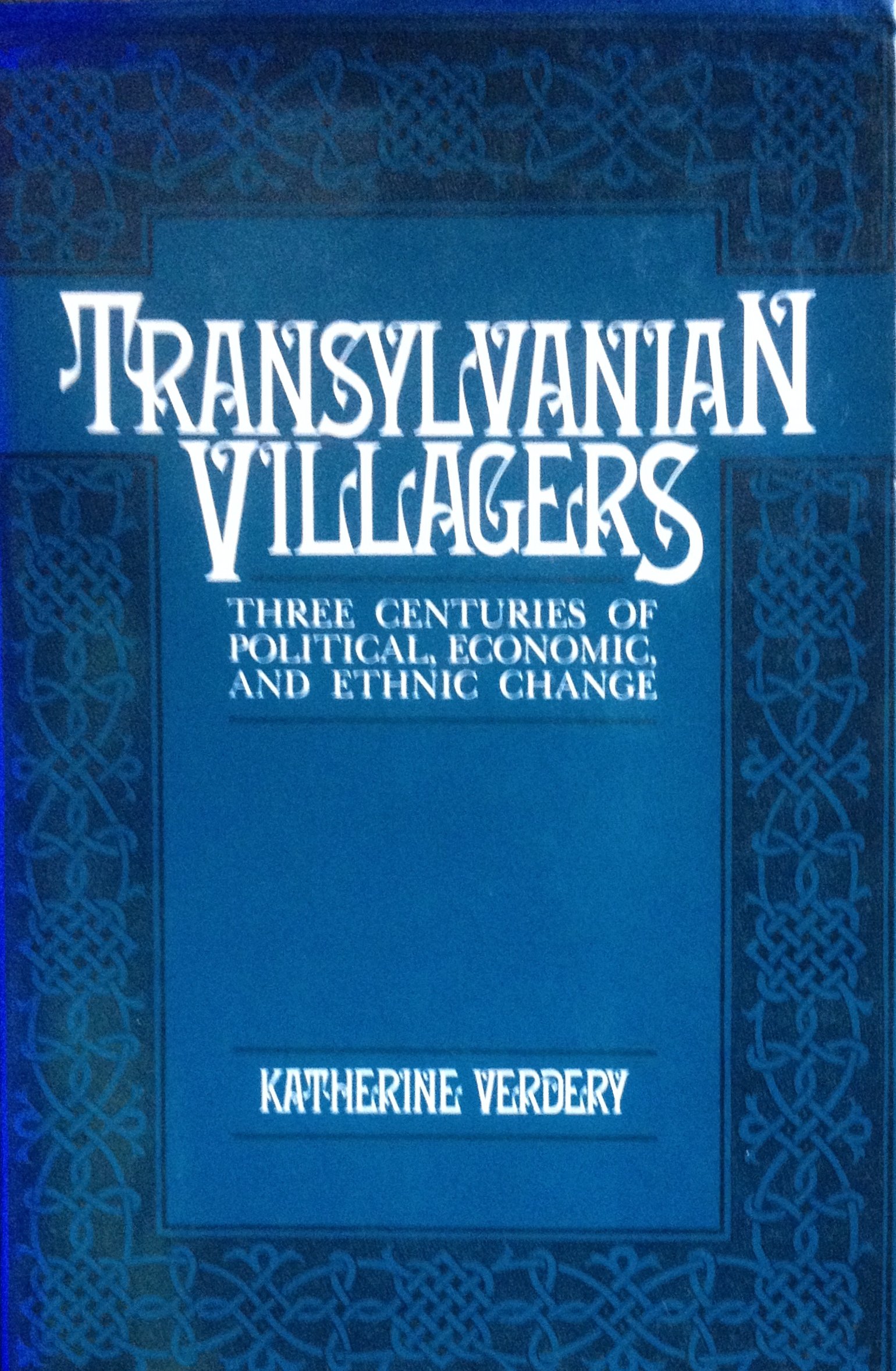
多年後,當凱薩琳翻開一整個行李箱的監控檔案,被出賣的痛苦,冷不防地迎面襲來。她驚駭地發現,當時的自己彷彿是一隻被巨幅隱形蛛網捕獲的獵物。每回落腳的飯店房間安裝了監控設備,入侵她生活最私密的一面;秘密警察的線民監控網,幾乎緊貼著她田野人際關係網絡而佈建,許多她情同家人的報導人與摯友,也在那張鋪天蓋地的網羅之中。「你怎麼可以如此對我?!」總是傾向信任,待人誠摯熱情的女子凱薩琳,悲戚地吶喊。
待情緒稍緩,凱薩琳展現了偉大人類學家的特質:將遠陌者拉近,以試圖理解,將近熟者放遠,以啟動反思。她選擇懸置定見與評價,把橫跨十餘年,高達兩千多頁的個人監控檔案,當成研究秘密警察監控體制如何運作的田野材料。民族誌學者凱薩琳返回羅馬尼亞,重訪監控檔案中經常以化名遮蔽、但終究被她猜出實際身份的線民/朋友,並且嘗試與那些負責網羅線民、擬定監控計畫的軍官會面。
原來,田野中親近之人都聽過凱薩琳是間諜的傳聞,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堅信不移,大部分無所謂是與否,但確實有不少成為當局監控網絡的眼線。原來,一九八零年代以降的秘密警察,一脫過去令人聞風喪膽的惡魔形象,以更複雜的面貌,嵌在羅馬尼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是禮拜天一起上教堂、打牌的朋友,是人們需要喬事情時求助的對象。當然,被他們主動找上門的,驚惶失措自不在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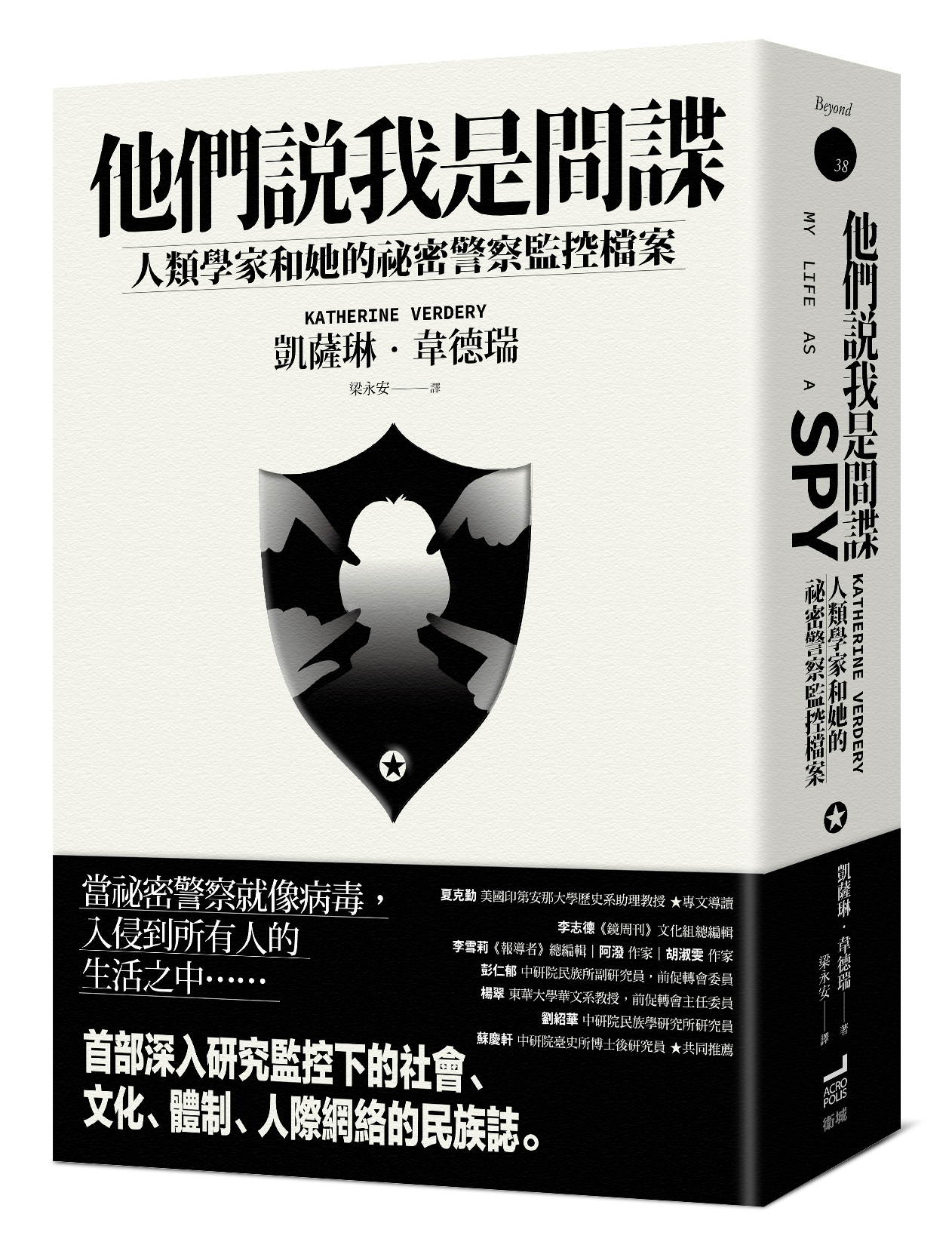
在如考古挖掘般逐漸出土的複雜「真相」中,教凱薩琳最難理解和面對的,是檔案中摯友對自己的負面描述。如果秘密警察對於她「邪惡分身」繪聲繪影的描寫,讓她懷疑自己是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果真當了CIA的間諜,摯友們親筆寫下的對她不利的報告,則從根本上撼動了她對於自己是不是一個好人的信念,以及她在羅馬尼亞維繫了三十多年的珍貴情誼的真實性。她假借其他被監控者的見證,坦承讀自己的檔案是個「讓人痛苦的過程,可以毀掉友誼,甚至毀掉婚姻」。
在與監控她的線民/朋友和秘密警察對質的時刻,凱薩琳將磨練多年的田野研究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或許是她最接近間諜心理狀態的時刻?)。儘管內在波濤洶湧,她沉住氣,騰出足夠的心理空間聆聽,讓對方盡可能安心地傾訴,試著同理說話者,與之共感,甚至如心理師般,涵容對方朝自己拋擲的情緒。然而,一名與她結識不久便被秘密警察吸收為線民的好朋友的真心傾吐,幾乎將人類學家逼至崩潰邊緣。好友揭露的內容從坦承經過,分享箇中糾結情緒,翻轉為指責:「你帶給我多大的傷害啊!」責任的箭頭驀地倒轉,被監控者竟反倒成了加害者?!這或許是難以直視無力抵抗壓迫體制、背叛了友人的自己,為求自保而出現的防禦投射,但是,逼使一個人成為不願成為的自己的,終究是壓迫體制中握有決策權的人們。
那麼位居壓迫體制指揮鏈上不同層級的情治機關負責人,是否曾意識到自己的任務對許多人的生命帶來嚴重程度不等的戕害?很多羅馬尼亞朋友告訴凱薩琳,不可能會有秘密警察想要跟她碰面的,他們都簽署了保密協議,現身吐露真相,會是對同儕的背叛。但也有朋友教凱薩琳以花束示好,表明來者非敵,竟然真的讓昔日特務軍官打開了門;儘管是暫時而有限度的打開。「我的指導原則是不造成傷害」。就如「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重要執行者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說詞,與凱薩琳會面的三位軍官,都以「盡忠職守」做為自我辯護的基調,認為自己不過是在工作崗位上盡應盡的本分,沒有做出傷天害理的事。然而,正如漢娜・鄂蘭藉「惡的平庸性」所欲指向的終極批判:毀滅性的惡,往往是由諸多看似平庸的決定及作為堆疊而成,進而令所有參與龐然非人罪行的人們的罪惡感,得以獲致救贖式的淡化稀釋,更難以藉由召喚良知,使參與者現身負責。
應是人類學訓練中對異己同理共感,以及對複雜事物多元向度保持開放性的要求使然,凱薩琳最終並未對線民和秘密警察是否應為傷害負起責任的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然而,這也可能是因為以她為原點的外擴監控網絡所含攝的人們當中,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那些被迫離開羅馬尼亞、丟失職位,或成為線民的朋友。倘若她周遭的人們,曾因被當局懷疑的「輻射性」或連坐法,遭到酷刑、被關押數年,甚至喪失性命,或許她會做出不同的結論。
在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中,常有論者指出,威權統治體制下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位置並非二元對立,而往往介於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灰色地帶。此言不啻為真,且直指許多被捲入其中之人的真實處境,如同凱薩琳在這部自我民族誌的案例所呈現的。但我們須謹慎地不讓思路就此停滯,避免讓抹除權力位階、主體行動選擇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差異的虛假和解論述,取代了對於複雜真相和責任釐清的追索;更不應落入人人皆是共謀加害者,或人人都是體制受害者的和稀泥式嗟嘆,而以「荒誕的歷史悲劇」草率作結,彷彿沒有人需要為威權統治時期大規模地發生情感撕裂、人性扭曲、生命驟然崩毀的個人和集體創傷負責。
《他們說我是間諜》展現了人類學民族誌擅長的細緻田野研究,有助於彰顯壓迫體制運作的特性和複雜度,精準地剖析位居其中不同環節人們的差異處境,因而能有效地在轉型正義工程探討如何適切究責時,為難以考量個別差異性的法律機制設計提供補充。即使同為負責監控和「養案」的特務機關幹員,主導審判程序的軍法官,主責取得政治犯自白書的審訊者,在每次執行任務時,仍然有著動機、態度、行為和對待上的差異,這在追究責任時是必須考量的變項。本書亦提醒了監控檔案裡所鋪陳出的「真相」有所缺漏和扭曲,因而延伸出許多轉型正義工程中需要詳加思考的問題,如歷史真相可能被還原到什麼程度?什麼樣的真相重建和認識,真正有助於社會成員確認彼此共享的核心價值?而社會集體又準備投注多少資源、精力和時間處理威權統治留存至今的諸多遺緒?闔上此書,我不僅開始期待台灣社會能盡快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花束,讓昔日威權體制參與者願意開口訴說,而我們的人類學家,是否準備好聆聽他們的心聲?
※本文最早發表於鳴人堂鳴人選書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彭仁郁 《他們說我是間諜》書評:最愛的人傷我最深?監控檔案中人類學家的間諜分身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44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