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民懂得怎麼笑,那是他們唯一的專長」之〈台北.郝郝幹〉篇

2012年3月28日,台北市政府批准建商以「維護多數都更戶」為由,通過強制拆除王家建物。這使得這股對於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的怒火,轉而自市府內部延燒:台北市政府顧問施正鋒率先辭職,接著擔任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等三名律師發表聲明請辭。此時,社會上持續蔓延〈都市更新條例〉中對於「居住正義」的藐視、相關「人權」議題,乃至「官商勾結」疑慮等憤怒情緒。
而在鄉民社會裡,對於台北市長的揶揄調侃自不在話下,其中包括:
◎第一次拆厝就上手

◎台北好好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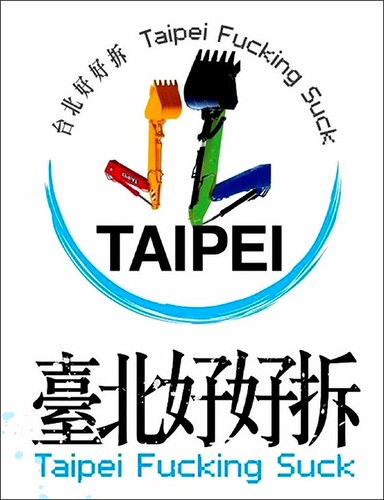
◎全能住宅破壞王

◎極權樣板之「同志們!給我拆」

在這些極盡挖苦反諷的文案中,〈台北.郝郝幹〉多了一分值得討論的內容:

要分析〈台北.郝郝幹〉的嘲弄技法,我們必須先談談200多前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個故事:「貓大屠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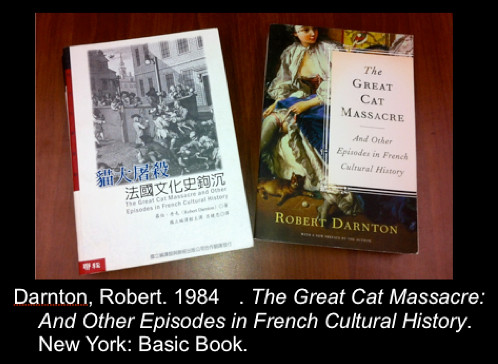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系Robert Darnton以18世紀巴黎的印刷廠工人,在狂歡節時屠殺貓作為該著作的主題,闡述了這群工人如何藉由節慶的儀式性顛倒常規,非常態式的恣情放縱中,以諷刺來達到羞辱資產階級老闆的娛樂方式。在此一狂歡節慶中,以貓在特定文化下的巫術魔法、性的象徵意涵(諷喻戴綠帽的丈夫),同時又是當時資產階級的寵物等三項影射,巧妙地(或者詭計地)將貓轉喻為印刷廠老闆的妻子,「彷如她是在叫囂、廝殺、姦淫同台演出的野貓夜會場合中發情的母貓」。結果是,在這場「無法無天卻又歡天喜地」的屠貓審判中,工人們意念式地強暴了印刷廠老闆娘,因此使得駑鈍的老闆「淪為喜劇人物中戴綠帽丈夫的樣板角色」,並且安然無恙地全身而退,閃避所有可能抵觸的社會規範以及因此帶來的懲罰——「印刷工人知道怎麼笑,那是他們的唯一的專長。」
相似地,我認為「鄉民懂得怎麼笑,那也是他們唯一的專長」。在〈台北.郝郝幹〉中,原先台北市政府的「北」字圖像交由挖土機的怪手所編輯置換(一如〈台北好好拆〉),接著鄉民以「2010台北花卉博覽會」中所舉辦「台北好好看」系列活動作為「台北.郝郝幹」的諧音擬仿。同時,此一「郝郝(好好)幹」又再現郝龍斌對自身的高度期許:
郝龍斌上午在追思會和新書發表會中指出,孫運璿有如他另一個父親,一直鼓勵他好好幹,不論是他選立法委員、選台北市長,孫運璿一直鼓勵他。他說,孫運璿是大是大非的人,一生奉獻國家,對事認真執著。在來追思會途中,他想,如果今天孫運璿仍在,他最想說,『孫伯伯,我一定會好好幹』。」
——2007.2.14《大紀元》報導

於是,〈台北.郝郝幹〉成為一件「正面期許」的制服外衣下,赤裸地曝露鄉民集體情緒下兩層面的羞辱語言:一方面郝龍斌市長被網路鄉民以父執輩之姿勉勵這位乖巧的公僕兒子認真做事——「有如他另一個父親,一直鼓勵他好好幹」。正因這類「長輩對晚輩」劇碼是如此的樣板,這種嫌膩感反被諷刺地刻意拋棄在郝市長的身上。另一方面,18世紀的法國屠貓審判中,印刷廠工人因為有狂歡節作為宗教背景的保護傘,虐貓行為成為一項暗諷式娛樂;相對地,網路鄉民也因為有了第一層面「正面期許」的加持,真正的意圖使得郝市長一如印刷廠老闆娘一般遭到意念上的強暴。更為淫穢地,郝市長當初的「我一定會好好幹」的「自婊」期許,仿若承諾了「立志成為一位毫不矜持、何其容易的公妓。」(抱歉!字詞選用應為[男支]。)如此一來,郝市長不僅是印刷廠老闆娘般的犧牲者,他也是那位資質駑鈍的印刷廠老闆,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遭到鄉民社會的訕笑。
很大程度上,〈台北.郝郝幹〉簡直重現了18世紀法國「屠貓」詭計的特徵元素:針對特定人物(資產階級老闆或是掌權的政府高官)的不滿情緒,卻反向表達刻意膚淺的良善關心,以一種集體狂歡的惡整方式,滿足性暴力的戲謔想像。郝市長在這波冷嘲熱諷的網路文宣中,自然無法正式回應任何玷辱的文案,因為他愈是認真看待自身受到的傷害,便愈是突顯並且證明這些侮辱性文案的正當性,而使得自己在鄉民社會的「當真你就輸了!」基調中再次出醜。於是,鄉民(一如印刷廠工人)在無法無天卻又歡天喜地的審判中安然無恙地全身而退。
網路鄉民特有的嘲諷技藝是一種de Certeau式的抗議戰術。或者,這也是對於權力(的現代性)集中,展現出狂歡式(後現代的)分裂寓意:在場景佈置(mise-en-scène)的經營中,「改編篡寫」使得歷史事件變得既真又假,「好好幹」便失去了原先意義的一致性。於是,意義變得更加多重難以單一指認。又或者,這也是Geertz(以及Bateson)以為的「精神氣質」,使得網路這種戲謔形式所形塑的「精神氣質」,無法以一種嚴肅的口吻反駁以保留自己的尊嚴。無論如何,郝市長是再也回不去了。
〈後記〉:這是小弟正在著手的「〈Emma的信〉(2010台大宿舍外籍生霸凌事件)——網路文本變裝秀與現實/虛擬交換術」中,討論「真實模倣虛擬」特徵(角色重演、同步摹仿、改編篡寫、山寨複製)中的篇外篇討論。我的中文不好,不成熟的地方,請各方前輩指教。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小林尊 「鄉民懂得怎麼笑,那是他們唯一的專長」之〈台北.郝郝幹〉篇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3363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原以為是大學、碩士生的知識理論演練或是鄉民的戲謔分析,沒想到是出自學者的學術書寫,這就得更為嚴謹的態度去閱讀。學者藉知識對社會現象進行「文化政治」的分析,不應只是將理論知識的概念予以「元素化」,去脈絡地挪用,就好像Foucault的「規訓」可以去脈絡、概念元素化地拿來分析各種權力關係。
以彈吉他來說喻吧。在缺乏封閉和弦(無論是用食指或capo)之下,相同的和弦指法在不同把位上移位並不會有升降key的和弦效果,而是混亂。本文便是用開放和弦的方式,用類比的指法進行位移: 郝市府(權貴或資產階級)、鄉民(印刷工人)、網路kuso(印刷品)、好好幹(貓的模稜象徵)。這些看似「合理」的對位,具有同樣的「巧妙」張力嗎? 讓本文的「開放指法移位」聽起來具有某種魔幻正當性的,便是de Certeau關於策略/戰略的理論運用--這樣的理論配置讓對比彷彿無須某種「封閉和弦」般的條件,讓各種元素化的東西脫離脈絡,在理論概念的作用下得以開放地悅耳(正當)--試想,如果本文沒有拿de Certeau的理論來加持,是否會少了些力道?
留意理論或知識的脈絡,或者說,要去掌握其背後的框作。譬如,Goffman提到監獄中囚犯可以把衛生紙、湯匙當作某種可利用的工具(傳遞訊息或破壞),這當然是對物品原先設定的「巧變」,並且在不同的框作(re-framing)下被挪取佔用。我們日常生活當然充滿各種物的挪用,然而,如果沒有任何特定的框作脈絡,我拿牙線棒當作水果叉、拿碗來喝茶、拿沐浴乳刷馬桶,這樣的指法看似合理對比,但有何張力和意義?
Robert Danton所談的年代和社會脈絡,有君主權威、有貴族、有查禁、有資源或條件侷限的文化生產,這是張力之所繫。在當今行政官員民選、行政依法(法由民選立委而非市議員片面訂定)、網路生產門檻低且形式多元、政黨政治對立等等全然不同的脈絡下,有關「鄉民」的分析還能開放指法般地對比於印刷工人嗎?當網路訊息是鄉民垂手可及的資源,當「鄉民」的身份如此飄渺,當鄉民的kuso戲謔成為當代網路社會的「過份景觀」(spectacle of excess),它還具有多少「貓的屠殺審判」那般的興味以及文化政略的作用?郝市長或市府如何被戲謔都無妨,但是,如果幾年前都更法在立院通過獲得立委諸公、媒體、學界一片好評,那麼今天該被戲謔的對象還有哪些?鄉民的戲謔的張力如何彰顯?如何把戲謔的張力轉化為一種對民主政治、官僚體制、媒體熱潮和遺忘更具整全的文化政略(而不只是淪為對個人的醜化,同時也可能是誤導)?這是不是說現今任何的kuso或凡鄉民所為所言皆達到戲謔的妙境(如同把選戰中的「非常光碟」當作庶民媒體而獲得正當性)?我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標準答案應該在座落在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當中。既然本文想要進行類比對位,我認為作者應該為自己的分析找到一條封閉和弦的脈絡條件,好讓指法在不同把位上不至似是而非,而是能夠聽得出升降key的巧妙。
怎麼覺得第一個回應本身在此部落格與這篇文章的脈絡中,是一種「開放合弦的位移」(對了,封閉合弦就一定是相對有脈絡與框架的嗎?被封閉這詞給影響了吧,封閉合弦反而可以有更多的彈奏變化。要看曲調與如何運用吧?這比喻總覺得怪,誰比較懂樂理,可以說明一下嗎?
毛毛!給你一個讚!(因為我也不會彈吉他...)
哲良,我沒有即時回應,主要因素是因為在你我的位子上,我已經機巧地佔盡便宜:「在〈芭樂人類學〉中,『當真你就輸了!』」於是你的認真期許反倒再次以另一種諷刺的語言形式被快速消化掉。(附加因素是因為我也不會彈吉他。哈!icep,你開心了吧!)但我很樂意面對你的批評並且謝謝你。我同意你的說法,但卻不是我所興趣之處。我用一種殘篇破碎的方式盡可能表明我的書寫立場:1) 這篇文章就是戲謔。把「郝郝幹」說得像是一篇研究,為的是去包裝書寫下另一個「包藏禍心兼自娛娛人」的壞心眼企圖。2) Darnton的新文化史「屠貓審判」,有一半顯然當真,另一半則是向我的母校老師致敬(另外來說,這恐怕是我處理自身「學術寂寥」的僅存形式了)。3) 我有興趣於「拉伯雷式的放縱大笑」,但最終我想回到人類學經典著作Bateson的《Naven》,一個在新幾內亞的Iatmul族人的特定儀式,其中內容涉及反串、變裝、嘲諷、性暗示等主題。(George Marcus曾經向我感嘆:「現在還有人在教《Naven》嗎?」「我還在教。」我這樣跟他說。另外一個原因是普林斯頓大學詮釋人類學對於修辭與詮釋學的偏好。)你可能仍會如此認為:「文脈和意義張力的問題仍舊一樣呀!」我並沒有企圖敷衍或是閃躲(其實我很想),或許「(我的)人類學的意義探討」與您的期許沒有很麻吉(不過這樣不是更好嗎?)。4) 雖說人類學家的工作場域終究在「田野」裡,但是在學院任教有很大的硬限制。有一次的機會下我向村上春樹提到他「書寫風格」的轉變(口氣正如同你一般當真),他這麼回答我:「我有好幾雙鞋子。。。」此時我如此地羨慕他。
小林尊,謝謝,也很高興得到你層次豐富的回應。很抱歉現在才發現你一個多月前的回應,因為前後兩次拜訪這裡,都是來自朋友臉書的分享(我以為系統會主動發出回應通知信件)。順道分享,第一次得知這文章是來自一位學圈朋友,她是出於捕捉到「芭樂」的興味分享文章。這次是另一位非學圈的友人所分享的,我貼出他附在分享前面的留言:
「請記得。
低級的謾罵,就像小丑,可以快速籠絡群眾,但也可以快速點燃瘋狂。
如果是為了這個社會的成長,批評絕對有更好的和理性的方式。
最近許多事件,暴露台灣的環境充滿謾罵,和毫無幫助只是煽動集體負面情緒的宣傳方式。(比方說:台大事件嘲笑校長的超能力,對於幫助居民到底有何意義?牽涉到人身攻擊,或是人肉搜索,這就是自由言論的展現嗎?)
很大程度上,〈台北.郝郝幹〉簡直重現了18世紀法國「屠貓」詭計的特徵元素:針對特定人物(資產階級老闆或是掌權的政府高官)的不滿情緒,卻反向表達刻意膚淺的良善關心,以一種集體狂歡的惡整方式,滿足性暴力的戲謔想像。」
這前後的對照剛好是詮釋學的效應,而且我相信不是單純的讀者方的"正解"或"錯解"(都屬於詮釋性的理解),而是巧妙的戲謔書寫策略所產生的異質空間。鄉民手法的拉伯雷式嘲弄,本身就有相當微妙且多義的曖昧屬性;要在二維層次上去捕捉或分析,卻又不失其原有的興/腥味(就像要幽默地去解釋幽默),就得有非一般學術性的書寫策略。其實,初讀你的文章,是可以領略出當中的「芭樂味」的。對我來說,除去貓的屠殺的對比,依然能保有這樣的閱讀興/腥味。
當然,如你所言,我有所關注但不是你所興趣的部分。我還難以明確地說自己是何種確切的關注下去看待鄉民在當代多元多層的複雜政治情狀中的嘲諷效應,或許,那是接近一種倫理學的關注吧,即便這是一種異質的出發點。
我很喜歡村上村樹給你「好幾雙鞋」的回答,也能夠感知你的羨慕。即便是「小說家」這樣的身份,可能都有好幾套衣服和好幾雙眼睛。他對我最有啟發的一篇短文,《地下鐵事件》末的〈沒有指標的惡夢〉,是比任何學者還深刻、細膩、包含靈肉的分析與省思。我的鞋子還不夠多,倒是能夠轉換閱讀的心境與期待。
先前給你的回應,起語有些不恰當,也請包涵囉!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