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瘟、薊馬與經濟人類學的啟示
「市場」是怎麼被造出來的?
農委會在2018年宣佈7月口蹄疫「拔針」,也就是說豬隻們將不再施打口蹄疫苗了。農委會這個舉動是希望台灣可以從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所列管的「口啼疫疫區」名單中「畢業」除名,以期恢復過往台灣豬肉外銷市場的榮景。
當年1997口蹄疫爆發後,一年近1700億左右外銷豬肉市場蒸發。過去二十年來,好不容易重新複甦的豬肉市場,在近月來非洲豬瘟(Asfivirus)的陰影下,再度如臨大敵。非洲豬瘟的個案,凸顯出看不見的病毒、市場、豬農、防疫單位等各方行動者,都被糾結在這個複雜的事件當中。

過去,我一直在關注台灣鄉村及農業發展研究,但在尚未深入田野之前,我其實沒想過我的研究會涉及多物種的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ants)(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所有的人及非人都等同具有能動性,而能動性乃是一種相互協作的成果)。
還記得在一個風勢強勁的十一月天,我站在田邊和來自農改場的研究人員,看著另外一旁的研究員將數袋的「緩釋肥」倒入轟轟作響的農耕機當中,然後慢慢地將這些肥料攪拌均勻、拌進田埂之中。農改場研究員指著一旁的費洛蒙驅蟲設備告訴我,透過肥料和這些小裝置,將可以有效地控制「薊馬」以及「夜蛾」等「寄生蟲」,如此便提高主要出口蔬菜之品質的穩定性。在開始進行我的「農產品市場形構」研究的田野考察初始,我已經愈來愈習慣不再單單是和農改場的研究人員、外銷業者以及農友等「人類」互動。我同時也意識到「農業外銷市場」涉及數不盡的「非人行動者們」。他們成為我必需回反覆回到研究室,打開電腦重新認識的對象,而且條目似乎愈列愈長。
在人類學農民研究(peasant studies)或是經濟人類學的「市場」領域當中,這些「非人」物種向來是被噤聲的,頂多被視為農民勞動過程的生產投入或是被馴化的對象。事實上,幾個重要的人類學農民研究相關的刊物,如《農民研究》(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所收錄的多數文章,仍然時常圍繞在少數幾個經濟人類學延伸出來的論辯:形式主義vs.實質主義或是古典的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s)等。前者的論辯主要集中在「市場」這個概念,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在分析非西方的農民社會。而農業問題的論辯,則是探討到底「小家庭農戶」是否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消失。這些研究在看待所謂的「農民社會」或是「農糧市場」時,總是千篇一律地仰賴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anthropocentrism)。
不過,關於何謂農糧市場的看法,近年來開始改變了。而這些具有新意及洞見的見解,和人類學領域近來的本體論轉向大有關係。這些研究成果受到晚近幾位知名學者的影響,如:Bruno Latour、Michel Callon、Graham Harman、Eduardo Kohn、Philippe Descola、Eduardo de Castro等。在此讓我簡單從Callon的市場化及經濟化開始談起。Michel Callon以及其同事,認為「市場」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多元行動者相互協作的產物。「市場」需要被各種行動者「造」出來。而要理解市場就必需從二個層面著手:社會制度架構以及物質性(materiality)。首先,他們認為過往的社會科學的市場研究,往往刻意忽略學者自己對於「某某市場」的建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要解釋這一點,就讓我們稍微回到上述的經濟人類學的論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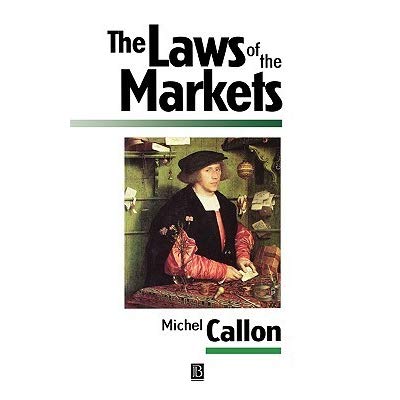
形式論者主張「個人的工具理性」在作經濟決策時的重要性,且此理性可以在每個「人類」身上發現。而為何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理性計算」方式,是因為不同的「文化」對於事物的「價值」有不同的定義。因此,某些持形式論者論點者(例如:經濟學者)認為,由於人的理性有限,因此需透過制度的設計,促使人的行為改變或是符合工具理性的形式。以形式論為基礎的經濟學觀點,經常和其他的經濟學理論同時存在、並相互競爭成為某國或某組織的經濟發展藍圖。從此角度來看,經濟學知識並非只是客觀地描述人類的經濟行為,而是具體地介入、改變、乃至創造了某些經濟行為與「市場」本身(例如:迦納的「外銷農產品市場」的出現,可是和世界銀行那些新古典經濟學專家脫離不了關係呢!)。相較於形式論者,實質論者則強調「制度結構」以及「社會」:即人類的交易行為,乃是到不同的「制度」所引導。所謂的「市場社會」只是人類不同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和其他經濟社會形式,諸如禮物社會、以物易物等並存。
從上述「經濟學知識如何誘導『市場』出現」的問題出發,人類學中的形式論和實質論,就不是完全站在對立面。相反地,他們共享了許多論點:首先,在定義經濟活動或是人的經濟行為時,二個理論都必需訴諸於特定的經濟學知識。例如:工具理性和形式論密切相關;社會制度和結構(如禮物、以物易物或是市場經濟)則和實質論的經濟學理論(如Karl Polanyi的論點)不可切割。第二,二個觀點都認為經濟行為受到二個因素影響:社會結構或個人。他們的差異僅在於何種較具影響力。看到這裡,聰明的看倌們可能就能理解行動者網絡理論健將Caliskan and Callon的企圖了。他們的論述技法在於進一步陳述「經濟學知識」或是「經濟學家們」到底是如何「改變」世界的?(正如Latour研究Pasteur等科學家是如何改變世界的。)顯然,他們認為「某類商品市場」的出現,並非自然而然產生,而是被異質行動者透過實作才出現的。畢竟,究竟什麼才算「市場」的問題,和經濟學知識、模型或經濟學家的活動,都密不可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花點時間去看另外一位傑出的經濟社會學者,Donald MacKenzie關於經濟學的計量模型,尤其是經濟學模型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造市」的影響。
除了考量經濟學知識對於市場的貢獻,Callon及其同事認為,市場的建構還必需考量技術、物質性、非人行動者等面向。從人類學關於物質性的討論出發,Caliskan and Callon稍微揶諭了一下繼承實質主義的新經濟社會學。他們後者認為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活動也是社會行為的一環,而不是經濟/社會截然二分。這樣的說法,的確跳脫了早期實質主義的限制(即區分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結構),但對Callon他們而言,卻完全沒有幫助釐清任何事物,而只是將一個有待解釋的概念(「經濟市場」),用另外一個「黑盒子」(「社會」)來加以解釋掉罷了。因此,相較於用「社會」或是「鑲嵌」等概念來詮釋「市場」,Callon等人認為,從形式論而來的「制度經濟學」反而對於研究「市場」如何被「作」出來,更具有啟發性。制度經濟學吸納了早期形式論的批評,強調制度或是慣習對於人類組織及經濟活動的重要性。此說法的核心論點在於:人類的認知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制度、慣習等扮演類似「輔具」或是「義肢」(prosthetic tools),來協助其成為「理性經濟人」。套句Callon的經典名言:理性人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適當的社會制度輔助。

除了上述的社會制度外,「作市場」的過程中,還需要再考量另外一個重要層面:事物(things)以及物質性(materialities)。Callon認為,人一旦被整拼進市場,意謂著其可以執行算計(或計價)的能力,而這算計的能力和技術、物和人的交互互動有關(例如:演算法、電腦輔助運算等)。人並非天生被賦與某些算計能力,此能力是一個社會/物/人共同協作的結果。第二,受到Appadurai、Jane Guyer以及Webb Keane關於物/人互動的啟發,Caliskan and Callon認為「創造市場」的過程,就涉及到了賦與或是判斷某些事物特定價值的過程(一公斤的高麗菜值多少錢?或是多少價值?)。然而,事物的價值並非如某些馬克思主義論者或是早期人類學禮物經濟研究所主張的那般,是由某種事先存在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此論述邏輯為:人們會送禮,乃是因為處在一個送禮的社會結構之中。對於此社會結構如何出現?如果轉變,則缺乏適當的解釋)。事物的價值是透過複雜的人、物互動的結果。除此之外,物本身的物質性,也會限制或是改變本身的價值。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些人愛吃脆脆口感的蘿蔓生菜,有些則偏好結球萵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看看Webb Keane關於旗幟的民族誌,討論旗幟的價值如何受到其物質性的影響。
在本體論轉向的影響下,經濟人類學的目的,不再是去區分哪個社會是屬於禮物社會或商品社會,而是放在事物的「價值」是如何透過複雜的人/物的互動過程與網絡而決定的。但根據上述這個問題,卻延伸出另一個關鍵問題:如果事物的價值是複雜的人/物互動的結果,那麼到底物/人的互動基礎是什麼?人一定總是事物價值的最終決定者嗎?
過往人/物(包含動物、植物)的非對稱分類(也就是認為只有人類才有能動性,其他物種沒有的預設,請參見本部落格左拉〈「自然」的文化意義〉),似乎開始被動搖了。Caliskan and Callon從Philippe Descola關於Achuar的民族誌出發,認為市場的研究應該要超越人/物二元對立的本體論,並賦與各種行動者對稱的能動性(行動者網絡理論強調用actant乃是所有人/非人事物都同等真實,能動性乃是取決於一個actant和其他actant如何發生關係;而actor則意謂著從行動者本身出發看待能動性,有興趣可以參見Latour的Resembling the Social)。(雖然在這裡捧了Descola一下,但Caliskan and Callon話鋒一轉,又認為Descola的本體論分類,具有結構主義傾向,而且把行動者如何能進行「算計」的能力黑箱化了)。
受到Michel Callon以及Donald MacKenzie等人市場化研究(也就是「市場」如何被創造)的啟發,人類學的農糧市場研究,不再強調市場的玩家僅限於農民/資本家,而是各種社會/技術的異質複合體。市場並非只有一種供給/需求決定,而是多元的、每個組成形式以及參與者(包含人/非人)都不完全一樣的存在。例如:「香蕉外銷市場」,不僅僅涉及到農民以及盤商,還有許多種苗技術、黃葉病以及物流系統;有機農產不僅是無毒施作,還有驗證方式、實驗室農藥檢測以及自然堆肥法等。簡單來說,市場乃是一個異質的社會/技術拼裝體(socio-technical agencement),而透過各個行動者的互動,產生或定義各種「物」的價值。

市場化以及經濟化的論點,拒絕人/非人、有生命/無生命、主體/客體等二元本體論來界定市場的行動者。因此,市場化論述的本體論觀點和行動者網絡理論一樣,又被稱為「扁平本體論」(flat ontology)(關於扁平本體論的視角,讀者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考政治學者Jane Bennett的相關作品,其以及此視角討論北美大停電以及營養物質Omega-3等)。從扁平本體論的視角出發,市場化及經濟化的相關文獻,進一步打開「市場」的黑盒子,並強調「非人行動者」在「造市」過程的重要性。
不過,「扁平本體論」也受到許多人類學者的批評(Callon雖然也強調非人行動者的能動性,但其市場化的理論深受扁平本體論影響,因此大部份市場化的文獻集中在討論市場的設計、出現及穩定,較少關注市場為何崩潰或是瓦解。Donald MacKenzie例外)。Tim Ingold就以蜘蛛(比喻他自己)和螞蟻(比喻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之間的對話,嘲諷了Latour等行動者網絡理論者。他認為把一把沙子和一隻昆蟲放在一起,高談他們都具有同等份量的能動性,是件相當愚蠢的事。小昆蟲具有神經元系統,讓他們具有學習以及發展出適應環境的能力,而也正因為具有這些能力,我們才足以說明那個行動者正在「行動」。唯有透過這個能力,我們才得以區份生命/無生命(inanimate)的事物。簡單來說,關於「人/非人」的討論,對於Tim Ingold而言,應該轉向區分那個行動者是「有生命/無生命」(animate/inanimate)。然而,Tim Ingold的說法,並沒有辦法說明為何人類當今的市場、社會或是政治,廣泛受到到無生命的事物—氣候變遷、洪水、颱風等具體的衝擊。
相較於Tim Ingold,Eduardo Kohn的民族誌對於上述的問題,則有重大的突破。Kohn強調,人類學民族誌過往思考符號互動的過程,往往將焦點侷限在人類的語言及文字上。他認為今日的民族誌應該納入多物種的互動,也勢必要超越這種侷限。在亞馬遜森林中,Kohn劃分「有生命/無生命」行動者的方式,是符號學的,而不是「理智主義?(誰有心智?)」。Kohn同意Tim Ingold的論點,認為有必要區分「有生命/無生命」的行動者。但和Tim Ingold不同的是,Kohn的區分方式是透過所謂的「思考」能力。對於Kohn而言,「思考」乃是一個行動者詮譯和再現其週圍環境的能力(即行動者得以和週圍環境互動、調適的能力)。受到Charles Peirce的符號學的啟發,Kohn將一個行動者和其週遭環境的互動視為一種「符號化」的過程(並非僅有人類可以詮釋其週遭環境。亞馬遜森林的狗可以透過不同叫聲,反映出其對於不同環境變化的反應)。為了不讓這個討論過於抽象,Kohn 用了食蟻獸如何演化出具備有長鼻以及長舌當作案例。巨型食蟻獸當今的樣態(長鼻、扁平長頭、長舌等),乃是其先祖物種和蟻巢外形樣態長期互動(或共同演化)的結果。換言之,僅有那些有思考能力的自我(selves),才能詮釋其週遭環境。而這自我,並不限於人類,包含森林、食蟻獸等。森林也可以透過其獨有的方式,和其週遭的環境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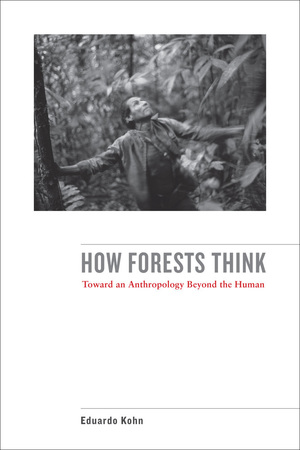
相較於Tim Ingold而言,Kohn的符號學(或自我如何和環境互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解釋諸如河流、氣候等自然生態系統如何可以被看成具有能動性的存在,而不只是無生命的物質。從Kohn的角度出發,Callon的市場化以及經濟化,將更可以解釋多元的行動者,諸如病原體、氣候、環境微生物等),如何積極的參與「造市」。從此角度而言,「市場」或是「社會」這些概念都必需被重構。並非僅有「人」,而是許多「非人」(more-than-human)都是「社會」或是「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多物種的觀點在於趨動我們重新思索這些不同行動者間的聯結(associations)。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非洲豬瘟,這裡我想引介近來動物疾病研究者如Steven Hinchliffe 和Nick Bingham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防疫(也就是防堵策略)的確重要,但是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多物種的「社會」。人並非是「市場」的絕對支配者,建立和這些物種相處的靭性能力也是在思索動物疾病時,重要的一環。
有鑑於芭樂文不能過長,在此先停住,不然Kohn等人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和近來在哲學界廣受注目的物件導向哲學(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乃至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之間,可是又有一番精采的對話,對於我們理解市場形構以及當代政治社會形態,可有著豐富的養份呢,下次有機會再來聊聊吧。(小編迫不及待預約下去了~)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王驥懋 豬瘟、薊馬與經濟人類學的啟示:「市場」是怎麼被造出來的?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697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我讀書少 一堆哩哩摳摳的術語理論概念繞得我讀不下去啦 不是說芭樂人類學適合給平民百姓閱讀的嗎 哎唷喂
說好的豬瘟呢?內文和標題差太多,有被欺騙的感覺。芭樂也流行釣魚文,衝人數?
操 是怎樣啦 一下子種菜 一下子賣魚,接下來還有什麼殺豬 泡咖啡的是不是!
讀不下去就不要讀!
精彩,期待下文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