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物種民族誌與資本的五十道陰影
松茸、昆蟲、蝸牛、思考的森林、還有鴿子,這些乍看之下迥異于經典人類學的主題,怎麼幫助我們理解都市環境,科技與技術,以及人類和非人物種(nonhuman beings) 的交往呢?人作為一個物種,與其他物種之間,存在著什麼樣錯縱複雜,愛恨情仇的關係,進而形塑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過程呢?人類學界近年來,在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書寫上的興趣,心心念念地就是希望能回應這些問題。某種程度上,多物種民族誌所接續的是上一波受到知覺現象學啟發的人類學取徑,在體物入微的面向上思索感官與知覺世界的民族誌。而正如身在島上的你我所知,潮間帶之間,漲潮退潮,鹹鹹的海水帶上岸的是時光芢苒間的各式新舊交雜; 面對日益逼近的人類世(Anthropocene)生態危機,多物種民族志成為許多當代人類學家,將民族誌的微觀筆觸,一筆轉去描寫各種不同物種與人類社會,在全球史間波盪的各種精彩故事。
面對全球環境變遷,以及現代社會裏被生命科技給主宰的狀態,多物種民族誌的建議是,何不先從思考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人,政治人,都市人,或是鄉民(不管是在宜蘭種田的鄉民,或是PTT上面的口水鄉民)這件事的本質?個人被賦予這些特定的社會能動性,這樣的過程,往往不是人類這個物種孤獨地去完成。多物種間的互動,其實無所不在:譬如說在"Golden Snail Opera: The More-than-Human Performance of Friendly Farming on Taiwan’s Lanyang Plain"一文中,人類學家蔡晏霖與Isabelle Varbonell、Joelle Chevrier以及Anna L. Tsing 共同描述了宜蘭平原,人們與蝸牛的友善共同耕種; Hugh Raffles則在Insectopedia(中譯昆蟲誌)一書中,精彩地演繹了不同歷史脈絡中,昆蟲與人的生命交織;或是人類學家Anna Tsing,在她自己的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一書中,透過松茸怎麼捲入全球化資本積累的新型態,從荒廢的腐植到與採集者身命與勞動交織的過程中,遷徙到地球的另一端,成為在日本的珍饈。Tsing 在此書,提醒了我們「人性的本質(human nature),乃是取決物種與物種之間的交涉關係」。這些多物種民族誌提醒了我們,人類在此世上,恆常地是與不同的生命形式,一同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低端物種在生物政治上往往被視為是天然資源,或是毫無能動性,就僅僅是生命形態,可以任人宰割(見Agamben的Homo Sacer) 。這些在生命階序裡「低端」的生命形式,也提醒了我們,動物與昆蟲的物種比喻,常牽涉到我們對於殺戮的概念:例如反猶太主義裏,將猶太人,類比成是蝨子,因而可以被正當地摧毀,物種範疇在語言與意識層面上的蔓延,反映的是更深層的,物種階序與暴力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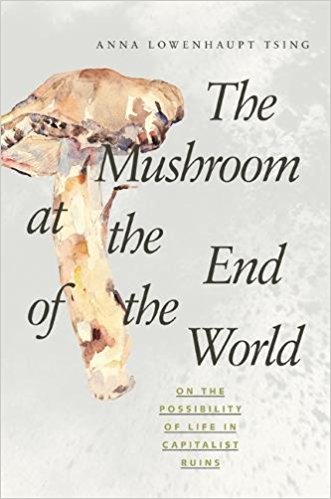
多物種民族誌對於這些低端生命所投下的細密書寫心力,再再地希望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環境,科技,以及生態世界共生的關係—無論這些關係如何地幽微又複雜。在這樣的脈絡下,1990年代末至2000年間,這個新的民族誌方向,逐漸地打開了人類學在書寫對象,甚至是與藝術界在生物藝術(bioart)這些面向上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2010年,美國人類學會的Journal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出版了一個特刊,名為「多物種民族誌的出現」(The Emerg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這個集刊也整理了幾年間,許多民族誌寫作者,怎麼將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放置到人類世的脈絡當中,衍伸出在研究題材,與田野工作形式上,多物種的面向。如同Donna J. Haraway在When Species Meet 一書裡所提問的:我們要如何省思當代人類生活中,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緊密接觸呢?這些不同物種的接觸,摩擦,陪伴,甚或是互相依賴,如何綿密地編織出此間的世界感,與社會性?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多物種研究啟發的民族誌,對於生態世界的基本理解,不是要複製古典人類學對於社會 vs. 自然,這樣二元對立的概念(譬如在1970年代的人類學性別理論裡,有關性別氣質究竟是自然或社會性的經典辯論),多物種民族誌的出發點是期待在更基礎的層面上,重新檢視在現代性裡,承襲自啟蒙運動而來的,種種對於人類本質基礎概念上的預設;最重要地是去提醒,這些基礎概念,例如人性,怎麼已然包含了我們與非人物種的共生關係。

Haraway的出發點,在於人類是一種仰賴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的物種; 而陪伴著人類一起在這個世界上,痛並快樂著的,不僅僅是其他的人類,還有伴侶動物,花草植物,或者甚至像是摩托車這樣親密的物質伙伴。而我們對於社會生活的基底藍圖,對於差異的容忍度與理解,從來就是在與不同物種的相遇裡浮現,進而與政治,經濟,道德,法律層面產生關聯。譬如說我們對家庭這樣的預設,在今天已經包含了非人的成員:毛小孩,大狗與胖貓,冷血的蜥蜴,乃至金魚或其他親密的收藏物。對很多人來說,這些不同的物種/物質已然是家庭生活裡不可或缺的成員。我們與這些非人的物種彼此間的伴侶關係,同樣反過來影響了每一個人在社會裡的位置,對你我好的或壞的評價。不同于人的物種,因而不僅是我們思考的好主題(good to think),Haraway 所談的,是在更基礎的層次上,我們所在的世界,以及人類自身的種種屬性,在本質上就是與其他的物種一起成形的(becoming with)。這個「一起成形」的想法,啟發了不少的民族誌寫作者。譬如說,在How Forests Think裏,Eduardo Kohn把多物種民族誌再拉回人類學有關意義本質的討論裏。援引十九至二十世紀初的哲學家Charles S. Peirce在象徵與指涉(indexicality)理論上的思考,Kohn把人類與自然之間,彼此對照,交互形塑出世界感,互相援引的這個意義架構,帶到他對於亞馬遜森林的民族誌書寫。這本民族志在概念上的突破,重新探問了環境對於世界感形塑的重要性:對於這些居住在上亞馬遜森林裡的村民,生命意味著已然與森林共同架構,與美洲虎緊密相關的,牽涉到生存與死亡的意義「世界」。

然而,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相遇,並非都是如17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的自然風景畫,或浪漫主義的田園詩歌,那麼地純真美好。在Pigeon Trouble: Bestiary Biopolitics in a Deindustrialized America 一書中,人類學家Hoon Song處理了在美國賓州中部,緊連著阿帕拉契山一帶,後工業化的煤礦小鎮Hegins,1985開始聲名大噪的年度勞動節射殺鴿子大會。在這個自二次大戰後,隨著美國整體對煤炭需求量減少的趨勢下,就持續地進入了後工業化歷程的偏遠小鎮,煤炭產業的就業人口,從1935年間的45,800 人下降到1986年的8,500人。每年九月,秋高氣爽的時節,整個小鎮熱烈地購買,運送數千隻鴿子,然而只為了集體舉槍,公開射殺這些飛鳥的節慶,即便沒有人可以準確地說這個節慶到底從何時開始,80年代至90年代間,動物保護團體的抗議,更激化了這個射殺鴿子大會期間的各種爭議,牽動小鎮集體認同的敏感神經。這麼一個針對動物的集體暴力展示,也扣連到社群內外的階級,種族,以及城鄉衝突的愛恨情仇,反映出美國後工業化白人社區的陰謀論述(conspiracy theory)與憤怒叢結。對於動物他者的想像,不只牽涉到鴿子怎麼在社群內部被分類為是食物,寵物,類似有害蟲的動物,或是野獸; 在這個媒體充斥,SNG車四處跑的年代,集體射殺鴿子的慶典,同時將動物階序與其他的政治與社會對立,在象徵的層面上交互質置換。動物之為動物,其實和人之為人,一樣地處在一連串的意義界定過程中,處在行動(例如公開射殺),互動(動保者的抗議與鎮民的更加激化),以及儀式性的象徵轉換(鴿子作為紐約市菁英的替死鬼),種種的意義叢結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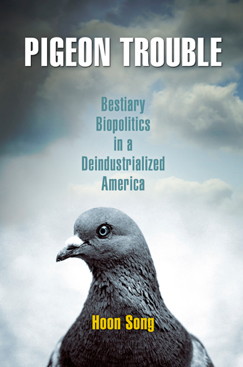
因此我們可以說,人們對於自然的想像與概念化,從來就不曾置外於社會:自然的概念向來就是一個歷史與社會的產物。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對於「自然(nature)」,和「大自然(Nature)」的概念,牽涉到的是歐洲殖民主義自17世紀中以來,在資本積累的驅使下,向世界各地進行的擴張與探查,以及其所伴隨的殖民掠奪與奴隸貿易(見Jason W. Moore的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與短文)。隨著這些歐洲殖民探查與移居者,而旅居到美洲與澳洲的生物學家,植物學家,昆蟲學家,以及動物學家,自17世紀以來,更一個又一個地從殖民地採集了大量的各種標本,帶回歐洲,而奠定了現代生物學的基礎;這個與歐洲殖民歷程緊密相關的,對於「大自然」的知識建構,也幫助創造了歷史上對於「自然=野蠻」,「自然=落後」,「自然=熱帶」,「自然=可掠奪的資源」等等既定的,延續至今的與自然相關的範疇與想像。在這樣對於殖民史與自然概念的省思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 Jason W. Moore近年來開始關心以資本世(Capitalocene)來取代人類世這個概念。多物種民族誌因而得以幫助當代的人文與社會學界,來看到資本積累的五十道陰影之間,是怎麼超越了人的範疇,而更大規模地影響了各種生命體共同賴以生存的世界生態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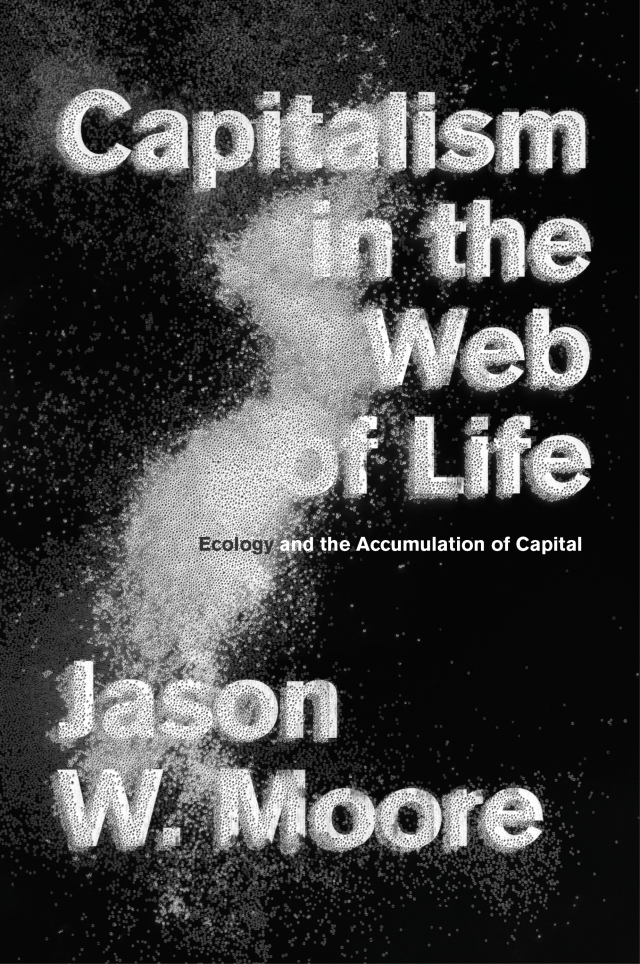
我自己對於北京蟲魚花鳥,民俗收藏市場的民族誌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上面這幾本多物種民族誌的啟發。埋藏在民族誌細節底下,我希望探問的是,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變遷,僅僅是一個人類的事件嗎?2012年間我開始在北京做田野,正值空氣污染攀升的時期,生態破壞儼然成為後社會主義商業開發,資本積累進程的昂貴代價。自2001年加入WTO後加速開展的北京舊城改造,搬遷的不僅僅是居民,還有整個被煙硝灰滅的城市生態世界:胡同裡的魚蟲花鳥,日常生活裡人與舊城融為一體的老北京況味。我的民族誌環繞著一群群即便是在新穎商場,超未來建築此起彼落的新北京,仍自詡為老北京的人們。買不起一瓶橄欖油但是堅決地花上數年間收藏,磋磨文玩核桃的老大爺,可以花上數小時談冬天怎麼養蟈蟈,夏天怎麼在酷暑養額頭紅金魚,上公車還得提籠駕鳥,週末在文化館裏坐上數小時聽說書的人們。 在這些「不」與時並進的人們,「不」與時並進的多物種互動裡,我們看到城市的轉變,不僅僅在於人,城市變遷同時是一個多物種的故事。是在與這些陪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的互動中,我們看到了全球化的北京裏, 更急切地尋求一個足以提供生存意義,以及個人意義的「環境」敘事:一個在急速變遷當中,仍然能讓人安身立命,連結過往的意義世界,這樣的環境敘事。在這些蟲魚花鳥市場裏,種種附著在物件與動物植物上的懷舊收藏情緒,更揭示了美感生活怎麼在本質上,就是建立在人們與環境,與物質之間的情緒流動。
多物種民族誌另一個特色是書寫元素精彩,在細節上極重專注力,也需要田野的交陪耐心; 涉及的面向則常超越既定的學門分野。我這兩天讀到柯裕棻專訪金宇澄的一篇稿子,也是講寫作的體物入微,怎麼對話時代動盪,政治變遷。細節無法人造,細節只能靠近,小說家進入歷史的瞳孔緊盯著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與細小的,與生命糾纏的東西:城裡的裁縫師,與一針一布,透過東西小說家穿過裁縫師與整個城裡的人們,政治波瀾間,怎麼過日子。多物種民族誌,心心念念,大抵也意在於此。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謝一誼 多物種民族誌與資本的五十道陰影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59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