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情緒、歸屬感
失去與存續的諷刺與兩難
「失去後才懂得珍惜」、「失去了才發現曾經擁有」,這些表述可能被認為老掉牙、為賦新辭強說愁,但或許也很大程度描述了我們生命中都曾經歷的荒謬情節。(所謂「人性」?)
書局一間間地消失,對所有人來說都已不是新聞,但即便遭受類似的時代洪流淹沒,每一間熄燈的書店都見證了各自的悲歡離合。最近一篇《鏡週刊》關於傳統書店的系列報導,記錄了高雄鳳山傳統聚落中心一間年屆半百書局最後的身影。報導中提及,業績不好自然是書局難以為繼最重要的原因;然而一宣布了結束營業,卻突然門庭若市,營業額飛升。但老闆與老闆娘也明白,「感恩…美好的ending,但一、二週後又會恢復平靜」。這間書店,想必很久沒出現在眾人生活中、甚至腦海中,否則不會業績不好;但在說再見的前一刻,卻突然牽動了情緒、行動,動員了不只在地人,就報導記載,還包括搭高鐵遠道而來的、三代同堂一起出現的、淚流滿面的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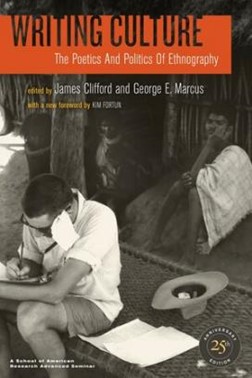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第25版
有次課堂討論「反思文化」(受到James Clifford & George Marcus「Writing Culture」與Lila Abu-Lughod「Writing Against Culture」觀點啟發),邀請學生思考:「不假思索地使用『文化』概念時,背後可能有哪些預設?」討論過程中學生問了一個好問題:「對『文化消失』的焦慮到底從何而來?」我請學生們發表看法:
學生A:想維持文化多樣性。
學生B:確保有各種不同文化存在,當一種模式不能運作時,我們才有其他參考、其他選擇。
我說:這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但為什麼很多人是焦慮於「自身」文化的消失呢?
學生C:一個人有自己認同的文化,會感覺到生命有重量、有依歸,且不再空乏、無聊。但認同的不一定要是「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是生命歷程中經驗到的其他文化,像我現在認同的就不是我以前熟悉的文化。
學生D:消失一定是危機嗎?一定是不好的嗎?世界上有那麼多事物隨時在消逝,然後又有新的事物出現,如果這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一定要人為干涉嗎?
我們接著討論:對於被視為「少數/弱勢/邊緣」的群體,文化消失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議題,且必須被解決,保存、復振因此被視為不證自明概念。但對於類似議題的關注度,卻並不適用於所謂的「強勢/主流」文化。以臺灣為例,原住民族和閩南社群共同經歷過一段不能說母語、不想說母語、父母覺得孩子不會母語更有前途的歲月。然而,對比當下復振原住民族語言的努力,閩南語使用人口下降似乎較少人關注,或根本不認為是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成因是什麼?對於語言、文化消失有「危機意識」的前提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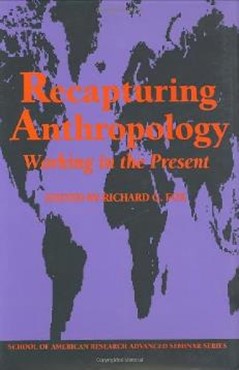
Lila Abu-Lughod著作〈Writing Against Culture〉收錄於此書:
Fox, Richard. 1991.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人類學對於記憶與文化資產的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民族誌紀錄。上個世紀六零到八零年代間,有許多關於國家建設造成大型聚落遷址的經典人類學研究,例如Elizabeth Colson關於尚比亞Kariba水庫與東加人(Tonga)的研究、Hussein M. Fahim關於埃及亞斯文高壩與努比亞人(Nubian)的研究、景軍關於甘肅省大川村淹沒於大型水利設施後重建社群與孔廟的研究、臺灣學者也有諸多關於漢人村莊或原住民族聚落「displacement」(非自願性遷移)的重要研究。這些研究中,紀錄了事件發生後種種社會組織、生活型態變遷與居民身、心狀況變化。可想而知,離開原居地對所有人而言,無論是自願或被迫離開,都將有深遠影響。然而,這種影響是否只關乎社群流離失散、文化語言佚失,民族誌中呈現的故事可能很反直覺。上述研究中,皆提及遷徙他鄉的移民們如何藉由種種社群行動,重建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事實上,正是因為日常中斷,才使眾人對以往視為理所當然(甚至不甚滿意)、如今已消逝無蹤的家園萌生強烈情緒,伴隨著流離失所的不安全感,反而產生重新凝聚認同和歸屬、尋找語言與傳統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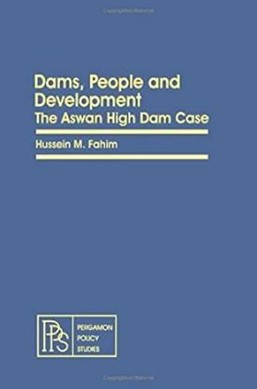
Fahim, Hussein M. 1981. Dams, People, and Development: The Aswan High Dam Case. New York : Pergamon.
Liisa Malkki、David Turton分別於坦尚尼亞、衣索比亞關於政治、環境難民的經典研究中,清楚描繪了,在這些被標示為遠離故土因此必然失去認同的「難民」心中,例如Malkki(1995)筆下的胡圖族人(Hutus),事實上發展出了獨特屬於「流亡者」(people in exile, Malkki 1995: 3)、「流亡者國度」(a nation in exile, 同上引)的社群認同感、歷史感、及與家鄉連結的、超越地理界線的地方感。Turton(2004)更指出,莫西族人(Mursis)在遠離飢荒肆虐家鄉、遷往有穩定水源和較豐富森林資源的新居地後,也不認為自己是「難民」,而是像祖先一樣跨出舒適圈、出發開闢新天地、找尋新生存機會的「先鋒」/「開拓者」(pioneer, Turton 2004: 23)。反而因為經歷了這個開拓旅程,讓他們感到與祖先更接近,自覺比留下來的人更像莫西人(more Mursi than those who stayed,同上引)。
對於人類學者而言,記憶、認同、歸屬、乃至「文化」可以是(但未必一定是)建構的,這並不是陌生的說法,但如果這個說法經常是成立的,那麼是否有可能,「還在的只是無趣日常,消失或快消失的才會變成文化資產」?在某樣東西—地景、語言、行為模式、生活方式、關係、某個人、某間曾經造訪的店鋪—消失前,只覺得過於日常導致乏善可陳、過於親近而生侮慢,直到失去前夕,才突然感到回憶的重量。難道真的是,某樣事物的逝去或即將逝去,是被珍惜的前提?
而此種無可奈何的諷刺關係,甚至可以透過想像力發生在沒有直接接觸的人身上。這個情況可從多位學者(可參考Maurice Halbwachs、Paul Connerton、Maurice Bloch)關於集體記憶的研究窺知一二,包含記憶之個體選擇性、社會性、超越時空性等。以此為基礎,不難分析為何年輕、或不曾經歷過歷史的世代,會對祖先、傳統感到深深的連結:後繼者處於歷史已失落的時空中,身旁沒有東西、腦中卻乘載著從不同管道獲得的記憶,這種記憶不免帶著情緒濾鏡、浪漫化、選擇性記得特定片段而非全貌,因此後繼者甚至比與已成為祖先的長輩曾經生活在同一時空的世代,感受到更強烈的連結與失落感,也更容易成為保存、復振的行動者。

Connerton, Paul.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直想到《大亨小傳》。對主人翁Gatsby而言,沒成真的都是夢想,成真的只是現實。Gatsby曾有過遠大抱負想實踐,一心想向女主角Daisy證明自己,但隨著對Daisy的羈絆越來越深,他不想實踐理想了,因為向Daisy訴說願景時的快樂已經滿足了證明給她看的需求,已經沒有必要去實踐理想。事實上,萬萬不能實現,實現了就不再能訴說、期待,且現實往往沒有想像美好,接著就會經歷失望與空虛。後來因為戰亂,Gatsby與Daisy被迫分開,Daisy選擇改嫁他人。2013年拍成電影時,其中有一句台詞:「I’m only 32…. I might still be a great man if I could only forget that I once lost Daisy. But my life, old sport, my life has got to be like this.」描述Gatsby知道,若非自己放不下失去Daisy的傷痛,他可以成就許多大事;但他說自己不可能放下了,因為永遠的失去帶來永恆的渴望,Daisy成為了他未竟的夢想,因為不曾達到,所以永遠閃耀。

「反思文化」那堂課快下課前,有位學生說:「像Geertz那樣的金頭腦,如果人類壽命不止一百年,他還能創造出多少偉大的東西?!他死後,後面的人又要重新培養、重新來過。」我當下沒想到怎麼回應,只說了句:「所以大家應該做好文獻回顧,才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累積知識…。」但我後來又想:「如果Geertz的生命是無限的,而他也認知到這件事,他會不會和好多人一樣,一直想著還有明天,因此至今還沒有生產出任何偉大的作品?」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雪裡紅 記憶、情緒、歸屬感:失去與存續的諷刺與兩難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7039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