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我們親愛的夥伴「芭樂貓」
芭樂人類學創始群、芭樂小編之一,筆名「芭樂貓」的陳伯楨,在今天離我們而去。千言萬語,無法言語。謹讓我們回顧芭樂貓寫過的14篇芭樂文,並分別寫下我們的回憶,感謝他帶給我們的美好。
首先請大家看看芭樂貓在芭樂人類學的農友簡介,點入後即可瀏覽所有他的芭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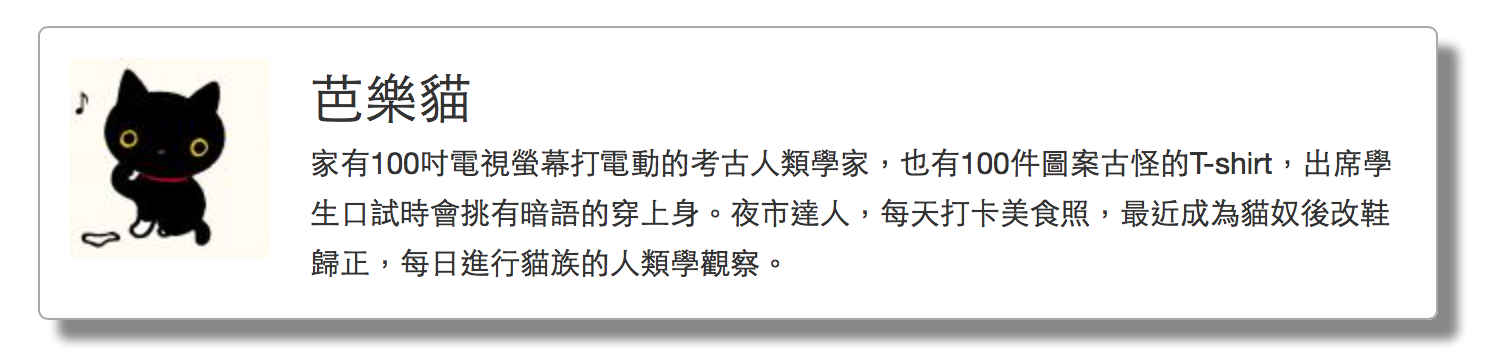
芭樂貓真是個奇葩!其實這個簡介是我寫的,本來只是開他玩笑,沒想到他欣然採納當成農友簡介。伯楨的幽默感是許多人難忘的特質,而且很奇怪的(算是物以類聚嗎),他的田野也充滿了爆笑的況味。芭樂貓的第一篇芭樂文「Z縣的聖誕節」,刻劃了在四川某個小縣城遇到的奇特經歷,目擊並被動參與了「聖誕節」在遙遠的角落「被發明」的過程。這是每年耶誕節芭樂粉絲頁就會拿出來重溫的經典文章!
然而外表開朗、逗趣的芭樂貓,其實內心充滿了仁厚,他的芭樂文也記錄了在田野中看到的無奈、震驚與反思。例如在「田野散記 - 我所遇到的那些離散人群」中,為了建三峽大壩而被迫拆遷流離的村民,從四川被搬遷到山東,又一一回流,成為家鄉中的「離散人群」。而在「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展演?」中,他更在田野地目睹了死刑槍決前的遊街,看著平日善良的人們看熱鬧的興奮,驚覺死刑犯成為政府展演的工具。
身為一個考古學者,芭樂貓總是讓讀者能見識考古田野的各種幕後,例如「米飯或麵食?考古田野中的食物」,挖掘的團隊要吃什麼,可是門大學問。除了上述田野故事,考古計畫進行中的種種考量與拉扯也是他常書寫的主題。在「人有失蹄,馬有失手,吃芝麻那有不掉燒餅粒?」中,他誠實而詳細地描述研究團隊在成都平原進行大規模系統性調查工作時,如何選擇鑽探點、鑽探工具、鑽探方法等,其中有失敗的部份──但伯楨特別指出研究本來就是「不斷在錯誤中修正、從失敗中學習經驗」,不要怕嘗試。在「考古遺址與逝者之城」中,他帶領我們思考考古發掘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關係──尤其當考古遺址成為「文化遺產」,隨之而來的種種法令限制與觀光人流,如何與當地人的生活協商?
芭樂貓看到的面向一直都是多層次而複雜的,他的研究專業主題是「鹽」,在「到了海南島才知道...「鹽來如此」!」這篇敘述到海南島做鹽業考察的故事中,他雖為了解傳統鹽業工序而去,但腦子一直在動,如何才能幫助當地的文化資產保護與發展?這樣的知識份子關懷,也展現在當他看到短視的立委質疑推動中美洲經貿的經費用在邀請學者進行瑪雅文化論壇時,即寫了「經貿交流也應兼顧文化」,指出文化資產也是經貿交流的一環。
這樣針貶的精神不只面向社會,也面對學術專業社群。在這篇重量級的芭樂文「要科學不要科科 – 我們該如何面對科學技術在考古學的應用」中,伯楨耙梳考古學與科學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犀利地批判某些誤用與濫用,批評之外更建設性地指出未來的方向。而他在書寫這麼嚴肅的課題時,也不忘來個芭樂風格的題目(科科)!
而伯楨對芭樂的諧音「拔辣」也有所發揮,「「拔辣」考古學」是一篇精采的食物的簡史,川菜以辣聞名,但辣椒原產於美洲,因此川菜其實要放在世界體系互動中來思考,打破「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迷思。同樣需要放在世界體系中思考的還有愛情──對學術人而言,求學田野找工作,不也是一種離散,是「世界體系觀點下的學術與愛情關係」?芭樂貓的朋友K曾勸他別寫這篇,否則學生看了更不敢投身學術工作了怎麼辦?
阿,學生!學生是伯楨最掛念、花最多力氣的人了。他曾獲得台大的傑出教學獎,實至名歸(報導)。還記得他剛回國教書時,幾乎日日睡在研究室,因為整夜做PPT是家常便飯,朋友都覺得他瘋了(現在回想他這麼燃燒自己,還是覺得他瘋了)。學生報告胡寫,他發文善誘;學生論文口試,他總在後面旁聽支持(還會挑一件「特別的」T-shirt);學生喝醉了,他背回家;學生在立法院抗爭,他日日去巡。連續多年芭樂貓和學生一起參加挺同志遊行、爭取人文大樓興建、處理系狗大小事。他也寫了許多篇教學相關的芭樂文──他關心在推甄制度中迷失的學生,芭樂貓點閱率最高的文章就是「高中生你推甄了沒?」;他鼓勵學生別擔心犯錯,而是從錯誤中體悟,於是有了「禪師與小沙彌的那根指頭」;他也關心學生的出路,在「從一個被婉拒的紅包談起…」中,指出考古學界需從提升中低階工作人員保障做起,讓結構中能夠有向上流動的管道。
這兩、三年來芭樂貓也是值班小編之一,許多芭樂文都是他上稿貼文貼圖,他默默地維持芭樂園的運作。在芭樂農友聚會中,他總是帶來笑聲。我們仍無法相信,這都已成為歷史。再次咀嚼他這14顆風格芭樂,我們仍無法相信,以後芭樂人類學中,不會再有芭樂貓的新鮮芭樂。我們都還在偷偷地希望這件事不是真的。
謹以這篇回顧文,感謝芭樂貓為大家所做的一切。
by 郭佩宜
──
本來只聽過紅心芭樂,今天開始,我對芭樂的理解要多了一個新品種:“傷心芭樂”。
我無法像佩宜可以這麼理性地去整理伯楨曾經寫過的文章,我腦中現在塞滿了他這個人。
對我來說,不能再看到他的人,聽到他的笑話或貓事,都讓我感到巨大的傷痛。
最讓我揪心的是:再也不會有人在星期一敲我的電腦對我說:“學姊,我文章貼好了喔。只剩下廣告詞就可以出了。” “學姊忙的話,廣告詞我來寫好了!”
好痛!
by 趙綺芳
──
人生中第一次從身到心從心到身,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殘酷是在爸爸離開時;第二回是畢業到暨大任教不久後,從中央山脈的那端傳來博論田野地的部落弟弟意外車禍身亡的消息;再來就是今天下午在豔陽高照的小米園中,突然聽到伯楨已經走了……
因為相差了好幾屆,我在台大人類所讀書時不認得伯楨,開始用臉書之後才知道有這個如此特別的學弟,看著他超有意思的po文以及對學生極其用心和貼心的舉止,簡直讓我崇拜,因此,當聽說伯楨要來郭素秋老師在暨大的課堂上演講,我就像個粉絲一樣慕名前往。那是我們的初次見面,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聽考古的演講,並且唯一一次覺得考古有趣的時刻。
其實我和現實生活中的伯楨並不熟,我們見面的次數不多且總在人多的場合,有過的對話只是寒暄或聊所上考古的學生,不曾有過深談。可是為什麼我會如此的痛,痛到實在超出自己的想像。或許是因為我覺得和他之間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都是和學生非常親密的老師,都愛在臉書上展露我們心中的喜怒哀樂,都把學生看成我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重讀伯楨一篇篇的芭樂文,一方面忍不住眼淚直流,一方面又覺得安慰,還好有這些芭樂文,可以讓不熟伯楨或不認識伯楨的人得以從中真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位如何與眾不同,既溫柔又熱情的考古學者。
by 邱韻芳
──
早上起床接到噩耗,完全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這幾年來亦師亦友,相識超過十年,一直是我研究上的標竿,走上中國研究這條路也要感念許多指點提攜, 謝謝你,讓我走向安陽,帶我進入芭樂人類學的寫手群,更新台灣人類學圈的消息,謝謝你告訴我看到我這幾年的進步。記得有一年從北京到成都十幾個小時的火車臥鋪,才發現護照留在北京的青年旅館,那是個冬天的深夜,旅館拒收、街邊冷清、人生地不熟、緊急打電話回台灣求救,我不知道你打了多少通電話,但一個小時後,我就被安置在往郫縣的哈佛考古隊歇息旅館的路上。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個晚上沒有你的幫忙,也許我就客死異鄉。而我受惠於你的又豈止是這些? 點滴在心,所以我說我要參加你的婚禮,因為紅包已經準備了好幾年,每回多一份幫助,重量就往上加。去年約莫也是此時接到光仁學長的噩耗還能點點滴滴的寫篇訃聞,可與你之間的友情,又豈是一篇文章能數盡,因你總是這麼地熱心於人。
一直看到你在學術上的熱情從你還是個博士生、助理教授到副教授,身分轉變並沒有改變你待人處事的態度,總是盡其所能提攜後輩,相識的師長、朋友與學生,都難忘你的陽光、爽朗的笑聲、對生活的熱情。無奈上天要你去當天使,看看這世間還有許許多多的師長朋友學生感念著你的一切,我想你會欣慰的離開,一路好走~
離台前你才找我吃飯像是tutorial一樣,那時的我很挫折也很徬徨,我會記得你的勉勵,突然覺得這一條研究的路,就剩自己在走了。
重讀你的芭樂文,彷彿你依然還在我們身邊...
by 王舒俐
──
我家的小朋友聽完我聊伯楨老師這麼輝煌的一生,談起他的黑貓生態故事、他的中國泥土田野,還看著他那從考古坑裡奮力爬出來的那股形象,小孩突然用他們國中最近教到一首詞比擬,讓我心頭一震:
1.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2.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虞美人・聽雨)
伯楨老師在過去好些年總有機會和我在學術會議場合相遇,有考古的、也有人類學的。他那慧頡的閃亮亮眼神都是帶著力量,沒有疲憊,放電地訴說著他新從田野感受回來的挑戰論點,諸如科技不敵苦工、或是當地人與事物現象的荒謬弔詭。我想想,我們也都算壯年了吧,但庸庸碌碌奔波這麼多年這些可憎的俗務,只有伯楨老師那樣有氣力的身影,算得上是一直滿懷熱情、充滿希望力量,卻又對抗體制、對抗壓力的不朽勞形。
3.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4.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宋・蔣捷的詞)
伯楨老師翻開的那些東西真是無情嗎?有些發掘應該是,有些則未必。伯楨老師用心最深的就是「物」的層位學,從鹽到辣椒,這些東西被埋藏、和發現後的歷史脈絡,不正是「人」有情地、糾纏地創造嗎?然而,他就這樣悄然無情地走了,對照他創造了那麼多爽朗的大笑,這像不像是一記刺向這個時代的巨大諷刺?
是真的有累了。我趕緊在悲憤地沈沈地入睡前提議:伯楨老師最後參與的「鹽古時代特展」,大家有空再去流連看看吧。在十三行博物館,到2015年8月31日。特展介紹裡有著一小條說明:
「因為鹽的可溶性,讓我們無法追溯到最早的鹽業生產,通常要發展到相當的生產規模時,考古學家才能在遺址中發現早期製鹽的行為。」
天哪,是怎樣等你走了之後,我們才發覺出你的規模,做了那麼多事,留下這許多記號。伯楨,你就像那重要的鹽粒,溶掉了,才讓接觸過你的味蕾世界遍布著你的味道,無法忘記的力量!
by 胡正恆
──
「一切關鍵的經歷都是負面的:生存的堆積缺乏厚度;心靈與存在的考古學家,挖掘它們,找到最後,就只會面對一片空虛的深淵。而他那時再怎麼懷念表像的裝點也都無濟於事了。 」(Cioran,解體概要:死亡變奏)
「不可能哭泣保養着我們對事物的喜好,讓它們得以存在下去:這種不可能,阻止我們嘗盡事物的滋味,也阻止我們掉轉頭去。當我們的眼睛,在那麼多條路上,在那麼多道岸邊,拒絕被自己淹沒,它們是在用自己的乾澀保存那些令它們驚喜的東西⋯⋯那些進入了我們的贊嘆與哀傷的東西能留下來,只是因為我們不曾以液態的訣別犧牲或祝福它們⋯⋯就這樣,每當夜已盡,面對新來臨的一天,必須卻又無法填滿它,這一事實使我們驚懼不已;而,身處光明這個異邦,彷彿世界剛剛經歷了震顫,發明了它的太陽。我們就要逃離淚水一一因為只需一滴,就可以把我們從時間中擠出去。」(Cioran,解體概要:寫在瞬間的邊上)
紀念讓人喜愛的伯楨,在你走的隔天清晨。
by 李威宜
──
上週,電影配樂大師James Horner在熱愛中的飛行中離世,伯楨老師則是在熱愛的學術工作中離開我們,他的典範、啟發和熱情的笑容則永遠長存在世人心中。
伯楨老師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不僅在研究上面很傑出(他在臉書上談以前半夜在洞洞館待到十二點目睹淹水的故事),在教學上面也極其認真(總是看到他在臉書上面跟學生頻繁互動),心想伯楨老師除了睡覺時間,應該是把所有的生命都燃燒在學術志業上面了吧!伯楨老師正值壯年卻離開世間,真的非常可惜,他在芭樂人類學上面的文章介紹考古學,文筆詼諧幽默,也啟發了我們對考古遺址、文化遺產及觀光化的研究興趣,還是要說聲:感謝伯楨老師。
by 林怡潔
──
自稱「人白木」的伯楨吾友:
認識你的時間不長,但是卻好像從小就互相熟識的朋友。第一次跑到你水源校區的研究室,是為了見證你說的那個不斷坍塌又鼠輩橫行的狹小空間。我看到研究室裡面資料堆積如山,你從裡面左蹦右跳,抽出一疊疊的資料重新歸位,讓我見識到「哲人日遠」之後,台大是怎樣把人文精神踐踏在侷促的狹小空間裡。
之後在不同的地方和你相遇,聽你講四川考古的種種奇妙故事(我想你可能是唯一被邀請到社會學課堂上去講課的台灣考古學者),說為學生備課上課甚至口試旁聽的種種秘密訊息,在台大附近見證各個曾經存在或慢慢消失的人與事物,還有大家天天期待的黑嚕嚕生活日記和美食饗宴:你的生活內容變成了大家生活當中不可缺少的部份,你的個人觀察成了我們的公共視野。
學期末的失聯,沒想到竟是你身體狀況的警訊。好友們都在自我安慰地想,等你硬朗地恢復之後,要虧你怎麼這麼容易就把大家就嚇到了,然後繼續期待你貼上美食訊息,各方好漢的學院路數,或者你已經默默耕耘讓大家期待好一陣子的好消息。我們都在等,你一定馬上就回到我們面前,靦腆又自在地嘲笑我們的擔憂。
收到噩耗是正在搭捷運準備出國的路上。當消息靈通的學生們開始對你表達哀傷和無法置信的不捨之意,我憤怒地認為這是個粗劣而過分的玩笑,即使想要激勵你快快回來也不該如此。但臉書上訊息越來越明確地湧來,胸口感覺一陣悶熱,隨著充斥腦海的是Ronato Rosaldo 曾經描述的那種失去親人的憤怒傷痛,模糊地混合著你一貫豪氣萬千的笑容。難以理解,難以接受。你的存在那麼地貼近大家那麼地真實,我無法理解你為何就這麼走了,卻又對你如此瀟灑的生命感到無比震撼和衝擊!
別了,伯楨吾友。你所留給學生和好友故舊的已經太多太多。留下我們無法停止地想念著你,想你在另一個世界,也如此瀟灑自在,令人羨慕。
謝謝你,一路好走。
宜澤(筆於荷蘭東部Enschede閣樓)
by 李宜澤
──
跟伯楨認識二十多年了,他晚我兩屆進人類系,他一向稱我學長,但我始終視他為好友,直呼伯楨。究竟跟他碰面聊天多少次,已不復記憶,其中有兩次確實是通宵達旦。有一回,我準備提出研究所口試的研究計畫,當時電腦還不怎麼普及,寫妥文稿,正在煩惱送到哪裡打字之際,他一口答應幫我搞定,我為此去了他家,熬夜趕工到天亮。
多年後,又有一次跟伯楨徹夜未眠,跟眾多師生職工幫洞洞館守護最後一夜。洞洞館化為花田,匆匆幾年又過去,近幾個月來伯楨為人文大樓疾呼奔走,如今,讓人類系及哲學系師生早日遠離危樓、重回椰林,已成為伯楨的未竟遺願。
伯楨,由衷感謝你多年來的幫忙,點滴在心頭。如今你已放下世間勞碌,請安息。
by 徐雨村
──
給我的學弟伯楨
2011那年四月底我和你走出波士頓劍橋的木蘭餐廳,一路上黃昏的光影灑向回家的方位。隔天我即將離開哈佛,你當時是燕京學人尚需多留兩個月,陪著我走了這段路。笑著說當年我大學畢業前夕,把你(因著一位韓籍同學未受照顧)罵了一頓,委屈卻戲謔地解釋了其中詳情。那一刻我驚訝那二十年前窩在洞洞館地下室(系學會)自在地翻閱《少年週刊》的學弟,竟是如此的信任與包容,一如那天夕陽餘韻令人驚艷。
我(或是任何人)總是可以自在地和你說話著,在你PS2電玩把手大辣辣擺在書桌的研究室裡、在台大滿是鬍渣酒瓶的單身宿舍、哈佛的租賃公寓中,或是波士頓的芬威球場上,從求學生活、授課書寫、指導學生,到社會運動、休閒嗜好、生活哲學。你總是以身作則又細膩真誠,特別懂得待人處事的道理。即便是情愛這一回事,你總替對方設想。我直誇你家教好,用照顧家人的方式對待身旁所有學生和朋友,和系上的狗狗們(還掏錢協助結紮呀你)。
這一路彷彿回到大學時光,十個月共同在哈佛生活,聽著你敘說高中、大學、為人師表的歷程。木蘭餐廳的菜極為好吃,我說:「等我中了樂透,就在這餐廳旁買下一間公寓,可以天天過來吃。」你虧笑著:「學長,等你有錢了,乾脆把木蘭的廚師請來煮給你吃不更好?真是窮到連作夢都不會呀。」(啊,學弟呀,你是對的。去年木蘭耶誕節遭了火災歇業。好在我還沒買下隔壁公寓。)
洞洞館傳說中的「狗與豬頭不得進入系館」是你給的封號(以紀念我不得系上師長緣),我笑著抗議「憑什麼狗排在我前面?」如今成為絕響。伯楨呀,我知道光是這一點,那豪情式爽朗笑聲會讓我更加憤憤不平(然後你會更開心)。
啊,親愛的學弟,謝謝你,這一切的生活相處。安心。我們依舊生活頹廢,但在某個時刻總會想起你的容顏。你將永遠年輕永遠如此美好。我會試著不那麼想念你。
by 林徐達
──
伯楨是我的大學同學。
伯楨是幽默的。我常驚訝於他如湧泉般的笑話與獨特的敘事風格,靈活慧黠卻一點都不尖酸刻薄。他是語言的藝術家,他的為人與他的語言風格一樣敏於觀察環境,卻沒有傷人的犀利。我總好奇,難道他從來都不會有情緒低潮的文青式憂鬱?
伯楨是溫暖的。聰明孤芳自賞(且天龍人居多)的台大校園中,他對待同學、學生與系狗之溫暖,是讓人相信這個世界的確有所謂真誠這種美德。特別是前臉書時代,他提到因為擔心學生的情緒與情感而必須每天監看他們的部落格,將所有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處理與對待,改寫了我將台大等同於冷漠的譬喻等式。
伯楨是充滿活力的,我常懷疑他是裝了金頂電池的兔子(如果是小黑貓該多好),永不斷電。
伯楨是忠於感官愉悅的,他提醒了生命本該投注在自己認為美好的事物上,例如美食、美酒、咖啡、甜點與陳昇跨年演唱會,這些愉悅與美好不該為了學術而犧牲。
伯楨是專業嚴謹的,他體現了專業與享受生命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是可以並存在。
伯楨是深具公民與社會歷史意識的,因為脫離了社會真實的知識,不過就是異化的學術資本。
伯楨是美好的,是入世、有人味的那種,不是超凡入聖的那種。正因為這種種貼近著人的美好,才會不捨、悲慟,縈繞心頭久久不曾散去。
在揪心的眼淚中思忖著,若有墓誌銘,老同學,我該為你寫些什麼呢?
「這裡躺著一位人間天使,他燃盡生命花火,暖亮了身邊的人;這裡躺著一個天使教師,他讓知識變得美味可口健康;這裡躺著一名幽默熱情、亦師亦友的人,他讓疏離人間時時溫煦。」
當你踏上了前往天堂的畢業旅行,塵事煩擾將不再入你眼簾---而我竟開始羨慕起這樣的你。
by 鄭瑋寧
──
伯楨:
只能在這第七天寫信給你。因為實在難以言說,你的離去之重。
或許是因為年紀相彷,或許是因為都剛升等(但你做得比我多太太太多了),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你是個讓人打從心底歡喜與佩服的好人。
某年一夥人同行京都,研討會前晚我請素玫協助法文翻譯(在你稍嫌混亂的房間裡),沒想到後來卻竟連你也下來幫我弄ppt。後來屢次想起都覺得神奇:一位考古學家幫我弄ppt耶,那ㄟ安捏?
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你,總是對任何人慷慨地伸出手,總是無視於那些我們在長年學術養成過程中一併內化的種種身份、領域、機構的隱形界限/線,雞婆地承擔許多「分外」之事。曾幾何時,那些一開始或許是用來自我保護、但到頭來其實是把我們綑縛於更多工作與工作與工作的界限/線,讓學術成為高度競爭、極少合作、同行相輕、位階重重的冷酷異境。某位前輩曾說:學術圈裡無朋友,彼時剛拿到入場卷的我聞言只能暗自心慌。然而現在的我卻想說:不,事情不是這樣的。學術圈就跟任何工作場域一樣適合友誼與合作,而任何有趣、開創性的學術工作也必來自於廣義同儕間的相互滋養。
單一種植(monoculture)或許讓作物長得快、產量高、好管理、有效率,但作物也容易生病,長期來說更有礙於種源創新。單一種植、自我封閉、為求績效而計點計分計日計時的學術勞動,也從根本違悖了人文學科厚植蘊積、反身對話的本質,而讓我們枯萎。 伯楨,你在這樣一個勞動體制的頂端求生,卻還是大方地為學生、為同儕、為社群、為阿貓阿狗、為公共對話慷慨佈施你的情感、時間與精力。在一個開放互助的社群中這或許是一種互惠,然而在多數敏於自保的學術圈(許多徒具形式的審查與評鑑真是累壞了所有人啊),如此不從眾地慷慨,或許也長期地讓你過勞了吧。
在我所學習的佛教中,羅漢與菩薩都是開悟的自性。羅漢開悟後不染俗埃,菩薩開悟後則乘願再入紅塵,只為以大佈施渡化眾生。無論是溶於水的鹽,還是包覆文物的土壤,你的肉身佈施,想來其實是一種最為「人文」的學術工作典範:允樂拔苦,除嫉無執,慈悲喜捨。如今你願已了,於是瀟灑證道,而在這遽然的告別中,你依然是在示現於我們:萬般不捨,依然要捨。
謝謝你的人間佈施,伯楨。
by 蔡丁丁

(接龍待續)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芭樂合作社 悼我們親愛的夥伴「芭樂貓」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445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本來只聽過紅心芭樂,今天開始,我對芭樂的理解要多了一個新品種:“傷心芭樂”。
我無法像佩宜可以這麼理性地去整理伯楨曾經寫過的文章,我腦中現在塞滿了他這個人。
對我來說,不能再看到他的人,聽到他的笑話或貓事,都讓我感到巨大的傷痛。
最讓我揪心的是:再也不會有人在星期一敲我的電腦對我說:“學姊,我文章貼好了喔。只剩下廣告詞就可以出了。” “學姊忙的話,廣告詞我來寫好了!”
好痛!
一直以來都喜歡看學弟對各種議題的關懷,也喜歡看他和小黑貓的對話,原來老師和研究者也可以是這樣的,我總是這麼地想。
感覺上失去了一位夥伴,這是個哀傷的週末。
人生中第一次從身到心從心到身,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殘酷是在爸爸離開時;第二回是畢業到暨大任教不久後,從中央山脈的那端傳來博論田野地的部落弟弟意外車禍身亡的消息;再來就是今天下午在豔陽高照的小米園中,突然聽到伯楨已經走了……
因為相差了好幾屆,我在台大人類所讀書時不認得伯楨,開始用臉書之後才知道有這個如此特別的學弟,看著他超有意思的po文以及對學生極其用心和貼心的舉止,簡直讓我崇拜,因此,當聽說伯楨要來郭素秋老師在暨大的課堂上演講,我就像個粉絲一樣慕名前往。那是我們的初次見面,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聽考古的演講,並且唯一一次覺得考古有趣的時刻。
其實我和現實生活中的伯楨並不熟,我們見面的次數不多且總在人多的場合,有過的對話只是寒暄或聊所上考古的學生,不曾有過深談。可是為什麼我會如此的痛,痛到實在超出自己的想像。或許是因為我覺得和他之間有不少的相似之處; 都是和學生非常親密的老師,都愛在臉書上展露我們心中的喜怒哀樂,都把學生看成我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重讀伯楨一篇篇的芭樂文,一方面忍不住眼淚直流,一方面又覺得安慰,還好有這些芭樂文,可以讓不熟伯楨或不認識伯楨的人得以從中真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位如何與眾不同,既溫柔又熱情的考古學者。
早上起床接到噩耗,完全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這幾年來亦師亦友,相識超過十年,一直是我研究上的標竿,走上中國研究這條路也要感念許多指點提攜, 謝謝你,讓我走向安陽,帶我進入芭樂人類學的寫手群,更新台灣人類學圈的消息,謝謝你告訴我看到我這幾年的進步。記得有一年從北京到成都十幾個小時的火車臥鋪,才發現護照留在北京的青年旅館,那是個冬天的深夜,旅館拒收、街邊冷清、人生地不熟、緊急打電話回台灣求救,我不知道你打了多少通電話,但一個小時後,我就被安置在往郫縣的哈佛考古隊歇息旅館的路上。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個晚上沒有你的幫忙,也許我就客死異鄉。而我受惠於你的又豈止是這些? 點滴在心,所以我說我要參加你的婚禮,因為紅包已經準備了好幾年,每回多一份幫助,重量就往上加。去年約莫也是此時接到光仁學長的噩耗還能點點滴滴的寫篇訃聞,可與你之間的友情,又豈是一篇文章能數盡,因你總是這麼地熱心於人。
一直看到你在學術上的熱情從你還是個博士生、助理教授到副教授,身分轉變並沒有改變你待人處事的態度,總是盡其所能提攜後輩,相識的師長、朋友與學生,都難忘你的陽光、爽朗的笑聲、對生活的熱情。無奈上天要你去當天使,看看這世間還有許許多多的師長朋友學生感念著你的一切,我想你會欣慰的離開,一路好走~
離台前你才找我吃飯像是tutorial一樣,那時的我很挫折也很徬徨,我會記得你的勉勵,突然覺得這一條研究的路,就剩自己在走了。
重讀你的芭樂文,彷彿你依然還在我們身邊...
記得2012年夏天初從加拿大到台灣進行博士田野的前期調查,經友人介紹下戰戰競競的到了被形容為「快倒下來」的水源枚舍找你吃午飯。你是我在香港遇上容老師後,第二個被我硬抓去提供有關鬼島研究的意見的台灣老師。在你帶我走進美男美女美食雲集的咖啡廳後,那1.5小時的天南地北,就和那份漢堡的味道般讓人回味。
2014年田野期間,帶著南部特產的黑皮膚上來台大聽人演講,我們的重遇簡單不過;三月份太陽花在凌晨一點的大街上相遇我沒有感到驚訝,因為我就知道您一直守護在學生身邊。後來我到台北做田野時,順道和你相約去吃東西,你帶我去哪裡我倒是忘了,只因為你t-shirt上的虱目魚和貓的故事更吸引我。你是為我而穿上台南虱目魚的紀念版吧(我可是嘉義來的)!
然後,在人類學年會好像只聊過幾句,但您那件龜派戰衣確實使我難忘。
感謝您,在我兩天前臨時拉伕 (香港用語) 下找你帶香港學生去逛校園,你不但沒推辭,還安排得比其他人籌備個一百二十天來得要周到。半年後,我離台回加國前往來台大圖書館看資料的日與夜,也不時泛起你細說台大的記憶。
原來,在校內博物館的樓梯邊臨時聽到傑出老師的課,已經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了。
我還欠你一頓吃到飽的虱目魚、白蝦和蚵仔盛宴,最後看到的是你慷慨贈友的wii fit踏板,以及瞼書上可愛的小黑咪照片。心裡的失落正和實際數小時的人生互動相互交織,裝作專業地稍為抽身再觀察我在你人生故事裡的短暫參與,你那可愛又熱血的處事方式早已烙刻在晚輩的心裡,成為我們日後教研處世的最佳指標。
再見了,伯楨師。
悼伯楨老師
我家的小朋友聽完我聊伯楨老師這麼輝煌的一生,談起他的黑貓生態故事、他的中國泥土田野,還看著他那從考古坑裡奮力爬出來的那股形象,小孩突然用他們國中最近教到一首詞比擬,讓我心頭一震:
1.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2.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虞美人・聽雨)
伯楨老師在過去好些年總有機會和我在學術會議場合相遇,有考古的、也有人類學的。他那慧頡的閃亮亮眼神都是帶著力量,沒有疲憊,放電地訴說著他新從田野感受回來的挑戰論點,諸如科技不敵苦工、或是當地人與事物現象的荒謬弔詭。我想想,我們也都算壯年了吧,但庸庸碌碌奔波這麼多年這些可憎的俗務,只有伯楨老師那樣有氣力的身影,算得上是一直滿懷熱情、充滿希望力量,卻又對抗體制、對抗壓力的不朽勞形。
3.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4.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宋・蔣捷的詞)
伯楨老師翻開的那些東西真是無情嗎?有些發掘應該是,有些則未必。伯楨老師用心最深的就是「物」的層位學,從鹽到辣椒,這些東西被埋藏、和發現後的歷史脈絡,不正是「人」有情地、糾纏地創造嗎?然而,他就這樣悄然無情地走了,對照他創造了那麼多爽朗的大笑,這像不像是一記刺向這個時代的巨大諷刺?
是真的有累了。我趕緊在悲憤地沈沈地入睡前提議:伯楨老師最後參與的「鹽古時代特展」,大家有空再去流連看看吧。在十三行博物館,到2015年8月31日。特展介紹裡有著一小條說明:
「因為鹽的可溶性,讓我們無法追溯到最早的鹽業生產,通常要發展到相當的生產規模時,考古學家才能在遺址中發現早期製鹽的行為。」
天哪,是怎樣等你走了之後,我們才發覺出你的規模,做了那麼多事,留下這許多記號。伯楨,你就像那重要的鹽粒,溶掉了,才讓接觸過你的味蕾世界遍布著你的味道,無法忘記的力量!
「一切關鍵的經歷都是負面的:生存的堆積缺乏厚度;心靈與存在的考古學家,挖掘它們,找到最後,就只會面對一片空虛的深淵。而他那時再怎麼懷念表像的裝點也都無濟於事了。 」(Cioran,解體概要:死亡變奏)
「不可能哭泣保養着我們對事物的喜好,讓它們得以存在下去:這種不可能,阻止我們嘗盡事物的滋味,也阻止我們掉轉頭去。當我們的眼睛,在那麼多條路上,在那麼多道岸邊,拒絕被自己淹沒,它們是在用自己的乾澀保存那些令它們驚喜的東西⋯⋯那些進入了我們的贊嘆與哀傷的東西能留下來,只是因為我們不曾以液態的訣別犧牲或祝福它們⋯⋯就這樣,每當夜已盡,面對新來臨的一天,必須卻又無法填滿它,這一事實使我們驚懼不已;而,身處光明這個異邦,彷彿世界剛剛經歷了震顫,發明了它的太陽。我們就要逃離淚水一一因為只需一滴,就可以把我們從時間中擠出去。」(Cioran,解體概要:寫在瞬間的邊上)
紀念讓人喜愛的伯楨,在你走的隔天清晨。
上週,電影配樂大師James Horner在熱愛中的飛行中離世,伯楨老師則是在熱愛的學術工作中離開我們,他的典範、啟發和熱情的笑容則永遠長存在世人心中。
伯楨老師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不僅在研究上面很傑出(他在臉書上談以前半夜在洞洞館待到十二點目睹淹水的故事),在教學上面也極其認真(總是看到他在臉書上面跟學生頻繁互動),心想伯楨老師除了睡覺時間,應該是把所有的生命都燃燒在學術志業上面了吧!伯楨老師正值壯年卻離開世間,真的非常可惜,他在芭樂人類學上面的文章介紹考古學,文筆詼諧幽默,也啟發了我們對考古遺址、文化遺產及觀光化的研究興趣,還是要說聲:感謝伯楨老師。
自稱「人白木」的伯楨吾友:
認識你的時間不長,但是卻好像從小就互相熟識的朋友。第一次跑到你水源校區的研究室,是為了見證你說的那個不斷坍塌又鼠輩橫行的狹小空間。我看到研究室裡面資料堆積如山,你從裡面左蹦右跳,抽出一疊疊的資料重新歸位,讓我見識到「哲人日遠」之後,台大是怎樣把人文精神踐踏在侷促的狹小空間裡。
之後在不同的地方和你相遇,聽你講四川考古的種種奇妙故事(我想你可能是唯一被邀請到社會學課堂上去講課的台灣考古學者),說為學生備課上課甚至口試旁聽的種種秘密訊息,在台大附近見證各個曾經存在或慢慢消失的人與事物,還有大家天天期待的黑嚕嚕生活日記和美食饗宴:你的生活內容變成了大家生活當中不可缺少的部份,你的個人觀察成了我們的公共視野。
學期末的失聯,沒想到竟是你身體狀況的警訊。好友們都在自我安慰地想,等你硬朗地恢復之後,要虧你怎麼這麼容易就把大家就嚇到了,然後繼續期待你貼上美食訊息,各方好漢的學院路數,或者你已經默默耕耘讓大家期待好一陣子的好消息。我們都在等,你一定馬上就回到我們面前,靦腆又自在地嘲笑我們的擔憂。
收到噩耗是正在搭捷運準備出國的路上。當消息靈通的學生們開始對你表達哀傷和無法置信的不捨之意,我憤怒地認為這是個粗劣而過分的玩笑,即使想要激勵你快快回來也不該如此。但臉書上訊息越來越明確地湧來,胸口感覺一陣悶熱,隨著充斥腦海的是Ronato Rosaldo 曾經描述的那種失去親人的憤怒傷痛,模糊地混合著你一貫豪氣萬千的笑容。難以理解,難以接受。你的存在那麼地貼近大家那麼地真實,我無法理解你為何就這麼走了,卻又對你如此瀟灑的生命感到無比震撼和衝擊!
別了,伯楨吾友。你所留給學生和好友故舊的已經太多太多。留下我們無法停止地想念著你,想你在另一個世界,也如此瀟灑自在,令人羨慕。
謝謝你,一路好走。
宜澤(筆於荷蘭東部Enschede閣樓)
跟伯楨認識二十多年了,他晚我兩屆進人類系,他一向稱我學長,但我始終視他為好友,直呼伯楨。究竟跟他碰面聊天多少次,已不復記憶,其中有兩次確實是通宵達旦。有一回,我準備提出研究所口試的研究計畫,當時電腦還不怎麼普及,寫妥文稿,正在煩惱送到哪裡打字之際,他一口答應幫我搞定,我為此去了他家,熬夜趕工到天亮。
多年後,又有一次跟伯楨徹夜未眠,跟眾多師生職工幫洞洞館守護最後一夜。洞洞館化為花田,匆匆幾年又過去,近幾個月來伯楨為人文大樓疾呼奔走,如今,讓人類系及哲學系師生早日遠離危樓、重回椰林,已成為伯楨的未竟遺願。
伯楨,由衷感謝你多年來的幫忙,點滴在心頭。如今你已放下世間勞碌,請安息。
給我的學弟伯楨
2011那年四月底我和你走出波士頓劍橋的木蘭餐廳,一路上黃昏的光影灑向回家的方位。隔天我即將離開哈佛,你當時是燕京學人尚需多留兩個月,陪著我走了這段路。笑著說當年我大學畢業前夕,把你(因著一位韓籍同學未受照顧)罵了一頓,委屈卻戲謔地解釋了其中詳情。那一刻我驚訝那二十年前窩在洞洞館地下室(系學會)自在地翻閱《少年週刊》的學弟,竟是如此的信任與包容,一如那天夕陽餘韻令人驚艷。
我(或是任何人)總是可以自在地和你說話著,在你PS2電玩把手大辣辣擺在書桌的研究室裡、在台大滿是鬍渣酒瓶的單身宿舍、哈佛的租賃公寓中,或是波士頓的芬威球場上,從求學生活、授課書寫、指導學生,到社會運動、休閒嗜好、生活哲學。你總是以身作則又細膩真誠,特別懂得待人處事的道理。即便是情愛這一回事,你總替對方設想。我直誇你家教好,用照顧家人的方式對待身旁所有學生和朋友,和系上的狗狗們(還掏錢協助結紮呀你)。
這一路彷彿回到大學時光,十個月共同在哈佛生活,聽著你敘說高中、大學、為人師表的歷程。木蘭餐廳的菜極為好吃,我說:「等我中了樂透,就在這餐廳旁買下一間公寓,可以天天過來吃。」你虧笑著:「學長,等你有錢了,乾脆把木蘭的廚師請來煮給你吃不更好?真是窮到連作夢都不會呀。」(啊,學弟呀,你是對的。去年木蘭耶誕節遭了火災歇業。好在我還沒買下隔壁公寓。)
洞洞館傳說中的「狗與豬頭不得進入系館」是你給的封號(以紀念我不得系上師長緣),我笑著抗議「憑什麼狗排在我前面?」如今成為絕響。伯楨呀,我知道光是這一點,那豪情式爽朗笑聲會讓我更加憤憤不平(然後你會更開心)。
啊,親愛的學弟,謝謝你,這一切的生活相處。安心。我們依舊生活頹廢,但在某個時刻總會想起你的容顏。你將永遠年輕永遠如此美好。我會試著不那麼想念你。
伯楨是我的大學同學。
伯楨是幽默的。我常驚訝於他如湧泉般的笑話與獨特的敘事風格,靈活慧黠卻一點都不尖酸刻薄。他是語言的藝術家,他的為人與他的語言風格一樣敏於觀察環境,卻沒有傷人的犀利。我總好奇,難道他從來都不會有情緒低潮的文青式憂鬱?
伯楨是溫暖的。聰明孤芳自賞(且天龍人居多)的台大校園中,他對待同學、學生與系狗之溫暖,是讓人相信這個世界的確有所謂真誠這種美德。特別是前臉書時代,他提到因為擔心學生的情緒與情感而必須每天監看他們的部落格,將所有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處理與對待,改寫了我將台大等同於冷漠的譬喻等式。
伯楨是充滿活力的,我常懷疑他是裝了金頂電池的兔子(如果是小黑貓該多好),永不斷電。
伯楨是忠於感官愉悅的,他提醒了生命本該投注在自己認為美好的事物上,例如美食、美酒、咖啡、甜點與陳昇跨年演唱會,這些愉悅與美好不該為了學術而犧牲。
伯楨是專業嚴謹的,他體現了專業與享受生命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是可以並存在。
伯楨是深具公民與社會歷史意識的,因為脫離了社會真實的知識,不過就是異化的學術資本。
伯楨是美好的,是入世、有人味的那種,不是超凡入聖的那種。正因為這種種貼近著人的美好,才會不捨、悲慟,縈繞心頭久久不曾散去。
在揪心的眼淚中思忖著,若有墓誌銘,老同學,我該為你寫些什麼呢?
「這裡躺著一位人間天使,他燃盡生命花火,暖亮了身邊的人;這裡躺著一個天使教師,他讓知識變得美味可口健康;這裡躺著一名幽默熱情、亦師亦友的人,他讓疏離人間時時溫煦。」
當你踏上了前往天堂的畢業旅行,塵事煩擾將不再入你眼簾---而我竟開始羨慕起這樣的你。
伯楨:
實在難以言說,你的離去之重。
或許是因為年紀相彷,或許是因為都剛升等(但你做得比我多太太太多了),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你是個讓人打從心底歡喜與佩服的好人。
某年一夥人同行京都,研討會前晚我請素玫協助法文翻譯(在你稍嫌混亂的房間裡),沒想到後來卻竟連你也下來幫我弄ppt。後來屢次想起都覺得神奇:一位考古學家幫我弄ppt耶,那ㄟ安捏?
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你,總是對任何人慷慨地伸出手,總是無視於那些我們在長年學術養成過程中一併內化的種種身份、領域、機構的隱形界限/線,雞婆地承擔許多「分外」之事。曾幾何時,那些一開始或許是用來自我保護、但到頭來其實是把我們綑縛於更多工作與工作與工作的界限/線,讓學術成為高度競爭、極少合作、同行相輕、位階重重的冷酷異境。某位前輩曾說:學術圈裡無朋友,彼時剛拿到入場卷的我聞言只能暗自心慌。然而現在的我卻想說:不,事情不是這樣的。學術圈就跟任何工作場域一樣適合友誼與合作,而任何有趣、開創性的學術工作也必來自於廣義同儕間的相互滋養。
單一種植(monoculture)或許讓作物長得快、產量高、有效率,但作物也容易生病,長期來說更有礙於種源創新。單一種植、自我封閉、為求績效而計點計分計日計時的學術勞動,也從根本違悖了人文學科厚植蘊積、反身對話的本質,而讓我們枯萎。
伯楨,你在這樣一個勞動體制的頂端求生,卻還是大方地為學生、為同儕、為社群、為阿貓阿狗、為公共對話慷慨佈施你的情感、時間與精力。在一個開放互助的社群中這或許是一種互惠,然而在多數敏於自保的學術圈(許多徒具形式的會議與審查工作真是累壞了所有人啊),如此不從眾地慷慨,或許也長期地讓你過勞了吧。
在我所學習的佛教中,羅漢與菩薩都是開悟的自性。羅漢開悟後不染俗埃,菩薩開悟後則乘願再入紅塵,只為以大佈施渡化眾生。無論是溶於水的鹽,還是包覆文物的土壤,你的肉身佈施,想來其實是一種最為「人文」的學術工作典範:允樂拔苦,除嫉無執,慈悲喜捨。如今你願已了,於是瀟灑證道,而在這遽然的告別中,你依然是在示現於我們:萬般不捨,依然要捨。
伯楨啊,謝謝你的人間佈施。
蔡丁丁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