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蓋婭》導讀
人類世的憂鬱與療癒
這幅喚做《憂鬱》(Melencolia I)的版畫可說是藝術史上最著名的圖之一。作者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日期為1514年。我們看到一名一籌莫展的女性,收起她的翅膀,左手托腮,右手拿著圓規。在她的右手邊,坐著一名同樣收起翅膀、愁眉苦臉的男孩。把視線移到女子腳邊。我們看到一條病懨懨的狗,幾枚釘子、一把鋸子、刨子跟一個球體。把目光投向女子身後,我們看到天平、沙漏與鐘,以及一個四階的魔方陣,各行列及斜線數字的加總都是34。再把視線移往遠處,我們看到一把梯子,一處城市以及一面海;海上有道彩虹,彩虹包裹著一枚發光的星體,有條怪獸哀嚎著,飛過海面,爪子上抓著標語,上頭寫著「憂鬱」。

藝術史家告訴我們,這張版畫上充斥著讓當時人們陷入憂鬱的象徵:知識。如薩諾斯告訴鋼鐵人般的,「你不是唯一受到知識詛咒的人」。不過,科學史家也告訴我們,《憂鬱》展示之憂鬱來源可能還不只是工程或數學。原來,那枚在天邊閃耀的天體可能不是太陽,而是一枚於1492年撞擊昂西賽姆(Ensisheim;位於今日的法國)的隕石。可以想見,在那個歐洲人普遍相信地球是個渾圓的球體,為宇宙的中心,而宇宙秩序係由造物者精心設計的年代,一塊從天而降、發出巨大閃光與爆炸聲、且在落地時摧毀一片小麥園的的石頭,會對此世界觀構成多大的挑戰。1492年的人們確實有一大堆憂鬱的理由。
等等,1492年!你心中似乎有個聲音,那不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年代?環境史家告訴我們,就美洲印第安人而言,當一顆火球撞擊昂西賽姆、讓白人陷入憂鬱時,他們憂鬱的年代也正要到來。當《憂鬱》成型之際,大西洋另端的白人移居者引入了槍砲與傳染病。到了1610年,印第安人的人口少了五千四百萬人。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森林開始再生,將大量的二氧化碳固定下來。此由人類觸發之地質現象是如此顯著,2015年,當地質學者開始爭辯,是否要在全新世中畫出人類世時,一度考慮將1610年視為人類世的起點。
2015年,法國人類學家、科技與社會研究者拉圖正改寫其2013年於愛丁堡發表的一系列演講,主題為自然宗教。他注意到,是年3月,著名的《自然》(Nature)雜誌出版了「人類時代」(The Human Epoch)專刊,試著以「人類世」取消兩個「對立了三個世紀」的詞彙。據他表示,當他讀到,1610年可能為人類世的起點時,「久久不能平靜」。「『大發現』、殖民化、土地佔領引發的戰鬥、森林、二氧化碳—與人類世有關的一切都到齊了」。博學如拉圖,他馬上就聯想到1610年還有另件大事發生:一名「大鬍子古怪工程師」伽利略出版他的《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令世界歷史(histoire universelle)走出它的『封閉世界』,朝向『無限宇宙』推進」。拉圖認為,「這兩個日期頗相互輝映」,第一個1610年「把我們帶到地球的盡頭」,第二個1610年「則使我們脫離這個地球」。
關於1610年的探索還沒結束。法國人拉圖又聯想到,1610年也是法國國王亨利四世(Henri IV)遭到暗殺的時點,「開始了恐怖的17世紀」。英法鏖戰三十年,「蹂躪全歐洲」。依拉圖的見解,「面對暴亂的絕望」,以及對純粹、絕對與確定性的渴望,一方面讓人們簽訂了西發里亞和約,奠下主權國家的基石;另方面,「理性主義者即將摒棄人文主義者的構思」,「對特殊事物的關懷變成對普遍性的執念」,「懷疑主義被代之以獨斷主義」,「為了精神便排除掉身體」,「用嚴肅替換詼諧」,「用邏輯替換拼貼」,「用不容置疑替換商酌討論」等。就拉圖而言,這一連串的取代與替換一方面讓所謂「全球思考」成為可能;另方面,也讓「全球思考」淪為一種「西方式的執念」,是「貨真價實的『白人男性包袱』」。在此全球思考中,「全球思考」就如《憂鬱》描繪的情景,一顆擺在地面的球體,思考者凌駕於上;即便思考者或許正擔憂著這球體上發生的大小事件,他的眼光甚至不在球體之上,而是飄向遠方,彷彿期待來自彼岸的救贖。1610年,脫離地球的我們開始不知道如何接地氣(earthy)的討論地球。
人們甚至失去憂鬱的能力。
拉圖就人類世的種種思考讓他完成各位手上的《面對蓋婭》。值得一提的,儘管拉圖做了大量的改寫,本書還是以講稿的形式展現。若各位讀者期待從中讀到拉圖對其著名之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摘要,或雄辯滔滔地駁斥研究者對其理論的誤解,可能會大失所望。或許是意識到讀者可能的反應,拉圖表示,他「之所以保留演講這種文類及其風格與口吻,那是因為四十年來我一路追索的『現代人的人類學』,日益呼應所謂新氣候體制的情境」。原來,拉圖繼續說道,「現代人從前認為理所當然的物理架構,這塊讓他們的歷史不斷上演的土地,如今已變得很不穩定。彷彿原本的布景也登上舞台,要與演員一同參與戲劇情節」。「說故事的方式全都變了」,拉圖表示,「我們原以為大自然浩瀚的循環位處後台,在前面的人類歷史則永遠與它沾不上邊」。人類世的概念攪動了這一切,拉圖觀察到,但17世紀的沈屙是如此牢不可破,導致環繞在人類世的討論如不是期待科學家或工程師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就是把氣候變遷視為政治問題,期待有個大無畏、至高無上的政體能「全球思考」,指導與規範人們的「在地行動」。就拉圖而言,這這些做法如不是打造一個終將傾頹的巴別塔,就是要實現一個終將成為他人之地獄的天堂。「人類世的人意味的不是什麼人類物種,甚至也不是『普遍的人』」。拉圖以三個驚嘆號表達他對人類世一詞的感受:「人類世的人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倒下之後的巨大巴別塔。人類總算不能再被統一起來!人類總算不再離開地面!總算不再脫離大地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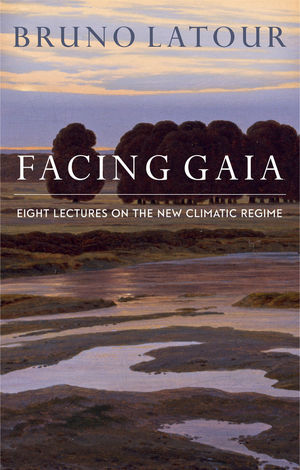
《面對蓋婭》提供了一個回到地表的路線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要激起人類回到地球表面或「處世」(with the world)的慾望。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種種挑戰,拉圖喟嘆,「我們忘記了,在研究應該要做些什麼之前,應該先是受到某類特殊的陳述所策動。這些陳述觸碰到我們內心,使我們移動」。於是,如果說80年代的拉圖鉅細彌遺地描繪科學家如何把自己打造為綜覽全局的計算中心,90年代的拉圖雄辯滔滔地把自己打造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計算中心, 2000年的拉圖是個劇作家、動畫師或舞台監製,主導一部叫做「蓋婭」的長片。「如果蓋婭是一齣歌劇,那麼這齣歌劇既未分段,也無終局,同一幕絕不二度上演。如果架構、目的、方向通通不存在,那麼我應該把蓋婭視為一段過程的名字—在此過程中,由於多變而偶然的因緣(occasion)而使往後的事件更有可能發生」。這會是部相當療癒的展演,拉圖認為,我們將共同「發現一種療程」,其目的與其說是要迅速地「痊癒」,更重要的毋寧是「重新思考進步的概念」,乃至於「發現其他感受時間之流的方式」。既然這是一部沒有終局的長片,就會如《終局之戰》般的沒有片尾彩蛋。甚至,如果說眾英雄們還有那一千四百萬分之一的希望去打敗薩諾斯,這部片卻要觀眾「不要再談希望」,而是要探索「一種夠細緻的方式去擺脫希望」。
當群學邀我為拉圖這本新書寫序時,我覺得受寵若驚,也陷入了憂鬱。我的憂鬱讓我想到了杜勒的《憂鬱》,謝天謝地,《面對蓋雅》沒把《憂鬱》當成分析對象,讓我在拉圖讓人喘不過氣的博學中,看到一絲希望。噢,還有,身為一個動漫愛好者,我想我有更直接的方式說明《面對蓋婭》的主旨。這裡的拉圖就相當於《JOJO冒險野郎》的喬魯諾・喬巴拿,其替身「黃金體驗」的能力便是透過重擊物質,賦予物質生命,讓生物的生命超載。黃金體驗讓物質不只是 “matter of fact” (即「事實」)。追根究底,matter matters。
《面對蓋婭》共包含了8次重擊。你準備好了嗎?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洪廣冀 《面對蓋婭》導讀:人類世的憂鬱與療癒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729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也太浮誇,跟韓國瑜一樣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