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風潮下之人類學教學隨想
2011年才過了一半,我們就已經歷了兩個末日。先有台灣王老師的511大地震預言,緊接著是「美國王老師」坎平(Harold Camping)神算出的521末日審判,當然事後都證實只是虛驚一場,但末世烏雲依然罩頂,明年還有流傳已久的2012人類末劫說等在前頭。末日預言出現的歷史幾乎就跟人類文明史一樣長久,有關世界盡頭的警示,一方面反映了面對現況的批判省思,另方面則具現了「毀滅重生」的集體期盼,意涵其實是相當積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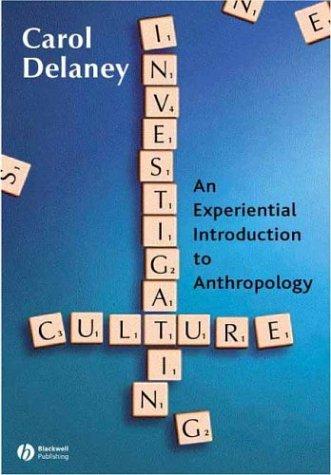
在所有學科之中,人類學擁有傳統最為悠久的末日論述。根據Karl-Heinz Kohl(2010)在〈人類學的終點─沒完沒了的爭辨〉一文中所說,人類學的滅絕,甚至在學科誕生之前就已經命運註定了;早自18世紀初期就有耶穌會士傷心地寫道,人類學學科命脈所繋的研究對象,也就是「野蠻人」(原文是sauvages),已在歐洲文明污染之下變得不再天真。到了19世紀,預期部落文化即將消失的焦慮感更是鮮明,因此才有搶救民族誌(salvage ethnography)的出現,以一種與時間賽跑的焦急心情,在(想像的)田野地毀滅之前儘快捕捉落日餘暉。
到了1960年代,當越來越多地方部落急速捲進國族工程與現代化浪潮時,新一波關於人類學危機的討論跟著浮現,Peter Worsley在1966年發表的論文,為廿世紀人類學敲下第一響喪鐘。然而,眾多唱衰聲中人類學依舊頑強地活著,直到世紀之交,美國人類學會前會長James Peacock警告說,人類學若不正視並力圖改變學科日趨邊緣的社會定位,則只剩下兩種未來選項:「滅絕」、以及「像僵屍一樣賴活」(Peacock 1997)。時間來到2010年,John Comaroff為《美國人類學家》期刊編了一個名為〈人類學(非)末日再度來臨?〉的專題,主標題驚悚,副標題〈針對學科未來的一些想法〉卻充滿向前看的樂觀氛圍,基本上,專題作者群主張,只要服用他們開出的各式處方,人類學是可以頭好壯壯地活到下一個世紀。
這些在人類學發展歷程中如影隨形的末世論調,顯現了人類學者「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魄力,希望藉由概念架構、研究方法、及知識生產的重組轉型,讓低迷許久的人類學振衰起蔽,重生再興。但其實人類學還有另外一個好好活著的理由,就是它在大學人文課程中應扮演的關鍵教育功能。黃樹民先生在今年的《通識在線》中寫道,介於自然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人類學,由於其「多面性」與「廣博度」,是美國通識教育中相當受學生歡迎的基礎課。美國各大學所開設的人類學導論,多半是上百人的大班(黃先生自己就長年負責教授平均四五百人修習的導論課),也由此,雖然高等教育市場中人類學教授薪水普遍偏低,但撰寫人類學教科書卻是件高利潤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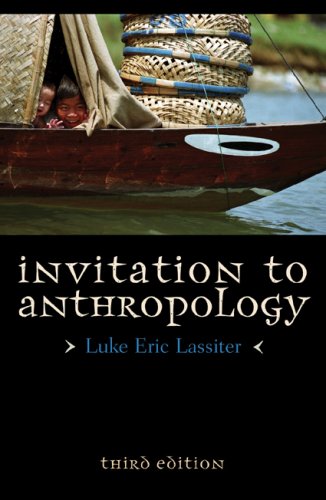
那麼,人類學課程的吸引力在那裡呢?幾年前,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教授同事曾對我說,當學生「通了」、「會了」、「懂了」的那個時刻,課堂裡彷彿可以聽到一盞盞燈炮綻亮的聲音。在我的教學經歷中,燈火最為通明的教室(這當然是意象式的隱喻),是在緬因州一個以勞工階級學生為主的小學院。該州許多傳統行業勞工在經濟再結構浪潮中淘汰出局,高等教育成為一種在職訓練,提供他們在新經濟時代必備的工作技能與知識。在該校課程設計中,人類學既是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也是「社會與行為學系」的必修基礎課,每學期出現在課堂的幾乎都是重回校園的熟齡學生,我的外國腔英語並沒有減少這些白人藍領學生喜愛人類學導論的程度。從學生反應可歸納出人類學的兩項魅力:首先是其工具意義,導論課當然是拿到學士學位的必備學分,不過更重要的是人類學豐富的異文化資訊,被視為晉身「全球化公民」的知識配備,是這些在新經濟體制邊緣掙扎的勞工階級學生向上流動的身份證。其次,由於經濟局限,大部份學生從未出國,許多甚至沒有去過西岸,人類學幾乎等同「一扇窗戶」,上課彷彿不花機票錢的國際旅行,讓他們認識各種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也提供反思自身處境的文化智慧。

只是,有趣歸有趣,學生們還是經常在討論異文化之異的同時,得到「當美國人真好」的結論,以他人異地更大的苦難做為讓自己接受現狀的理由。人類學如何能說服這些學生,在主流價值之外尚有許多改善生活的另類可能方式?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在教學方法與教材選用上,將靜態的文化多樣性轉化為動態的文化可能性,讓學生了解,異文化研究並不只在於揭露人類曾有的豐富生活形式,更隱含著貼近自身的改變源頭。如Hannerz(2010)提醒我們,人類學必須站在前衛位置,描述正在成形與可能成形的文化形式,不讓「未來」淪為當代經濟思維的投射或延續(Rabinow 2008)。例如,描述狩獵採集社會共享倫理的民族誌文章,可以與當代建立社群經濟的村落實例做比較,讓學生知道,改變是可能的,而且有愈來愈多深具勇氣的理念團體,正在世界各地分頭進行有別於市場經濟的另類生活實踐。而這其實就是瑪格麗特.米德在四十年前提出的主張:「對於異文化的知識是當今所需的文化創造性的最佳源頭」(Mead 1967: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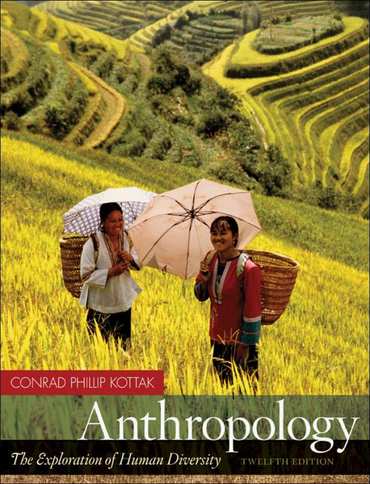
在今年一篇回顧自己學術生涯的文章中,Jean Comaroff談到她如何看待學者的公共責任:
妳可以從立足點開始做些有用的事… 人類學的視野提醒我們,不論改變的工程如何龐大…其中都包含了尋常人們的施為(agency)與他們在立足點上的踐行…身為學術工作者,我們的立足點就是學院,因此我們必須從最貼身的工作〔開始〕,積極介入教育體制的生產政治…在大學企業化的壓力之中捍衛人文教育。(p.165)
換句話說,在末日烏雲罩頂之際,作為一位小小的人類學者,即使缺少力挽狂瀾的技能,或許還是可以為課堂帶進一道曙光。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呂欣怡 末日風潮下之人類學教學隨想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759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我們實在太需要這麼陽光的人文學者! (不是像胖虎這樣的陽光宅男吼?) 依稀記得米國學制中都讓博士班的研究生去帶大一人類學導論的討論課,那些迷濛的好奇小眼睛凝視一下對於他者文化、親屬系譜、儀式生態...的Orientalism,先是震驚後是欣賞(但願有吧!)。我所知的只有在米國的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每個學院都有出一些核心必修的大一通識課,像College of Liberal Art 就是以文化人類學與世界考古學最受歡迎,還有把全校修課的數百人拆成20餘人的小班實作課成為許多sections,由TA 帶討論活動、甚至實做些小調查。那如果是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 則是讓其他專業的大一同學都來上些演化的小實驗,例如人為栽培選拔青菜的絨毛、回交果蠅的白眼殘翅(非野生型)、乃至於萃取看到真實DNA後再跑電泳分辨基因。換句話說,大學之大是各學院的豐富建構出來的,不能少的正是穿梭於人文/科學的理想價值!
看起來人類學不僅不會是末日,而且還可能是挽救人類免於末日的良方(自我陶醉一下,雖然我隨時做好背離的姿勢,因為我的身分稱不上叛逃)。很多的知識宣稱要打到強權,卻不由自主地使用強權的語言和速度感。人類學知識有著它特殊的質感和時空感,是其天生麗質之處,但是也容易成為逃避的港口,如何保有其特有的質感又能和主流對話,或許是很核心的議題。而人類學知識被數位典藏之際,如何保有這個知識特有的屬性可能又是應該有所思考的。
有機草莓:「人類學知識被數位典藏之際,如何保有這個知識特有的屬性」
正好是我和disorder正要提的一個計畫主題,呵呵
有點懂了,我最近在偏遠原住民部落烏雲罩頂,正需要老師這道光呢!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