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心靈》導讀
從躺椅到藥丸:見證精神醫學的文化變遷
當我們情緒受困、睡眠困難,甚至感到精神折磨而必須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時,醫生為什麼會說那樣的話、開那樣的藥?這些都是有其背後千絲萬縷的理由。人類因心靈受苦而求醫,在長遠的歷史中只是一個短暫的篇章,如今卻也成為某種主流;讀者也許會好奇,當代精神醫學的知識系譜與技術操作究竟是如何長成現在這個樣子?《兩種心靈》或許能提供一些答案。
《兩種心靈》是一本記述1990年代美國精神醫學教育訓練與臨床實作的實況,以及其治療典範移轉與醫療系統變革的民族誌。本書所提到的「兩種心靈」,指的是精神醫學對精神疾病與心智狀態的兩種主要解釋模式:一種是以神經學理論,強調精神疾病源自於神經傳導物質的失衡,精神科醫師通常會採取「大腦生病了」的說法來解釋精神疾病;另一種則是精神分析,它源自於佛洛伊德解釋精神系統的理論,強調人的意識與行動往往受到潛意識或無意識所驅使,人們的精神行為往往與早期經驗相關。這兩種模式有著很不一樣的治療方法,前者著重在藥物治療,後者則是談話為主;它們曾在美國一度同時主宰了精神醫學界,可以說是相形益彰,但日後卻有所消長。
本書由美國人類學家譚亞.魯爾曼所著,她透過精神科醫生的訓練過程,逐步描繪90年代美國精神醫學實作與變遷的圖像。這本書不但是一本特殊的醫療/心理人類學著作,也是精神醫學近代史,更是精神醫學的文化研究。英文原書的副標是「一個人類學家看美國精神醫學」,即使它談的是美國的案例,對普世精神醫學界仍有重要的啟發。一方面原因在於,雖然本書是世界精神醫學史中的一小段地方誌,但其田野地美國如今早已成為向全世界輸出精神醫學知識與醫藥產業的重鎮;同時,本書細膩而淋漓地表達了醫療作為一種歷史文化與政治之體現,足以作為不同時空的醫療之借鏡。一開始,容我先從作者的學術歷程與關懷來旁敲側擊,回答本書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並分述本書帶給台灣讀者的若干啟示。

探索精神症狀的文化形塑
譚亞.魯爾曼目前是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她在英國劍橋大學取得社會人類學的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是研究當代英國的巫術,後來改寫出版成書《巫術的信念》(Persuasions of the Witch's Craft), 該書研究居住在倫敦的中產階級高知識分子如何成為巫術的信徒,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何能同時接受不相容的、分屬於由科學與魔術所解釋的「兩個世界」。從那時候開始,魯爾曼一直對人類的心靈保持高度的興趣,並且了解到,只要透過信念與訓練,人的心智是能夠改變的。基於此,我們也能明白她後來為何對福音派基督徒如何感受上帝的話語感到興趣。而正因為對人類心理的高度興趣,精神疾病之後更成為魯爾曼的學術關懷之一。
當我還在杜倫大學修讀人類學博士時,該校受衛康基金會資助進行一個「聽見聲音」(Hearing Voice)的研究計畫。這個跨領域的計畫涵蓋了哲學、醫學、心理學、人類學與文學的研究取徑,企圖將人類的幻聽經驗進行盤點與分析。魯爾曼受到該計畫的邀請,以「聽見上帝說話」(The Voice of God)為題進行演講。她以美國民權運動者馬丁.路德.金恩聆聽上帝話語的例子開場,進一步介紹她對信仰者聽到上帝說話的理論。針對這種不尋常的聽覺經驗,魯爾曼不僅研究教徒,也研究精神病人。魯爾曼對精神病人的感受有敏銳的觀察。她曾在印度的清奈與迦納的阿克拉做研究,發現該處的精神病人的幻覺經驗較不那麼負面,而且那些幻聽的內容也是有文化差異的。無論從福音派基督徒的內在知覺,或是精神病人的幻聽,這些不尋常的身體知覺現象其實都共享了某種類似的社會形塑過程。無論「聽見聲音」的研究計畫,或是魯爾曼的研究,都顯示了人的經驗往往是本於社會與文化經驗,某些被視為幻聽幻覺的經驗,其實都是一種真實的主體經驗,也不一定有正常與疾病的分野。
對臨床醫師來說,強調正視並尊重病人的主體經驗,是存在某種道德焦慮的,因為下一步可能就會被簡化成尊重病人而病人有權利拒絕治療的結論。但如果深諳魯爾曼的核心關懷,便知這樣的焦慮可能帶來誤解。對魯爾曼來說,她深知精神疾病讓人陷入困難處境的現實;她的研究,在在顯示她並沒有忽略深受疾病困擾而亟欲復原的渴望。舉例來說,她曾在美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下研究芝加哥的遊民與精神病人的主體經驗。魯爾曼發現美國患有精神疾病的遊民拒絕治療,是因為美國的衛生政策將收容機構與精神疾病牽連在一起,這使得病人會因為拒絕示弱而拒絕被標籤。後來這也影響了某些地方諸如紐約的收容政策,能進一步與疾病脫鉤,反而改善了精神病人的處境。
從這些研究的取徑便能了解魯爾曼的基本立場;她關切弱勢者的處境,卻也盡可能予以同理。從一名人類學家的視角來關切精神醫學,有時候與醫療工作者的邏輯有根本上的不同。以精神疾病來說,醫師可能必須先確立疾病本身的認識論再提供協助,但人類學家的進路則是將精神醫學這樣一個建制化的學科進行拆解剖析。醫療本身不只是一種工具,醫療實作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實作的體現。
醫療作為文化之體現
過去在醫療人類學的分類當中,曾將大眾或民俗治療的形式放在民族醫療(ethnomedicine)的框架下來理解。民俗醫療的治療過程有其特殊的儀式與意義;但是那樣的理解顯然有些西方中心主義,忽略了所謂「現代西方醫療」也是某種文化的產物。後來有論者提及,當代醫療其實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民族醫療。換言之,所有的醫學都有其文化與歷史,正如所有科學其實都有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醫療人類學始終關切著日常生活中的病痛與生命經驗,並將「文化」視為影響主體經驗一個相當重要的脈絡性因素。「文化」也常常被指向與特定的族群有關,因此也有些人發現在特定的群體之中會有特定的疾病表現。按照過去的想像,人類學研究似乎大多聚焦在那種小規模的、地方風土的、傳統民俗的框架。後來,醫療人類學研究逐漸轉向特別是以西方醫學為主體的現代醫學,並探究西方社會的健康信念或醫藥世界,原因在於過去西方現代生物醫學往往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普世科學,有學者稱這個轉向的過程為「將西方人類學化」(Anthropolizing the West);《兩種心靈》關切現代精神醫學,可以說是這個路徑下的研究。
魯爾曼從事了大約四年的田野研究才足以寫就《兩種心靈》這本民族誌(那幾乎也是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時間了)。這其中包括了十六個月在臨床場域中的觀察,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觀察精神科住院醫師的各樣工作,包括查房、會議與教學場景。魯爾曼本著人類學家「成為當地人」(going native)的自我許諾,除了與醫療工作者進行深入的訪談,甚至自己也投入了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工作並接受督導。過去,人類學研究固然不乏對精神疾病的探討,但是像《兩種心靈》這樣將醫療從業人員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並不多,稱之為專業人員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的先鋒,應該不為過。然而,這樣的研究並不只是在探討專業人員的生涯實踐,反而是從他們的訓練過程來反映整個醫療文化的現況,這種聲東擊西的策略,算是一絕。
作為人類學研究,魯爾曼的田野蹲點不是聚落、家屋與祭場,而是醫師值班室、治療診間,乃至於精神醫學會的會議現場。作者與她的報導人(人類學家用這個詞彙來稱呼提供田野資料的關鍵人)──住院醫師們──窩在一起。作者透過幾位關鍵報導人來陳述他們在成為一名醫師的過程中如何思索、面對與病人的關係。她的田野筆記仍然充滿了各種「部落儀式」,這些「儀式」使得醫師成為醫師,病人成為病人。在這樣的研究之中,作者所記錄的並非只是醫病關係,也包括了醫療工作者之間的同儕關係。作者參與觀察的現場對臨床醫師而言並不陌生,但魯爾曼做得更多。她一方面能深入學科領域的核心探問精神醫學的知識建構,也能夠以抽離之姿分析學科的文化現象,甚至進一步討論影響精神醫學變革的外部因素。
《兩種心靈》也足以作為一冊醫學臨床教育的教案。作者透過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反映出精神科醫生養成過程中的價值觀是如何被形塑。年輕醫療工作者將知識轉化為實踐的過程,往往充滿了道德困境與倫理思辨,比方說,菜鳥醫師常常在模糊的診斷邊界上躊躇,猶豫在什麼條件下必須將病人收治住院、何時應該給予藥物、在什麼時機終止治療。醫學訓練本身不同的理論基礎與知識權力也影響著終究身而為人的醫師的情緒與感受。這使我想起哈佛大學的醫療人類學者拜倫.古德(Byron Good)與瑪麗-喬.古德(Mary-Jo Delvecchio Good)在他們針對醫學教育的敘事研究中,透過現象學的角度來觀察醫學生如何進入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生活世界。 他們觀察醫學生如何透過知識與技術的累積和實作,將自己形塑成一個專業工作者。醫學生在那個過程中被醫學的權力所吸納,換言之,醫學生的生活世界也被醫學所殖民。這同時意味著,年輕醫師在將醫學知識內化成為實踐的依據時,醫療專業訓練過程也是一個異化的過程;醫學的某些技術與信念(好比本書所提及的知識典範,或是醫療的治療指引),並非永恆而穩定。
看見醫療照護的結構性因素
探究醫學的發展與更迭,本來就沒有單一線性的史觀。本書推論「管理式照護服務」是使心理治療消退的主要原因,或許稍嫌不足。畢竟,科學實作的變革必然涉及了諸多行動者的參與,若從當代科技與社會研究的立場觀之,需要對所謂的行動者網絡進行更縝密的盤點分析。但是,作者的推論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畢竟她深入醫療實作的現場,她以田野研究之姿取得的資料(雖然人類學研究者往往不喜歡「資料」這個字),也足以成為無可取代的證據。事實上,對醫療照護系統的關切,正是當今探究醫療品質相當重要的取向。
所謂的「管理式照護服務」,其基本精神在於由雇主預先為員工付費的醫療模式,有點類似台灣民眾熟悉的健康保險制度,這也是美國健康商業保險的模型。換言之,這種透過付費在前而總體費用不變的付費邏輯,與案件事後收費的模式不同。美國的這項制度的確也常被拿來作為台灣健保節省開支的他山之石,包括透過論人計酬與審查的方法來控制成本。在作者的田野經驗中,無處不見專業工作者的立場衝突,那些致使醫生選擇藥物治療而捨棄心理治療的,確實來自醫療背後的經濟因素;此一制度也為美國的精神醫療帶來鋪天蓋地的影響。誠然,作者的觀察是悲觀的。但是一如作者所言,管理式照護本身並非邪惡,它讓醫療「科層化、理性化」,它希望花更少錢來照顧更多人,只是可能影響了治療的品質。如此雙面刃般的效應,足以作為我們思索醫療制度改革的借鏡。
本書說明了兩種醫療典範的差異,更說明了影響兩種醫療模式的消長來自醫療系統變革下的成本計算,而這進一步影響了治療的動機。換言之,決定醫療內涵與品質的,不再只是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而是醫、病與醫療照護系統,亦即與國家政策的三角關係。近年來,美國醫學教育興起了一項呼籲,這是由身兼精神科醫師的社會學家強納森.梅索(Jonathan Metzl)和人類學家海倫娜.韓森(Helena Hansen)所提出的「結構識能」(structural competency), 他們強調醫學訓練不光是要訓練醫學生的文化識能,同時更要認得形塑臨床互動的結構性環境,包括影響醫療決定的經濟的、社會的,乃至於政治的外部力量。回頭來看《兩種心靈》的書寫策略,尤其是透過新自由主義式的健康照護(雖然作者並無直接使用這個詞彙)來解釋醫療形式的典範移轉,可以看出作者對醫療系統的結構性因素有明確的洞見,而這也是今日探究醫療文化與品質的基本路徑,是討論醫療化議題不可忽略的面向。
超越身心二元之必要
如前所述,《兩種心靈》不但是近代醫學史的一小篇章,亦是精神醫學的文化研究。因此,本書的潛在讀者群必然相當多元,閱讀時肯定有不同的視角與關心的面向。筆者身為臨床工作者又身兼人類學的學徒,在此希望能特別強調這本書對台灣讀者的一些啟示。首先,這本書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範例,它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批判視角。相較於其他科別的醫學,精神醫學本身的學科特性時常讓人覺得「不科學」,也偶爾給人非人道待遇,或是行社會控制之實的印象。加上「精神疾病」本身時常被汙名化,精神醫學被解構剖析的面向也大異其趣。但本書破除了討論精神疾病時,常落入的「病理化」與「去病化」的虛假對立。
魯爾曼深諳精神疾病之於個人的意義,了解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正如她所言,「認為他們(病人)只不過是和一般人不一樣,是一種錯置的自由主義。」她並不挑戰疾病的本體論,但是將不同模式的醫療典範的實作視為文化並進行分析。她嘗試將精神疾病除魅,但是卻不採取批判醫療化的方式。如果從結構識能的角度來看台灣先前對於精神疾病的某些爭議,包括過動症的診斷與治療,以及強制住院的人權議題,許多論者強調醫療實作應該這麼做那麼做才對,其實都可能忽略了更前端的條件。換言之,健康照護系統的設計(比方說健保給付的限制),極可能從一開始就壓縮了某些社會心理介入的空間。而從病人端來看,人們對疾病角色的認同、對診斷的需求、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生活處境、對治療的期待,也都影響了治療形式的變革。不過,魯爾曼點出「管理式照護」制度的影響,指出該制度解決了許多醫療現場中人謀不臧的財務管理,以及疾病的定義與治療缺乏標準化的問題。
再者,即使作者刻意將兩種醫療模式進行並排比較,我也不建議讀者直接將精神分析與生物精神醫學模式視為必須對等存在的治療策略;畢竟,它標誌的是一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醫療人類學的研究者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持續地提醒,人的身體痛苦,甚至是心理/精神症狀,難以單純從身心二元論的角度觀之。在本書中,作者一度提及精神醫學科學家討論「經前症候群」究竟是否該成為診斷的一個類屬(見第四章),當中其實充滿了生理事實、科學知識與性別權力的交織,這也是後續許多醫療人類學者不斷提點,人的受苦經驗不光是身體與心靈的,更是社會的、政治的加總體現。
小結:讓治療室持續穩定的存在
英國艾克斯特大學的醫學史教授馬克.傑克森(Mark Jackson)在他的著作《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 中,做了這樣的結語:
我們可以從醫學史中學到什麼呢?首先,歷史研究揭示出醫學知識總是會引起爭議,也很少處於穩定的狀態。不論是在哪個時代、哪個地方,醫學知識和實踐總是以相互競爭的形式存在。每個時代的患者都能夠向不同主張的治療者徵詢,並且接受不同形式的醫療照護。在某個時代或某個文明中,會出現具有主導地位的特定醫療保健方式,但它們從來沒有完全排除其他的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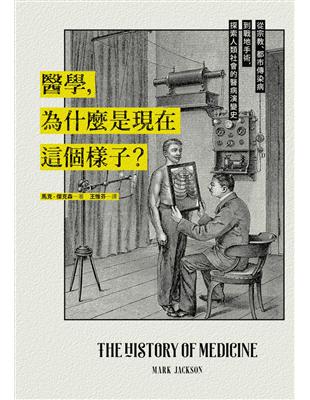
這段文字,可以說是給了《兩種心靈》所記述的這段精神醫學變遷史,一段貼切的註解。《兩種心靈》不但適切地回應了這段文字,更透過作者在場的觀察,記錄在不同醫療形式的競爭消長過程中,醫療工作者的衝突與掙扎,以及如何直接影響仍受苦於疾病中的人。對本書作者魯爾曼來說,「管理式照護」的實施,是致使美國精神醫療轉向生物醫療模式「文化變遷」的主要原因。
然而,魯爾曼的觀點並非無懈可擊。歷史學者強納森.薩杜斯基(Jonathan Sadowsky)在他近日出版的《憂鬱帝國》(The Empire of Depression) 中提出精神分析被生物醫學取代的原因,包括抗憂鬱劑的發明、基因研究的興起,以及DSM-III的改版,這些事件都遠早於「管理式照護服務」的興起。如果從美國的社會史來推敲,除了作者在書中也曾提到的反精神醫學運動以外,1960年代的戰後美國也興起了一股公民運動,精神科醫師也關注街頭,對他們來說,醫學的實踐本身也必須是要被解放的,因此精神醫學也要從高貴小眾走向平民。同時,跨國的行動者,主要即世界衛生組織,也基於謀求人類社會和平的動機,萌發了將精神醫學與公共衛生結合的實踐模式,而這也順勢引領了診斷標準一致化與流行病學研究的興起。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論者嘗試解釋美國精神分析在60年代後沒落的原因,其中包括了女權與同志人權的興起,挑戰了精神分析過去被視為厭女與恐同的理論。 繼之而起的一些短期的、行為取向的心理治療也是原因之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精神分析也不見得是在精神醫學的轉向後「式微」。即使魯爾曼有提到精神分析輸入美國之後的改變(例如第四章討論精神分析師的部分),但對當時的社會脈絡的討論相形有限。其實在戰後,個人化的精神分析理論顯然不足以緩和當時美國社會的集體焦慮,因此精神分析在當時也有了某些新的創見,這使得精神分析在往後誕生更多新興學派,那恐怕需要更多篇幅才能將故事說完了。
從這些歷史過程看來,至少可以得知兩件事:首先,精神醫學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即使過去曾有一股看似反對的力量,但它也間接推動精神醫學的改變;再者,無論是朝向診斷標準化的醫療,或是精神分析本身,都萌發了更朝向社會醫學取向的理論與實踐。換言之,當我們將醫療化的批判對象放在新自由主義邏輯或藥物工業的興起,其實可能忽略了醫療化本身也讓精神醫學走向更親民、更社會化的境地。
《兩種心靈》成書至今,精神醫學又走了二十多年,並且在多元的社會文化中開枝展葉,也在相異的政治經濟條件與醫療系統中形塑出各種繁複的實作樣貌。不可否認地,在實證醫學被高度推崇的今日,當代精神醫療的訓練確實大幅倚重生物醫學的知識,現代人對自身的認同也逐漸接受了神經生物學的定義,借用醫療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羅斯(Nikolas Rose)稱之為「神經化學之自我」(neurochemical selves)來說明,他認為:「這些用以治療精神疾病的新興藥物治療的浮現,其重要性不但只存乎於他們的效果,也在於他們如何重新形塑專家與一般人去看待、詮釋、言說與了解他們的世界。」 然而,精神科醫師也仍無庸置疑地受惠於精神分析,無論是在一般的門診診間或是在談話的治療室,都能應用相關的理論與技巧。但是,除了作者強調的兩種模式以外,當今的精神醫學實作中,包含了更多元的心理治療種類,亦有更豐富的安置選擇與心理社會處遇模式。
本書最後,魯爾曼以道德為題作結,但絕非說教。如同她在引言中所說的,「這裡所謂的『道德』,與其說是一種正確的行為準則,不如說是我們直觀地認為什麼是應該負責的、何時該咎責,以及如何打從內心確定我們的雄心壯志是正確且良善的。」罹患精神疾病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助人工作亦是艱辛的。臨床工作者在有限的條件下做治療的決定,往往面對繁複辯證過程。許多時候的可為與不可為,並非只是基於一種基本的疾病解釋模式與信念,也在於整體社會的結構性條件。
也許讀者在讀完此書後,不禁想問,在我們這個時代,什麼才是好的醫學?我們可以提供(或得到)最好的治療嗎?精神醫學需要的是尖端科技,還是古老技藝呢?其實,這些都不必然是衝突的。魯爾曼在寫這本書時,也嘗試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在治療室中以身為度,如是我做。她毫不保留地推崇那種無私的大愛,正如她在第四章書寫精神分析師的特質時提到,「當我們有愛,我們就會信任他人並保護他們」,這顯然是作者對理想的治療關係的殷切期待。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治療效果必須取決於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礎,也需要足以共量的文化信念,以及一種具有結構識能的道德責任。換句話說,好的精神醫療並不只是取決於治療者如何予以治療,還需要能夠維持治療室裡對等與互信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醫療需要具有公共性的政治與社會承諾,來確保治療室能夠持續穩定地存在
※本文為《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之導論大部分內容,全文請見原書。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吳易澄 《兩種心靈》導讀:從躺椅到藥丸:見證精神醫學的文化變遷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8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