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苦的性別們與性暴力循環
一個抵抗壓迫,同時自我毀滅的內城故事
在幾本經典的美國內城民族誌當中,《尋找尊嚴》一直是最令我難忘的作品。在台灣,《泰利的街角》、《全員在逃》、《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都已經有繁體中文譯作,如今《尋找尊嚴》能問世,通往美國內城底層世界的通道也走得更深。不同於上述幾本重要的都市民族誌與公共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尋找尊嚴》更為深刻地呈現出內城的女性視角。從華盛頓特區、費城、芝加哥到紐約,上述每一本著作都論及貧民窟居民受苦的結構性成因,然而只有《尋找尊嚴》花了最多篇幅,針對個人受苦的性別化與性暴力的循環,做了毫無保留、走到瀕臨道德臨界點的呈現。這樣的露骨呈現超越了民族誌工作者自身的倫理煎熬,直指任何存有厭女文化的社會都必須面對、卻往往難以公開討論的議題:性暴力的養成、集體輪姦的少年儀式,以及倖存者矛盾的生命圖像。
儘管碰觸的是棘手的禁忌話題,本書作者,資深人類學家布古瓦,非常有意識地致力於寫出一本為活在紐約底層的波多黎各裔社群辯護的書。他追溯波多黎各的被殖民經驗,從西班牙到美國的軍事策略與經濟殖民,一路來到二十世紀期間人們如何因貧窮而大規模移民至美國本土。然而美國內城的生活彷彿注定了新移民被迫面對種族化的不平等就業命運,而將一部分人的生計捲入販毒的地下經濟之中。這些殖民與後殖民的結構因素已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分析,布古瓦做得更多的是從這些歷史的軀幹與骨架的縫隙,鑽入人們的血肉與靈魂之中。見證了人們的受苦,他決定不避開性暴力的難題,不畏懼極具爭議性的描繪,在倫理上拒絕漠視女性的受苦與性暴力的常態化。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同時不將人們扁平化與去人性化,他必須避免再度複製特定少數族裔身上已經加諸的各種暴力與色情的刻板印象。因此,他在書中提供了大量而仔細的對話逐字稿,以及那些對話產生的脈絡、報導人說話的神情與肢體動作,讓讀者充分地感覺到,每一位報導人都是活生生的真實存在。因此,讀者不會只停留在快克藥頭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壓迫或是文化生產理論分析,而是能真實有感地碰觸到這個邊緣社群裡頭,人們的個體自主性及性別化主體的養成,是如何與自我毀滅相互扣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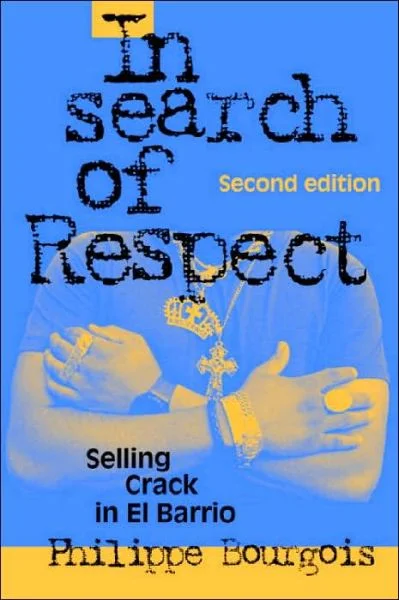
雖然布古瓦在這本書中並未特別深入地針對性與性別來進行理論創建,但全書的主軸一直緊密地貼合著波多黎各男子氣概、後殖民父權及厭女的深層心靈結構,就連女性自身的視角也高度內化了仇女的意識。因此,在本篇導讀中,我想嘗試從一種著重性與性別的角度切入,將全書的精神性別化。為了使讀者能身歷其境般進入販毒貧民窟的生命經驗與心境,我將儘量不破哏民族誌的細節菁華,但提點全書主要的論證結構,並依序按照本書的三個重要環節──東哈林區街頭文化的殖民系譜、正式經濟的陰性辦公室與服從文化、性暴力的習得與受暴者的尊嚴,並提示每一環節中,性與性別的重要性。
跨世代的吉巴羅性別化主體:東哈林區街頭文化的殖民系譜
在丟滿吸食及注射藥物器具的人行道及謀殺率超高的公宅區背後,是一長串顛沛流離、持續經歷剝奪的被殖民者經驗。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西班牙殖民者購買非洲奴隸來波多黎各種植農園,但最主要的目標仍是把這塊土地定義為軍事戰略地點,而非盈利場所。接著,美國殖民者在十九世紀最後兩年進駐並沿用西班牙的統治模式,但逐漸加重這塊土地的經濟投資角色。二十世紀初,波多黎各的土地有一大部分都落入大型國有農業出口公司的控制底下,導致成千上萬的小農戶不得不離鄉背井去到其他地區的大甘蔗園工作。政治上,所謂的波多黎各「自由邦」裡的人民並未擁有選舉權或任何的民主權力。尤其在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後,美國政府以遏阻共產勢力擴散為名,將波多黎各打造為自由經濟展示舞台,以「投資換來免稅,免稅換來利潤」等政策,將波多黎各土地上所有的投資利潤都放入跨國公司的口袋。種種獨厚跨國公司利益的政策,終究造成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在二戰後的二十年內,一百五十萬人,相當於島內三分之一的人口,紛紛來到了紐約城中最破敗不堪的公寓,他們帶著苦幹實幹就能爭取到更好生活品質的願景,但真正迎接他們的,卻是一九五○年代大型工廠紛紛轉戰海外廉價勞工之後,取而代之的種種毫無保障、只提供不穩定最低工資的服務部門。「後工業」經濟轉型所宣稱的進步僅僅優惠了中上階級,而將跨國的勞工階級置入不堪的勞力條件之中。對剛進城不久的「吉巴羅」而言,後工業轉型意味著一種美夢破碎的末日宣判。
「吉巴羅」(jibaro)一詞,原先是指在這些殖民經濟系統底下生存的農民後代,尤其在二戰後作為譏諷這群「落後貧窮」社群的詞彙,可粗略譯為「鄉巴佬」。在西語中,jibaro含有「野蠻」之意,而把人描繪成「野蠻」的,正是那些剝削非裔奴隸、美洲原住民與混血兒後裔的西班牙殖民主子。奇妙的是,布古瓦敏銳地捕捉到,波多黎各移民翻轉了「吉巴羅」一詞原有的負面意象,進而與這個標籤產生認同感,並將jibaro視為「波多黎各人自尊心與文化完整性的象徵」。這其中的理由,當然與遭受壓迫及抵抗主流社會的邏輯有密切關聯。對於不願意被統治、決心放棄在作物莊園出賣勞力賺取微薄薪資的「逃跑者」而言,這個詞彙保留了抵死不屈的抵抗意涵。當這些「逃跑者」的後代穿越時空來到紐約街頭,他們將「野蠻」的貶義轉化為挑戰殖民者、使統治者恐懼、無法駕馭的正面意涵,而成為具有反抗者尊嚴的自我認同:「我就是吉巴羅。」

攝影師Edwin Rosskam於1938所攝(圖片出處)
然而,「吉巴羅」認同是一道雙面刃。它提供內城勞工抵抗的骨氣,卻也是邊緣化自身的溫床。但「吉巴羅」之所以歷久彌新,正因為它涉及的是性別化的主體,也就是人們的自我構成中最深層、最頑固,同時也是最脆弱的那一塊。布古瓦說:
老派的家庭經濟是圍繞著一名獨裁男性的生產力而建立起來的,但長期以來,這種定義已在波多黎各的離散處境中遭到嚴重挑戰──尤其是在內城。無論男人或女人都會反覆想起過往的回憶,並美化那段吉巴羅的歲月,他們遙想著平原上的甘蔗種植園、高原的農作社群,又或者是都會裡的貧民窟,而眼前的現實卻是他們被孤立地困在公宅大樓中,身邊全是不認識或不信任的人。
人們憧憬著被浪漫化的過去,認為以前在家鄉甘蔗園勞作,雖然貧苦,但至少身邊的社群都是自己熟悉的人,男性家戶長或許勉強也能從家庭中的地位維持自己的男子氣概。現在,他們卻在美國都會裡被陌生的人群圍繞,被陌生人鄙夷。他們的尊嚴蕩然無存。這也是為什麼,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始終圍繞著尊嚴及自主性的議題,而他們所發明出來的生活模式,甚至比他們的祖先更具有反叛的意味,以至於有些波多黎各學者將此稱為波多黎各裔特有的「對立心態」,並認為這些「抵抗文化」背後的驅策力就是面對長期殖民支配力量的結果。
曼哈頓島上也存在著內部殖民的力量。東哈林區幾乎像是帶著一種「詛咒」的封印,不管誰去誰來,什麼種族或什麼社群,東哈林區彷彿「永遠都在製造兇暴的吸毒罪犯」。一開始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前還沒成為「白人」的愛爾蘭移工;接著是被黑手黨意象濃厚籠罩的義大利移民;還有猶太移民、東歐移民;最後才是波多黎各人,以及在他們之後的墨西哥移民。東哈林區是給新來的窮人住的地方。最新來的人,都是最窮的人。而窮人並未團結起來抵抗種族歧視,往往急著向上流動,最好自己可以成功融入主流社會,接著再轉過頭來,輕視最底層的人。
在波多黎各社群所經歷過的美國外部殖民與內部殖民中,語言與文化都是迫使人屈從的重點。
由於美國殖民政府直到一九四九年都在波多黎各的學校推行全英語政策,因此對於波屬移民而言,他們的言談與舉止在美國社會是低人一等的。原本在家鄉,一個人的自尊心是圍繞著人際之間respeto(尊敬)的鄉村網絡而建立,由各種不同的年齡、性別,及親族關係之人結合而成,然而就在一夜之間,他們成為了茫茫的陌生人海之中,種族上,包含語言上,較為低劣的「賤民」。布古瓦因而評論:「他們自從抵達美國開始就一直受到輕蔑及羞辱,這種惡毒正是北美歷史種族關係的兩極分化,及移民勞工市場的種族隔離,所造就的特定產物。」
可以說,在祖父母輩的殖民經驗之後,那種抵死不屈的、逃離被統治的、能夠從家庭獲得父親尊嚴的波多黎各父權體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大部分移民能夠找到的工作,都是過勞低薪、極不穩定,且嚴重損害他們對尊嚴定義的職場關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選擇對抗正式經濟。
合法陰性辦公室文化: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交織
東哈林區的波多黎各第二代與三代移民所面臨的,是一個正在面臨經濟轉型的美國社會,而他們受到的壓迫是一種典型的階級、種族與性別交織的三重歧視。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原本以工廠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正快速遭到服務業取代,帶來一種我稱之為「後工業末日」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裡,許多內城的人們被迫在地下經濟與合法工作之間不斷轉換,而唯一恆常不變的,卻是他們持續的貧窮處境。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在正式經濟裡,他們費盡心力努力找到的工作,都是美國社會中最沒人想做的低薪過勞工作:無證照的石棉清除工、家庭照護員、在街角發傳單的、炸物廚師、夜班病房守衛,或是麥當勞店員。布古瓦的報導人凱薩曾直截了當地說在麥當勞工作是一種奴隸的工作:
你知道我都說,在漢堡王和麥當勞工作等於什麼嗎?就是在當奴隸。
我很清楚,因為我在那裡工作過。在麥當勞工作根本就是過勞又超低薪。你可以全職在那裡工作──一整個星期喔,五天都在工作──都已經全職囉,每週帶回家的薪水還是只有一百四十塊,或者一百三。
你知道為什麼這份工作爛透了嗎?不只因為過勞又超低薪,還因為你要──我是指已經過勞又超級低薪囉!──你還要去他的炸漢堡肉、要刷地板。你得為了那點屎錢做一大堆這種工作。
貧窮如同凱薩的青年男女,如果不是在漢堡王工作,也必須要搭地鐵去市中心的辦公室做那些只有最低薪資的工作──甚至還得兼差做兩份最低薪資的工作,而那些微薄的薪資,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等於朝九晚五又加班,到頭來卻只能糊口飯吃。最慘的是,在正式經濟裡,他們永遠都是「最先開除,最後錄用」。
內城人們不只占據勞工階級中恆常被剝削的經濟底層,與白人勞工處境不同的是,他們還需要每日每夜在職場上面臨文化衝擊與種族歧視。書中最深刻的例子,來自布古瓦最親密的報導人普里莫。他曾經在一間貿易雜誌社擔任郵件收發員兼打雜小弟。期間,他的一位白人女性主管到處告訴其他同事「他是文盲」,而他必須要查字典才知道「文盲」的意思。這個事件帶來的羞辱感完全擊潰了他。專業服務部門下意識地將屬於盎格魯、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視為在此工作的必要條件,因此他的英語咬字發音不清楚就變成了一種專業的大忌。事實上,老闆禁止他接電話,因為客觀來說,波多黎各口音會讓潛在的客戶退避三舍,因而害她賠錢。諷刺的是,之所以會發生普里莫接電話的爭議,正是因為他看見主管在忙或離開辦公室,為了表達積極及善意,他才接了電話。
不只是言談,甚至是波多黎各人走路的方式,都可能驚嚇到白人世界的服務部門。「他們沿走廊走向飲水機時一定會下意識地搖擺肩膀,一副充滿攻擊性的態度,彷彿在巡視自家地盤」、「他們會因為用帶有性攻擊意味的行為冒犯同事而一再受到譴責」。他們往往被年輕的白人主管粗魯地頤指氣使,而這些低階主管的兩個月薪資可能比他們一年的薪資還高。他們幾乎只拿最低薪資,曼哈頓金融區的驚人財富更讓他們感到羞辱。

除了辦公室工作之外,普里莫曾經也想發展自己的合法事業,他把影印的傳單貼在公車站,宣傳自己修繕家用電器的「修理先生服務」。遺憾的是,每當有電器壞掉的潛在顧客透過電話找到他,也就是撥電話到他女友瑪麗亞的公宅公寓時,只要一聽見他提供的地址,他們就卻步了,就算他提議去他們家,對方通常也會拒絕。甚至,「他們常一聽見我的聲音就不說話了」,因為白人聽見了波多黎各口音,就判斷他們不想要跟這樣的人有任何來往。根據布古瓦的觀察,普里莫本來就已經特別沒自信又容易受傷,因此類似像這種「改邪歸正」的嘗試,「還得在一次次對話中面對種族歧視的羞辱」,總是慘敗收場。藥頭老大雷伊也是,因為不識字,總是無法順利走完任何行政官僚程序,以至於每次想合法創業,最後都被政府部門打槍。
無論是辦公室服務工作,乃至自己創業,都意味著街頭男性必須不斷面臨的制度性種族歧視,而這當頭棒喝了街頭文化的尊嚴定義。白人「雅痞」勢力和內城「語無倫次的垃圾話」以及過分擺動的身體之間的文化衝突,俯拾皆是。無論兼差當郵件收發員、影印人員,還是在金融區高聳的辦公大樓擔任派送各種公文檔案或郵件的最低薪資勞工,少數族裔內城年輕人在面對中上階級白人世界時,總是發現自己格格不入,而陷入極度痛苦的文化衝突。其中,白人世界最讓波多黎各年輕人最受不了的工作,就是服從白人女性主管。那可以說是他們的街頭文化中,嚴重損害自我尊嚴的終極反命題。大樓與公司都有各式各樣的規範,而服從規範卻跟街頭文化中所定義的個人尊嚴有所抵觸,因為這些年輕男性從他們的祖父輩以來早已學會,一個男人必須公開自己的不服從、自己的抵抗,才能顯示自己的尊嚴。街頭文化的源頭來自遭受統治階級殖民或主流社會排除而產生的對立心態。進入白人世界工作,基本上就是街頭文化無法相容的反命題。然而,每個人卻也都曾經想要老老實實地做合法工作。這樣的複雜心境造成他們心理上的衝擊,更常使他們丟了工作。
被正式經濟排擠,與販賣非法藥物有極大的關聯。普里莫曾經連續數個月,每個月都被五、六個雇主拒絕,最後自信心跌到谷底,也加劇了物質濫用的情形。受創的自尊與階級、種族和文化緊密鑲嵌。許多人像普里莫一樣,打從自高中輟學以來,就不斷在合法經濟中感覺受辱而離職,而地下經濟所帶來的空白履歷,也注定使他們難以回到正式經濟。這種處於結構中的邊緣性,內化進他們心中,而抑鬱與空虛也融進了嗑藥經濟中。最後,反而是回到街頭販毒,從他們的角度看來才是「自由意志及反抗姿態的展現」。甚至,幫普里莫把風的班奇,是因為在合法工作中受到挫折才陷入藥癮,反而是成為藥頭才能真正擺脫快克、成為一個負責的企業人。換句話說,有時候反而是地下經濟幫助他們恢復自尊,脫離物質濫用。

總結而言,這種種內心與外在同步衝突的兩邊,一邊是後殖民街頭文化對尊嚴的定義,一邊是服務業工作中必須受人頤指氣使的規範。當辦公室初階工作的主管大多是女性時,高舉大男人主義的街頭文化更加深了街頭男人受辱的感覺。服從本身就是一種羞辱,服從女性更是羞辱中的羞辱。一切都與當初男人們夢想可以在工廠中表現出強悍、領固定薪水的願景完全相反。在工廠中,一個男人至少還可以對領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反抗姿態,呈現自己的陽剛氣概。然而當場景換到了服務部門,一個人就必須採取謙卑、服從,又低聲下氣的社交互動模式,甚至服從女性、接受她們的鄙夷。當舊有文化價值無法在新的白人都會情境與種族壓迫下維持,而舊有文化價值本身其實也來自前幾個世代的殖民壓迫歷史時,雙重的文化壓迫與經濟剝削便不斷地使男人從合法工作陣營中退敗收場。舊有的男子氣概,如今透過各種自我毀滅的方式來達成。除了販賣毒品賺取糊口的本錢,性暴力也病態地成為了維持男子氣概的通過儀式。
性暴力的習得與受暴者的尊嚴
比起藥物濫用,性暴力是更令人卻步的禁忌問題:內城的男女是如何學會當一名強暴犯,甚至學會被強暴?這個燙手山芋,對任何人來說都一樣棘手。或許,一些人類學的研究,足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至少讓我們有力氣討論。
集體輪姦作為沙文主義與男性情誼的培養,常在許多戰爭犯罪、殖民暴力與經濟剝削體制的脈絡中出現,甚至,在遠離戰爭的大學校園同樣存在。集體輪姦並非只是個人的一時興起,相反地,它是一種組織與傳承,使得「一個女人的身體成為男人們彼此溝通的符碼」,比如在印巴分治的動盪時局中,輪姦成為「執行印度國族主義任務的一種想像」。[1] 南斯拉夫內戰期間,集體輪姦乃至「強暴集中營」成為塞爾維亞男性支配的性別意識形態戰場,對波士尼亞女性身體的占領成為塞爾維亞男子氣概與父系後嗣的勝利。[2]這樣的性暴力並不只發生在戰場,也發生在非戰期間,甚至在這兩者之間,如人類學者瑪麗亞.歐盧吉奇所言,存在著一種相互關聯的性意識形態(sexual ideology)。在美國大學校園中,兄弟會集體輪姦女學生的案例屢見不鮮,而受害女性甚至可能在過程中早已完全失去意識,因為重點並非女性,而是男性之間的聯誼與男子氣概的彼此宣示。[3]這些跨文化的集體輪姦顯示出,輪姦是一種特定社會情境下被組織的產物,絕非某種男性生物性驅使下帶有任何「必然」意味的結果。事實上,正如許多人類學家所揭示的,一個人如何性交以及如何感到性興奮,儘管有潛在的生物機制,但往往是透過後天的習得與培養,才獲得最終的體現。[4]
布古瓦是在多年田野後期,也就是已經與他的報導人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友之後,才意外地發現輪姦的存在對於這些青年來說,完全是成長的必經。從普里莫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少年是如何經由學習,包含對什麼狀況能夠感到性興奮的訓練,才足以變成一位強暴犯。當他第一次接觸到他的兄弟們準備與一位女性集體性交時,他年紀還太小,內心其實不想參與,也無法感到性興奮。然而隨著年紀漸大,為了鞏固男性之間的同儕情感,普里莫開始主動參與這個暴力的男性儀式。一直要等到參與了好一陣子之後,普里莫才學會如何在輪姦的情境下,感生性興奮的感覺。得知報導人參與性暴力後,人類學者感覺到受到欺騙,甚至懷疑自己該如何繼續做田野。從此,布古瓦常在田野對話中不時與這些男性報導人對罵,痛罵他們是變態。而與他最親近的普里莫則在許多對話中透露出自己的懊悔,對於參與這些性暴力的回憶,感到痛苦而無力。
布古瓦非常謹慎地要求讀者不要將性暴力與波多黎各文化牽連在一起,希望他的書寫不要加深波多黎各人的汙名,因為他一方面揭露結構性壓迫所導致的男性尊嚴低落,另一方面則是將重點放在人的受苦,尤其是女性的受苦與尊嚴。他深知,如果沒有這些性暴力的揭露,內城的心靈故事將會是多麼地不完整。因此,他把重點轉向性暴力倖存者的生命經驗,將第六章與第七章完全奉獻給這個討論。
「若專注於快克藥頭對於集體輪姦的單一個案描述,讀者可能會被憤怒及絕望的情緒淹沒。然而街頭上的女性沒有因恐懼而綁手綁腳。…….就像歷史上敵對群體之間所有主要權力的轉移一樣,女人在為自己開創全新公共空間的複雜過程中,也充滿了各種矛盾的結果及人性必須承擔的痛苦。」第六章的開頭,就是糖糖說明自己如何槍擊丈夫的自白。接著,布古瓦鉅細靡遺地脈絡化糖糖的故事,一個刻骨銘心的故事。
糖糖是逃離暴力虐待父親的少女,後來卻變成受虐兒妻子,甚至在那之前,還先被自己未來配偶菲立克斯的一群朋友輪姦過。然後,在她自己當了母親之後,她的女兒婕琦也再度經歷被父親家暴、逃家,然後被男性友人輪姦,而社群也同樣地不認同那是脅迫下的性暴力,認為只是相互合意的行為。糖糖要求大家共同認定自己的女兒是遭到強暴,普里莫和凱薩卻拒絕這麼想。接下來幾週,他們針對這次的事件進行的大多數對話都在為強暴犯脫罪,並對婕琦的行為大加撻伐。他們完全說服了自己:婕琦沒有被強暴。他們將這個十二歲孩子經歷的所有磨難明確怪罪到她自己身上。糖糖一方面悲傷憤怒不已,但另一方面也內化了社群中男人對女人的暴力。在家中,她甚至認為「被打就是被愛」。她說:
我老公就像我的父親:我之前是受虐兒女兒,後來又變成受虐兒妻子。我逃離我媽家,因為我是受虐女兒,但之後又成為受虐妻子。我以為這樣就是愛。
我不騙你。我很愛被打,因為我從很小被打到十三歲早就習慣了,然後我老公再從我十三歲打到我三十二歲。所以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不停被毒打。我以前還會找理由讓他打我。
這種虐待與被虐的暴力循環,來自吉巴羅大家庭傳統的一種過時理想的失落,以及這個過時理想的勉強執行。就在菲立克斯的上一代,若是為了應付小家庭農場的急迫農務,一個男性家長作為一名需要協調家務勞動分工的「正當」父親,某種盛氣凌人的暴力行徑與對家人拳腳相向很可能可以「獲得理解」,甚至讓男人在波多黎各的吉巴羅山丘上得以獲得respeto(尊敬)。只是,當時空轉換到糖糖與菲立克斯所處的後工業破敗公宅中,不只是時空錯置而已,更在當下成為虐待雙方互相毀滅的加速器。
最後,糖糖用槍射了她的丈夫。
然而這樣的槍擊抵抗並非女權甦醒,而是父權再現。事實上,糖糖和她的親友都服膺一種波多黎各的傳統民間見解,也就是把女性的「發神經」(ataque de nervios)醫療化,定義為「特定文化相關的波多黎各人症候群」(culture-bound Puerto Rican syndrome)。根據波多黎各精神科的說法,這種症候群最常在童年開始遭受男性虐待的女性身上出現。在盎格魯文化中最接近的現象或許是恐慌發作。在鄉村及勞工階級的波多黎各文化中,當男性的施虐行為超出了可接受的範圍,女性若要對抗支配自己的男性,發作(ataques)就成為一種宣洩怒氣的合理互動。不過,傳統上來說,這類文化腳本編寫出的女性突發暴力行為,觸發點是配偶不忠的忌妒情緒。換句話說,糖糖槍擊菲立克斯的整個過程,具體而微地遵照著傳統受虐倖存者的傳統腳本在進行。雖然一顆子彈射進丈夫的肚子裡確實帶有淨化作用地代替了女性的怒吼,但那個跨世代與跨時空的父權虐待鎖鏈並未被掙斷,反而受到了肯認:忠誠地相信著幸福家庭的想法,並因這類父權理想被挑戰而忌妒,最後以暴制暴。她對丈夫的譴責並沒有超出母親及祖母這兩代的文化規則界線。到頭來,槍擊丈夫不但並未使糖糖脫離暴力鎖鏈,反而加深她自身的暴力傾向,讓她在快克販賣站擁有一席之地。
糖糖透過藥物經濟獲得了經濟獨立,並與普里莫開始交往,表面上她終於擺脫施虐丈夫菲立克斯的掌控。然而,糖糖的憤怒持續盤旋在她的身體裡,她對他人展現出極端暴力且偶爾帶有自殺傾向。糖糖始終沒有逃離施虐丈夫的掌控。她仍然步上著他的後塵:賣藥、忽視孩子、到處炫耀性的戰利品。糖糖養了普里莫這個情夫,於是在挑戰波多黎各街頭文化中的性別禁忌時,普里莫成為她用來進行衝撞的載體。當時,普里莫假裝自己是在實現內城男性的街頭幻想:靠著女人來白吃白喝(cacheteando)。不過事實上,在私下回顧這段過往的對話中,普里莫坦承自己似乎創造出了一個「科學怪人」:這名有五個孩子的前受虐婦女,變得比她人生中的所有男人還要更大男人。
在糖糖為雷伊賣古柯鹼,並把普里莫當情夫養的那幾個月,布古瓦明顯看出了街頭文化針對父職與母職的雙重標準。遊戲站藥頭網絡中的男人幾乎沒有例外地總是嚴厲批評糖糖,認為她不是個成功的單親母親和一家之主。明明她被關進牢裡的丈夫菲立克斯同樣擁有養家的義務,他們卻對此視而不見,而且沒有人提議幫糖糖的孩子提供食物、住處和關愛。他們反覆提出的批評與建議,不外乎就是糖糖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男性角色來好好教訓她。街頭文化仍理所當然地認為,父親在地下經濟中追求狂歡及意義時擁有拋棄孩子的權利。當男人因為男子氣概被挑戰而發展出一系列的性暴力循環與拋棄家庭之際,女人也內化了那樣的不負責任的陽剛氣質。單親母親家庭的安排中,沒有任何「母權」(matriarchal)或「母主」(matrifocal)的勝利意味。這樣的女性只會被剝削得更厲害,她們被預設為有義務無條件為孩子奉獻,而她們的男人則拒絕共同負起責任,且被視為常態。
糖糖的生命經驗有兩個層面可以分析,一個是父權體制下的男性暴力,另一個則是女性內化上述的暴力。父權體制的危機確切展現於家庭暴力及性虐待的極端化。街頭上的男人失去了原本在家的絕對權力,所以將怒氣發洩在自己無法再掌控的女人及孩童身上。男性不接受女性逐漸獲得的新權利和角色,相反地,他們迫切嘗試重新主張,在祖父那代能夠掌控家庭及公共空間的獨裁權力。男性家戶長一旦遭遇了最不理想的情況,就會成為經濟失敗的無能者,而他所經歷的這種歷史性結構轉變會對他的男性自尊造成極大打擊。更糟的是,原本可能緩解這類創傷且具有穩定功能的各種社群體制並不存在於美國內城。於是這些男人暴虐地在充滿敵意的文化掏空環境中奮鬥,希望能回頭掌握祖父那代擁有的權力。
女性內化上述的暴力,展現在自己極端地對配偶出軌的忌妒之心,以及自己要以暴力陽剛的方式來重申自身地位的行為之中。「糖糖知道怎麼獲得大家的尊敬,你看不出來嗎?你難道沒聽說她對她老公幹了什麼好事嗎?」雷伊對糖糖的敬重及信心再次提醒了布古瓦,在街頭建立自己的名聲時,公開展示的暴行扮演了多麼關鍵的角色。
然而,藥頭網絡中的女人,並未因此害怕成家,反而許多都懷有想要生一打孩子的願望,即便自己的經濟能力根本不允許。
究竟是何種社會情境與文化價值造就了這樣的心理結構?原鄉的那種父權結構,恐怕不會讚揚妻子對丈夫槍擊的這種反抗。原鄉既有的性別歧視,來到新的情境中,是如何被加深為更慘烈的性暴力循環?移民、快速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製造業變成服務業的結構重整,是所有人都有的壓力來源,也是反抗的原因。但究竟這些新的結構性因素對性別壓迫造成什麼影響?移民普遍必須經歷的外界敵意,以及地下經濟導致暴力極端化的現象,是如何加深了性暴力的循環?當人們實踐反抗文化、丟掉合法工作、試圖尋回自己最後的尊嚴之際,我們可以說這樣就是他們的主體性嗎?這已經是布古瓦無法回答,只能拋給讀者的問題:在反抗文化中,系統性的自我毀滅、父權思想的內化、結構性因素與個人責任,該如何被理解?

受苦的性別們與性暴力循環
「這些快克藥頭清楚向我傳遞了一個訊息,那就是他們的選擇不只是基於經濟上的窘迫。就跟地球上的大多數人一樣,除了需要足以生存下去的物質基礎,他們也在尋求尊嚴及成就感。在波多黎各的脈絡中,這點還納入了他們對respeto的文化定義。」
無論是對抗主流社會的宰制,還是因為街頭文化認同而產生的傲氣,東哈林區的藥頭們都不斷地跟吉巴羅的叛逆精神遙遙呼應。這樣的精神拒絕屈服於西班牙及美國殖民主義之下菁英社會對他們族人的詆毀,同時也幫助他們反叛紐約陰性辦公室文化與白人中產階級所定義的世界。然而其中的悲劇在於,在這執著追尋文化所定義的尊重的過程中,他們所能擁有的物質基礎仍侷限於街頭經濟;甚至,在這個經濟當中,受苦的性別化進而轉變成受苦的性化,緊緊扣著性暴力與其循環。
閱讀此書,我們終於能夠用一種跨越種族的、白話的、同情乃至同理的,卻又感覺受騙的心情;有機會深入了解性暴力的養成,以及那不忍卒睹的集體輪姦少年儀式,哪怕它已經被化為文字。而所謂倖存者堅韌的生命圖像,是否其實是內化施暴者的「剛烈」並複製那種「陽剛」,而這才是街頭始終如一的生存之道?為了反叛與報復主流社會、不時渴望合法世界卻又常被拒於門外,東哈林的女人與男人們,一個個性格鮮明地被布古瓦描繪出來的波多黎各裔美國人們,究竟是如何在尊嚴與合法之間,選擇了尊嚴?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菲利浦.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著,葉佳怡譯。左岸文化。2022/7/13出版。
[1] Das, V. (1995). Critical Events-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Olujic, M. (1998). “Embodiment of terror: gendered violence in peacetime and wartime in Croatia and Bosnia- Herzegovina.”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2, 31-50.
[3] Sanday, P.R. (1990). Fraternity Gang Rape: Sex, Brotherhood and Privilege on Campu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4] Sanday, P. R. (2020).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Rape: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 Gender Violence, 3rd Edition (pp. 70-87).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恩潔 受苦的性別們與性暴力循環:一個抵抗壓迫,同時自我毀滅的內城故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42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寫的又臭又長,跳來跳去的,所以重點說啥?
請樓上認真看文章,連重點都要別人幫你畫,是不是欠缺基本閱讀能力?還是抱持著別人都會幫你唸書的心態?
很感謝趙教授精彩的評論~雖然最近沒時間看社會學的書~但是從教授的評論中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樣的社會文化!! 很好奇如果這些波多黎克社群離開大都會與藥頭文化~來到一個農業的~人口不那麼密集的偏鄉地區!! 人生是不是會有新的發展~也脫離過往那種父權陽剛跟性暴力的宰制!! 抱歉自己過去往往有些意見跟教授針鋒相對~或是觀點不同!! 但是這篇評論寫得很好!! 也希望趙教授繼續寫下去~幫這世界的他者與異文化發聲!!
謝謝老師 真的是很精彩的一本著作 您的導讀也很精采
趙老師寫的真棒
之前說要好好討論問題?
結果???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