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瞬
從「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談起
這篇是我的第二篇芭樂文。在第一篇的〈真理公車亭〉中,我說明了「實驗室」這個地點如何成為「科學事實」的生產地;在這篇芭樂文中,我將試著說明另一個科學事實的重要生產地:田野。
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養成端賴在實驗室中長期專注的工作,那麼,就不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這個專業養成所便是田野。的確,如果你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學徒,那麼,在你的必修中大概少不了一系列關於田野實作、田野倫理、田野方法論與田野調查等課程;如果你不是,在目前大學的教育體系中,你大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以田野調查為核心的課程,從而明白田野工作強調的觀察、搜集資訊、以身為度、設身處地等原則並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專利,而是各行各業在解決問題時的根本態度。這就像並非每個人都有機緣成為科學家、還是得在義務教育中學習「理論-->假設-->實驗-->接受或拒絕假設-->理論」的科學方法一般,該如何「將生活化為一處田野、如人類學與社會學家般地思考」允為當代國民的基本素養。
不過,做為一個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研究者,當我聽著我的人類學與社會學朋友們娓娓道來他們的田野奇遇、秘辛與酸甜苦辣時,我感到好奇的是,為何這些「如何做田野」—或者,更準確地說,「田野如何做出來」—的細節幾乎不見於他們最後出版的民族誌與論文中?為何翻開一本民族誌時,你讀到的不是這些細節,而是在「田野上」發生的種種深具社會與文化意涵的現象,彷彿田野就是個裏頭裝著很多「事實」的抓娃娃機,田野工作者可做的便是仔細操控那機器手臂,從中抓取得以對特定理論做出貢獻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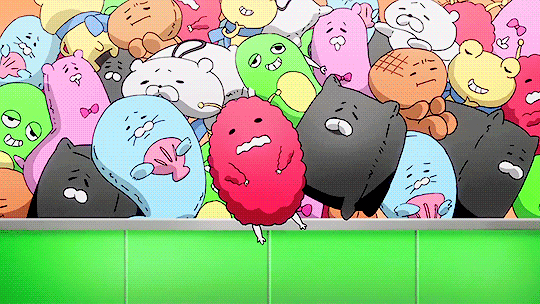
我對於田野工作的興趣並非來自「如何把田野做得更好」這樣規範性的考量,也非來自「田野工作的知識論基礎」如此科哲式的反思—我的問題意識是非常實際的,就像是科技與社會研究者為何一開始會把實驗室當成研究對象時的發問:科學家明明在實驗室中做很多的事,像是開會、用餐、寫計劃、在儀器上放乖乖、在中元普渡時祭拜因實驗被犧牲的猴子、白老鼠、渦蟲與大腸桿菌等,為何這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行禮如儀的小事總不見於最後出版的事實中?
必須指出的,就某些深受地理學影響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者而言,之所以對這些行禮如儀的小事感興趣,我們並不是站在一個建構論的立場,即認為這些小事建構、扭曲與形塑學者們發掘出來的科學事實—相反的,我們關心的是,如果說實驗室與田野是如此重要的科學知識的生產地,那麼,這個生產地本身是如何被做出來的?要回答此問題,我當然可以列舉一系列的理論洞見,說明空間既非舞台也非容器,空間既是權力也是社會關係本身等—但在此我只想指出一點:不論從英文還是中文,「田野」或 “field” 一詞均已隱含該空間不是片荒野(wilderness),而是被開墾或耕作過的(cultivated)。任何做過田野的人都知道田野是需要耕耘的,而田野工作絕不是在無人的荒野上開疆闢土、勇往直前地搜集事實。只是,當田野工作者往往把這個耕耘的過程放在幕後、為讀者端出晶瑩剔透的事實時,做為一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者,我感興趣的便是這個耕耘的過程;我想要證明,目前關於田野與田野工作的研究,關心的多是研究者在田野上做什麼,而非他們到底如何把田野做出來。
在九月十八日上午十點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演講中,我想談的便是這個田野培育的過程。我的講題是:一個「不尋常的古董收集者」: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延續我對田野與田野工作的興趣,我想分享的並非一九二零年代於中國的種種震驚國際的考古發現,而是當時的田野工作者如何將「中國」此夾帶眾多意涵的詞彙收斂為值得研究、能夠研究,且具不可替代性的 「田野」。
業配文的部分到此結束—在過來的篇幅中,我想談談的是,以田野工作為核心的科學是如此多,為何我會選擇考古學?簡單來說,我想說明的是,當科學家的幕後告白往往變成科技與社會研究者的起點時,做為一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者,即便我根本還沒站上舞台,我自認有責任先揭露我自己的幕後告白。
帷幕緩緩地降下了,我走到了台前。以下便是我的幕後告白。

http://museum.sinica.edu.tw/education_detail.php?id=14)
我研究的對象都是科學史上的名人;關心的都是這些名人是怎麼煉成的;取向都是名人之所以有名,絕對不會是因為他把手錶放在鍋裡煮、被蘋果打到頭、在火車上偷做實驗被打到耳聾之類的,而是反映了這些名人的「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在以七百頁的博士論文寫完皮革匠之子Asa Gray如何變成美國植物學之父後,我現在關心的對象是哈佛人類學博士、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創所台柱、臺大人類學系奠基人的李濟。至於為什麼我會對李濟感興趣,故事得從二零零六年說起。
那時的我,剛被哈佛大學科學史系錄取,在忙著打包之際,我在唐山購得杜正勝先生的《新史學之路》(2004)一書,準備好好認識傅斯年、李濟等略有耳聞、但遲遲不見廬山真面目的學術界名人。雖然我不準備到哈佛攻讀中國科學史,甚至也沒打算涉獵中國史,我總在迷惘之際讀上幾頁杜先生的書,希望能從杜先生所說的「前賢的鏡鑒」中得到一些啟示。即是在這樣「以人為鑒」的過程中,李濟的形象逐漸生靈活現起來。例如,在 「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一章中,杜先生如此評價李濟於一九二六年的西陰村考古工作:
中國人的科學考古當從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算起,至今超過七十年。以這年為基點,五年前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發覺仰韶村,創造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概念;三年後中央研究院在小屯展開大規模、有計劃的殷墟發掘,揭露三千多年前的王都。總而言之,192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科學考古發掘的時代。(頁174)
緊接著,杜先生便帶入「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史學」的兩大派別: 疑古與重建。「疑古派證成古人認定的古史其實只是春秋戰國秦漢人的古史觀而已」,杜先生寫道,「重建派則在樓臺拆毀後的空地上重拾一磚一瓦,以建構新的樓臺,其所依憑的材料大部分是考古的證據」(頁180)。杜先生認為李濟便是重建派的關鍵推手—而讓李濟得以以「考古證據」建構「新的樓臺」的關鍵推手則是傅斯年及其於一九二八年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於李濟加入史語所的淵源,杜先生在「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中做了如下說明:
傅斯年創立的史語所既要「發達我國所能歐洲人所不能者,同時亦須竭力設法將歐洲所能我國人今尚未能者亦能之」。最終目的是要「後來居上」,勝過西方漢學家。凡能達此目的之學者,皆在傅斯年聘請之列。(頁148)
儘管傅斯年與李濟素無淵源,杜先生緊接著指出,從李濟自哈佛返國後的文章中,傅斯年看出這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兼具有『我所能而歐洲人所不能,和歐洲人所能而亦能之』」的本事(頁148)。

http://ndaip.sinica.edu.tw/content.
jsp?option_id=2441&index_info_id=2084)
不過,杜先生也提及,在史語所的創所三巨頭(即傅斯年、陳寅恪與李濟)中,李濟與「外國人共事經驗最多,感受也最深」。杜先生寫道:
李濟在十二年(1923)回國,十四年開始與福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的畢士博(C. W. Bishop)合作,包括有名的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十七年底轉任史語所後,雙方合作關係依然持續。發掘安陽,斯密索利恩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資助中央研究院經費,李濟建議研究院宜出津貼。他向傅斯年傾吐心聲,說明建言的心路歷程:
完全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想硬硬骨頭。同外國人(即畢士博—筆者按)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腳。他們面子上雖說是很客氣,心裏總以老前輩自居;對於我們這種窮小子,只是提攜獎勵而已,而自己以為是站在無所不容的地位。這也未嘗不是實在情形,不過我們實在覺得難堪;自然,能擺脫他們的勢力幾分就擺脫幾分;實在沒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彎著脖子走走再說,耐性等著那『天演的』力量領著我們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許我們的兒子(應該說我的)可以替我們出這口氣,希望總要有的。
李濟和陳寅恪一樣,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頁145-146)
對於即將負笈美國、到李濟的母校就讀的我來說,讀到杜先生的文字,自然感到熱血沸騰。當時的我還在臺大森林所念博士班,對於當時學術環境對本土博士的歧視感到不滿,將近而立之年還在靠報工讀生工資才可勉強餬口感到自慚;我認為我是是留著長髮的三井壽,對著眼鏡發出閃光的安西教練說「我想打球」。

七年很快就過去了,當時的我是個一無所有的哈佛博士。依然對未來感到茫然。很幸運的,我在杜先生所說的「斯密索利恩研究所」(以下改稱史密森研究院)有了個做博士後的機會。很快地,我就發現了關於李濟與畢士博的巨大收藏。為了要從無止盡的焦慮中掙脫出來,我開始了我唯一會的定心之法:抄史料。
即是在日復一日的抄寫史料的過程中,我對於李濟與其置身的學術網絡開始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說,我會很好奇,為什麼在跟傅斯年抱怨外國人「面子上雖說是很客氣,心裏總以老前輩自居」的幾個月前,李濟會致信畢士博(日期為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六日):
當我在十日離開你的時候,我的心情是糾結的,就像我在一九二三年離開溫哥華時一樣。在那個時點,我想我再也無法再訪美國—但不可能的事就在五年內發生了!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地難以逆料!在我待在美國這段時間,我不相信我已經說了夠多來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你知道很清楚,就像我也明白,有些感受是不能以詞語表達的。但至少我相信,在生命更高的國度中,地理界限並不存在。福利爾藝術館,萬歲!史密森研究院,萬歲!
同樣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八日,李濟又致信畢士博,告訴他已經決定辭去清華的職位,擔任甫成立的史語所考古主任,並前往安陽從事該所主持的殷墟挖掘。至於這個史語所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李濟寫道:
在中國方面,該組織的催生者相當清楚地理解到,在近代科學的發展下,中國現在有多落後其他國家。同時間,他們對於現代國家在過去兩百年對中國所做的傷害幾乎是過分地敏感。所以,這是一種混和了急切的國族主義的「自卑情結」,使得整體情勢在中國方面難以處理。
緊接著,我又發現,與其說李濟在返國後是與畢士博「合作」,倒不如說他是畢士博手下的「博士後」。既然是博士後,就不時得應付老闆急著作出業績的壓力。例如,一九二七年三月二一日,畢士博致信李濟,指出若李濟不能在今年春天「秀出成果」的話,負責掌管福利爾遺產之應用方式的委員會將會拒絕撥給經費—也就是說,已經有個好的開始的西陰村挖掘將會無以為繼。李濟則於三月二十三日回信,表示他並不清楚「秀出成果」到底是指要他趕快完成西陰村的挖掘報告,還是要他趕快出田野。就他而言,李濟寫道,他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況」(a very embarrassed situation):他在清華的職位「多少是在臨時的基礎上」(more or less on a tentative basis),導致他必須教學來正當化他的位置;而同樣的,他與福利爾藝術館的聯繫也從未正式地確立。如果說羅紀不願意繼續支持他的考古事業,李濟寫道,他猜他應該就會失業了—因為清華沒辦法給他一個正式的職位。不過李濟說他對此不會過於擔心—因為「在中國疆界中,我想去那就去那」(I can go almost anywhere inside the boundary of China)。即便如此,李濟說他還是想知道他到底該做什麼以避免這樣的結果。

(資料來源:福利爾術館檔案室)
相較於撰寫《新史學之路》時的杜先生,我自認為還在學術底層掙扎的我更能理解一九二零年代的李濟(至少我可以看到杜先生當時無法看到的外文檔案)。九月十八日當天,我要說的不是個寒窗十年終於一舉成名的讀書人,而是個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卻又知所進退的學術工作者(持平而言,在李濟曾主持的考古挖掘中,沒有一件古物流失到畢士博手裏);我所體會的史語所,至少在創設初期,不是什麼與世隔絕的修道院,而是江湖好漢雲集的梁山泊。
之所以說創設初期的史語所是梁山泊—或者,更一般地說,以傅斯年、李濟等知識份子為中心的學術社群是梁山泊,目的在於強調,在那個外有手握豐沛資源的外國科研機構進駐、內有虎視眈眈的社會觀察家認為與外國機構合作即是賣國的年代,傅斯年與李濟等知識份子必得施展一些手段,才能在這內外夾攻下長出一點中國學術的主體性。
舉例來說,一九三零年二月,當畢士博來到北京,面會傅斯年,準備驗收已花了史密森研究院三千八百多美金、且由該院一手栽培之李濟主導的安陽挖掘,甚至據此要求分享安陽挖掘的 “credit” 時,他遭遇到傅斯年悍然地拒絕。面對畢士博的質問,傅斯年表示,安陽挖掘自始自終便是史語所構思與主導的事業,是史密森研究院自願提供經費,史語所並未主動要求;至於李濟,雖說在其主導安陽第二次挖掘期間(一九二九年),李濟的薪水是由史語所與史密森研究院共同支付,但這也是史密森研究院自願負擔李濟一半的薪水,與史語所無關。
畢士博大為震怒。在一封給福利爾藝術館館長羅紀(John E. Lodge, 1876-1942)的信中(日期為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畢士博忿忿地寫道,他終於明白,傅斯年之流自始自終便不打算與史密森研究院合作。他會著手準備一份文件,畢士博宣稱,詳列史密森研究院與史語所的衝突始末,且在將之公開前,寄給傅斯年存參。一旦看到這文件,畢士博寫道,他預期傅斯年會羞愧地在口袋中裝滿重物,跳北海(北京北海公園;過去史語所的所在地)自殺。

(資料來源:福利爾術館檔案室)
我與考古學的糾纏並未隨著我的博士後時期的結束而結束。二零一六年 秋天,我有個可與活生生的考古學者共事的機會。「環境史導論」是我在臺大地理系任教以來首開的課程之一。在教過一學期後,我深深覺得,如果說環境史這門學問便是探索在歷史上的人地關係的話,歷史學者能處理的了不起數百年—與目前所知之智人的歷史昔比,可說是百年一瞬。因緣際會下,我認識了臺大人類系的江芝華老師,我們一同構思了環境史的新課綱:
相較於臺大類似的課程,「環境史導論」的特色在於其時空的縱深。從距今約兩百五十萬年至一萬一千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出發,我們將一路往下追溯至十八世紀至今的「人類世」(Anthropocene)。我們不僅會討論智人(Homo sapiens)的演化,以及該物種與環境間的互動如何創造了所謂的「文明」;我們也會針對這群「文明化」後的智人如何在十八世紀以降發動了工業化,乃至於建立「資本主義」此生產模式,從而激烈地改變了地球環境,讓當前的地質學者陷入究竟要不要讓「人類世」列入正式地質年代的爭辯。結合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視野,「環境史導論」邀請各位同學一同來省思人類做為一個物種的過去,並據此思考我們到底有沒有—或者需不需要—一個共同的未來。
至於同學們的學期作業時,江老師提議,據她所知,是年下半年,會有支西班牙的考古團隊來到基隆的和平島從事考古挖掘,同學或可以在旁參與觀察,從中了解考故學家到底在現場都做些什麼?對於已經深陷在畢士博、李濟、史語所與史密森研究院之恩怨情仇的我來說,這當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當西班牙考古團隊在一家水餃店對面的停車場上搭起棚子、以電鋸破開堅硬的柏油路面時,我們已在現場守候。隨後幾個月,我們跟著這群西班牙人,緊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試著以攝影機來說一個故事:不是一個關於這群考古學家到底從地下挖出多少寶藏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停車場是如何轉化為考古田野的故事。
是的,寫到最後,這還是一篇業配文。現在帷幕緩緩地昇上了,燈光已經熄滅。現請各位觀賞這部由環境史導論師生自製的紀錄片:百年一瞬。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洪廣冀 百年一瞬:從「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談起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612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